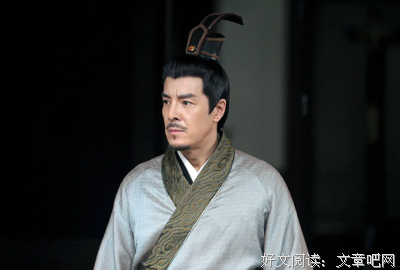《申不害》读后感摘抄
《申不害》是一本由【美】顾立雅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3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申不害》精选点评:
●我咋记得标记过...
●周、郑的现实主义政治传统或比三晋更为古老且烂熟,申不害用心更险地寻求君主的权力安全。今天即便是真诚的国家主义“法家”同情者,也往往愿意相信儒学三晋化的李悝、吴起、商鞅们怀有富国强军的治世理想,而鄙视黄老学周、郑化的申不害阴险诡诈。顾立雅先生对中国早熟的官僚政制念兹在兹,对申不害评价甚高,以扎实的文献工夫辑其佚书,对标于西方现代公管理论。又试图洗白其部分道德问题,可谓爱屋及乌。对春秋至战国文献中“法”从作为“范”(model)的常法演化为作为“术”(method)的治法的梳理很精彩。对“名”的解读同于连对“势”的解读一样远未及其邪恶本质,充满了非中国人的naive。
●三星半,迂回奔袭战法,不作正面硬攻,凭残存的只言片语,没爆炸性的文献出土,提供佐证,休想彻底攻陷这座尘封千年的迷城。对“刑名”二字的释义,为前代学者所忽略,这位洋学者读书细致入微倒是不假,可最大的缺陷是没能力阅读原文,而是依据译文逐字逐词分析,拿西方著作去解读是否完全恰当也需另议。子产相郑,申子相韩,纵有一二栋梁,失之地利,形格势禁,终究是他人侵吞对象,欲振乏力,苟延残存。三晋各怀鬼胎,韩联魏或联赵的外交方针,是避免造成孤立,一面弱敌,一面伺机,在大国夹缝中挣扎求存。秦韩之间的关系也颇微妙,秦视韩为腹心之病,将韩引向楚,韩又无力楚在身上讨得多少便宜。所云“强秦弱燕”,其实一流人才似乎都不愿往韩走动,燕昭王称雄时的几位文武能为后世记住,“十杰”中的王廖到底是否韩之名将,究属哪国,至今还是个谜。
●申氏片言只语,实难以支撑如许篇幅。顾氏为赋新书强作辞,可为一笑
●下月上市。被顾立雅的辑佚学和校勘学功力唬住了,我心想,怎么老外能用得这么溜?其实也好解释,语文学传统是大家的吧。在顾立雅看来,申子是个很现代的人。当然,我也只懂这么多了。译者说他最赞赏顾立雅思想诠释的部分,只是现在国内的学风是重学问而轻思想,可能大多数人只是一笑了之。
●申不害是在韩国主政变法的早期法家学派代表人物,韩非认为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本书可以看出汉学大师顾立雅深厚的中国古文功底,申不害的思想是战国时代思想史的一种主流声音,阅读本书也可以看作是阅读《申子》这部冷门子书的入门笔记,可惜引进中国时间有些晚了,学术史基础意义,远大于目前学术圈研究之前沿地位。
●在米国是属于开创性著作?
●郑国,一个不太失误的起的国家。而三家分晋后的韩国吞并郑国并吸纳到申不害这样的人物确实有意思。 一个终究很难做大的韩国,却并不甘于醉生梦死、混吃等死。日子一天天的过,领导也尽心尽力的打理自家那一亩三分田。 为我们留下的是更为朴实的生存理念。
《申不害》读后感(一):极好
没有过时,难道国内做古代史的对治术(治理技术,本书重点在其中包括的行政技术)研究很多吗?我怎么记得阎步克前一阵子才刚开始倡导这个研究方向呢?国内做申不害的更少,有啥资格说这本书过时了? 我和作者的观点一样,申不害和商鞅没啥关系,韩非之前如果有法家也仅指商鞅学派,韩非之后法家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影响到了汉人的观点,现在说的法家通常是跟随汉人的界定。所以后记译者反驳不力,显然并未理解作者力辨申不害不是法家的意图。许倬云有点吹捧顾立雅了,刑名和形名起初是一个意思,好像是胡适先讲的。比较遗憾的一个地方是作者想到了,但是没有展开讲赵高的问题,赵高也是申不害后学,只不过是逆炼了一下,借架空二世,将督责之权收入己手而控制了朝臣,并垄断了政务上达的渠道,这是申不害教导君主要避免的。申不害的术治可以和儒家结合,例如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纯任德教,搞泛道德主义,大谬矣。这点批判的人不少,例如徐英瑾就正确地指出,泛道德主义标准单一,也无法应对复杂情况,当情况超出道德准则所依附的情境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依赖于道德直觉的判断方法,难以治理一个大国。还有我们熟悉的黄仁宇,经常念叨中国落后了就是因为没有数目字管理,就是因为泛道德主义。汉宣帝深明此理,而且身体力行,不难发现汉书里对宣帝的抱怨都是当官的说的,因为宣帝对百姓好,把当官的盯得太紧,中国士大夫自古以来的尿性也可见一斑。
最后说一个问题,作者说申不害讲的“法”都是方法,这个恐怕不太对,有些指方法,有些应该理解为统治原则,划定政策的总目标,什么算做的好,什么算坏,用党的话说叫政治路线,比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动摇。尧舜也懂这个,所以申不害夸他们的“法”变得少,人民很受用。尽管循名责实是万年不变的法宝,但具体的方法不应该因为变得少被夸,反而应该因为随机应变而被夸,不同的时代要有不同的“名”,我想这无疑更符合申子的意图。
《申不害》读后感(二):关于申不害及本书的一些浅见
我对申不害这个人物颇感兴趣。以前想读《申子》来看,找来找去只发现一本时代文艺出版社的“中国古代文化全阅读”版,后来下决心想买来的时候发现已经绝版。顾立雅这本书是我去年才发现的,当时搜索关于“申不害”的英文论文找到了此书,似乎是七十年代的作品,也已经绝版,买来差不多要人民币近三百,纠结了半天还是没买。幸好,今年出了中文版,这才赶紧买来精读了一遍。
申不害是个在现代社会受冤枉的人物,大家仿佛都认为他是个搞阴谋的人。《大秦帝国》小说就曾专门辟了一章论述“术治亡韩”,作者举出韩国曾经是多么忠厚老实(韩厥),后来却陷于小伎俩(上党)——当然,这段论证是肯定有问题的,但他认为申不害思想是“厚黑学”的想法倒并非原创:早在梁启超、钱穆的时代就有这样的表述(可能源出于“术者,藏之于胸中”),目前也是,我曾读过一本将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比较的论文,里面就把“势”和“术”类比于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君主两大特质,“狮子”和“狐狸”。但其实,术治实在不是个亡国的思想,而是一种行政组织技术(这一点,可能电视剧《大秦帝国》比小说理解得更准确),王充就说过“韩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盖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书,兵挫军破,国并于秦” (《论衡•效力》),在他眼中,韩国之亡甚至是由于不用申不害的“术治”。我本人当初看史书的时候也判断失误,认为申不害变法失败,主要源于其阴谋的哲学太过于主观,导致韩昭侯之后后继乏人。这也是完全错误,申不害言君主当“身与公无事”,又能类似于“镜设精无为,而美恶自备;衡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这就完全不是主观了,申不害是想建立一种政府自上到下都能自行运转的官僚体系,大臣能像齿轮一样运作,君主也能像镜子、权衡一样只反映(而非创造)正义。
初看到顾立雅的书,第一个想法就是,一个申不害怎么能写这么长,其实作者是详细阐述了申不害的生平、哲学术语、思想渊源、与他人的比较和后世影响。对“刑名”和“术”的解释我基本上赞同。“刑名”只有解释为名实相符,才能符合“周合刑名,民乃收职”之类的表述,也能与“循名而责实”、“形名参同,用其所生”的做法相合。开玩笑地说,顾立雅似乎很类似于申不害,全力于对“名”(概念)的钻研(这也可能是作为美国人的他需要准确翻译概念之故)。只不过,有一些概念的判断似乎走得太远,顾立雅大概是援引了许多西方思想,把一些引申的东西都填补进来了。例如:名是分门别类,这个确实隐含着有这个意思,但申不害大概着重于名称的明晰并与实际相合这一点,分门别类可能只是一种申子意料之外的副产品;“术”源于“数”(这个问题不大),顾氏认为可以从人口普查来理解,这个合乎道理,但缺乏证据;将考试制度等等归于申子的思想,这个申子只是认为需要判断官吏的才能,但正如作者所承认的,他并无明确介绍判断的具体方法,暂时还不能将考试算到申子头上(就像说亲人回避的方法符合孔子思想,但我们不能将亲人回避和孔子的思想等同)。
至于申不害的思想渊源及与其他各家的比较,我也曾想到过子产是其渊源(虽然还缺乏明显证据),其思想当来自于郑国的环境。申子与儒家的关系,正文和译后记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过我觉得可以再做考证,似乎儒家和申子的思想有不少可融合的地方(所以儒者贾谊也学刑名),例如《左传·襄公九年》子囊答楚共王里,也有不少各守职分的内容(“举不失遗,官不易方”)。与道家的关系不好说(顾氏认为是道家吸取了申子的“无为”概念),还需再考证,我个人认为申子可能源自道家,包括列子。《战国策》有“史疾为韩使楚”,提出“列子贵正”,内容便是各守职权(“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洁胜任。今盗贼公行,而弗能禁也,此乌不为乌,鹊不为鹊也”)。列子正好也是郑国人,大概是郑国的思想大环境塑造了申不害。与法家的关系则说到底是个学术划分的问题(顾氏认为申不害非法家而是术家,与梁启超等人观点类似),看研究的需要。从君主集权思想的角度说,申不害就是法家;从重法派的思想来说,他不是其中的一份子(其实法家三派“法”、“术”、“势”这个划分就很有价值了)。
申不害的生平部分,我不赞同的地方较多,我认为顾氏理解的太过僵硬死板了。他几乎把申子所有的“劣迹”都反驳了一般,例如“请仕从兄官”一章,他赞同杜守素等人的意见,认为这是在试探;“始合于韩王”的部分,也认为不合史实,当时韩国并未帮助赵国(其实战国局势纷繁复杂,很可能助赵后不得不执圭见魏王以求和,考诸史料,韩魏之间龃龉甚多:执圭是韩国不得已而朝魏,魏惠王曾让韩国复郑国,韩魏在梁赫大战而魏国击败韩国将领孔夜,等等)。这些史料本身,正如译后记所言,并不影响申子的整体行为。此外,顾立雅认为韩昭侯并不是个优秀的君主,这是从“祠庙之牲”等史料中推断出来的,不过在这篇文章中,并不代表申子完全否定昭侯,其意并无否定昭侯监察祠庙之意,只是觉得方法不对——君主不该暴露自己的听力而被下人所察知(“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其他材料也如是,“昭侯佯握一爪”、“使骑于县”等章,顾氏解释为昭侯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屡屡表现自己对国家无所不知,是申不害反对的类型,但其实,我认为这完全符合监察之要,也就是申子所批判的“蔽君之明,塞君之听”之现象。事实上,申子并未反对监察手段本身,只是反对君主暴露其能力。除了监察问题之外,“使人藏蔽裤”固然非“赏罚”之说(如顾氏所言),但符合申子“见功而与赏”的表述。从这个角度说,我可能更认同钱穆所论证的大方向(虽然细节上可以商榷),即昭侯确实在行使申子之说,而非顾立雅所说的昭侯是“申不害‘明君’图景的反面”。
后世影响部分考察得很到位,基本上我所知道的受申子影响的人物都提到了,包括汉宣帝、诸葛亮、张居正,尤其是对汉文帝的刑名幕僚们以及张居正《陈六事疏》的介绍很合理。当然,我所知道的还可以补充一位,就是曹操,不过没有关于他本人阅读《申子》的记载,只是陈寿点评时提到他“揽申、商之法术”,似乎也可钻研。
关于申不害的叙述,顾立雅用大段话描述了其语言的艰涩,并认为因此导致了其学不传。我认为这点可商榷,我个人觉得,申子的句子“艰涩”之处,或者是用了些中国人常用的比喻词(“圣人之符”),或者是用了大量的悖论式语言(“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而后者在其他先秦作品中也并不罕见,甚至在申子同时代的《商君书》中,亦有“法详则刑繁,法繁则刑省”(法律详细了,反而百姓不犯法能省刑)这样的表述。
《申不害》读后感(三):新发现的申不害
昨日读完《申不害——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政治哲学家》,【美】顾立雅 著,马腾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1版1印,16开平装369页,定价68元。本书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最新(192)一册。
申不害是谁?如果不看副标题,估计绝大多数非历史专业人士可能都一头雾水。的确,可能比起儒家之孔孟、道家之老庄、法家之商韩以及墨家等在后世影响(与争议)颇大的诸子百家来说,申子的影响力可谓微乎其微,许多人甚至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位位列“法家”的人士是何许人也。从个人而言,通过一些个人阅读,对“申韩之术”、“申商之术”有所触目,但是也仅仅限于这是一位讲求法律的人士,在战国七雄之中最弱小的韩国占据过执政的相位,后世提及申子的地方也寥寥可数,有印象的比如《三国志》(裴注)中即有载“ 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其中“申”即为申不害。正是抱着想了解这位处于云山雾罩之中的法家人士的目的,我读起此书。
作者顾立雅(1905-1994),美国汉学家,其学术地位堪称汉学“元老”,汉语古文的文字、考订功底极为深厚,可以说明显高出很多所谓的“汉学家”(人形翻译机)一大截。这个结论通过阅读此书即可明确得出。正是顾先生深厚的文字功底和辨析能力,得出一个令人(我)瞠目结舌的结论,即申不害这位讲求“刑名”的政治家,并非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刑律建设者或强调者,此处的“刑”并非是刑罚,而是“行为”之意。申子这位“法家”的“法”,也并非“法律(law)”之“法”,而是更多的是强调行政考核之“方法(method)”之“法”。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世官世卿,国家并未有明确的官员考核办法和成熟的行政制度,“刑”(官员行为)与“名”(职务职责)并不一致,往往一人兼任多项职务,权责不清当然会造成行政混乱,效率低下,在此情势下,“刑名之术”便应运而生。刑名之术与商鞅倡导的严刑峻法之“法”,显然在对象与目的方面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刑名之术面对官员,商鞅之术主要用以统治百姓;刑名之术在于“名”、“实”相应,是一种制度规范,商鞅之法重在“奖惩”,带有明确的强制性和独占性,所以有人认为,商鞅之法其实就是早期的“军国主义”,把民众绑架在秦国的战争大车之上,以军功为先,毫不关注秦人之生活水平的提升,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商鞅之法最酷烈之处,或可视作“将人变兽”和“率兽食人”。可悲的是,最后商鞅自己也丧生在他自己的苛法下(《史记.商君列传》载“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了解了申、商同侧身于“法家”而有如此巨大之差异,也就似乎可以理解秦末汉初的另外一桩令人(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即众所周知 “汉承秦制”,然而汉朝是在反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么汉朝到底“承”了哪些秦制呢?秦统一六国前后,李斯在集申商之大成者的韩非子这位法家影响下,与秦始皇共同建立了影响中国数千年的行政官僚制度(郡县制为其中一项而非唯一),毛泽东有诗云“百代都行秦政法”,可见其影响后世之深刻。然而我们却不能忽视的是另外一个事实,即秦二世而亡,被后世称为“暴秦”,固然这与两汉政治正确的“反秦”情绪有一定关联,但却不能抹杀其“暴虐”之事实。《史记.高祖本纪》《陈涉世家》等就有多处就有“天下苦秦久矣”类似的说法。高祖先入关后与秦民“约法三章”、“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从秦人的反映来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唯恐沛公不为秦王。”汉军后来与楚军对垒,也是以原秦军和新征发的关中士卒作为主力部队,甚至迫使项羽乌江自刎,瓜分项羽的尸体的,也是秦人,可见高祖的宽待政策对原秦国人民来说,是多么地受到拥护。
很明显,反秦是反其“暴”,即统一六国后继续推行严酷的对内对外政策,在“马上治天下”,把法家商鞅一脉的苛法继续推行下去,导致了自己的灭亡。所以汉朝初建时,汉政府以黄老之术为基本治理方针,政策讲求清静无为,萧规曹随是其最大的特点,也是社会上下的共识。则其继承的,无疑不能是商鞅严刑峻法的一套,而是承续了经韩非中和过申商之二法(尽管韩非也更多地偏向商鞅),李斯建立起来的官僚管理体系。从史料可以看出,有汉一代,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官员有着明确的政绩(绩效)要求,官员甚至需要经过考试,如晁错就曾经是考试的第一名,才能担任相关的职务。这在秦汉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史料中“上计吏”的存在更是说明了汉朝政府对考核的重视程度,这对于申不害及其学术认可而言,的确是一个令人欣慰的事情。从第8章《名学》来看,作者把“刑名之学”的“刑”解读为“行”,即行为之意,”行“不仅为个人的行为,且为职务行为规范,并举《韩非子》中君主“以刑名收臣”为例。若此说成立的话,则叔孙通制定朝礼,汉高言“今日方知为皇帝之贵也”似也可以作为一项证据。汉初君臣粗鄙不知礼,定然对权责范畴不可能做到精细化、制度化,通过制度(即”刑名“)的建设,方能差强人意,而要达到蔚为大观,则要待宣帝时期了。
但是历史却有其莫测之处,在文、景、贾谊等政治家重视政府构建和强调君主的驭人之术(这都是申不害的学术精华)之后,社会渐趋稳定,财富增加,国力强大,汉武帝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加强了对思想的掌控,这就使申子的学说一方面内化成君主的个人修行之术(驭臣之道,南面之术),另一方面则已经成为政府的行政习惯性方式,而其学术影响在外朝却由于无法帮助那些有志为官的读书人(只能通过儒家经典来获得官职),最终成为“屠龙之技”,无法获得回报而导致影响力减弱。这既是申子的愿望,也是申子的不堪。汉代甚至出现了把申商同质化的观点(刘向),申、商并列的结果,把申不害也混淆成了legalist,而不是带有“模范”、“技术”等意义的“法”的含义,这在本书第十章中有着精彩的辨析。对申不害学术造成的误解,就使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本该大放异彩的政治家,逐渐淡出了主流,在诸子百家里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陪衬,甚至连较为完整的篇章也难以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这是尤为可惜的事。通过顾立雅先生的论述,我们似乎又重新发现了这位堪称伟大的行政哲学家——申不害。
本书翻译用词讲究、准确,如p73“祖述”、p74“放伐”,颇有得译文之信达雅之“雅”意。这些词基本已退出常用词的使用范畴,可见译者汉语功底的确深厚。当然,也有几处需要编校更正之处,在此一并指出:
21注24“应合”应为“迎合”
197第三段“祁望”应为“祈望”。p234第三段同误。
183下注89大谬。言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考订韩非子生于前280年,死于前233年;李斯生于前208年,死于前280年。此处时间完全错误。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把韩非子生年放于前281年,因为不确定加了“此时前后”。李斯则是生于前284年,死于前208年。 注90倒数第二段“谴”应为“遣”。 倒数第一段“李斯晚节不移,为世诟病”,语句不同,似应为“晚节不保”。
205第三段“谴使”应为“遣使”。
241第二段“但是,那些反对他观点的人,才不直指其控制官场的主张,而是斥之为“法家””此句中“才”似应为“并”。
在封底,许倬云先生谈到“洋人读书不简单,咬文嚼字,比中国人认真”。是啊,申不害是中国先贤,然而被正名却是由一位外国学者完成,这确实令国人(我)汗颜呢。
推荐有兴趣的朋友阅读。
《申不害》读后感(四):【转载】孙晓春:如何认识和评价申不害的“行政哲学”?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往古时代一个一个的历史人物和具体事件构成的,如果既往的历史过程中没有了某一个人物或者事件,这历史便是不完整的,甚至有可能会是另一种面貌。然而,由于许多方面的原因,有许多历史人物,甚至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我们实际的历史研究和叙事中,在有意无意间被忽略了,申不害便是其中之一。
申不害(前385年-前337年),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本为郑国人,公元前175年,郑国为韩国吞并,因此申不害也就成了韩国人。申不害在韩昭侯时被任为相,主持变法,“内修政教,外应诸侯”,韩国遂致富强,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不害曾著有《申子》一书,后来散佚,只是在唐人编纂的《群书治要》中保留了《大体》一篇。在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中,韩国并不是最成功的,再由于申不害的著作大多散佚,因此,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无论是社会史还是思想史,申不害都是很少被提到的人物。据我所见,只是在刘泽华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才用较大的篇幅阐述申不害的政治思想。以申不害为主题展开专门研究,似乎是超乎想象的事情。然而,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GlessnerCreel)却花费二十年时间来研究申不害,并为我们奉献了《申不害: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政治哲学家》这部力作。
顾立雅(1905-1994),1929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曾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亚洲学会会员,与吴宓、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容庚、钱穆等著名历史学家相识并多有交往。著有《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孔子与中国之道》等。顾立雅对于《申子》佚文辑佚、考订,功力颇深,所著《申不害: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国政治哲学家》(ShenPu-Hai:AChinesePoliticalPhilosopheroftheFourthCenturyB.C)一书,1975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近日由厦门大学马腾教授将其译为中文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从申不害生活的历史时代入手,就申不害与法家、道家之间的关系、申不害的思想中国古代的行政系统、申不害的思想学说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等问题,做了相当系统的分析和讨论,本书的三个附录,《申不害史料考述》《〈申子〉辑佚》和《申不害佚文》,是作者对有关申不害的史料、《申子》佚文的系统考订,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作为颇负盛名的汉学家的思想史论著,《申不害》让人耳目一新。不同于常识意义上的人物纪传式的思想研究,作者试图在广阔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去理解申不害的思想。顾立雅不仅把申不害还原到战国时期的变法与百家争鸣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还试图从春秋晚期的郑国,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去追寻申不害政治思想的源头,对于申不害与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政治过程的关系更是大着笔墨。可以说,作者既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理解申不害的思想学说,与此同时,也是在透过申不害这个人来认识中国古代社会。
关于申不害的思想,顾立雅将之概括为“行政哲学”,并且认为他的行政哲学与中国古代的行政系统是密切关联的。作者认为,自殷周鼎革,“武王独擅政治大权的景象”已有显露,“普天之下广袤王土之统治模式”(P.38)渐露端倪。到了春秋时期,虽然周王朝对整个华夏的统治日渐式微,但“控制行政官员的技术已经应运而生”(P.39)。循着这一逻辑,申不害的“行政哲学”就是思想家对于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政治主观认知的结果。这个解释逻辑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来说无疑是有效的。
思想史研究是一项很有主观性的工作,即使面对相同的研究对象,从不同的认知意向出发,研究者却可以形成各不相同的认识,顾立雅对申不害权术思想的理解也十分独到。目前所能见到的申不害的著作表明,申不害思想的核心是“术”,亦即“权术”,简而言之,就是君主如何愚弄和驾驭臣下的技术或手段。顾立雅把申不害所说的“术”解释为调解行政关系的技术,“在申不害看来,不言而喻,国家在理念上确为‘老谋深算,沉思熟悉之产物……是一种艺术工作’”(P.47)。申不害权术理论的精髓,就是把君主看作是当然的权力所有者,“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申子·大体》)。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申不害那里,维护君主权力便成为最高的目的,而君主的主要职事便是防范手中的权力旁落。于是,君主用阴谋手段对待臣下便成了一门技术。顾立雅或许以为,依据这门技术能够衍生出一个高效能的官僚结构,这便是他把申不害的权术理论解释为“行政哲学”的原因。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在现时代仍然适用。顾立雅是欧美学界负有盛名的汉学家,其在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造诣自不待言。但是,由于自身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历所限,和西方许多汉学家一样,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理解也有可商榷之处。兹举几例如下。
首先是关于申不害的学派归属。战国法家的核心论题有三个,曰法曰术曰势,思想家只要以其中一个为核心而提出系统的思想主张,便是法家。《汉书·艺文志》也是把《申子》六篇归于法家,对此,汉魏以下绝无异议。但是,顾立雅却以申不害不像商鞅那样讨论法与法治的问题,认为其不是法家。这样,申不害究竟属于战国时期的哪一家便成了问题。
其次是关于申不害与道家的关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司马迁这句话是有问题的,黄老学派是道家学派的变种,是老子的无为思想与法家的刑名之学相结合的产物,很难断定这个学派是否出现于申不害之前,顾立雅也看到了这一点,不过,司马迁的说法也不是全无意义,它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申不害的思想与道家有着某种渊源关系。申不害“君无事而臣有事”的权术理论,明显带有老子无为主张的印痕。但是,顾立雅却否认申不害与道家学的联系,其理由是老子其人其书晚出,申不害没有讨论过形而上之“道”等等。作者显然受到了上个世纪之初疑古思潮的影响。另外,作者又认为,先秦道家是无政府主义者(P.145),因此,申不害的“行政哲学”与道家扯不上关系。事实上,先秦道家只有庄子思想才具有无政府的特征,甚至庄子后学都没有无政府的思想倾向,传世的《庄子》外杂篇中有许多讨论圣王治国的篇章便是其证。
再次是有关申不害思想与中国古代专制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解。顾立雅把申不害的思想定义为“行政哲学”,因此,对于申不害思想的认识便离不开对中国古代的“行政结构”的评估。顾立雅在本书中引述斯普林克尔的话说:“几乎到十八世纪末,中国在行政组织问题方面仍远比世界其他地方先进。”(P.4)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是否可以通过这个被高估的古代行政组织来评价申不害的“行政哲学”?作者虽然没有明说,但其评价取向却还是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些。在本书一开篇,顾立雅先是说到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顾立雅认为,罢黜一些治异端学说的贤良,是“‘儒家胜利’的第一步”(P.1),我猜度作者的言外之意,申不害的“行政哲学”被禁断是不小的损失。
有一件事情需要明确,拒绝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治的本性。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上,历代王朝的统治者的人品、学识以及治国能力虽然人自相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想把自己的偏好强加给整个社会,他们自己喜欢什么,也就要求举国臣民喜欢什么。秦汉时期,帝王的文化素质大都不是很高,自己无法冒称思想家,只能在百家之学中选择出一种作为统治思想,于是便有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看,无论是焚书坑儒还是罢黜百家,都不是人类思想进程中的幸事。但历史地看,在思想多元已是不可能的中国古代社会,专制国家选择了哪一种思想学说,却不可等而视之。这是因为,就思想内容而言,传统儒家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方面有着更为强烈的关注,而法家刑名之学却只能导向社会政治生活的残酷和恐怖,正如作者在本书后面所说的那样,“恐怖主义政治走向极端,必将暴露自身局限”(P.194)。在这一意义上说,秦王朝的暴政,申韩之学是应该负有责任的。而汉王朝最终选择了儒家伦理政治学说,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进步。
(作者为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刊于《中华读书报》2020年4月15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