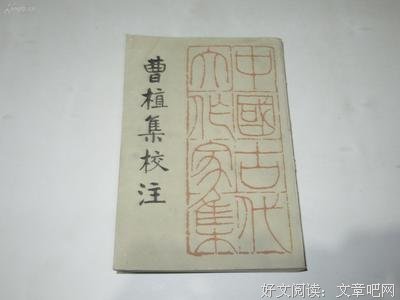曹植集校注读后感100字
《曹植集校注》是一本由赵幼文 校注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60元,页数:59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曹植集校注》精选点评:
●虽然不喜欢子建同学的诗风,但这本书编得确实不错…………
●大爱的诗人。
●跟曹丕一对比,曹植就是一个早期嚣张啰嗦,晚期抑郁啰嗦的大叔
●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
●台版精装本
●我没有读完就还给兔鼠馆了,我知道错了呜呜。
●以前在漯河图书馆借阅过。
●二十年后重读,始登堂入室。
●“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
●真是步兵的先驅,一對比就覺得步兵不夠博大了。
《曹植集校注》读后感(一):建安至于大谢
今天在艺园吃饭,说到古体近体,说到杜律以及白元二人的J情,阅读初唐盛唐的繁复华丽,平仄,对仗以及工整,又说到陶潜诗中的禅意,陶潜之被苏轼等宋代人所喜爱,读的不多,也不算少,我还是最喜欢建安以至于大谢之间的诗。
一般来说,大谢和陶潜是近体古体的分水岭,大谢的山水,摆脱不了游仙诗的禅理尾巴,陶潜的田园诗,无志于山水田园风光,在于寄情怡情,陶潜的农夫,个个都能够“疑义相与析”。大谢之山水色,便在于山水的描摹,并不讲究理趣。山水色如在眼前,画中自有山水之情之理。
之所以是古今的分野,乃是在于一个融情于景,一个景语即景语,情语即情语。
魏武之朴素骨感,魏文之哀婉,陈思之华丽,当得起“风骨”二字。
“惊风飘白日”,随着父亲在塞北战场,黄沙漫天,黄沙掩日,军旗猎猎,透过军旗萧萧,远处一轮白日兀立。
“朱华冒绿池”,颜色的对比度和“冒”字的朴素,是被称赞的原因。
《送曹彪》应是陈思的得意之作,“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
钟嵘诗品,陈思为文人诗第一,此后,鲍参军,左太冲,以朴素,硬朗的语言,撑起来“文人”的形象。
而到了田园,大谢之后,融骨于血肉,无处见“骨”。
《曹植集校注》读后感(二):但幸人间存陈王华篇,一唱千年
《文心雕龙-时序》中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是呵,他的满纸华章透过一千八百年的风烟,留下了邺城那一段“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的风流岁月,留下了山长水阔走多远也不会丢的一段段友情,更真实地记录下了他流离转徙后半生的寂寞与痛苦...
或许他至死都在盼想,期望哥哥想起他们邺下放歌,西园宴游的少年时光,念及骨肉之情,和他重叙旧好。每每读到《七哀》《美人篇》等,我总忍不住心伤。这些诗中的女子纵被丈夫抛弃,却仍然忠贞不渝。“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她们坚定的相信丈夫一定会回心转意,与自己重回到那琴瑟和鸣的幸福日子里。
虽怨却不怒,哀婉而不忧伤。我真的很难相信为什么他被如此折磨之后还能对哥哥怀有如此美丽的幻想。
再看到他卑躬屈膝地歌颂曹丕曹睿父子的应制诗,心里更是一阵抽痛。是什么样的苦难,居然磨平了这个张扬的孩子所有的棱角。或者..如果他能早些明白生存的法则,历史是不是不会如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
然而他们都已经不在了,建安风骨和正始之音都已成了历史的绝响,黄河无数次改道,曾经繁盛一时的邺城也早已荒凉,铜雀台只剩一抔黄土,哪里还有昔日魏武横槊赋诗的霸气与风光?
千年不变的,只有他那一篇篇真情流露的华美诗章,还有那个洛水之上的神秘女子,无数次飘进后世大家的画作里,容颜美丽而忧伤。还有他那任凭时光洪流恣肆也冲不淡的绝世才情,反复被后人吟唱。有羡慕,也有叹息;然而那些人终是无法真正地懂得你。
放下书卷,在叹息之余,有时候也会陷到自己的臆想里,洒脱直率的弟弟和那个固执不肯退让的哥哥,或许早在另一个世界,微笑着握手言和了吧..
《曹植集校注》读后感(三):曹植——步衡薄而流芳
溯洄而上,我们的故事从洛河之滨开始。江面开满芙蓉千朵,恰似一张张温柔的笑脸,迎风而舞。我涉江而过,风中扬起一片清香,将我包围,劝我留下。
但这些都不是我所期待的。江月无情,早已将昨夜星辰交给猎猎西风,吹散我所有的儿女之情,留下永夜无涯,空锁楼中燕。碧海青天,夜夜无眠,银汉迢迢,找不到一叶舴艋小舟,载我到达爱情的彼岸,与佳人相会。
波心荡漾着你的笑容,我俯首掬起你的身影,拥入怀中,久久不放,直至消失天与地。其实我也知道,这只是一场幻觉,结局早已写好,我等待在风中的手,今生今世是无法等来和你的深情一握,只能紧紧握住留有你丝丝发香的玉带金缕枕,痴痴守望。原来牵挂千年,我们始终没有相逢,肠断他方。
爱情的错肩,缘起就是缘尽。
乱世桃花,能幸免于难,已属万幸。故人故园故国都已破碎不堪,不敢回顾,总怕触痛记忆的伤痕。从此,她将移植,江南,只能以后午夜梦回,深藏记忆之中。家愁和国恨,瘦肩难挑;美丽与哀愁,随她北上。
烽烟满路,掩盖不了她的天香国色,相遇的刹那,爱怜在曹植的心头翻涌,纵使我给不了她一生的幸福,我也要对她送上我一生无尽的牵挂。
书剑之间,逐鹿中原,在父王的千秋伟业中,我也想以毕生之力,添上华丽浓彩的一笔。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将身躯与刀锋并驾,把性命交沙场驰骋,在刀光剑影中痛饮敌血。大漠孤烟原该留下我的名字,燕京幽都本应是我系马的地方!
然而战官渡,收河北,下江南,入西凉,只身转战数千里,一剑曾挥百万师,因一己之欲,使万众流离,所建立的大国,当中到底要填埋多少热血青年作基石?家国之间,肩负是如此的沉重。
生于将相之家,我别无选择,每一仗后,惟有一醉,才能找到众多有名字或无名字的死国者的栖息之地,心中将其一一祭奠,以慰亡灵。
西北有高楼,楼上有佳人,远眺成为她们每天惟一要做的功课。情人在回归的视线之外。千山暮影,知他今夜梦枕何处,万里层云,念奴昨宵醉守空闺,雪舞笳厉,吹断几缕相思情怀,马蹄的答,踏碎一帘浓蜜幽梦,南来北往,可惜都是过客,不是爱人。
希望总在辗转中落空。
遥望春闺梦里的情人,正在轻骑逐单于,刀锋过处,头颅和梦想一起跌入尘土,又一段爱情没有归期。鲜血湿润干枯的大地,泪水模糊我的视线,斜晖下依稀听到他们在风中呜咽的声音。
当千窗同景一齐跌入暮色,功名富贵如彩霞满天,转瞬即逝。我于风中伫立,无言无语。
她们始终等不回爱人相聚的清脆铜铃声。
铜雀春深,锁不住深情的二乔,二乔自有她们的风流倜傥少年郎,为她们守驾护航。那一夜铁锁横江,夜如白昼。帐内数百幕僚将士,高谈阔论,胜利仿似就在眼前,伸手即可触及。我的《登台赋》也一挥而就,在尚未干透的墨香中,我好像闻到未来的美好气息,芳香扑鼻,我的生命花树,原本就要璀璨闪耀在这乱世的夜空。
然而一夜骤雨,将河岸边的小舟冲得不知所踪,也将我的华美锦绣打得七零八落。在自己的沙场上,我再也无法挥剑书写我的传奇。酩酊之后,我失去了终生朝夕相依的笔和剑。我还能拿什么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阳光缓缓升起,信念冉冉下沉。
永恒中,她踏着凌波微步,施施然向我走来,左脚轻云蔽月,右脚流风回雪,明眸皓齿,顾盼生辉,江面上所有的芙蓉黯然失色,不敢仰首。我守候多年的梦在这一刻开始绽放,她的端庄淑美轻轻飘落我的心头,凝固在水的中央。曾经在风中挥毫沙场点兵的手此刻却是不知所措,心情随江水簇涌,震荡不怡。
原来痴情是可以等到缘来的,哪怕是一则神话,也会生根发芽,长大开花。
然而匆匆的脚步无论再如何匆匆,却也无法追上流云的回首,我的精诚情怀始终无法开启玉石的心扉,手足之情在君临天下的快慰睥睨中显得是那么的孤独无助,兄弟阋于墙在历史的沸点开始爆发,我知道,七步成诗只是一个引子而已,悲剧将会陆续上演。
我是不会输的,我不能让我所爱的人失望,在“吱吱”的豆汁声中,我跨出的每一步,都是那么的惊心动魄,仿似踏进他们的心头,令场上的每个人心头颤抖不已。
我仿佛看到多年以后同样的一出悲剧正悄悄上演,故事轮回总会有它蕴酿发酵的过程,不必急不用急,含在苞中的剧情总有待放的那一天。当明年春日融融的时候,燕子衔着新泥在梁间筑构它们新的爱巢,它们并不知道,这雕梁画栋的主人早已易换。
我赢了,但也是输。
我已无家,君归何里?在首阳山的泥泞道上,我们徘徊不前,频频回首,这里曾经是我们的家和国,是我们生长壮大的地方。如今我们再也不能随意在高楼系马了,宫殿的飞檐勾不住日益疏薄的手足之情,响亮的钟声唤不回去意决绝的孤高背影,所谓血浓于水只是太傅所教的一句谎话,金碧辉煌的皇宫,只怕都是用血浆涂成的吧。风回处,我对曹彪寄出最后的珍重,“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
在这一刻,我坚信我的爱,时光是无法将它稀释的。
神光离合之际,河面粼光闪闪,似千面镜台,反射出流光逸彩的天然舞台。在水一方,她含一朵微笑,为我翩然起舞。我的悲伤和愤懑,京城与贵气在她轻拂的长袖中,都黯然离我远去。
迷离中,我看到在光的中心,那个神仙人儿,不沾尘世的一点烟火,赠我绿洲与家园,温柔与缱绻,然后对我说,虽潜处于太阴,却长寄心于君王。
人神纵然道殊,一刻相聚已成永恒。此生愿长醉在这川烟水,每日畅饮她那醉人的雨露芳泽。
让一切在洛河的空中随风散去吧!我的故事已落幕,爱恨已入土,前世今生,花开花落,我只想做一棹舟江上忙碌的舟子,日复一日载红尘寻梦的男女到彼岸,山一程,水一程,永不歇止。
《曹植集校注》读后感(四):陳王詩學源流略論稿
陳王詩學源流略論稿
顧一心 撰
自敍
余之愛陳思王詩亦久矣。嘗謂陳王稟仁人之心,抱英雄之器,高樹悲風,盈虧異勢,終不得翺翔於宇內,然其沉鬱高華、翩翩君子之致,終焉未改。至於繼軌風騷,爭流雅頌,舉兩漢之詞章,開六朝之文苑,源流之備,子美以前,一人而已。夫論詩家要指,知其人、論其世、辨其體、溯其源而已矣。執此四端,則一代之文章、一人之心史,斯可明焉。或曰陳王之詩,前哲之述備矣。其考史者,本於建安黃初之事;其論詩者,祖乎彥和仲偉之言;校勘之則,功在儉卿;評注之精,典推晦聞。雖然,夫若求諸辨章源流之間、體悟深微之際,甚而於漢魏文章學術之會通處得一發明者,則千古秘鴻,或有未覩。此余孤篇之所爲作也。乙未年春,折馨室主人顧一心謹序於南海。
劉向
漢末詞章大興之所由者,“治古學”與“貴文章”二事之貫通也。而子政實暢其機。昔者向典校秘府,遂於百家九流之書,靡所不覽,其所輯纂者如《國策》、《新序》、《說苑》、《列女》諸書,皆博洽多聞之屬也;今覽陳王辭賦篇什,凡引風俗人物,每出於彼。如《七啓》之用儀狄、南威,典出《國策》;《鼙舞歌》數篇連用伯瑜、董永、齊杞梁妻、趙津女娟故事,悉見之於《說苑》、《列女》、《孝子》。其餘如《矯志》“都蔗雖甘,杖之必折”,語見向之《杖銘》;《七啓》“插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典出向之《新序》,皆博物引類以助其詞華者也。又陳王撰《列女傳頌》一卷(《隋書•經籍志》),可爲其親向之證。向本楚元王交之後,學與申公同源,世多以爲其習《魯詩》,陳王用《詩》兼取三家古義,其《七啓》、《洛神》用漢濱遊女故事,事義皆與《列女傳》同,竊謂陳王詩之用魯說者,或亦源出於向也。論曰:夫劉向者,本非詞章之士,然既通覽先秦以來藝文百家之書,則其智識學術之系統,必與兩漢拘守家法之儒異焉,是以遠通六藝,近接謠俗,下暢漢末諸子博物洽聞著述之風也矣。又曰:漢末經學大變而詞章蜂起,然則詞章之興,實亦源出經典之一脈爾。夫今學既暗,則古學爲明;古學既明,則士以通博爲務;士既以通博爲務,則益以詞章才藝爲能也。以此視蔡中郎至曹、王諸子,豈獨辭人之流也哉?
班固
兩漢藝文學術之分野,存乎今古學範式理路之爭,此余論之所宗也。班氏學無常師,不爲章句,博稽經藝,潛心文章,其論藝文大要親乎劉向父子,是亦博物洽聞著述之流也。況夫陳王畢生詩文學術,源流多出齊魯、關中,班氏素扶風之郡望,兼受師丹齊魯之學,其有所澤溉於陳王或可知矣。今觀植集取法班氏諸子處甚多,如《送應氏》“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句,《九愁賦》“野蕭條而極望,曠千里而無人”句,率皆本自班彪《北征賦》“野蕭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家”。《歸思賦》“城邑寂以空虛,草木穢而荊蓁”句,本自班昭《東征賦》“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荊棘之榛榛”。《節遊賦》“亮靈后之所處,非吾人之所廬”句,本自班固《西都賦》“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文帝誄》“遙投骨於山足兮,抱恩養於下庭”句,本自班婕妤《自傷賦》“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至其詩賦所用事義典故,亦多取《漢書》,殊不亞於《史記》。如《三良》詩用《秦風•黃鳥》舊典,即采《漢書》“良士殉死”之說(即詩之齊說也),而不用《史記》、《毛詩》“穆公殺賢”之義。又陳王傳有古人畫贊一卷,今存者二十六篇,自始祖聖王、漢室先帝之外,有德無位者居其四,而班婕妤竟得其一。可知婕妤才德文章之傳世者,非惟班公作傳褒美於前,亦有陳王作贊鼓吹於後也。以此推陳王詩歌學術之源流,豈非必有得乎班氏之秘鴻也哉?
張衡
兩漢賦家,多自古學以入於文章之門,而平子亦預其流焉。觀其辭賦,通博淵雅,至如《東京》、《西京》、《南都》之屬,中古文苑,推爲大宗,豈虛也哉!今視陳王本集源出張平子處甚多,玆擧數例如下。《七啓》“下無漏跡,上無逸飛”、“金墀玉箱”、“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等,率皆出自《西京》、《東京》兩篇。《酒賦》“素蟻浮萍”,本乎《南都賦》“浮蟻若萍”;《責躬》“天啓其衷”,本乎《西京賦》“天啓其心”;《車渠椀賦》“命公輸之巧匠”,本乎《西京賦》“命般若之巧匠”;《洛神賦》“嗟佳人之信修兮”,本乎《思玄賦》“伊中情之信修兮”。又陳王援引古句,常變其體,故每有以賦語化入樂府古詩者。如《妾薄命》云“客賦既醉言歸,主人稱露未晞”,遠出《小雅•湛露》,近本平子《南都》;《公宴》詩云“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千古摘爲名句,而實本自平子《東京賦》“芙蓉覆水,秋蘭被涯”。以上章法句意,率皆相類,而追摹之跡明矣。
魯詩
漢末傳《詩》,漸脫藩籬;鄭君箋《毛》,兼採古義。是皆古學通儒之風使然也。三家詩湮於中古,然其遺說深意,間或存於詞章。世稱陳王源出《國風》而情兼雅怨,其深於《詩》者可知矣。今觀其篇什,文辭典故祖乎三百篇處甚多,於諸家勝義,皆有所取。其與魯說相近者,如《七啓》、《洛神賦》之用“漢濱遊女”,取義於神仙,事見劉向《列女傳》;如《釋思賦》之用“白駒”,托喻於朋友,義同蔡邕《琴操》;《朔風》五章,自“昔我初遷”以下四句,盡得風人深致,系從《小雅•采薇》一篇模擬而來,其旨則與《白虎通》所據《魯詩》行役哀思之義相似。以此觀之,則陳王之習《魯詩》雖無師承可考,然其藝文源流之一脈必與通焉。曹氏建安一脈,聲情風度,多本蔡邕,文帝嘗記曹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好”,至於仲宣、元瑜,皆從遊受學於邕者也。邕乃漢末魯詩大宗,竊思陳王用《詩》之采魯說者,或亦出於彼乎?又子建之文章,事義風俗,每出劉向。向乃元王之後,亦《魯詩》之世家也,設使陳王秉燭以宴諸子,則子政其與蔡中郎並驅爭先者哉?
齊詩
齊詩授受盛於西京,而衰於漢末。今覽陳王詩賦,齊說古義,猶或存焉。觀其《敍愁》、《靈芝》、《卞太后誄》諸篇,數用《邶風•凱風》之章,皆本齊說,以陳情實;《三良》、《王仲宣誄》、《文帝誄》諸篇,辭義本乎《秦風•黃鳥》,均采齊詩良士殉死之說,而不用毛詩刺穆公殺賢之義。又子建之本乎齊說者,每與鄭箋相合,似亦可明漢末傳《詩》之譜系。譬如《黃鳥》之詩,鄭箋之旨,蓋同齊說;又如《責躬》用《曹風•鳲鳩》七子之歌,一則用齊說“均而不殆”之旨,二則合鄭箋“今上不均”之義;《王仲宣誄》用《小雅•常棣》瑟琴之句,其義與《毛傳》鄭箋、《禮記》鄭注略同,康成禮學本自后蒼,疑此詩之《箋》亦源出齊說也。蓋鄭君箋《毛》,通覽古義,其訓故多宗毛、魯,而詩說多本齊、韓,原系兼採諸家而自由闡釋之大宗。漢末經學,壁壘漸消,而海內咸奉康成,曹王諸子,得無沾溉其中也哉?斯人已遠,吾將登陳王之堂而問焉。
韓詩
韓詩傳習,漢末轉興,故當世治古學好文章者多預其流焉。康成學韓詩於恭祖,伯喈傳《詩細》於京洛,二君海內大宗,固不必論矣;又子建所交遊親善者若仲宣、元瑜,皆受學於伯喈,邕本魯詩學者,竊思子建之兼用魯、韓詩說者,或源出於此焉。世多謂子建爲韓詩家,如王先謙《集疏》、黃節《詩注》皆主是說,異代相襲,幾爲篤論。夫子建詩賦文章合於韓詩者固多也,譬其《七啓》、《洛神》用漢濱遊女故事,義與魯、韓詩同;《責躬》“胡顏”一辭,典出《鄘風•相鼠》,諸家作“何”,獨《韓詩外傳》作“胡”,此皆可證其從《韓》之源流。然遍取陳王詞章與諸家遺說覆對,則四家古義實並路而爭驅,豈韓詩之所獨擅哉?此古學者之失也。竊疑古人之以陳王爲韓詩家者,或以李善《選注》多用韓《序》、《章句》、《外傳》等書以注植文之故,然善注《文選》之本意,固不在源流之發明,而在文辭之訓故,故徑取當時存世之韓、毛而不及於齊、魯爾。又古人輯佚三家遺說,每用辨章師承之法,凡一人有某家祖述源流可考,則徑錄爲某詩家。予謂此法或可用於恪守師說之學者,而固不足論治古學貴文章之通人也。夫詞章之學興於漢魏,原博物洽聞、學兼今古者之所爲,故其隸事用典必不拘於一家,惟曉暢文意以盡其情而已。康成、伯喈以碩儒之姿,而不拘一家之學;況陳王諸子妙思六經而逍遙百氏者乎?此中固有今古兩派學風之大分野,不可不察也。
樂府
樂府本秦漢之官署,漢世歌詩之所自出,故後世以文體稱焉。中古以降,文籍散佚,考論卒難,至每與古詩相混,零落無歸者衆矣。雖然,漢末詩樂既分,則樂府、古詩,終爲二體,其風貌之異存焉,自可循聲辨體以別之。陳王本國風之變,發樂府之奇,嘗與楊德祖書曰,“匹夫之言,未易輕棄”,蓋謂閭里歌謠之質也。如《送應氏》、《節遊賦》、《贈白馬王彪》諸篇數曰人生不永,其“人命若朝霜”、“去若朝露晞”、“忽若風吹塵”之類,皆《薤露》古歌之變體,漢魏間樂府古詩多用之,固不足奇也。又樂府中多有辭意佳妙、鋪敍可玩者,亦加熔裁隱括,入於辭章。如《箜篌引》“盛時不再來,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四句,系《董桃行》“年命冉冉我遒,零落下歸山丘”兩句之拓展;《美女篇》“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隅”四句,系《陌上桑》全篇之壓縮。其餘如《秋思賦》“扇箑屏棄兮絺綌捐”句,語自班婕;《感節賦》“欣陽春之潛潤,樂時澤之惠休”句,辭本《長歌》。是亦皆取樂府佳妙之制,而文猶過之,介乎擬則與奇創之間也。
古詩
“古詩”一詞,南朝文士多用之,蓋指晉宋間所傳前代無名作者之五言徒詩也。《世說》載“古詩”之名,《詩品》列“古詩”之品,《隋志》存“古詩”之目,又《文選》、《玉臺》,閒取英華,貽諸後世。觀諸家之遺說,則晉宋間固當有“古詩集”一類抄本傳世,其數約計五十餘篇,至於作者,悉未能考,或傳爲枚叔、陳王、仲宣之流所制,亦不足以爲信説也。今以之與陳王本集對觀,則章法句意多相仿佛,而質稍過之,至遲應作於魏世,而年代差近於建安也。如陳王《朔風》首章“願騁代馬,倏忽北徂”、“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四句交映,顯是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兩句之敷敍。又如《遊仙》之“人生不滿百”,《贈白馬王彪》之“自顧非金石”,《浮萍篇》之“裁縫紈與素”,均與古詩“生年不滿百”、“人生非金石”、“被服紈與素”之辭絕類。此類“古詩”情旨,多遊子思婦之辭,怊悵切情而有所寄托者也,其修辭則猶未脫古樂府之遺意。觀陳王之與“古詩”合者,但取其章法句意,化入全篇,以成風人氣象,復摹以兩漢賦家之遺翰,以熔裁鍛煉其修辭。由是知陳王得乎雅俗之際、文質之中,寧虛也哉!
《曹植集校注》读后感(五):关于曹植诗文的几个命题
如果说写出亘古稀有的诗篇是一种幸福,那么诗人的付出是不是就所有值了呢?那种在乱世不能自主的命运,那种在现实遭遇束缚的痛苦,如果是上帝眷顾天才的字符,那么诗人就可以了无遗憾了吗?无处找寻幸与不幸的分界,只能讲——生逢乱世是为诗人之不幸,有幸瞻仰诗人的辞华却是我们之福音。
【友谊】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离别是古人诗中常见的一个主题,从古远的《诗经》到汉末的《古诗十九首》,千百年来一直毫无厌倦的吟咏着。人生在世,何处有不散的筵席,谁又能不遭逢别离?正因为它有着普遍意义,所以才有着长盛不衰的魅力。曹植之前的诗作多是歌咏游子思妇,而曹植的则是偏重于友谊。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在曹植之后,友谊成为中国诗歌中最为重要的主题,它所占有的地位,如同男女爱情之于西洋诗。这个诗题的创始者,就是曹植。换言之,是曹植发现了友谊对于人生的价值。」如他的《送应氏二首》、《赠王粲》、《赠徐干》,每一首都是那么深情雅致,诚恳真切。
离友诗二首
王旅旋兮背故乡,彼君子兮笃人纲,
媵予行兮归朔方。驰原隰兮寻旧疆,
车载奔兮马繁骧。涉浮济兮泛轻航,
迄魏都兮息兰房,展宴好兮惟乐康。
凉风肃兮白露滋,木感气兮条叶辞。
临绿水兮登崇基,折秋华兮采灵芝,
寻永归兮赠所思。感离隔兮会无期,
伊郁悒兮情不怡。
这两首《离友诗》是写给夏侯威的,其一诗中用了「驰」、「奔」、「涉」、「泛」,不厌其繁的渲染路途的遥远,凸显送者(夏侯威)的真挚。其二诗中曹植赠与友人秋菊,为后会无期而苦闷无端,离思的愁绪应和着孤独的苍凉。微妙的空间感和敏锐的节序感,仅仅勾勒一个片段,就可以让我们睹见曹植对于友谊珍视的性情。
【玄思】
曹植所处的年代,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汉王朝构筑的经学谶纬一夕崩溃。人生的短促,命运的难卜,个体的无能为力,荣华富贵的不可信不可靠,逼迫着诗人思索价值的内在性,那么此时的诗人返归真我也就自然而然了。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薤露行》)将自己的理想抱负,置于宇宙的无极和人生的短暂强烈的对比色之中,慷慨的基调浓烈的氤氲了悲凉的氛围。「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赠徐干》)光景的倏忽而逝,兀然的让人心惊,人生惜短,可怜的是自己怀抱荆山之玉却不见用,连引荐友人也做不到。无奈无力的情感中嵌入终极思考,更显出生之悲剧性。「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送应氏二首》)天地久存,而嘉会难得,人无法摆脱生离死别的困窘。功业、个人、友谊,所有的一切在无垠天地、时间的流逝中,都是那么的脆弱和无助。翩翩年少的诗人无从找寻解救的答案,只能干渴的呐喊,做出勉强的姿势,而这种骨气在文字背后却无意识地加重了悲剧的色彩。
箜篌引
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
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
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
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
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
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
久要不可忘,薄终义所尤。
谦谦君子德,磬折欲何求?
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
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
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
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
谢灵运说「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即使在年少轻狂的时期,曹植也未能沉醉于夜夜笙歌的欢娱,往往贵介公子的情怀未抒尽时,彻骨的悲凉便涌上心头。声色犬马并不能稀释他内心的忧患,反而深化了死亡的真实性,末句的「知命复何忧」不过是无可奈何的自嘲罢了。
如果说上面是从外在价值的不可靠来体认生命,那么《愁思赋》、《洛神赋》、《髑髅说》则完全是玄学的思辨。
愁思赋
四节更王兮秋气悲,遥思惝怳兮若有遗。原野萧条兮烟无依,云高气静兮露凝玑。野草变色兮茎叶稀,鸣蜩抱木兮雁南飞。归室解裳兮步庭前,月光照怀兮星依天。居一世兮芳景迁,松乔难慕兮谁能仙。长短命也兮独何愆。
曹植的诗多少有些昂扬的色彩,他的赋则常常展示出他内敛、玄思的一面。例如这篇《愁思赋》丝毫没有附加以往的功利色彩,在解构愁思这种情绪时,完全将自己置身于无边的秋景,与星月的寥廓之中,比对出个体的渺小;也没有像写游仙诗时那样,慕求自由与长寿,而是很现实的表达命途的无可捉摸,只有死才是真实的无奈。永恒只属于造物主眷属的天地,个体永远不能摆脱自然法则的时间制约,无论是他本人还是细微的生命体都消解不了这种亘古的悲剧性。
当人意识到个体的存在不过是茫茫沧海的一粟,恒久时光的一瞬,难免「自失」于宇宙进程的无限性中,「因人生无常而生的种种痛苦也将在这庄严的无限性前自惭其渺小俗浅,自失指引人步入齐万物,等生死的超然灵境」。
夫死之为言归也,归也者,归于道也。道也者,身以无形为主,故能与化推移。阴阳不能更,四时不能亏。是故洞于纤微之域,通于恍惚之庭,望之不见其象,听之不闻其声;挹之不充,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嘘之不荣,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冥漠,与道相拘,偃然长寝,乐莫是逾。
《髑髅说》在曹植的诗文中是非常奇特、浪漫的一篇,借曹子与髑髅的对话抒发与天地物化的生死观,很自然的让人联想到《庄子•至乐》篇的「庄子见髑髅」,两者在思想情趣上极为相似,即「万物一府,死生同状」。虽然曹植在结尾处,来了一句「夫存亡之异势,乃宣尼之所陈。何神凭之虚对,云死生之必均」,似乎回到了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模棱两可状态,然而从曹子的询问来看,「子将结缨首剑,殉国君乎?将被坚执锐,毙三军乎?将婴兹固疾,命殒倾乎?将寿终数极,归幽冥乎」,在死生困窘的状态下,诗人是很倾慕庄子的洒脱的——与其说曹子是诗人本人,不如说髑髅更能代表他的心绪。那么曹植众多的诗文都关乎终极的念想,释然于逍遥境界也就自然而然了。
本身存在的偶然性与荒诞性,和宇宙的绝对性、不朽性不可同日而语。诗人在这种终极思考时产生过恐惧,也有着对生存意义的困惑,但他最终能「超脱身内卑下的欲求,透破功名利禄的束缚,进抵不为形躯之我所圄的境界」。诗人的自我救赎,一是如上文,「用至大无外的永恒宇宙来吞没个人人生,让个体通过把自身的有限性投入到宇宙的无限过程来获得自我超越,实现不朽」,即自失;一是「用至大无外的『我』来吞没宇宙及其他在者,把居于无限时间流程中的宇宙当作『我』之自我完成的内容,由此铸成『我』之永恒」,即自圣。
《洛神赋》从情节上简单来讲,是描绘人神浪漫梦幻的邂逅,与无从结合的惆怅分离。透过华美凄婉的文辞,我们隐约可以窥见诗人的白日梦,其实存在着个体的自我完成。洛神宓妃,也不是单纯的香草美人的意象,而是指向着完美的自我。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
轻盈柔美的洛神风姿秀逸,清丽的眼瞳顾盼生情。诗人极尽笔墨之力,书绘出洛神容颜的天生丽质,仪态的飘逸妩媚,绰约的风骨难描难画。而贮藏的纯洁灵魂,又是那么美丽贤淑,「嗟佳人之信修兮,羌习礼而明诗」,不仅通达礼仪,也明晓诗书。超脱于尘世的形神之美,赋予了洛神在广袤的天地间至善至美的超然存在,也意味着诗人完成了在浩瀚恢弘的宇宙秩序中自身的圣化。然而这种对不朽美的渴慕与满足,并不能摆脱自失的困境,终究也将被宇宙所拘束。正如「我」和洛神之间,永远横亘着无情的纲纪、人神的殊途,难以结合让人扼腕叹息,诗人也无从真正的超越于宇宙——看似无意义的宇宙秩序其实存在着神圣的意志,个体的自我完成是无从超脱宇宙的无限性的。
【复调】
诗人在我的观念里永远构不成信仰,能构成信仰的只有Jehovah。诗人也是人,也有平凡人的脆弱与无知,自私与愚蠢,和全知全能主宰一切的上帝永远不可能对等的。也缘于此,诗人的意志即便在同一时期也往往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支离破碎的呈现多重旋律。尤其像曹植的那样棱角鲜明的诗文,这种复调的美学风格非常的显眼。
曹植的早期诗歌,《白马篇》气势昂扬发人振奋,「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一位幽并游侠的形象呼之欲出;而《名都篇》中的京洛少年,华服丽饰放荡无端,识「骑射之妙,游骋之乐,而无忧国之心」。完全两极的人格,一个憧憬着建功立业,一个在及时行乐中骄逸豪奢,都是这位相府公子的本真——它们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有着全然平等的意志上的对话,形成了多元的艺术魅力。
这种不同声音的对话形态,在后期诗文中比比皆是。曹植一面哀怨温柔的借喻香草美人试图打动君主,指摘鸱枭以讽小人猖獗;一面渴求在有生之年能为国效力,慷慨激昂的再三表明志向;一面绮思遐想着自己凌云飞翔,随心所欲的往来仙境。时而恭顺,时而悲壮,时而觉悟,不同的面具诉求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及人格概念。
桂之树行
桂之树,桂之树。
桂生一何丽佳!
扬朱华而翠叶,流芳布天涯。
上有栖鸾,下有盘螭。
桂之树,得道之真人咸来会讲仙,
教尔服食日精。
要道甚省不烦,淡泊无为自然。
乘蹻万里之外,去留随意所欲存。
高高上际于众外,下下乃穷极地天。
读此诗篇,念想着花瓣恣意盛放、飘香天涯的仙境,我们所感知的诗人洗脱凡尘,超然于物外,有羽化登仙的风姿翩然。《杂诗》「拊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之句,则体味到诗人在困窘中,仍不减俊秀的风骨,毫无颓废萎靡之态的情怀。而《美女篇》便娟婉约移人情思,显露出诗人敏感多情的一面。他的每一首都是那么的强调人格的存在感,这些人格倾向又是那么并行不悖的直抒自己的声音,仿佛一颗灵魂在挣扎中进行着多层次的对话,将人性深处的矛盾巨细靡遗的诠释出来。
很显然,这种多重旋律的复调风格是同时代的诗人所不能比拟的,他们多偏向于一种思想流向,或古直,或悲壮,或婉约,缺乏思维的辩证色彩和开放的可能性。即便在后代也很少有人达到这样的美学高度,苏轼算是不多的一个,这应该与他们的自身经历与登峰造极的学问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