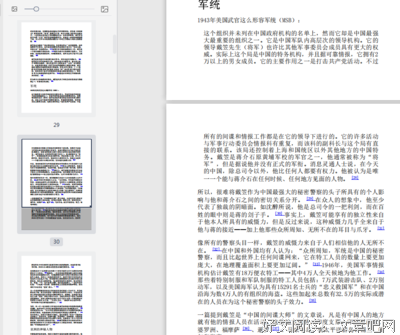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读后感精选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是一本由[美] 魏斐德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584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201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精选点评:
●动荡的乱世、变革的时代中,一位流氓知识分子的权力之路,一张地下秘密世界的吞噬之网,一段现代警察制度的荆棘之生。——纪念魏斐德先生诞辰八十周年,增订版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首度公开魏斐德访谈陈立夫的笔记。
●通过地摊文学的渲染,戴老板的确称得上名满天下,他不苟言笑,总是沉默的在角落。然而本书补课作为纯传记来看
●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
●满篇资料堆砌,读之无甚高论。
●前1/3把老蒋和戴笠几人的关系,力行社蓝衣社复兴社等略微梳理了下,后2/3才是正题,资料多出自沈醉等人的回忆录,从整个叙事来说未见高明,多是平铺直叙对我来说到也无谓,有些字里行间的倒值得玩味,不过旁人不仔细看容易忽略,盖因多是琐碎之故?!真想知戴笠其生平,记得当年在天涯追的军统往
●还好。知道一些关于蓝衣社的前世今生。其他的了了,甚至有点夸大了军统在内战中的作用。
●我相当喜欢和欣赏魏斐德提出的问题和这本书代后记里传递的历史观念。然而本书却未能好好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史料来源是最大的问题。这些层层表述之中,戴笠本人不见了,他究竟怎么想?他为何这么选?他和蒋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问题都没能解答出来。书里复刻的是《红岩》之中早已在我们心里留下深刻烙印关于戴笠和恐怖的印记。当然能把这样的故事讲得新颖漂亮,也是难得的。(三星半)
●典型的魏斐德风格作品,拿史景迁来比是比错了。
●与其说是个人传记,更像是军统情报系统发展史…
●重人物描写,想看的史实还是披露很少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读后感(一):民国时期的秘密警察
作者魏斐德,美国汉学三杰之一,第一次接触他还是在图书馆看到的《洪业》,这次接触到这本《间谍王》,还是熟悉的感觉。
前面一大部分讲的是国民党秘密组织的历史由来。力行社,复兴社,蓝衣社,特务处……这些秘密组织可谓是让人五味杂陈,现代国家居然用秘密组织来影响国家。至于戴笠,我觉得这本书主要不是讲他,而是讲他一手创立的军统保密局。里面涉及的军统的一些手段也令人打开眼界,思想的训练、政治教育、刑讯、与帮会流氓分子的结合、新技术的应用……等等这些都说明作者不志在褒扬戴笠。戴笠被称为中国的“希姆莱”,他的坠机死亡,是在他事业的巅峰之时,虽然各方都表明只是天气原因,但仍让人唏嘘不已,共产党都对他是绝对的恨之入骨,这都从另一方面表明,他的工作成效是极其“出色”的。
这本书总的看下来多是资料的堆砌,而且很喜欢利用沈醉写的《军统内幕》那本书,对台湾方面的资料引用较少,尽管很努力做成学术的样子,很可惜,水平还是小小的遗憾。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读后感(二):建议:不要浪费您的时间。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读后感(三):魏斐德果然长于史料而短于叙事
魏斐德的这本书对于大众而言,其实可读性并不强,介绍了大量关于戴笠、军统、中统等特务机关的细节,例如如何培训特工,内部组织编制,具体实施的行动等等。因此很容易迷失于茫茫史料之海,而更适合历史专业学者研读。
代后记所引用的李凯尔特名言,“历史从不描述事情的结局,而向来是描写它们的进展过程”。从这本书来看,魏斐德和史景迁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数,魏斐德试图多方寻找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筛选后从各历史事件当事人角度来描述该历史事件,稳扎稳打的基础上仅作偶尔的历史想象。而史景迁则长于叙事,同样基于搜集的史实,但在描述时会插入历史当事人的内心独白,拉近他们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可读性和趣味性更强。不过史景迁的做法也时常遭人诟病,认为他是历史小说家之流。确实从严格历史学意义上来说,那些内心独白与想象的历史不能称之为真实,但它们也是史学家对史实的“有依据的想象”,丰富了后人对当时历史情境再现时的想象。如同太史公写的鸿门宴,通过其历史文笔,我们才能如身临其境般观看紧张的宴会现场。
因此我真心希望历史学者能够善用魏斐德整理的这份史料,重绘那段隐秘的时光。
: 两处编辑错误
Kindle 约5913处,“同时还能够向英国租借的古岭领地的外国人管理的警察部队显示:中国人完全能够管理自己”。其中“古岭”实际上应该是“牯岭”,身为庐山脚下人对此名称还是有充足把握的。
Kindle 约7353处,“但他力图效仿成为爱国典范的团指挥谢晋元在1932年捍卫四行仓库的壮举”,其中“1932年”应为“1937年”,淞沪战役中八百壮士保护四行仓库。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读后感(四):游侠和法西斯
戴笠的身后是蒋介石,本书几乎将戴笠呈现为蒋介石在国民党特务工作中的影子,两者的个人风格和管理方法都颇有相似处。借着戴笠,魏斐德展示了蒋介石领导下党内(尤其是军队)体系的制衡特点,我粗略总结为:
1. 几乎所有任务都由多于一个组织负责,相互监督、相互牵制。
2. 以蒋介石为绝对核心,蒋本人的影响力可以渗透到下面数层,他高度忌惮其他人的克里斯玛形成竞争。戴笠在这一点尤其复刻蒋介石。权力和情感威望的同时集中确保了统治的稳固、体系的凝聚,但我们很快看到这样的体系难以维持,因为过度集中的克里斯玛无法传递给继承人(这一点问题20世纪众多民族国家的领袖都共享)。
3. 大量采用“套娃”结构,核心组织扩展出外围组织,外围组织又继续孵化其前沿组织和外围组织。所有人都在若干维度上成为核心或外围,拥有明显残缺的权力,被编织入国民党的人事网络中。这种嵌套结构至少在局部等级严明,距离绝对核心——蒋介石的距离与地位、权力,以及信息的持有量绝对挂钩。蒋介石希望这样他会成为信息的最终所有者和权力的垄断者。
然而和大部分社会组织一样,正式关系需要非正式关系的支撑,也受到后者威胁。纪律严明,要求割舍个人关系的特务组织,恰恰要通过复杂的社会关系完成任务,让蒋介石获得他权力的重要部分——信息。比较有趣的一点是戴笠的人际网络既包含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伴随着加剧的地理流动经常出现的那种同省、同乡、亲戚情谊,也包含城市化和殖民共同培植的帮会关系,还包括清末民初独具特色的那种,由于广泛兴办有针对性快速培养专业人才的学校/培训班而产生的同学情谊。全书中军统涉及的培训班/学校有六七个之多。黄埔军校也有类似的背景,流行文化一般将黄埔军校毕业生描写为衣冠楚楚、教养良好、胸怀大志的上层阶级子弟(典型的“民国青年”),然而据魏斐德言,军校生的主体是渴望飞黄腾达的县镇子弟,家境一般而受过基本教育的于连·索黑尔们,其中部分入学前是黑社会成员。他颇有洞见提及的另一个群体是当时地方院校师范生们,他们出身较差,“从大城市高校毕业的受西方影响的青年们往往能感到自己政治野心的阻力和障碍”,而地方师范生们“未能意识到他们的雄心将会受到正常局限……认为自己的命运中大而洪福匪浅,充满着传统文人的自傲,并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戴笠本身就是其中一员。
这种被魏斐德称为流氓知识分子(另一个角度说也是有机知识分子)的大量出现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很大影响。来自民间传统和秘密社会的游侠气质、个人英雄主义助长“提携玉龙为君死”的效忠情绪,与舶来自日本、德国的具有类似倾向的法西斯主义充分结合,将民族复兴和个人集权纽结,以绝对服从单一权威来追求现代化所需的效率。在这一过程中(德国也经过了类似过程),浪漫主义的游侠式效忠逐渐转变为针对受过训练的专业人才的军事化“科学”治理——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现代的集权国家机器于是得以形成。
魏斐德提出了一个有待思索的好问题:蒋公的犬马戴笠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巩固了蒋家王朝,还是构建了一个影子王朝,用监视、恐惧和掣肘阻止了现代国家真正渗透入社会,从而加速了王朝的崩塌呢?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读后感(五):明暗黑白
世间本没有黑白,人类之所谓色彩,也不过是人类眼中的世界。
自然没有是非,牛羊马鹿无所谓苛责豺狼虎豹的猎捕,反之猎手也无从指责猎物的逃遁。自然,自然是自然的一套“生存之道”和天定的运命。只有“智慧”如人类,发明了规则与是非,从而大大降低了冲突的代价。如果,谈判与交易可以解决问题,谁还愿意用血和命的代价去抢夺?习惯了规则,人无比珍视命,生怕轻易失去。
然而,人类的规则几乎从来不曾,“普遍适用”。那些不用、不愿或取巧的人,常常是人类规则制度下,最大的赢家。而不适用规则的规则——“潜规则”——或许才是人类社会真正的规则。这种规则迎合了人从动物界带来的“生存之道”。
台湾海峡两岸官方对戴笠的评价显然是两极化的。至于两岸民间乃至政党轮换后的台湾地区,观点恐怕更加纷杂。1949年,中共军队进入南京,发掘了戴笠的坟墓,毁弃其遗骨。[1]稍晚,戴笠唯一的儿子与胞弟被押解回到江山县(今江山市)当众枪决。[2]只剩下养女戴淑芝由其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共事的美国同事梅乐斯上校(U.S. Navy Captain Milton E. Miles)供给在美生活及求学。[3]不过稍早之前,蒋中正夫妇数访戴笠墓园,亲与指导,倍极哀荣。[4]数年后,军统故旧在台北为他们的“老板”建起了纪念堂。[5]今天,戴笠在家乡江山保安乡为母亲营建而“后继无人”的宅子也已成为一处引人好奇与遐想的旅游景点。
戴笠是个好人吗?“在本书接近尾声时,一位中国朋友不带倾向地问:‘最终,他到底是坏人还是个好人?’”作者答道:
“像戴笠这样一个模糊不清的异种是无法用如此简单的语言来概括的。他曾一度是法西斯恐怖的象征,现代警察国家的化身,严格的儒家理想的执行者;在他永不休止的梦想中,他是传说中的中世纪那些在王朝颓落时应运而生的战略家们的一个雄心勃勃的继承人。在所有这些形象下面,戴笠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所处的复杂时代的产物,身居传统与现代政治斗争的顶峰,坚信自己生必逢时,但终究难以摆脱命运的叵测无常。"[6]
戴笠谱名春风,14岁取学名征兰。30岁报考黄埔时,改名“戴笠”。[7]戴笠后来自己解释说,“有一首古诗这么说:‘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8]
戴笠的一生几乎都活在他与蒋中正的“君臣”关系中。而戴在蒋数度危机中的选择,都进一步加深了蒋对这一“臣”的器重。西安事变中,戴笠怀着必死决心飞赴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戴笠在西安初见蒋时,戏剧性地“冲向前去,跪在总司令面前抱住领袖的腿失声痛哭,责骂自己保护领袖失职。”“蒋介石当然被戴笠愿冒生命危险赶来西安与他会合而感动。”[9]
这一切,始于民国十六年,戴笠决定进入蒋时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六期的一员。而他自己,则曾后悔,没有早一点投奔蒋。[10]
随后的几十年间,戴笠成为蒋最为得力的干将之一,“甘愿为他效劳,做他的‘鸡鸣狗盗之徒’”。[11]
虽然,戴笠也曾作过许多慷慨激昂的抗日、反共讲演。然而他整个情报生涯的使命都是为蒋一个人做事。后来人无从知道,是戴笠对蒋太过信任,以至于将自己所有安国兴邦的理想转换为对蒋的无限忠诚;亦或,出自对蒋的忠诚,而以蒋之哲学为自己之哲学。恐怕二者兼有,而后者约略多一些吧。魏斐德认为,情报工作者天然地隐匿于大众,从而幻觉出一种无比安全与控制大众的优越感。[12]作为军统的最高领导,恐怕戴笠对这种感觉的迷恋尤为强烈。着多少也可以解释,为何戴笠在公众场合尤为低调,且极其敏感于被人摄入相片。[13]
历史不容假设,甚至往往难以证实。戴笠之死至今观点纷呈,偶然的故障或者美方、中共的成功谋杀。如果,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并未形成文字或留下铁证,随着当事人的纷纷逝去,当年尚且无法厘清的事实,又从何而留待后人去解其未解?
假如,戴笠不曾死于当年?
戴笠是不可替代的。几十年的经营,使军统网络遍及几乎所有有华人的地方,使戴老板的面子几乎在所有的场合有用。戴笠一个人的离开,大概使得军统所赖以维系的最重要的关系网,全断了。这也能够理解,为何有观点认为,是中共在内战行将开始之际,设计谋杀了戴笠。
假如这一切设想是对的,共产党人当然不乐见其成。共产党人宏大的解放人民与国家的事业或许因此而夭折。这无疑是令人扼腕叹息的。
然而,也幸而历史不容假设,共产党人解放了人民与国家之后短短二三十年的故事,大家都亲眼看到了。这无疑是更加令人喟叹的。
假如蒋公赢了呢?
1960及70年代,因应大陆文化大革命,蒋公在台湾兴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蒋是民族主义者无疑,然而蒋公的复兴运动这瓶酒里装的到底文化多一点,还是政治多一点?
老蒋去后的台湾,如果不是因为被迫依附美国,以蕞尔小岛实在无以抵抗外界的压力,台湾会解严吗?台湾人民会在世纪之交亲身参与、亲眼参与华人社会的第一次真正民主选举与“和平政变”吗?
泱泱中华民国以南京而武汉而重庆而昆明,抵御住了日本的侵略,会以泱泱大国而轻易屈服于美国的民主说教吗?试看今日之沙特阿拉伯?
所以,戴笠是英雄吗?军统昌盛的几十年,死了那么多人,折磨了更多的人。它带给国家和人民的除了恐惧,还有什么?
他们以崇高的理想和国家、人民的字眼辩护自己的残忍。他们以未来的蓝图来鼓动人们加入他们宏大的计划,让所有的死与牺牲都显得光荣、伟大、正确和值得。
但从来也没有谁,可以让世界依着他或他的主子的理想而进展。他们的信念越强,国家和人民的悲剧越沉痛。北方的大国苏联,南方的小国高棉,不过目下悲剧未远。
[1] 陨落之星[M]//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467.
[2] 同上.465-466.
[3] 同上.467.
[4] 同上.466.
[5] 同上.467.
[6] 同上.467-468.
[7] 打流[M]//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23.
[8] 多面人戴笠[M]//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6.
[9] 裙带[M]//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298.
[10] “他曾对文强说,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早一点投靠蒋介石。”投奔[M]//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45.
[11] “蒋听说戴笠甘愿为他效劳,做他的‘鸡鸣狗盗之徒’,非常高兴。”同上.36.
[12] 多面人戴笠[M]//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16-17.
[13] “他【戴笠】许多令人费解的特点与他不让人察觉他在场及保持隐姓埋名的奇妙能力有关,部分也与他不愿被拍照有关。”同上.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