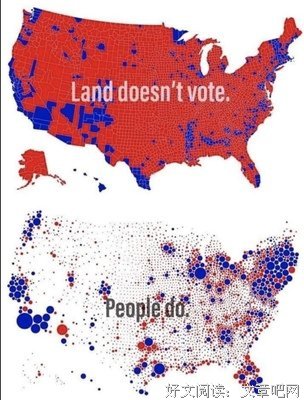乡下人读后感锦集
《乡下人》是一本由孙德鹏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元,页数:5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乡下人》读后感(一):读懂中国那段残酷的历史,从民间的角度,从作家的眼中
沈从文少年离家从军,跟着一位军官开始了读书识字,成了军中一个特别的存在。之后,他远离家乡,开始了“北漂”生涯,在北平一间租来的破旧杂物间里写作,不断地写作,即使是生病,即使是寒冬腊月忍受着北方的朔风。他自觉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始终觉得自己是个乡下人。于是,他将对家乡的映像、思念诉诸笔端,我们在他的文字里可以看到湘西的美景和淳朴的乡下人。他也不断回忆从军时候的往事,他用文字直白地记录了残酷的战争和杀人场面。
读《沈从文与近代中国》,读懂中国的乡下和乡下人,也读懂中国那段残酷的历史,从民间的角度,从作家的眼中。
《乡下人》读后感(二):从沈从文作品中探讨“乡下人”的共性
沈从文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一再地说: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以及小说作品中众多的人物描写都机具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凸显乡下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
孙德鹏在《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中写道:
在沈从文的世界里,乡下人是一种语言,一种法则,原始、粗野、质朴,无法琢磨,始终处于一种戒备状态。透过乡下人的眼目,我们看到了人们对于城市、进化、创伤、混乱、死亡、重生的最初印象。《边城》是沈从文不幸之中的万幸,之后,他把所有幸与不幸捏得粉碎,洒在《长河》中,洒在《小砦》中。
“乡下人”这个概念与沈从文的作品有什么关系?作者孙德鹏从小说文本内外推演沈从文 “乡下人”的人生经历 ,以此绘出近代文学的辉煌光谱,探讨更为深层的“乡下人”的共性。从“乡下人”的视角回顾沈从文前半生,在沈从文作品中重建近代中国的记忆,在进步与落后的对峙语境中,理解近代中国的问题。另外,沈从文凭借着什么越过间隔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深深沟壑?为什么在城市中当了教授的一位作家非要横下心来做“乡下人”? 透过《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这本书,我们可以一览无余。
沈从文虽然只有高小文化,却成为北大教授,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而这条路正是他用“乡下人”的执拗闯出来的。而“乡下人”身份和“都市人”角色的冲突,也一直贯通在沈从文生命的始终。
1923年,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怀着“我想来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救救国家”的一腔热情初来都市,都市却给了年轻的沈从文太多的挫折和创伤。为了维持生计,他在一间“窄而霉”的小公寓里伏案写作,在饥寒交迫中学习不懈,以在湘西学到的坚韧来应对生活的艰辛与困窘。都市在沈从文的心目中曾是一个新奇、神秘的、令人神往的地方。然而文化的差异、理想的受挫、生活的困顿、生存的压力、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灯红酒绿背后的空虚无聊、都市世故和虚伪的冷漠使这个从民风淳朴的湘西冒然闯进都市的青年茫然若失,对都市充满了激愤。
沈成文开始对都市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和难以弥合的对抗心理。这些早年的遭遇直接导致了他的都市小说,对都市人充满讽刺和丑恶的描写。作为乡下人,他带着一个局外人的目光,深刻地看到物质化的都市人,金钱和欲望已经将他们的思想侵蚀,人性完全埋没在污秽丑陋醉生梦死的生活当中,“这种城里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老实说,我讨厌这种城里人”。
而另一面,在沈从文朴素平实的笔下,有许多卑微的却又个性鲜明的“乡下人”,这些下层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天地之间活出了小小的悲喜,活出了有情有义的模样。沈从文用《边城》《长河》《丈夫》《湘行散记》等一系列作品营造田园牧歌色彩的湘西世界,把乡下人的世界写得如此让人倾倒,征服了千千万万的城里人。翠翠,三三,夭夭,成为最纯粹的美的化身,即便是吊脚楼上的妓女也是虽粗野而多情,闯滩的水手也是虽剽悍而温柔。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背后,共通的还有他的历史观。比如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他责备中国过去的史学只写帝王将相,大多未将国民的整体活动写进历史;只注意一家一姓的兴亡,而不注意人民、物产、财力等等。历史只为朝廷君臣而写,‘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沈从文心之所系,是在这样的历史书写传统之外、被疏忽了若干年代的更广大的平凡人群。”张新颖说,“引用汪曾祺的形容,沈从文是‘水边的抒情诗人’,一个人不知疲倦地写着一条河的故事。那么沈从文的后半生,就是在对家乡河流的印象和怀念之外,又在现实境遇中找到了另一条历史文化的长河。”
作者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见识高远,其文字极具想象力,笔触深刻有力,与其说是对沈从文作品的解读,毋宁说是点燃了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篝火;跟随沈从文的成长记忆,我们可以目睹一个传统与现代并存且相互冲突、融合的乡土影像,感受大时代变迁的忧郁和苍凉。
《乡下人》读后感(三):假如以文人的角度来审视时代中国……
假如以文人的角度来审视时代中国……
近代中国是华夏千年文化延续中最辉煌,却也是最激荡的一段历史。在这个时期,“五四运动”是文化无法避免的一个节点,文化的觉醒和彻底的叛逆,在这个时期显得如此特别。也正因为这个时期的特别,时代诞生的文人中,颇有很多别有个性、另有风骨的人,比如《沈从文年谱》里记载下来的那个时代特立独行的文人。所以学者孙德鹏在《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92—1947)》写到,“沈从文那些触动人心的作品和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山水里看到了诗意和忧伤”。
对于沈从文,在他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探究的地方,入京,读书,求职,恋爱,婚姻,下放,当然,避不开的是他的小说《边城》,那种独特的时代味道和独有的下乡的气息,让沈从文一直称呼自己为乡下人。所以拿到这本《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92—1947)》的时候,首先让我有所触动的其实是封面,封面的设计用色相当大胆,没有采用取悦读者的丰富色彩,也没有故作深沉的其他色调,只是用大块的绿色交杂墨黑,同时以苗族的头饰作为底色,封面就融入了湘西元素的设计,让我们一眼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更多的是带给读者一种图腾化的感受。非常喜欢这样的象征意义的设计,毕竟,沈从文从来就不是单一的人,他的边疆性始终烙印在他的人生痕迹里,但是他的原始性和对儒家的叛逆性,其实都源自于详细风情里最直接的影响。
阅读这样的书籍是需要静心来品读的,因为从沈从文的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那么,乡下人所经历过的,其实也是当时中国所经历的历史;乡下人在时代浪潮下所被剥离的一切,也正在当时之中国悄悄被剥离。写沈从文和沈从文的作品有很多,但是像孙德鹏在《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92—1947)》里一样,立足于沈从文自称为“乡下人”的生活经验,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回顾沈从文的前半生和阅读、写作经历的,却是相当之少。而这本书不同于普通传记和文选的地方还在于,作者不是从生平出发,而是对沈从文的生活经历和情感变化做了实地的走访和考察,在实际的经验上面,开始推演和想象小说人物的精神和内心世界,这样的书可以让小说的虚构性融入到现实性中,实现了文学对真实历史的补充。
纵观近代历史,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近代中国的一些独特的变化,落后和进步并存,激进和保守斗争,封闭和开放竞先,没有一个时代如同近代中国这么复杂,也没有一个时代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交错其间的人应该有的心理状态。这本书里,展现了很多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照情景,更展现了近代中国是如何从封闭落后的封建国家开始走向现代化,让人置身于进步与落后的对峙中,更能够真切地理解近代中国究竟是为何而来,又要走向何方。我们总是习惯了从历史的高度来俯瞰这段时间,但是很少有人真的可以站在一个真切的时代背景之下,来一个立足于土地,扎根于现实的人来审视这个世界。而文人视角的沈从文,无疑对这片土地有自己的独特思考,这样的文字和这样的描写,已经足够吸引人,足够给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真实展现近代的中国了。
有别于以往的沈从文传记,作者自身是学者身份,他结合了自身的法史学的学者经验,以史学的立足点,以沈从文的个人生活和文学创作为审视的支点,撬动是整个文学的杠杆,可以说,这其实是从另一个学科来与文人身份的沈从文对话。加上大量的走访的图案的摄录,在这里,作者更多的是以一个阅读笔记的方式来展现社从文,对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做了一个清晰的梳理,同时收录当时与这个时代息息相关的各种读书札记、社会平路等,这样就将个人的阅读史和当时的时代发展结合了起来。在学者的努力下,《乡下人》一书更多的是血泪,是时间逻辑之后那种跳脱了时代的心路历程,读来,自然分外吸引人。
《乡下人》读后感(四):变与不变——再读《边城》
在《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92—1947)》的序言中,孙德鹏写道:
沈从文出生边地,二十岁来到北京求学,彼时五四运动过去三年。学习写作多年,直到三十年代才在文坛站稳脚跟,成为自由派作家的代表。在宽泛意义上,沈从文是五四的儿子,救亡图存在他的文学要旨占据相当的地位,和同辈或前辈的作家一样,他也愿意并且热切地为中国开出药方;但沈从文又与五四的很多旗手们保持着距离,对时髦的、被认为是进步的革命文艺怀有强烈的怀疑态度,并且再三重申文艺本身的独立性和自足性,这使他在三四十年代饱受攻击,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完全放弃写作。
沈从文是一个独特的样本,他介于“新”与“旧”、“进步”与落后之间。他热情歌颂乡野美而健康的精神底色,却常常不得不承认其背后的无法调和。这种矛盾的倾向在他的代表作《边城》体现得极其明显。
一
在《长河》题记中,沈从文写道:
沈从文痛惜现代文明入侵湘西造成的人情泯灭、原始自然的社会形态被破坏。而就在这次返乡前后,沈从文写下了小说《边城》,追忆二十年前那个梦中湘西。
二十年前的湘西何其不同!从沈从文的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边城》是作为“堕落”了的湘西一种比照,它代表了湘西曾有的“真实”(既有审美上的,也有自然意义上的)。作为反映“民族的过去伟大处”的标准文本,《边城》的精致(甚至是过分精致)构筑了沈从文湘西世界最纯净、最具审美意味的范本,但这样的用心不免让人怀疑作者内心是否同样“纯净”。事实上,《边城》牧歌式的咏叹调后一直积蓄着毁灭性的力量,这股力量潜滋暗长,最终“击溃”了他苦心经营的田园。
二
边城的时间不是线性的,而是停滞的;边城的空间不是开放的,而是封闭的。
但“变故”还是在发生,内外的世界都起了大变化。
这些变故所以产生,一方面源于沈从文赋予他人物所谓“自然的”秉性。老船夫在船总顺顺面前似乎有种天然的自卑感,加之担心翠翠出路,面对顺顺父子更是局促。他拖宕、不利索,只为给翠翠找个好归宿,却与天保傩送兄弟产生罅隙;而翠翠,因了害羞,与傩送有见面机会,却只是回避,逃入竹林中,她对傩送的爱情,几乎是在幻想中构筑的;翠翠与祖父之间,也不能完全畅通地交流,祖父不知道翠翠其实心仪的是傩送。天保为成全弟弟,外出经商,不幸淹死后,顺顺父子对老船夫只是敷衍:
“一同把日子打发下去”,不就是“不变”吗?双方都在拖延,似乎都想借助时间解决一切。试问,既然个人的性情都是如此的可爱可敬,为什么却无法坦诚的沟通,而造成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呢?也许沈从文认为人在本质上是无法沟通的,注定寂寞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他们各自“自然”的,换个说法,也是无法变通的、难以超越自身局限、对自己处境无知无觉的性格最终毁灭了他们自身。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不变”,而“不变”的悲剧业已造成,沈从文精心构筑的湘西神话也告破灭。沈从文几乎是不得不承认了“变”:
这等于否认了“不变”的可能性,也即承认了古老的边城继续存在之不可能。
三
变故产生的另一面是外来力量侵入边城,如妓女便是随着大都市商业发达而产生的寄食者来到边城的,但她们还不足以有力量腐蚀民风,而是被当地风俗同化。但大都市带来的金钱至上的观念已深入边地人心中,甚至翠翠也不免受影响,翠翠对过渡女孩子手上一副闪着白白亮光、麻花铰的银手镯很歆羡,也唱出这样的歌:
翠翠竟下意识中将团总女儿(象征财富拥有者)作为第一个被老虎咬的人,实在有些“恶毒”,何况此时她并未知晓团总女儿是她的“情敌”,“豆芽菜”与“金簪子”、“银钏子”的对比,显出内心的自卑;老船夫对来自碾坊的危险也显出惶惶,“又无碾坊陪嫁,一个光人”。在边地,“一个撑渡船的若想有座碾坊,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妄想。凡碾坊照例是属于当地小财主的产业”;顺顺作为中年发迹者,也倾向于让傩送接受碾坊。只有傩送还坚守着自己内心的想法,只要渡船。但无疑,他与翠翠的爱情,早已四面楚歌。
边城已受到外来商业文明的侵蚀,更何况它也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边城故事的悲剧结局不可避免。沈从文从批判城市、赞美乡村出发,最终无奈地发现乡村自身的悖谬。
《乡下人》读后感(五):写作,就是哭泣
时间不可逆,生命不可逆,然而在写作中,一切不可逆的都可逆。
——朱天心
2020年2月,距离《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的交稿时间还有6个月,我的作者(孙德鹏老师)正踏上前往英国兰卡斯特的飞机,按照计划,他将在那里访学一年。
他背包里装着两本书,杜拉斯的《写作》,以及《沈从文年谱》。依照计划,看完这两本书,喝下一杯威士忌,盖上毛毯,昏昏沉沉地睡足一夜,他就能踏上英吉利的土地,那片哈代、毛姆、莎士比亚曾生活过的土地。
那些修道院酿造的葡萄酒,那些闪耀着数百年积尘的教堂穹顶,那些被岁月磨蚀得经纬毕露的彩窗。他或许还可以找个沙滩,在海风中书写那个湖南西北角的穷书生,那个湘西的乡下人,那位差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沈从文。
这些美好的憧憬,在梦里显得又高又远。
飞机还未落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作者所有的计划成为泡影,时钟像是被拨快了一年,又像是被拨慢了一年。那是他从未经历的时间,尤其是身处异国他乡。一望无际的荒原感,一望无际的时间,汹涌而来。
得知所有航班停飞,回国遥遥无期,作者打开电脑,望着尚未完稿的《乡下人》,以及几个TB的资料硬盘。想到国内各行各业都在对抗疫情,对抗这段特殊的时期,他收拾沮丧的心情,决意活出一种姿态,一种写作者的姿态。
他带着一份确信,在沈从文所欣赏的自由状态下,一字一句,打算写完《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这本书。
撰写书稿期间,他尝试着与《沈从文传》的作者——金介甫(费正清、史华慈弟子,公认的海外沈从文研究第一人)联系。那位面壁10年写《沈从文传》的美国汉学家,当时只有30多岁,金介甫的资料卡片多达6000张,注文字数几乎为正文的一半,堪称史料。
金介甫很快回复作者,他们保持着稳定的联系,聊创作经历、想法、湘西,更多地,是聊沈从文,那位给湘西题名,耳聪目明的“乡下人”。金介甫说,沈从文所有独立的小说,都像一个矿坑里开采出来的一条条大理石,全部都能看出母体矿的纹理和疵点。
得知作者的遭遇,金介甫对作者说“我所写的只不过是一本微不足道的小书”,并鼓励作者“你写的一定比我的更好”。
写作及与金介甫先生的聊天似乎成了作者打发时光的唯一方式。
2020年8月18日,我如期拿到《乡下人》书稿。作者说:“我好像不太舍得这么快把它交出去,我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办,少了一个可以聊天的伴儿啊。”
“您放心,之后还有三审三校呢,这才刚开始,您有的忙了。”我笑着说。
作为《乡下人》一书的编辑,我每每为书中字句打动,在作者笔下,沈从文不是大仁大勇、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而是一个小兵模样的身影,赤着脚向河边走去。我们与他并肩而坐,凝望水中的一切。他显得孤独、雅致,陷在回忆某种悲伤经历的情绪中。
时间是一条长河,但回忆比长河更长。《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的英文标题为“The Shape of Water”,可以译为“水之形”,或者“水形物语”(电影《水形物语》给了作者启发)。
沈从文在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前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后半生则陷在对那片土地的回忆里。潮湿阴雨的湘西,让沈从文的文字充满了水的感觉,那是专属于水的寂寞。正如作者所说,雨下得越大,沈从文越寂寞,这就是他的童年。
同时,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水,是一种文学思考的方法。在水的包围中,他成了一个作家,处在世界的中心,使人及事物获得意义。在那里,他独特的文笔才是作品的力量所在,相较而言,那些离奇情节在时间中慢慢褪去色彩,像历史本身一样沉默了。
或许是在重庆生活久了,他常常觉得沈从文那些故事中的空气,像江风一样真实。作者说:“他(沈从文)就在我面前,有着旧书封面那样的皮肤和笑容,苍老、神秘、令人着迷。”
生活无须猜测,真正的生活永远值得谈论。
对作者来说,他遇到的最大挑战,并不是身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异国他乡,也不是寻找进入文本世界的角度问题,而是事关真实性的历史效力,或者说,是经验透过文本扑面而来的“共时性”效应。
沈从文所处的时空,是个巨大的梦境:革命者挨过无数的不眠之夜,民众却鼾声如雷;读书人彻夜高谈阔论,洋车夫却梦着面包。很少有人在乎什么失落的家园,倘是家破人亡也就罢了,痛苦的是家破人不亡……
“在那个时空里,有人径直、粗暴地占有他人的生命和财富,被劫掠的人,比如那些乡下人,除了沉默领受,练就微笑神情,还懂得随时隐没于山林江湖的本领。他们返回‘自然’,越走越远,情愿与恶劣的环境相处,也要躲避可怕的同类。我们称这样的一个群体为‘乡下人’,他们是我们不忍嘲笑的受难者,而现实的情状是,人们发明了‘乡巴佬’一类的词来做不对等的称呼。”
沈从文的作品,往往就是诞生在这种令人费解的落差之中,从早期的《在公寓中》《绝食以后》《落伍》《船上岸上》等,到中年时期创作的回忆性文字,以及为读者熟知的《山鬼》《贵生》《三三》等作品,都潜藏着一种隐忍的力量。
和作品相比,沈从文的一生是一个质朴又离奇的故事。
在兰卡斯特的公寓中,写下这些文字时,英国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作者哪也去不了,有时在电脑前枯坐一天,看着新闻报道日益增长的数字,流泪,那是一个个无法挽回的生命。
想起重庆的辣子鸡,他学会了一个新词“nostalgia”(怀旧,思乡),作者开玩笑说:“这个单词发音像‘老实待着’。”
想像力也需要休耕,休息两天,他看了《无依之地》,改稿两千字,顺畅了许多。
他说,《无依之地》与有无大地的居所无关。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在漂泊无定的路上,带着回忆和岁月留下的伤痛;遇到一些人,坦诚相待,于是,又遇到一些人;没有诀别,只望在下一段路程上的相遇……
诗句摘自莎士比亚,影片以台词的形式出现过。
“看了这部电影,我想应该请导演和主演来重庆,多吃火锅,有疗愈功效。”作者笑着说。
重庆,忽高忽低的街巷,似远还近的楼宇。山城棒棒军,沸腾的火锅,夜晚的江风,魔幻的8d交通,许多人都说江湖气是重庆的底色。在作者看来,江湖,更多的是茶和酒的味道,那是一种时间的味道。歌乐山下有个烈士墓,作者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正与之守望相对。“Lancaster(兰卡斯特)每个角落已走遍,这个城市已成为我生命旅途中的又一个烈士墓,该回家了。”此时,作者已经困居兰卡斯特14个月了。
离开兰卡斯特的那天,花期到了,好像一夜之间花全开了。2021年4月2日上午8点15分,作者落地上海,随后前往酒店隔离。一切都如作者出国前那般顺利,仿佛他从未到过兰卡斯特。酒店离张爱玲故居不远,作者有时候会打量窗外,好像可以看到某个窗内,那穿着旗袍的“狐女子”,她翻书,夹烟,举杯,捻香。她抬头的时候,风好像正好翻过她小说的某一页,《半生缘》,《倾城之恋》,亦或是《红玫瑰与白玫瑰》。
“《金锁记》《封锁》这样的文章,是在常德公寓或附近咖啡馆写成的,单凭这一段历史,上海就足够迷人了。”
4月17日下午6点,作者回到重庆,他长舒一口气:“朋友所在,即是吾乡。《乡下人》一书和书内外的友朋让我有归家的大大喜悦。”
诗人伦纳德•科恩说,美好人生,烟斗为伴! (If your life is burning well, poetry is just the ash.)回想自己在兰卡斯特的创作经历,作者好像不觉得苦,或者说,人生百味,苦是最不苦的那一味。
湘西人常说,“治不好的病,就是命运了”。人与人在苦难中得和解,得安慰,这或许是最接近信仰的一种人类关系。
生命无非是,苦来了,我们将它安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