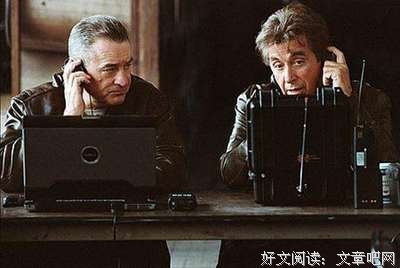于无声处听惊雷 ──评艾尔桑·蒙塔克《寂静之家》
艾尔桑·蒙塔克(Ersan Mondtag)的《寂静之家》(Tyrannis)入围了2016年柏林戏剧节,并和《假面》《轻松五章》一起成为“柏林戏剧节在中国·2020特别版”的放送剧目。由于疫情,中国观众得以在线上看到该剧的高清影像。作品描述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庸常生活。舞台上布置了五个监视器,透过监视器的画面,可以看到一家五口在一栋二层洋楼里行尸走肉般地作息、洗漱、移动、进食,从头至尾毫无交流!他们行为举止僵硬、怪诞,仿佛遵循某种神秘教义的苦修士,又像是不属于人类社会的外星生物。不速之客的到来像一颗石子投入死水,生活的惯有模式瞬间被打破,但很快,涟漪消失,外来者顺利地融入了家庭生活。一切看似回到正轨,却又似乎在悄无声息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剧中人日复一日地消磨生命,当代人际关系的崩溃、政治的冲突、资本主义的衰落都渐渐浮现在观众眼前。
黑色“彩蛋”
观众会在某个瞬间惊讶地发现,演员们竟然都是闭着眼睛表演的!那硕大、圆睁的“双目”,实际上只是用颜料画在闭合眼帘上的假象。蒙塔克曾在2016年的一次访谈中这样解释:假眼睛的灵感来源于电影《加勒比海盗》,那位瞎了一只眼的海盗船长给青少年时代的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因此,导演恶作剧似的让舞台上的人物在“失明”状态下完成吃饭、喝水、打扫卫生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漫画式的、鬼魅般的假眼睛无疑增强了本剧的阴森恐怖感──这不是属于人类的眼睛,承载它们的也不是属于人类的肉体。汉斯-蒂斯·雷曼将这种另类的舞台美学比喻成“一抹有毒的绿色”,并指出舞台上所展示的“美不能仅仅是正面的,它甚至必须是传统口味难以消化的”。[2]蒙塔克剥去那层名为“完美身体”的保护罩,毫不避讳地将呆板、僵直、粗鄙的身体放置在舞台上,以恶作剧的方式激起观众的不适和惊恐。在这一瞬间,观众所熟悉的幻象的“美”弃他们于不顾,他们唯有鼓起勇气直视那一双双空洞无物的“眼睛”,才能和导演、和舞台,或者说和真正意义上的“美”建立起连接。
蒙塔克在剧中埋下的“彩蛋”远不止“眼睛”这一个。另一个“彩蛋”在开幕伊始就展现在观众眼前:女儿长裙上的图案及客厅地毯的纹路和恐怖电影《闪灵》中酒店地毯的花纹一模一样;剧中的洋楼与《闪灵》中酒店的诡异气氛也如出一辙。改编自斯蒂芬·金同名小说的《闪灵》曾被列入各类恐怖片榜单,虽然该片涉及恶灵、僵尸、血腥、镜像等众多恐怖元素,但我以为,其让观众汗毛倒竖的真正根源在于杰克一家三口之间的纠缠与矛盾。父亲、母亲、儿子,这些名词本应指向融洽、和睦的关系,但在《闪灵》和《寂静之家》中,它们都变成了钳制、胁迫、憎恶的象征,家庭关系如同摇摇欲坠的危楼,随时都有坍塌倾覆的风险。
在本剧中还能看到其他电影导演的影子。约翰·卡朋特于上个世纪80年代执导的《怪形》可谓是开了科幻恐怖片先河,片中的人们被围困在阴森吊诡的幽闭空间内,像是即将被审判的猎物,不论如何挣扎,都无法逃出这个牢笼。而《寂静之家》中庞大的二层别墅看似华丽、精致,本质上也是一个让人窒息的幽闭空间。除父亲之外,一家四口都被囚禁在这栋漂亮的牢狱中,日日夜夜服着名为“重复”的苦役。最后,年轻的儿女喝下来自老一辈的牛奶后轰然倒地,生死不明。
在色彩及光线方面,《寂静之家》让我联想到法斯宾德电影中变化多端的斑斓色块。剧中,走廊鲜红的墙壁以及黑白间隔的地板给观众极强的视觉冲击,客厅内铺排了大片波普风格的红黑色花纹,壁纸及地板上的纹路和剧中人的生活一样都像是无尽的复制与粘贴──重复、重复、重复,不知何时才是尽头。
我还想提到导演大卫·林奇,从《穆赫兰道》到《象人》再到《我心狂野》,他的作品总给人以畸形、扭曲、压抑的视觉体验;同时,他也极擅长摧毁原本的叙事结构,将观众置于危险、陌生的恐怖环境中。本剧中陌生女人的到来无疑继承了这一点:第二日天色微明之时,一头红发的外来者突兀地站在玻璃门外;屋内,父亲莫名其妙倒在客厅。陌生人到来之前,《寂静之家》的叙事结构虽然诡异,但至少因重复而获得了一种另类的“安全感”,可随着陌生人的降临,屋内仅有的“安全感”被彻底剥离。“如果没有伤害或冒犯的风险,艺术仅仅是一种商品”[3]──唯有激起观众的恐惧,才能进一步引发他们的思考。
大卫·林奇曾坦言,他最喜欢的画家是弗兰西斯·培根,巧合的是,培根的旧友卢西安·弗洛伊德的画作《沉睡的救济金管理人》出现在了剧中女儿的房间里。在这幅画中,一位异常臃肿肥胖的妇人裸体侧躺在沙发椅上,身上的赘肉似乎叫嚣着争先溢出画面。而画中的女子和画外的女儿何其相似:她们双乳下垂、肚皮凸出、四肢肿胀,甚至奇怪的神态和僵硬的姿势都如出一辙!高度的相似性增强了诡异可怖的气氛──既像是画中人走出了画框,又像是女儿被封印在画框中。
还有一个“彩蛋”隐匿在本剧的原标题中。“tyrannis”本意为暴君、暴政──剧中究竟谁是暴君?暴政又如何体现?我认为,可能的暴君有三个:女儿,父亲,观众。女儿是显性的暴君:她脾气暴躁,吸尘器的声响就让她暴跳如雷;她家庭地位高,每天早上都需要奶奶来帮她穿衣打扮;更关键的是,她是唯一有勇气替陌生人开门的人;另外,她裙子的花色与客厅的壁纸、地毯一模一样,似乎整个家庭都生活在她巨大、沉重的统治阴影下。父亲则是隐性的暴君:在这个被围困、被囚禁的家庭中,父亲是唯一能够走出屋子的人,戏剧一开始,他甚至拎了一把颇具威胁性的斧头走上舞台。此外,如本文开篇提到的,舞台上布置了五个监视器,分别监视不同房间的生活动态,这些监视画面是通过客厅一角的电视机来放映的,而父亲是唯一能够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监视画面的人。但若是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俯视剧场,我们会惊觉父亲只是在观看监视画面,而身为观众的我们不仅和父亲一样通过监视器画面获取各个“分会场”的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在观看“父亲观看监视画面”这个画面。同理,是否也有人在观看、监视我们?
至于暴政在剧中如何体现,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若不是外来者闯入,剧中人的生活不会掀起丝毫波澜,他们仿佛在某种权威的勒令下日复一日地机械行动。其二,暴政是否会加剧人的愚钝和无知?虽然被压制,但是剧中人似乎又是暴政的忠诚拥护者。最明显的一点是奶奶和母亲对陌生人极为恐惧,为了清除异己,不惜痛下杀手。
消失的语言
“毛骨悚然”是我观看《寂静之家》时的第一感受。这部戏剧从头至尾没有一段台词、没有一句对话,长达两个小时的沉默,加上屋外不时响起的乌鸦哀号和女人尖叫,鬼魅般的音效像是一只令人窒息的手,死死地扼住了我的咽喉。导演有意禁绝了“说”这种人类最重要的感官方式,通过对失语状态细致入微的描绘,激起观众无尽的遐想。
自上个世纪起,剧作家们的种种尝试极大地冲击了文本及对白的地位,而在当今盛行的后戏剧剧场中,在排演文本的层面,以文本为中心的等级制度更是瓦解了,文本不再居于剧场等级关系的中心。若沿用“文学性=思想性”这个简单的等式来谈论《寂静之家》这类作品,就不免因循守旧、不合时宜。
雷曼在描述后戏剧剧场的特点时指出:在同一场演出中,各种表演形式(舞蹈、说书、展演艺术等)结合在一起,所有剧场手段的地位变得同样重要。[4]也就是说,所有的舞台手段可以是并列的、非等级性的。蒙塔克用他的舞台呈现呼应了这一观点。他认为:“舞台上的一切,无论是物体、道具还是身体,无论是舞者、演员还是音乐家,对我而言都一样重要。”[5]本剧中人物虽然一言未发,但舞台上幽暗的灯光、诡谲的背景音、突破常规的监视银幕,乃至阴森的房间本身都成为了绝佳的表现方式。同时,由于全剧并无真正的剧本(script),连广义上的文本(text)都不复存在,因此,演员们的身体成了关键性的表意工具。机械的动作、僵硬的姿势、怪诞的舞姿,“身体成为了剧场艺术的中心”[6]。但和理查·谢克纳、杨·法布尔等导演通过演员身体呈现向外的、进攻型的痛苦不同,《寂静之家》中的身体所承受的痛苦是向内的、塌缩的,剧中人日复一日被庸常的生活倾轧,其肢体看似健全,心灵和头脑却在渐渐腐坏。
该剧舞台上贯穿始终的静默、固定不变的布景以及不断复制的机械化动作实际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长时间持续:“在持续性表演中,观众拥有难得的机会,占据一个耐心的观察者的位置,自觉地感知和体验时间的流逝。”[7]一方面,观众惊异于剧中人的庸庸碌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消耗自己宝贵的时间来观看这份庸庸碌碌!此时,舞台和观众席间的屏障被打破了,剧场成为“表演和观看的参与者的聚会”[8]。同时,由于演员们的“失语”,叙事的权力被移交到观众手中,他们需要通过自己的想象去构建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正因如此,舞台呈现有了无限的可能。
在颇有新意的舞台形式之外,《寂静之家》还继承了现代文学中的一个主题──交流的无望。契诃夫《三姐妹》中安德烈和管家貌合神离地交谈;卡夫卡《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虫,彻底失去了人类的交流能力;萨特《禁闭》中三位主人公深陷在“他人的地狱”中无法自拔;荒诞派戏剧中答非所问与自说自话随处可见……正如马丁·艾斯林所言:“(作品中)人际之间的交流常常被表现为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而这仅仅是事情的存在状态的一种嘲讽性放大。”[9]作家们希望借文字描摹的人的孤独,在《寂静之家》中再次得到了呈现。这一次,导演索性让演员们噤声,通过人物的沉默来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障碍。反观现代社会,四处充斥纷杂冗余的对话,人们习惯了单方向的“表达”,却忽略了双方向的“交流”,滔滔不绝的语言洪流掩盖不住日益苍白空虚的精神世界。可以说,在这层意义上,蒙塔克呈现的不仅是“寂静之家”,更是“寂静之社会”。
闯入的不速之客
戏剧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时代、社会保持着密切联系。德国戏剧总是影射政治的,《寂静之家》也不例外,由黑人女性扮演的外来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下德国所面对的严峻挑战:难民问题。在这一点上,蒙塔克的态度模棱两可。一方面,他曾表示:“在创作《寂静之家》时,我始终会想到难民问题。一名难民就站在露台门前,迫切地想要进屋。但是屋内的人们却对此感到恐慌。他们担心陌生人会进来毒死屋内的人,会扰乱房屋的内部结构和秩序”;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不是陌生人带来了危险,而是陌生人的投射使屋内的人们发疯”。[10]这般复杂的态度也许和导演本人的双重身份(土耳其移民的后裔,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有关。蒙塔克的态度也反映了当代德国人乃至欧洲人的共同心理。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无论何时,只要存在应对他者差异性的必要,人类历史上通常就运用以下两种策略:“禁绝策略”和“吞噬策略”。所谓“禁绝”,就是指毫不留情地隔离、清除乃至屠杀异己,而“吞噬”则是指对外来者容纳、吸收、吞没。[11]这两种策略在剧中皆有体现:不速之客到来的早上,父亲无缘无故仰面倒下,好像隐喻既有的体系必须作出一定牺牲,才能吸收门外的新人;当外来者出现在阳台上时,母亲和奶奶爆发出惊恐的尖叫,这显然代表着德国及欧盟内部反对难民政策的“禁绝策略”支持者的诉求,但是这时女儿走上前去打开了房门,外来者顺利入屋,并且迅速融入一家人的生活。女儿的行为是否象征着“吞噬策略”支持者的态度?毕竟正是欧洲左派人士挥舞着人道主义的大旗,呐喊着自由与民主的口号,敞开怀抱接纳了无数难民。然而,不速之客彻底打破了家庭原有的生活轨迹,她不仅抢占了音乐演奏中奶奶的位置,和年轻一代一同歌唱(这似乎暗示着他们可以共享文化),还进一步侵略了妈妈的地盘,心安理得地坐在餐桌前大快朵颐。长辈们的家庭地位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井然有序的生活也顷刻间变得一片狼藉。同样,难民的涌入也给一向安宁和谐的欧洲社会制造了不小的麻烦。性侵、强奸、抢劫、盗窃……社会治安被扰乱,更不用说本地白人和外来有色人种、左派和右派、难民政策反对方和支持方之间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凡此种种,都在无形之中加剧了社会矛盾。在戏剧结尾,母亲和奶奶在唯一没有装监视器的房间里企图欺骗外来者喝下有毒的牛奶,她们选择在这个相对“安全”的房间内痛下杀手,是否影射了相对保守的欧洲居民对待难民的实际态度?出人意料的是,被毒死的只有女儿和儿子,外来者毫发无损。故事至此戛然而止,剩下的三口人将如何与外来者相处?现实中欧洲人民又将如何应对持续输入的难民?导演没有给我们一个清晰的结局,现实也没有给欧洲指出一条安全的道路。
《寂静之家》的目光不仅向外展,同时也向内收;它不仅关注外部的威胁,同时也聚焦于内部的坍塌。漂亮的洋楼,华贵的地毯,触手可及的高级餐具、电脑与望远镜,茶余饭后的音乐演奏,女儿房中装裱的油画……《寂静之家》通过各种小细节向观众呈现了一幅极富条理和规划的欧洲中产阶级家庭景象。然而,当外来者闯入后,人们立刻不知所措起来,他们不知如何分配餐桌座椅、在厕所门口焦躁不安地踏步。这个看似高贵、完美的五口之家,实际上不堪一击。渐渐地,大大小小的阴暗面展现在观众眼前:儿子房间中手淫时用的纸巾散落一地,身材肥胖的女儿自卑又易怒,母亲和父亲分房而眠,家庭成员彼此毫不关心……外来者的出现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精致虚伪的外壳被轻而易举地击碎了,汹涌的暗流倾泻而出。舞台上的寂静之家,何尝不是欧洲大陆千千万万个寂静之家的缩影?今时今日的欧洲外表依旧熠熠生辉,但是其内核已经失去了原动力。导演敏锐地观察到欧洲的衰落这一现实背景,并将其巧妙地糅入舞台创作。正如剧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在不经意间轻而易举地破坏了原本严丝合缝的生活齿轮,现实生活中的一次意外或许也能激荡繁华表面下的汹涌暗流。
当灯光熄灭,演员们站在台前谢幕时,他们突然齐齐睁开双眼,先是惊诧地望向台下的观众,继而慌张地连连后退,仿佛眼前是一个陌生且危险的新世界。随着观众们的掌声与欢呼声渐次响起,演员们平静的脸上终于浮现久违的表情,只不过这是属于傀儡的表情,呆滞、僵硬、诡异。他们尖锐干涩的叫声越来越大,最终变成难以抑制的癫狂。帷幕渐渐拉上,尖利的笑声却不绝于耳。《寂静之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好看”的戏剧,正相反,它是一部离经叛道之作,其故事情节、舞台呈现及政治色彩多多少少都突破了观众的审美习惯。它就这么突兀甚至瘆人地立在舞台上,静静地接受观众的审视和质疑。荒诞与混乱,不堪与肮脏,或许不是我们希望在舞台上看到的东西,但恰恰是它们突破我们固有的认知、更新我们老化的审美,让我们恍然大悟:戏剧舞台不仅如此,世界亦不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