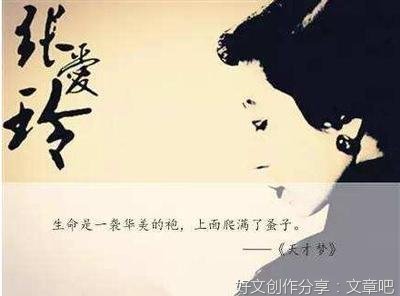《秧歌》读后感锦集
《秧歌》是一本由張愛玲著作,皇冠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NTD 260,页数:20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秧歌》读后感(一):。
重读。即使抛开所有的政治立场和偏见,不问缘由和目的,单纯看成另一个时空发生的完全虚构的故事,小说的完成度也是惊人的高。张爱玲和每一个场景都保持距离,持观望态度,不流露情感意向,不过度渲染,不夸张不掩饰。像鬼,所有事情都并不参加,却比当事人还要看得清楚,写杀猪那段的纪实程度和纪录片的镜头一样,直勾勾对准每一处细节,甚至连人物的心都对准了,似乎在她眼里没有可以隐瞒的,深深浅浅的想法都是赤裸裸摆在台面上的。更绝妙的是其中但凡出现过有台词的人物便不是扁平的形象,没有理想化的高尚和低劣,都是活生生的俗人,真人。除了最后为着冲突的必要让金根看似“突然”得爆发--这种处理如果不仔细便会觉得突兀,其实是有支撑的--其他人物从来没有被安排去推动情节发展,都只是淡淡地活着,仿佛和小说本身没关系,一切的言行举止都是再自然不过地发生。“秧歌”在小说提到的次数并不多,象征性也十分明显,在饥荒的土地上连饭都吃不饱的人们扭动着喜庆的步伐和身躯,带着微笑,像黑白电影里的红色,突兀而诡异,有强烈的视觉张力。其实在平常的日子里,本身根本没有政治嗅觉和相关概念的农村人念着学着那些新时代新话语,也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秧歌表演。
《秧歌》读后感(二):太阳在这里老了
在偶然阅读到此篇小说之前,张爱玲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描写痴男怨女悲欢离合的典型代表,“世鈞,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上面布满了虱子”...这些种种爱恨嗔痴的经典语录,似乎构成其所有写作风格。因此,当我接触到《秧歌》时,足以感叹转变之大,开头对乡村景况的描写细致入微,虽然相较一些真正的乡土作者多了些诗意,但也让人很难不相信张爱玲是真正在此成长过的。
“太阳像一只只狗拦街躺着。太阳在这里老了。”这句比喻如此精妙,但反复咀嚼之下也说不清其缘由,于是我带着这个感叹和疑惑继续往下阅读。
人物塑造中没有全善或全恶,这是我最大的感受之一。尽管张爱玲对农民阶级抱有同情,对某些群体隐含讽刺和抨击,而她却能够不因同情去塑造全然善良无辜之人。金根勤劳朴实,却暴力冲动,他对妻子的思念是如此的细腻与真切,对妹妹金香的手足之情的回忆更是动人,但他身上仍有农村社会下无知和冲动的特性,以及封建社会中大男子主义的暴力。王同志是第一大恶人,但作者几乎没有用他人之口对王同志进行口诛笔伐,而是从对他过往经历的简单叙述中,构造出一个充满理想信念但郁郁不得志的人物,与其说是施暴者,王同志更像是一个某种洗脑下的牺牲品...此类种种,每个大小人物都有来龙去脉,都是生动真实、立体多面。
毋庸置疑,在这部小说里,张爱玲最为关注的仍然是人性,是人情世故,是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虽然和前期描写城市男女之间的情爱相比,《秧歌》算是重大题材,可是这个故事里大部分讲述的还是日常生活情景:夫妻关系、兄妹情感、姑嫂矛盾、邻里纠葛、干部与农民等。《秧歌》大部分笔墨于此,刻画人物心理的微妙,捕捉隐含的戏剧性,这也正是张爱玲游刃有余所在。
再者,与人物塑造相同,张爱玲对事件描写的笔触也是相当冷静的。每当在触及到某人将要爆发的情感时,却又适时的退出,替以冷静的观望态度,和每个人物与场景都保持距离,仿佛一只游走在这个平静又动荡的村庄上空的鬼魂。
让我惊异的是小孩子阿招的死亡,作为小说中最无辜也是最弱小的人物,她的死状是悲惨的,死因是不明而荒谬的。前期对暴乱的情感铺垫已经接近极致,月香极力的担忧和呼唤,人群极力的疯狂与混乱,身为母亲的她不顾一切的冲撞,一触即发时刻,作者却用极为冷静的态度描写了死亡。发现孩子死了的时候:“她其实早已知道她抱在手里的那瘫软的压烂了的小孩是已经死了。”,而在向别人描述时:“她又很轻松似的加上这样一句,用一极明快的表情望着金花,‘阿招死了。给踩死了。’”。这些描写,一下从一位母亲绝望的视角跳脱出来,代为客观的,甚至是冷冰冰的,笼罩了一抹鬼魅的阴影色彩。
关于《秧歌》的真与不真,一直是读者乃至评论家探讨的问题,如果具体地讨论此问题,就要以历史材料为基础,从政治、历史的层面出发。因此,我仅仅就文本中出现的蛛丝马迹发表一些自己的思考。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在小说中已经隐约给出了答案,那便是一个似乎无足轻重的人物——来采写素材的顾冈。作者笔下的这个人物似乎对情节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一直是一个旁观者,有信仰但不坚定,有同情心但不能吃苦,他观察农民生活,观察干部与农民的关系,却从不真正参与其中,也没有表达任何看法,乃至最后动乱暴发,他也没有因此受到影响。这个角色很大程度上和张爱玲的作者身份重叠了,张爱玲虽然有过一段苏北农村的生活史,也间接收集过一些素材,但她的成长环境、身份认同始终和农村有着天壤之别,在写作这部小说时的政治倾向、社会环境也在影响着她,那么在她接触到这些生活、这些素材的时候,心中是否也像顾冈一样摇摆不定,我应该一五一十的写下来吗?这到底只是特殊现象还是典型案例呢?顾冈最后完成了一部与真实事件完全不相吻合的作品,甚至将暴乱的人群与火光作为灵感,强加到反映团结的虚构故事中,极具讽刺。同样的,张爱玲将多少真实或虚假掺杂其中我们不得而知,这种真假参半的写作给读者带来了对历史真实的不确定性,但不能否认的是,她的确有着在大环境下的敏锐的预见性,以及在较少的经验下感知生活的优秀作家素养。
最后再回到那句话,太阳是明媚的、炽热的,就像最后的秧歌一样,在革命者的心里更是胜利与光辉的象征,而在《秧歌》这部小说中,一开始就以太阳的比喻奠定了一个酷热难耐、疲惫不堪的基调。故事的结尾,新年伊始,喜庆的秧歌声响彻大地,但读者到此处无不是空虚、绝望之感。太阳一轮轮升起,这片天空却不再有任何变化。
《秧歌》读后感(三):自由予人,久假不归
在上海城里帮佣三年的月香在“鼓励劳工回乡生产”的号召下告别城市,回到山乡,暂时的被豪言壮语激动着,憧憬回到山乡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她的丈夫是“新社会”的劳模老实人谭金根,一个只看到地契上写有自己名字而忽略其它主张,忍气吞声的青年农民。在嫂子归来的时候,金根的妹妹金花要出嫁到邻村的周村去了。
月香在回来的当夜就发现回乡完全是错误的决定,是被宣传鼓动的盲目回乡,因为她看见山村到处蔓延着无边无际的“饥饿”,尽管长辈谭老大、谭大娘还小心翼翼的竭力掩饰,并说一些口号和标语式的话,但月香已经看破玄机了,她开始后悔。现在连金根最疼爱的女儿阿招都在嚷着肚子饿,因为,但凡有一口吃食,金根会毫不犹豫的给阿招,这个时间出嫁相依为命的妹妹金花,也是因为贫困与饥饿逼迫的。
很快,月香就被借债的乡亲们包围住了,连她亲娘和亲戚谭老大也来借钱,显然,月香微薄的钱很难让所有人满意,尽管他们开借的仅仅是城里一副油条早点的数字。现在,比饥饿更难堪的,就是让村干部王霖偶然看见中午吃稠粥,这是一种极大的罪恶和恐惧,因为在目睹过“土改”的金根看来,所有人都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稠粥”意味着“三反之一”的“富农”行径。王霖是某种党机器教化的化身,他是失意的青年老干部,在各种权利运动倾轧中求得缝隙生存,他是一个没有多少感情的冷漠的人。
尽管,饥饿与恐惧攫住了所有人的内心,但大家见面还都笑哈哈的,并时不时讲一些时髦的标语口号,这以积极分子谭大娘最为拿手。但她指使媳妇金有嫂第一个来借钱时,就已道出实情:
“收成虽然好,交了公粮就去了一大半。现在那些苛捐杂税倒是没有了,只剩一样公粮,可是重的吓死人。蚕丝也是政府收买,茶叶也得卖给政府,出的价特别低。”
饥饿笼罩着山乡,但似乎大家有化解的“精神胜利法”,甚至这两天村子上天天押着秧歌队在那里演习。
饥饿使得月香只有无奈的顺从,因为她已经没有退路了。但这时还有人到哀鸿遍野的饥饿里来寻觅所谓的“乡村神话”,以便到更大的空间去宣示、布道这里的优越性,一个城里文联的电影编导顾冈,来此收集资料体验生活。他被安排住在积极分子谭大娘家,顾冈也看穿了房东大娘是王霖“最得意的展览品”。王霖虽愤愤不平鄙视接待这些“‘解放后’才加入他们阵营的投机分子”,但觉得可以借他们“体验”出的“神话”来换取政绩,以使自己离开这穷乡僻壤。而顾冈也觉得王霖如此资深的资历却在山乡当一个村干,肯定是一个被“清”掉的危险分子,接近他对自己不利,也疏远他。
顾冈面对这里的饥饿世界,但是他很清楚,城里派他下来是要编造一个“乡村神话”,而不是来写写饥饿真相场面的,这一点,顾很清楚。所以,顾想臆造一个不存在的水坝故事。张爱玲刻意要让顾在饥饿现实面前,还编造假故事、假剧本,显然是要借此讽刺当时文学读物的“神话性”来源。
年关到了,饥饿已经到了悬崖边沿了,山村笼罩着一股死亡的气息,却还要承担军属的年礼:“每家摊派半只猪,四十斤年糕,上面挂着红绿彩稠,由秧歌队带领,吹吹打打送上门去。”或折成现金,限一个日子交齐。王霖带领人上门索取,金根怒不可遏,拒绝捐献,面对王霖强硬的姿态和不顾死活的盘剥,悲愤的说:“等不到秋天,我们都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月香为了息事宁人,就将自己仅有的一点钱拿给狂暴的王霖,请他去置办爆仗竹,半只猪,但王还要他们置办四十斤年糕,金根被月香的妥协激怒了,他隐隐觉得那个贪婪的盘剥黑洞永远不会填满的,为此,他对自己深爱的月香大打出手。
金根还是在满腔愤怒中蒸了自己都没有尝过的年糕以作捐献,并在第二天去村公所缴纳捐献。终于,金根在王霖的言语激衅下,忍无可忍的带头反击了,暴动终于发生了,村民冲击粮仓准备抢粮食,与守卫的民兵发生冲突,乱枪之下,阿招被践踏至死。金根身受重伤,但借助月香之力得以逃脱,由谭村去往周村。月香只有求助于金花,但金花权衡兄妹、夫妻利弊,最后也放弃了收留这个“反革命”兄长,金根也不忍连累月香,自己找一个隐秘的地方悄然死去。月香发现时,金根已杳无踪迹了。最后,她悲愤的回到谭村,用满腔怒火将自己当作火种,烧掉了屯着金根缴纳粮食和蚕丝的粮仓,自己也随之化为灰烬。
最后的最后,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
“送礼的行列一出村口,到了田野里,就停止扭秧歌了,要等到快到邻村的时候再扭起来。然后那些挑担子的,他们扁担上坠下来的负荷永远一纵一纵的,他们顺着那势子,也仍旧用细碎的步子扭扭捏捏走着。他们缓缓地前进,缘着那弯弯曲曲的田径,穿过那棕黄色的平原,向天边走去。大锣小锣继续大声敲着。但是在那庞大的天空下,那锣声就像是用布蒙着似的,声音发不出来,听上去异常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