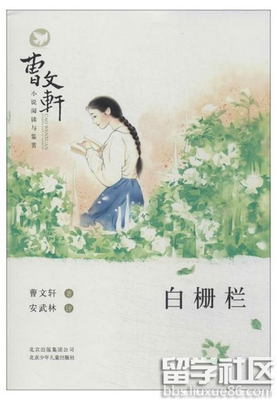白色的虹经典读后感有感
《白色的虹》是一本由[苏]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著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页数:2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白色的虹》读后感(一):日常那些闪光的瞬间,让你感到活在珍贵的人间
封面的水彩画风设计也比较别致——雪花冰晶弥漫和包裹的城镇,给人以一种冷冷的神秘感——尽管我也不是封面党。
我本能地将这本书当做小说来读。尽管编辑比较谨慎,将副标题定为“短篇集”,而不是“短篇小说集”。的确,读帕乌斯托夫斯基这部作品,这个界限并不明确。看得出,编者是个认真的人,体裁的标签不能随便贴,这是个细节。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之前读的本来就不多,但很有特色,对于俄罗斯这个地处西伯利亚的北方雪国文坛,除了官方流行的几个作家外,个人比较熟悉和喜欢的就是普里什文。而读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确也很容易让人想到普里什文,想到两者作品中同样具有的优美的自然或田园气息,想到它们同样的人间温暖,而后者经常被误解为只是儿童文学领域的大师。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短篇,与其他作家的短篇小说相比,往往让人很难分清它们是一篇篇的小说,还是叙事性散文。这样说,并不是指这是它的缺点,恰恰相反,而是它的特点。一句话,它的作品并不追求戏剧化的冲突矛盾,它的故事情节平淡(并非平铺直叙),像日常生活一样缓缓流淌。
所以,他的短篇容易被看作是有叙事性质的散文作品,这也是他这些短篇作品,有时不被称之为小说的缘故。
帕乌斯托夫斯基读来,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滥情”——穿插了大量的景物描写和环境描写。而这些描写又富于诗情画意,从而对故事背景进行的抒情性渲染,让他的这些故事常常蒙上了一层层令人难以忘怀的诗意。当然,长期受悬疑科幻类故事熏陶的读者们,可能会难以接受,甚至会认为这些“过分”的描写会削弱故事情节,浪费时间。不过,阅读体验从来就是多样化的,对此我们可以姑且称其为“诗性小说”。这一点又让人容易想到中国上世纪文坛的沈从文和废名的诗性田园小说,不过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这里暂且不谈。
从这些描写中,透露出帕乌斯托夫斯基对大自然的情有独钟,而不少作品的标题也可窥其一斑,如:《鳟鱼游荡的小溪》《雪》《海风》《柠檬树的故事》《飓风》《细雨蒙蒙的早晨》《白色的虹》《雪原》《野蔷薇》《巨型红杉树》《面向秋野》……这些标题无不是以大自然的景物进行命名的,它们的故事也都大都以这样的自然场景(或者说舞台)进行展开的,没有都市化的那种灯红酒绿、狂欢放荡,因而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小说整体上具有一种质朴的品质,然而他却又不是乡土作家,没有将自身囿限于乡村题材,这点确实难得。
最后说下故事。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故事的视角大多关注的那些行走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而他们的故事许多可以说来自于深藏于内心的多年回忆,来自于以前发生过的某个真实事件,或者跟当年的战争有关,或者跟以前某个新闻事件有关,等等,所以它们往往以一种怀旧的气息将这些故事演绎出来,由此给人产生一种淡淡的伤感和怀念。此外,这些故事的情节没有多少张弛,也没有鲜明的高潮迭起的戏剧性,却往往从某些挖掘某些日常生活的瞬间或片段,来展示人性,人性的丑陋或自私,以及人性中始终未被泯灭的闪光点,从而使得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人性的温暖。
读帕乌斯托夫斯基这些抒情性的短篇叙事作品,总能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间田园般的诗意,感受到人间的一丝丝暖意,也可以说,它们是“正能量”的,尽管这个词说出来有些官方式的滥俗和轻浮。
《白色的虹》读后感(二):自古以来,好人才是大多数
然鹅,我只读过他一本《金蔷薇》,和几篇小短篇罢了!
不过我自信地想,或许我这样普通到淹没到人海里的人,才是大多数吧?
——真的是短篇小说,每一篇都不够看!
还因为,以我浅薄的阅读经验来看,译者似乎不止一位——或者是不同时期的译著。
先聊翻译,外语翻译成中文,尤其是英语、法语等,由于语法结构的问题,中文译过来的句子都偏长。偏长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句子清晰的话,也好懂,句子不清晰的话,译者们也有办法。
什么呢?
而这本书呢?
有些篇用破折号,有些不用,如此内部不统一,我想,是不好自洽的哟(^U^)ノ~YO
不过幸好,翻译没啥大毛病——如果非要吹毛求疵的话,句号“。”就这玩意,用的太多了,语意未尽之处,建议用“,”、“;”,别用“。”……
聊完了翻译,我们来看正文吧~
这本书最打动我的,乃是一种“平常心”,当一个人失去了为善的信念,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我们知道,那个歌唱着的流浪汉,他有一百个理由可以跟那位“小职员”对着干,当然,他也确实这么做了。
不是,在有人被迫为恶时,我们尽可以也把他们当作普通人——需要这份工作来养家糊口的普通人,而不是敲骨吸髓的“那批人”。
我们都一样,都是芸芸众生里的一员,我们实在不应该再分化。
如果有时间的话,请去读一读童话;如果没时间的话,请去读一读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吧,这位“名字辣么长”的苏联作家。
读童话,和读这位作家,并不在于教会我们如何分辨“善与恶”、“美与丑”——成年人的三观实在是太稳固了!
我之所以建议读,也建议学,是因为我发现了一条真理:善良最大的好处并不在于能够得到外人的夸奖,善良里可没有黄金屋、颜如玉,可善良里有现世最大的安慰,最多的问心无愧,简而言之,善良能让我们这些不够“心狠手辣”的人,更自在、更舒服。
我们为善,是为自己。
是因为我们秉性纯良,有赤胆真心,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也没什么可耻的——自古以来,我们好人就是大多数。
《巨型红杉树》是这本短篇集里让我感到最特殊的一篇了。这是一个听起来很简单的故事。讲的是一名植物学家,有一次他到一个作家疗养所去度假,在那里他用自己植物方面的专业知识帮一个作家修改了他的童话。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不像故事的故事,却像是有着魔力一般,不仅在读者心中留下了神奇的种子,还表现出了帕乌斯托夫斯基对待生命以及创作的态度。
帕乌斯托夫斯基是这么讲述这件小事情的。在长满茂密山杨林和老云杉林的山坡上,坐落着一个专门的作家疗养院。因为到那里疗养的都是些阅历丰富的作家们,他们有趣,却性格各异,而且总爱挖苦别人。至少在故事的主人公林学军和育种学家杜波夫心中就是这样。所以他到这疗养院来以后,一方面静静地观察着这些作家们,听他们每天激烈的争吵,一方面又继续在自己的自然世界中漫游。因为相比听争吵,他可能更喜欢后者。他到山下的小河边散步,感受夜色中雾霭的变化,看那些在在雾霭中的矗立的云杉······正是在这真正的宁静中,他遇到了一个比那些作家们都让他更感兴趣的人——一个作家的女儿,一个九岁的小姑娘。这小姑娘也经常来河边玩耍,她爱看书,又对世界对自然充满好奇,她到这小河边,每一次都能从水中发现有趣的东西:云杉的树枝、百合的叶子、铁皮罐头盒······她这小孩子纯然的天性使得杜波夫心中升起了许多美好的情感。他是多么愿意和这小姑娘做真正的朋友,可是他却发现自己无法满足小姑娘心中真正的渴望:当小姑娘问他“冬天,水里的小甲虫是不是没有死,只是在石头底下睡着了?”等等这些问题时,他只能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来解释原因,却无法把对生命的阐释变成属于幻想世界中妙趣横生的童话故事,讲给小姑娘听。
而转机有天到来,一位作家写了一篇童话读给大家听。童话中讲了一棵特别大的树,树里的小矮人在树中建造了一个类似人类的世界,这是一个并不太有童话想象力的童话,或者说只是借着童话的外衣来描述人类的世界,它和它的世界本身可能和那颗神奇的树没有太大关系。当这位作家寻求杜波夫作为植物学家的意见时,杜波夫就描述出了一种真正和大树密切相关,根基于现实的幻想。他说有一种真正的巨树,巨型红杉树。“它可以长到一百五十米高。它的树干大的出奇,直径达到五十米······早在荷马时代,他们就长成大树了,到哥伦布时代,已经长成巨型大树……”在杜波夫的描述中,这棵树真正的活了,它是那样真实、神圣、神奇,又饱含着人类的情谊,仿佛它身上凝聚着世世代代许多人的目光。
当然,帕乌斯托夫斯基没有停留去过多描写这些,他只是让故事自然地进行下去,他让杜波夫继续说,其实这样的树它已经种下,并且不用等七千年,很快就能长得又粗又大,因为他正在研究怎么加快树木的生长方式。
“这才是真正的童话!”小姑娘听了说。此后,故事还是那样平静自然,不着痕迹地进行着。写童话的作家撕掉了自己的作品,杜波夫和小姑娘还继续着他们的乐趣,一起欣赏雪的美丽。
一切就是这么简洁,帕乌斯托夫斯基只是在写故事本身,写故事中的人,写他们见到的山谷、小河、雾霭、雪花。他没有多花笔墨来描写人们的心理活动,可是我们从杜波夫最后的讲述中,已经能够感觉到有什么变化发生了:杜波夫种下的那些红杉真的可以很快就长得像巨型红杉一样吗?那是杜波夫不断研究的成果还是他美好的愿望呢,或者两者都是,不过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感到杜波夫心中一只潜藏着对植物对自然的柔情被唤醒了,它变成了一种想象力,一种极具有现实感又美妙无比的想象力,一种真正的想象力!
我想,帕乌斯托夫斯基也正是如此,作为一个极其喜欢描写自然的作家,他一方面像植物学家一样,客观而又认真地观察自然,就像在《黄色的光》一篇中一样,他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秋叶发出的光,感受到了秋天自然中所有色彩和光的变化。另一方面,他的观察中时时刻刻又有着奇妙的感受,时时刻刻都跳动着一颗宁静温和、对万事万物充满理解的心。所以他爱写那些美好的期待,写人与人之间流淌的美好善意,即使是在残酷的战争中,他也把这种期待和善意放在一个心地纯洁的个体身上,让它变成永不消逝的光芒,变成一种温柔的力量。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所有文章都在传达这种温柔的力量,大概正是俄罗斯广袤的土地给予了他这样的力量。
《白色的虹》读后感(四):虹可以是白色的
本评首发于《文汇读书周报》第1757号第六版“三味书屋”(2019年4月1日发行)。有修改。 《白色的虹》是前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短篇小说集,收文二十六篇。它的文字,如同俄罗斯广袤原野上浮动的暮霭,忧郁地泛着银光。帕乌斯托夫斯基更像是一位诗人,以浪漫主义诗歌为散文和小说的魂魄。屠格涅夫是小说家中的诗人,帕氏则比他走得还远。 他的小说,情节大多淡化,且推动情节发展的,常常不是事件之间理性的因果关系,而是外在气氛与内在情绪关系的极微妙的变化,是一种“感性逻辑”,类似于乔伊斯《都柏林人》中的“顿悟”。文学里的世界有其自身的事件发展逻辑,同样,每个作家也是一个独特的系统,有各自的文学逻辑。 他的主人公大多是孤独的,要么是远行的旅人,要么身处战争之中。他自己年轻时就游历过苏联和波兰全境,深谙孤独的滋味。对他来说,孤独是诗人必备的特质,让人的感觉敏锐,给人“顿悟”诗意的能力。短篇《白色的虹》(本书就是以这一篇的标题命名)里,男女主人公在战争中偶遇,此后一直在孤独中冥冥地寻求对方,如同诗人从生活中寻找诗意,直到有一天,他们永远地得到彼此。 这篇小说诗意盎然。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小说世界里,仿佛人人都是诗人。在他看来,诗意不仅来自生活,诗意还推动生活;是生活的果实,又是生活的种籽。诗意无处不在,却微妙而易逝,需要人机敏地捕捉。这篇小说里,男女主人公正是在诗意的引领下走进新生活的。 也如这个短篇所示,帕乌斯托夫斯基常常写到人物在一瞬间体验到“幸福”。什么是他所指的幸福?在他笔下,人对生活的追求与诗人对诗歌的追求是一致的,当生活与诗意相契合的时候,就是完美的生活,完美的诗,这就是幸福。 当这个幸福临到的瞬间,生活升华了,一切都升华了,就像这个短篇的主人公在心灵里感受到的,“一切都仿佛是雪山上吹来的旋风,让人无法呼吸,一切都变得耀眼夺目,将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白色的虹”。这是诗的极致,在这极致中,白色的虹出现了。虹为什么不能是白色的呢? 这类作品,收入本集的,还有《雪》、《细雨蒙蒙的早晨》、《电报》、《野蔷薇》等。 用绘画作比,帕乌斯托夫斯基是印象派,注重光线和色彩编织的气氛。曾以为这样的作家不大讲究人物性格的刻画,只注重人物的气质,就像印象派画家看重色彩甚于素描一样。他的人物,的确都具有浪漫的气质,与文字所洋溢的诗意相和谐。一般来说,这样的小说容易写得浮光掠影,千篇一律,可是像《制帆行家》、《碎糖块》这两篇,却写出了异乎寻常的深度,而且主人公——两位从事快要被时代抛弃的行业的倔强老人,都具有极其鲜明而又互不相同的性格。帕氏好像毫不用力,这里涂一点,那里抹一下,人物、情感就出来了。他是语言的魔术师。 他诗化的笔触适合写女性,他也确实喜欢写女性,善于写女性。他的女性美得像月光。 俄罗斯不乏写风景的大师,屠格涅夫就是一个。但是把风景当作人来写,把生命写进风景,或者更准确地说,把风景本来就有的生命彰显出来,我没见到像帕乌斯托夫斯基这样的。在他的世界里,天空,大地,云彩,河流,雾霭,风,海,山,森林,湖泊,草地,树木,雨,雪,飞禽,走兽,都是有生命的。它们不仅为人类搭建了生活的舞台,自己更是生活的参与者,每一样也有着自己的命运。他的笔下,连树叶从枝上飘落的过程都是有生命的。他特别喜欢写落叶。 “我凝视着槭树,看见了一片红色的树叶是如何小心翼翼地离开树枝缓缓落下的,我看到了这片树叶在轻微地颤动,某个瞬间好像停滞在空气中,尔后开始斜落在我的脚前,轻轻地颤动着,发出微弱的沙沙声。这是我头一回听到落叶的沙沙声响,那是一种非常模糊的声音,有点像儿童的悄悄话”。《黄色的光》用很大的篇幅描写落叶,称得上一篇“落叶赋”了。 作者对人与大自然相互交融的关切,也深深影响了后一代作家,比如《鱼王》的作者阿斯塔菲耶夫。而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风景如果变成绘画,其忧郁的气质与萨符拉索夫极为相像。 集子里有几篇以真实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如《老厨师》、《鳟鱼游荡的小溪》、《雪原》、《一篮云杉果》等,与他著名的论艺短文集《金蔷薇》相类,具有童话般恣肆的想像力。还有一些,比如《玛莎》,比如《巨型红杉树》,既像童话,又像小说,这位大师好像根本不在乎文体。 以上所谈,不过是以管窥豹,看到的几个点,并不能概括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风格。文学评论最忌讳削足适履,把作品装入现成的框框。其实,每个大师都有多变和捉摸不透的一面,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感觉帕乌斯托夫斯基尤其是这样,所以作为读者,我应该老实一点,安于这种多变和捉摸不透。 译者董晓的译笔清丽,平和,节制而不失舒展,传达出了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那暮霭般忧郁的神韵,就算这是帕氏原文,也很了不起了。顺便说一句,《雪原》其实写的是爱伦•坡,董先生译为“阿兰”,又没有加注,算是智者也难免的一失吧。
《白色的虹》读后感(五):人生充满邂逅,邂逅便是永恒
雅众文化一个月前的赠书,到今天才读完写评论,感到十分惭愧。
——读帕乌斯托夫斯基《白色的虹》
说到帕乌斯托夫斯基,可能大部分人会想到他著名的《金蔷薇》。的确,这本散文集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传入中国以来,受到了细水长流的好评。它写给作家,成为在不同的文化中都可以共通的艺术作品创作指导,也写给内心柔软的普通人,人们的经历、情感,在不同的时空里都可以相通。
我不是一个作家,感受到更多的是经历与情感的相通。我喜欢帕乌斯托夫这个人,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作品,还因为他这个人。他在儿时与好友布尔加科夫一道在,栗子树下的旧书摊上看小说的回忆,总让我想起儿时和好友W,溜达到小县城的第二新华书店,买书的情节。追忆往昔,既觉得美好,又觉得伤感与感慨。而他浪迹天涯,从事搬运工、电车司机、救护员、捕鱼人、锅炉工、钳工等等不同的职业,又是多么令人艳羡!
作为一个读者,我把帕乌托夫斯基和《金蔷薇》归入温柔的作家与柔软的作品行列,与他们并列的还有斯托姆与《茵梦湖》、圣·埃克苏佩里与《小王子》、尤里·巴基与《秋天里的春天》、奥尔科特与《小妇人》、王尔德与《夜莺与玫瑰》、安房直子与《狐狸的窗户》。这些作品虽然体裁各有不同,但都让人的心柔软到让人们的心灵融化,用细腻的情感无条件地征服读者。
然而这样的作品往往读起来很慢,并不能像读一个故事那么读。因为只有你真正地沉静下来,慢下来,才能真正到作者在作品中想表达的东西。——那并不只是一片森林,而是其中细微的风声,叶子的沙沙声,鸟虫的鸣叫声,小溪的潺潺声,听得久了,也许还能听到大地的声音。所以对于浮躁,沉静只能片刻计数的我来说,帕乌托夫斯基的这个新的短篇集《白色的虹》和《金蔷薇》一样难读。
不过好在作为枕边读物,26个短篇是读完了。这些短篇就像一筐果子,虽然都是果子,但却各自有不同的风味。或者有感动,或者有思索,或者有联想,或者有感悟。我仅仅写几篇印象最为深刻的。
如果要挑一篇,像《金蔷薇》中《珍贵的尘土》那样最为感动的,我要选《一篮云杉果》。作曲家格里格在森林里邂逅了小姑娘达格妮,他没有礼物送给了她,答应她18岁时送给她一件最好的礼物。达格妮来到城市生活,被生活的洪流冲击地迷茫,早就把森林里这个偶遇的陌生人抛到脑后之时,在音乐厅里听到了这首给她以生活的方向与力量的曲子,而此时格里格已不在人世,就像《珍贵的尘土》里的夏米不在人世一样。
我想不清楚,《珍贵的尘土》中夏米对苏珊娜,以及这篇中格里格对达格妮算不算爱情。不管是不是,它都是属于人类共通的超脱的感情,像尘土、一篮果子那么平凡,但更如金子那般宝贵。
《兔爪子》是感动到我的另一篇作品。我很难想象,在苏联铁血与骄傲的那个年代,在环境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还没有被重视的那个年代,作者能那么细致地描写感人至深的一段人兔的邂逅。读到那被烧伤的兔爪子,我想起小时候被我蹂躏,剪毛时又在背上剪了一个大洞的那个兔子,它只会轻轻地嘶嘶叫,眼睛还是那么温柔。动物是有灵性的,完全又有一种和人类共通的温柔。
另外一篇印象深刻的是《时间飞逝》,画家拉夫罗夫在船上作画,邂逅了女领航员萨沙。他总想为了抓住某个最美的瞬间,让萨沙把船停下来,可是这艘有时刻表的航船却始终没有停下来。最后画家体悟到:
“……可是生活任何时候都不会停下来的,它将永远像一条宽广的多彩的河流,流向我们所称之的未来。你一旦落伍,生活的洪流就会滚滚向前,将你甩在后面,就会从你的视线里淡出,你就永远也追赶不上了。”我很难对整本书做一个整体的评价,因为它所要表现的即使细微的,又是广阔的,既是瞬间的,又是永恒的。可能人生,更长远的说时空,就是由那么一个个作者所描写的邂逅的片段所组成。真如同培根所说:
幸运之光犹如天上璀璨的银河。银河是由许许多多小星星聚集或何在一起而成立的,不是一个一个地看得见的,而是一起发光的一条光带。而使人幸运的也是由许许多多微小的、难以分辨的美德,或者更确切地说才能和习惯之合成的结果。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书之美,也在于这样的点滴汇聚吧。而人类口中的美,隽永的文明,不也正是由个人为单位的星辰,汇聚而成的绚烂星河么。
到这里,我想到了米沃什的一首诗《邂逅》(Encounter),来表达这种不能言说的体悟:
邂逅 [波兰]切·米沃什 黎明时分我们驾驶马车穿过冰原,一只红色的翅膀从黑暗中升起。突然一只野兔窜过道路,我们中的一位伸手指向了它。已经过了很久。如今他们都已不在人世,那只野兔,还有那个伸手的人。哦,我亲爱的,他们在哪里,他们又去向何方?那伸手的人,那闪过的动作,那石子的沙沙作响。我询问,不因悲伤,而是惶惑。Encounter By Czeslaw MiloszWe were riding through frozen fields in a wagon at dawn.A red wing rose in the darkness.And suddenly a hare ran across the road.One of us pointed to it with his hand.That was long ago.Today neither of them is alive,Not the hare, nor the man who made the gesture.O my love, where are they, where are they goingThe flash of a hand, streak of movement, rustle of pebbles.I ask not out of sorrow, but in wo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