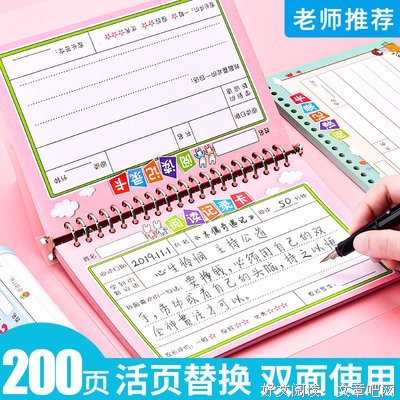All Souls' Day读后感摘抄
《All Souls' Day》是一本由Cees Nooteboom著作,Picador出版的Paperback图书,本书定价:GBP 6.99,页数:3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All Souls' Day》读后感(一):人们相信亡灵的归来
小说标题的万灵节(All souls’ day)不同于我们常说的万圣节(All Saints’ Day),在天主教等宗教中,万圣节是11月1日,纪念已经升入天堂的圣徒。而万灵节则为罗马天主教、圣公会等宗教的一个节日,在万圣节的次日,亦即11月2日。该节日纪念死去的信徒,但是这些信徒的罪还未洗净,故而尚不能上天堂。和中国清明节一样,在这一天,人们相信亡灵会归来。
《All Souls' Day》读后感(二):希德嘉•冯•宾根
《万灵节》这小说中一再介绍中世纪才女,女修道院院长Hilgerd von Bingen的音乐。书中借德国哲学家阿诺之口,这样介绍她的音乐:“希德嘉•冯•宾根?如果宇宙是个问题的话,那么答案就是神秘主义,不过她的神秘主义体现在歌曲中。没有什么答案是完美的,不过比较起来我更愿意选择艺术。你到了日本,听够了这些严肃的男声后,回来听听她的音乐吧,那是一种执着与另外一种执着在较劲:一种执着是虚无感,是自我如若涅磐般消失;另一种执着是确信灵魂与上帝在一起,共享永生,在宇宙的和谐中哼唱。神圣的低音与神圣的高音!你得承认,这实在太美了,不管经历的事何等恐惧,何等坎坷,何等救赎,何等喜乐,他们总能写出相应的音乐来。几千年前,行星们以一种完美的和谐,合唱着赞颂上帝的歌曲,但是它们显然不再唱了,或许是因为它们知道我们就要来了。我们被放逐到宇宙遥远的角落,与此同时,我们的世界却又在缩小。不过尚有音乐,一慰平生啊。它里面既有和谐,又有撕心裂肺的不协调。你有没有随身听CD机,可以在飞机上用?…等你到了3000英尺高空的时候,听听我这些中世纪的唱诗班献诗吧。这样,你就可以接近天国了,人说此曲只应天上有啊。”
以前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听Nooteboom这么推崇,不禁找来一盒CD,The Origin of Fire,竟欲罢不能,每回做点什么事都要带上耳机,一遍一遍去听。这音乐能让人一下子安静下来。久而久之,竟觉得这小说和音乐在气质上如此类似,都带点神秘主义。回头去查Nooteboom的传记,发现他以前曾想去修道院做个修士,难怪!小说中想出家又舍不得老婆的法国语音师伯特兰,大概就是作者的化身吧。
再看阿诺对此人作品的其它介绍:“她们唱的是Studium Divinitatis: 圣乌尔苏拉席上的晨祷,是早晨的第一支赞美诗,那时玫瑰上还缀着朝露,河面的薄雾开始消散…”顺便说一句,圣乌尔苏拉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传说。相传公元五世纪时,有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威尔士公主,叫乌苏拉,与一位信奉异教的王子订婚,她要保全处女身份,去罗马朝圣还愿,于是与十位贵族女伴结伴出游,女伴各有一艘大船,上携千名少女。就这样,浩浩荡荡的11000处女大军沿莱茵河而下,谁知不幸遇到了匈奴军队,乌苏拉拒绝嫁给匈奴首领,匈奴首领遂将她和11,000名少女全部惨杀。今日的科隆原来就是以这位女子命名。希德嘉•冯•宾根似乎很喜欢这个传说,多首乐曲献给这位中世纪圣女。
“希德嘉•冯•宾根…还是哲学家和诗人呢!‘Aer enin volat…当那空气飘过…’瞧瞧,它一直在D和E两个调子间变幻…我们在第四唱和颂听到的是E调,现在又在第七唱和颂中听到了。这是女性原则…然后是第六,第八。换言之,他们当时想的是男性的尊严,女性的属灵,男性的权威。好了,这毕竟是中世纪早期。在现今的时代,这么说就存在政治正确的问题,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她把这对照表现得这么美?这在我们身上已经丢失了,我们这些现代的耳朵已经听不出这些细微的分辨了。”
《All Souls' Day》读后感(三):摘录
摘录:
-- 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会把死亡和苦难,变成温和的追忆,叫那已经死去的人,音容笑貌重新出现?
-- 你不相信艺术的不朽。真可笑。写作的人总信这个。他们是不朽的大师。完全相信他们会流芳千古,却不知文字印出来会被发霉,会被虫咬。即便真有什么存留下来了,我们说的是个什么时间概念呢?3000年?我们通过今日眼光阐释的作品,和当时写作者的原意有天壤之别…
--…你为什么不拿本黑格尔的著作,来换那条鱼呢?
--阿诺举起了杯子。“为我们短暂的生命干杯。为那些遨游在我们上方的成百上千万幽灵干杯,”阿诺说。“死去的王后,士兵,妓女,牧师…你们永远都不会孤寂。”
-- 拥有(拥有是他的说法)主要语种的人,不管说的是德语、英语,或是西班牙语,总是想当然地认为,那些不幸说着小语种的人,不管一开始多么费劲,总是有义务让全世界其它人听懂自己的话。
--(论欧洲语言中的阴性阳性)“你们的词语一跨过莱茵河就变性了。月光一照到斯特拉斯堡,就变成了女性,时间变成了男性,死亡成了女性,阳光变成了阳性。”
--荷兰语和德语是远亲,只是分道扬镳了。你们德语本该和我们在一起的,不过却变种了,荷兰人觉得它听起来古怪。有时候声音太大。因为你们这个国家山多,谷也多。这声音带回声的。荷兰的地比较平,什么都在表面上。我们缺乏深度,不过好处是我们更清晰。你们德国人总是在寻找隐密的山洞,黑暗的森林,阴暗的山谷,茂密的山坡,怪不得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瓦格纳式的迷雾,...女孩就是个例子。我说的是“女孩”这个词,在德文里,虽说的是女孩,你却得用its这样的代词:’Das Mädchen hat seine Puppe verloren.’女孩把自己的布娃娃丢了。你得承认,这听起来很古怪。好像女孩真是遇到了多大的不幸。在我们的荷兰低地,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发生。每个人都会看出这一点。荷兰过去被大海覆盖,我们将海水抽干,晾上一阵,然后在上头盖房子,现在你可以从窗外看到一切。我们没有什么可藏匿的,没有迷雾,没有秘密,只是小女孩和她的布娃娃。在我们那里,‘女孩’这个词我们用阴性。你有没有听过翻译成荷兰文的歌德作品?
--有知识的人遍地都是,不过很少有人既有知识,又能这么深入浅出讲解出来,且不居高临下,而是让你感觉到你能听懂所有细节 —— 至少是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后来,你在脑子里回忆的时候,你发现你其实懂得太少,不过总能记住一星半点。
--一个体系设计的时候只需几个人,其余的人得一直受其害。
--他的希腊课老师谈到奥德修斯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完全自由的人,才有可能问:“我应该走向那一边?”
--统一,他们对统一简直一点都不懂。整个国家像装在盘子上一样端给了他们,他们却不知如何下手。
--现在是西德给他们的梦想埋单,不过是咬牙切齿地给他们埋单。
--大部分人只是手气不好,拿了一手坏牌。不过就像人类常做的那样,他们尽力而为:他们遭封锁而自由,受操纵而清醒。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帮凶,参与这样一个恐怖的误会,一个类似现实世界的误会:一个腐败的乌托邦。等钟摆摆向另外一边的时候,这乌托邦终告结束。不变的只有那痛苦,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还得承受另外一半人的自高自大,而他们只不过是拿了一手好牌而已。
--一个城市之所以是城市,靠的都是建筑和声音。包括已经逝去的建筑和声音。每个城市都充满声音。
----阿瑟说,“我昨夜的酒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呢。要是再喝,今天又废掉了。”
(阿诺回答:)“你这一天废掉总比把酒废掉好。"
--“是谁的书?”
“我的。”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谁写的?”
“啊,你猜猜看?”
“我知道作者的名字吗?”
“我不知道,不过他知道你的名字。”
阿瑟把手伸到报纸下,把书拿出来。是一本圣经。
--“欧洲人还没有转换到欧元呢。要是我们说了算的话,永远都不会转到欧元。我们辛辛苦苦一点积蓄都被见钱眼开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给浪费了。更不要说波兰人和捷克人。他们已经在敲门了…”
“不过你也得想想,五十年前,你们(德国人)还巴不得把他们占领过来呢!”
--"我自己翘辫子前,现在的政府也倒不了。“
“真没有想到你这么喜欢他们。你不是老骂他们‘这伙混蛋’吗?”
“是啊,不过也算是我的混蛋。我习惯他们了。"
--人总是两个方向都可以跑的,你只要告诉他们去哪个方向便可。
--她根本不屑去纠正他。男人无法容忍他人来纠正自己。
--原来这位就是和自己睡觉的女子,不,是睡了自己的女子,只是这种事情谁主谁次也看不出来。
--这位仁兄看起来活像一根穿着正式西服的胡萝卜。
--他感觉好像是回到了青春年少的时候,骑着个自行车,从心上人的家门口路过,却又生怕被她看见。
--在当初构思出这些话语的城市,当年的奴仆成了主人,却又牢牢陷入另外一种奴役,一种更糟糕的奴役!奴仆们投票选举自己的主人,好去继续做奴仆,他们和主人只有名义上的平等!哪个白痴想出了这样的办法来?可是这样的疯狂却在扩张。成百上千万的人甚至为此而死。
--人们都陷入了致命而肤浅的无思考状态,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体存在,去看同样的笑话,猜同样的字谜,买同样的书(通常买了不读)。他们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地做这一切,叫人郁闷不已。她认识的所有人都在练瑜珈,去巴厘岛休假,做指压按摩。他们忙忙碌碌参加各种活动,在家根本呆不住。很少有人能够享受独处。
--“科学家要不就是计算工具,要不就是神秘主义者,你自己挑好了。"
--真有恋爱这回事吗?我们只是听说有人被刺杀,被暗中跟踪,或是妒火中烧时互相开枪射击,可是爱情在哪里?
--从前,女王和英雄们才是神话、悲剧的的题材。比如受罚的俄狄浦斯王,复仇的美狄亚,反抗的安提格涅。你们已不再是国王,或者公主。你们的故事对自己或许重要,对他人十分琐碎。不断持续的片段,新闻,肥皂剧。你的的哀痛不会再产生大量的文字,叫他人去潜心研究,直到你被人淡忘。这使你更趋肤浅,更趋短暂,照我们的看法,更有悲剧性。你没有回声。没有观众。
待续
《All Souls' Day》读后感(四):灵感是那“一小滴”:塞斯·诺特博姆访谈
塞斯•诺特博姆18岁那年离开天主教寄宿学校,此后五十多年间,他走遍了全世界。22岁时,他出版处女作《菲利普及其它》,此后陆续出版《荷兰山间》、《真相与表象之歌》、《木星!》、《骑士死了》和《下回分解》。他最近的小说《万灵之日》去年才出英文版。1983年,因《仪式》的出版,塞斯•诺特博姆首次被介绍给美国公众,此前他在荷兰和德国享有盛誉,尤以他自称的“旅游文学”著称。他的旅游文学结合了日记、散文和简介 。我们在纽约的阿岗昆酒店的大堂会面,坐在低低的沙发上聊着,如同两个绅士般的阴谋家。 诺特博姆看起来个头要比照片上小,个性随和,说话有趣。当天上午,他早早起来在街上行走,很想去斯特兰德书屋一游,希望能找到一本米兰•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晚上,他要去看昆德拉此书中提到的雅纳切克歌剧。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我很好奇,你再一次坐下来,接受这种采访的时候,脑海里都想些什么呢?
塞斯•诺特博姆:再一次坐下来接受采访?什么意思?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过去几年你接受过很多次这样的采访。
塞斯•诺特博姆:是的。但你知道,写作是私人的事情,而采访则是一种交互。接受采访时,受访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采访者。有些采访者对我的作品很熟,有的只是给某个日报或其它地方应付差事,并不是真的对我有什么认识。我得看采访者是谁,然后调整说话方式。采访最大的好处,是迫使你将某些观点明晰化 ,你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这和写作一样。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你有没有想过在采访中新造出一个自我出来?我记得纳博科夫曾经说过,在接受采访时总有诱惑,为不同的采访者创造出不同的自我。
塞斯•诺特博姆:过去四十年来,我一直在第三世界国家旅游,我写过我在欧洲、亚洲、南美的旅行。人们总是问:为什么你一直都在旅行?旅行是不是一种逃避呢?多年来,我为这个问题编造了不知道多少答案,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了。不过今日接受采访,我不打算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我想先从《万灵之日》说起。你的其他小说短得多,这一部的篇幅是其它小说的两倍以上。为什么?
塞斯•诺特博姆:这一点岂不是不言自明?是小说中的人物要求有这样的长度。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人物?
塞斯•诺特博姆:没错。还有柏林、共产主义、二战、恐怖主义,这些都是大题目。小说牵涉到这些历史性的话题,还有一个人对这些话题的反应,另外这里还有个人命运的反思,写少了怕是应付不了。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万灵之日》讲述了一个记录片制作人的妻儿前往西班牙度假,遇飞机失事身亡,制作人接着住在柏林,常在这个城市漫步。柏林这个城市有什么地方吸引你?
塞斯•诺特博姆:我与柏林很有渊源,只是这本书不是自传(比如我没有在飞机失事中失去妻儿)。首先,对荷兰人来说,柏林是一个从前敌国的首都,小时候我也常听到来自“元首”从这首都发来的消息、讲话、指示,这些东西都来自柏林。孩子的生活中会蕴涵这种强大的、神话般的内容。战后,我们和德国并无多少相干。我那时候还年轻,但一旦可以去旅行的时候,我就去了南方,去那些有光亮,那些还没有遭受破坏(或者说没有遭到同样破坏)的地方。关于德国的想法整个就像一个诅咒,只是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而已。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真相与表象之歌》中,你写道:“一个人坐到桌子边,突然想到了一个句子:上校爱上了医生的妻子。”
塞斯•诺特博姆:这是真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不明白,我写书是没有预先规划的。去年11月,我在休斯顿跟一些创作系学生做讲座,说到我动笔写小说的时候并无计划,他们都不肯相信。但是我真是没有计划。我会枯坐在那里,感到有些绝望,然后会想出第一句:上校爱上了医生的妻子,接着慢慢把一本书写出来。《真相与表象之歌》说的是小说和小说创作。我从来没有去过保加利亚,可是看过这书的人都以为我去过。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这和很多作家的做法相悖,他们写书事先会布局谋篇,会像插花一样去安排。
塞斯•诺特博姆:我记得我访问过在密西西比牛津市的福克纳故居。他用铅笔在墙上计划出了《寓言》中的每一天。对此,我只有羡慕的份,可惜自己做不到。相反,我的写作是进行细致绵密的描述。我的写作来自于旅行见闻。旅行让我能够更敏锐地描述《下回分解》中的里斯本和《万灵之日》中的柏林。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据我所知,在一定意义上说,你不是天主教小说家,但是你的小说中充满天主教的精神。
塞斯•诺特博姆:我的父亲在战争中去世,我妈妈1948年改嫁给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我被送往天主教寄宿学校,因为修士们能够提供最好的教育。也许继父希望我会成为一名牧师,这个结果并没有出现。但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我所有小说中都有修士,我现在还常有诱惑,在所有小说中安插一个修士。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你这种东奔西走的生活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塞斯•诺特博姆:我想任何一种生活都有不利的一面。但就像我在《诺特博姆酒店》中说的那样,过去五十年我去过太多地方,已经在自己心目中建立起一个酒店了,它是穷人的酒店,也是富人的酒店,是第三世界的酒店,也是第一世界的酒店,它的一侧是极地冰海,另一侧是加勒比海滩。它的房间不计其数,在每一个房间,我都写了一些东西,因为我的很多前期工作在旅行中完成了。《万灵之日》写于加利福尼亚州、澳大利亚、西班牙。我把这本书一直带着走,如同一个固定任务:积雪和柏林,柏林和积雪。这个意象一定深入骨髓了, 因为我写书的时候,离开德国已经有几年,动笔时我在阳光明媚的南加州。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像卡尔维诺或纳博科夫一样,你的书有独立的生命。你邀请其他人加入在这样的生命当中。
塞斯•诺特博姆:恐怕没有邀请人。举例来说,《真相和表象之歌》是我很珍惜的一本书。我不想再在欧洲出版它。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这是为什么?
塞斯•诺特博姆:嗯,我想它恐怕也不会畅销。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那么一定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写畅销书呢?你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你走过很多地方。为什么不写出一部约翰•格里沙姆那样的小说呢?
塞斯•诺特博姆:我不能。我做不到。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看过这类书籍。不过他们的书都有情节。显然是很独创的情节,写得好,不然大众不会这么喜欢。可是你让卡尔维诺写一部格里沙姆式小说试试?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我已经注意到,继你其它几部小说之后,在《下回分解》中费尔南多•佩索阿 再次出现。佩索阿是什么地方这么吸引人,你自己对他又是什么感受呢?
塞斯•诺特博姆:他做了一件我们许多人都想做的事,只是如果我们现在来做的话,就显得像在模仿了:他创造出除自身之外的其他作家来。也就是说,将自己分裂,分裂成虚构的其他人,但又能写出真实的小说来。我相信,这是你所能想到的最大的虚构。记住玛丽莲•梦露的一句话:“真实的花园中有想象的…”,不,“想象的花园中有真正的蟾蜍”。我是说创造出虚构的诗人,写出真正的诗歌来。很棒。他们没有护照,他们却能写书。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喧嚣之书》 中有那么多美丽的忧伤,无尽地重复,书中还写了各样的应对方法。
塞斯•诺特博姆:他酗酒死了。留下两万七千页未发表的手稿。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最后,我们可否讨论一下你唯一翻译成英文的旅行作品《绕道去圣地亚哥》 。我想知道为什么此书没有那么零散?叙述者长篇累牍,一说就是好几个章节,而此书分明可以分散成很多自成一体的文章。
塞斯•诺特博姆:我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书来写,它只是一系列文章。我常会回头去写圣地亚哥。对我来说,它是西班牙的精神首都。西班牙就如同不同国家的结合,只是通过这个地方汇聚在一起,因为它是西班牙守护者、使徒雅各的埋葬地。我只是一篇一篇地写,没有想到它会成为一本书。不过最终还是成了一本书,但是我想这书也会原谅自己吧,但愿你能理解这一点。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目前来说,你是不是像你自己说的那样,在“等待下一部小说”呢?
塞斯•诺特博姆:没错,我始终这么看,觉得自己是在“等待下一部小说”。这一点很难准确描述,不过这有点像化学里的情形。你加一滴什么东西进来,固体能变成液体。所以这一两年我还只能忍一忍,脑子里得想些主题,不管是不是急迫。在某个时候,但愿那“一小滴”会来,这样我就可以重新开始…担负起给新的小说虚构人物的重任来。我记得在《洛杉矶时报》上看到过,《万灵之日》的情节很淡。我哪里会去在乎情节?谁会去在乎情节呢?以情节见长的作家成千上万。这本书里当然也有些情节,但主要还是散漫的思考和哲学论述。你要是问为什么这么写,我会说这么写的书太少了。所以我就写得这么散漫,当然了,取舍都是读者的权利。不过我很想念…想念小说里的这些人物,这是不是自我陶醉呢?时间会告诉我们的。我真的想念这些人物。我觉得自己创作出了一些很了不起的人物,就算小说结束了,他们还可以一直在一起神聊,永远这么海阔天空说下去。为什么不这么说下去呢?如果他们真能这样的话,那么我就算是创作出了一部普鲁斯特式的小说,当然我这里说的是类型而不是质量。另外,我耳朵里也常回响起一种声音来。1962年,因为一次偶然机会,我结识了玛丽•麦卡锡。我那时候还是个初出茅庐的作家,在爱丁堡参加一次作家会议。我在那里遇到了几个人,如诺曼•梅勒…还有玛丽•麦卡锡。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这是1962年那次关于威廉•巴罗斯的会议。玛丽•麦卡锡是《裸体午餐》的坚决支持者。
塞斯•诺特博姆:是的,这些都对。玛丽不知何故,怎么说呢,喜欢上了我。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她去世。我经常去她在缅因和巴黎的家中拜访。这种关系维持得很困难。她无法看我的书,以为还没有翻译过来。对她来说,这交往基于直觉或曰本能。我可以看她的书。我很佩服她的散文。她的思维很敏锐。当然,看到这样的人物觉得我有些才华,我受宠若惊。《仪式》翻译之后,我就像是要赶考一样,因为她完全有可能说她不喜欢。我曾听到她跟别人评论一些书籍时说:“这是我一年来看到的最糟糕的书。”诸如此类,听到这些话我都会感同身受浑身发颤。但她却决定喜欢我这本书。后来,等我们更熟悉了,她曾在信中问我:“荷兰的某某某现在怎样了?”我会回答说:“某某某刚出版一部600页的小说了。”她回信说:“塞斯,你给我写短点。”
译自:http://www.bookforum.com/archive/sum_02/interview_nooteboom.html
《All Souls' Day》读后感(五):每个人都被万灵环绕
塞斯•诺特博姆(Cees Nooteboom)是荷兰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游记作家、翻译。《纽约时报书评》杂志称其为“20世纪的乡村说书人。” 纽约的《村声》周报称其为“作家中的作家,其著作常象征着艺术本身,其作品中的典故随手拈来,尽管其作品都不长,但是有些读者读起来,可能得重温一下西方(甚至还有东方)文化和文学史才行。”《华盛顿邮报》说“诺特博姆作品主题宏大,但他绝非眼高手低之辈。他在寻常事物中灌注哲学思考。他的思想会不经意地突然出现,叫你猝不及防,如同一个荒废橱柜里藏着的天使。”
对中国读者来说,诺特博姆的名字还略显陌生,但他的部分作品已经开始引进,如其游记作品《绕道去圣地亚哥》。《万灵节》被德国一杂志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50部小说之一。
《万灵节》(All Souls’ Day)这部小说标题的万灵节不同于我们常说的万圣节(All Saints’ Day),在天主教等宗教中,万圣节是11月1日,纪念已经升入天堂的圣徒。而万灵节则为罗马天主教、圣公会等宗教的一个节日,在万圣节的次日,亦即11月2日。该节日纪念死去的信徒,其罪尚未洗净,还不能上天堂。和中国清明节一样,在这一天,人们相信亡灵会归来。
这部小说的主要场景并不是发生在万灵节,然而故事的主人公阿瑟•唐恩倒像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节日当中。阿瑟是一个荷兰纪录片摄影师,除了经常接受国际拍摄任务之外,他还有个爱好,就是拍摄黄昏或者凌晨,其时暮色或晨光半明半暗。阿瑟个人也生活在半明半暗,阳间和冥界的交错之中:十年前,他的妻儿在飞机失事中丧生。其亡灵不时浮上心头来,而他却又要努力习惯新的生活。他孤身一人,“了无牵挂,却又藕断丝连,通过看不见的线路和世界连接。语音,留言。都是些朋友,多半是同事,一些和自己生活差不多的人。他们用他的公寓,他也用他们的。要不就住便宜的旅馆和寄宿公寓,一个漂浮的世界。纽约,马德里,柏林。”这漂浮生活中,他落脚最多的是德国柏林。而统一后的柏林本身,也在历史和现实的明暗交错之下。历史的幽灵,仍在这个统一后的城市徘徊。阿瑟在柏林的街上走,就如同一个导游一样,带我们进入这个城市的东西结合处,带入这个城市的现在和过去,带入这个城市的灵魂深处。
阿瑟在这个城市有一群古怪的朋友,酗酒的俄国女物理学家,多才多艺的荷兰雕塑家,口才迷人的德国哲学家。他们常在德国的一个小酒馆喝酒,品尝各式德国传统美食,如酸奶酪、烩猪肚、中世纪食谱做成的黑面包、做成大教堂状的香肠大拼盘。他们在一起吃着,聊着,他们的谈话充满智慧。和这样一群朋友在一起,想庸俗一点都难。连酒馆的老板舒尔泽先生,也都文质彬彬,如我们所说的儒商。他执意保留着德国美食传统,不叫那全球化中的美式快餐,打败饮食世界的多姿多彩。几个德国、荷兰、俄国知识分子在一起相聚的时候,他们对传统流连忘返,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对一个动物的灭绝而大呼小叫,而对一道烩猪肚这样的美食,对格拉斯笔下女子的优雅气质的灭绝无动于衷。唯有粗俗和无礼代代相传。
只是曲高者和寡,深刻的人是孤独的。这群知交一旦离开酒店短暂的相聚,回到自己的生活,就如陷入了各自的孤岛。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万灵作伴,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过去要去对付。俄国人季诺碧亚常会记起在俄国吃不饱肚子的那些漫漫长夜。饥饿让她脱离困境后不停大吃,吃成了胖子。漫漫长夜中的失眠,让她习惯了仰望星空,开始热衷于外星探索。
这小说当中,阿瑟还有个红颜知己,在荷兰的厄娜,他们的友谊让人看到男女之间也可以这么无限接近却永不越轨。阿瑟是厄娜的禁果。而厄娜则是阿瑟永可倚靠的安慰,我们谁不希望找到这样可贵的朋友呢?
友谊地久天长,而爱情朝夕万变。阿瑟在柏林偶遇一个历史专业的女博士,同样来自荷兰,却在研究西班牙某个中世纪女王。在书斋之外,她是空手道高手,是个女妖一般的舞者,是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尤物。博士自有自己的幽灵在折磨她。过去她曾被强暴。往事不堪回首。她纵深一跃,跳到了中世纪的故纸堆中。
阿瑟爱上了她,爱情让他日渐走出过去的阴影。可是还不如说是她爱上了阿瑟。阿瑟去找她找不到,却在黄昏的时候,像猫一样抓门,进门之后,一言不发,脱个精光,骑到荷兰摄影师身上,女博士成了女骑士。她显然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女权到不能容忍男方的任何主动行为,包括打电话找他。这场恋爱注定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游戏和梦在柏林的图书馆,在日本四国的八十八寺,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展开。最后的下场却是悲剧。大家回到各自的生活,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每个人还如同那万圣节的亡灵一样不得超脱。然而一些变化确实又在发生,阿瑟在友谊当中找到了安慰,而女博士看来是要心无旁骛,矢志钻研学问了。
人世间多少个这样的事情在发生着,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人类在一男一女的关系上生发出气象万千的故事来。好多事情被埋没了,然而人类的对话还在绵延不绝,穿越正史的记录,回荡在不间断的时空之中。人类是孤独的,当我们将人类历史作为一条长河的时候,我们又不是孤独的。书中的德国哲学家阿诺举杯说:“为我们短暂的生命干杯。为那些遨游在我们上方的成百上千万幽灵干杯,…死去的王后,士兵,妓女,牧师…你们永远都不会孤寂。”
小说中每个人都被过去的幽灵纠缠,而过去合在一起,便是历史。而作家似在暗示,历史是一种虚构,而文学却是一种真实。常听人说: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
小说中的女博士研究一个非常冷僻的话题,中世纪西班牙女王。虽然她最后跑到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资料,可是所有这些资料加在一起,又能说明多少真相呢?在那遥远的过去,我们对真相又能有多少了解呢?治史其实就是一悖论,你写历史,你的使命是要接近真实,可是你不去想象,如果填补文献之间的沟壑?作者引用马可•布洛赫的告诫说:“历史现象,脱离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则无法理解。”而你若是去想象,就开始在打虚构的擦边球了。小说的最后一页,引用的是罗伯特•卡拉素在《卡什亡国考》中的一段话:“近数十载,今人治史,好取毫枝末节,虽渺远无关亦趋之也。史家吞吐之故纸汗牛充栋,及至成书成文,虽誊録书手,问津者亦鲜也,而况学人乎?治史者偶可诉诸动机,自我欺哄耳。学者涉于文献之海,自觉拨云见日,去伪见真。或饰其文以数字、图表,自诩科学。然史之辙迹,皆无声之谜。史料搜罗日众,则此理益昭昭也。逝者如斯,曩昔之生灵运命,沉寂无边,自成一体,与前无涉,与后无干,非名号、公证、文书之考订所能涵括也。”
然后这个女子却要放逐自己到中世纪,我们跟着一道放逐,哲学家阿诺也跟着研究起中世纪的音乐来。这小说提到的中世纪圣歌,或是冯•宾根所作的曲子都很好听。可是今人的演绎,又有多少还是原貌?
历史和现实纠结,故去的亲人和自己的生命交错。亡灵和过去成了生命的场,在我们每个人的周围。过去看不见,琐碎,有些正在发生之中就开始被人遗忘,历史学家不会去关注,它们却形成了我们的生命,影响着我们各式各样的决策。科幻小说中常言“回到未来”,而这部小说,则是让我们迈入过去,因过去写就了我们的现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也写道:“于是我们划着船,继续向前,逆流而上,船毫不停歇地倒退着,迈向过去。”
小说中记载了两个历史,一个是史家笔下的历史,它们是大事、大人物,另外一部历史是“无名”的历史,无数发生过的琐屑,它们构成了人类的历史传承,虽然它们一直在流逝,甚至还在发生的时候就被人遗忘。沉默寡言的摄影师一边记载着柏林墙倒塌这样的重大事件,一边自己在捕捉自己的“无名”历史:它们是脚印,雪地,倒影,形形色色的声音…历史学生奥瑞恩吉的研究则和他的捕捉形成一种有趣的回应。如果说阿瑟在捕捉、挽留当下的历史,奥瑞恩吉则在回溯历史,试图捕捉历史中的“当下”。二人奇特的交往就如同一首曲子,两个主题往来交错,韵味无穷。
坏小说如可乐,爽快而不健康。好小说如陈年佳酿,入口回味不尽。这小说情节并不曲折,甚至有时候显得沉闷,但是故事却很有嚼头,情节所串起来的那些思考最为精彩。这部小说被评论者称为“思想小说”(a novel of ideas)。故事的每个枝节都被作者用来连缀自己的思绪的片段。我最喜欢看的是阿瑟的狐朋狗友在酒馆里的胡侃,或是阿瑟自己柏林雪地漫步时的遐想。这些聊天和遐想无所不及。《卫报》说诺特博姆在艺术、哲学、语义学和纯粹咬文嚼字的胡说八道都驾轻就熟。澳大利亚《世纪报》(The Age) 则说读者最好带一本百科全书来看此书。从奥德修斯的远航,到尼采抱着驴子哭泣;从冯宾根的音乐,到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画作,作者的思路四通八达。诺特博姆自由穿梭于欧洲的各国文化,以至于阿瑟和女博士的恋爱,反成了冰糖葫芦中间的那根棍子。
有时候这个棍子还不够用,不足以串起他的思绪,故而诺特博姆还用了几个章节的画外音、插入语。在这几个章节,作家直接叙述他所看到的故事,直接开始讲述自己的思想。这样的颇具实验色彩的夹叙夹议算是怎么回事呢?作者没有明说这些章节的叙述者是谁,是观察一切的亡灵,还是作家自己?看过电影《柏林苍穹下》(Wings of Desire) 的朋友们一定都对柏林上空的天使们印象深刻。这些天使们可以看见所有的人间行为,他们知道一切,但是他们并不干预。这本小说穿插的几个章节就如同这部电影里天使的视角,也可以说作家把希腊戏剧里合唱队的做法嫁接到小说上的大胆尝试。通过小说中阿瑟的例子,我们似乎也能看出作者是要直接进入作品,却又试图不留痕迹。阿瑟在亚特拉斯山脉南部一骆驼集市上所拍镜头中,曾经留下自己的阴影,而本人不出现在画面当中,用阿诺的话来说,这是“上镜而不出镜的一个办法”。不管这样做的是作者本人,还是其笔下的人物,这种作者和作品的有趣互动,都让人寻思良久。如阿瑟自己所想的那样,他倒不是想抢自己作品的镜头,和作品一起不朽。他不过是一个人间万象的收集者,狩猎者,他收藏意象、声音,却又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流失。他甚至想进入其中与其一起消逝。
诺特博姆小说的文字有时充满诗意,有时则有浓厚思辩色彩。作家带着我们在欧洲思想的沟壑和山峦之间奔走。《万灵节》中的诺特博姆是一个具有大欧洲情怀的欧洲人,他对德国、西班牙文化的了解恐怕不亚于德国和西班牙人自己。他也时刻在思考德国人的忏悔、忧郁和严谨、荷兰人的敞亮、透明与狡诈的来龙去脉。他眼中的欧洲有时候是一个地形上的整体,“柏林总让他觉得他是站在一个大平原的中央,而这平原一直蔓延到俄罗斯腹地。柏林、华沙、莫斯科,这些都是途中的小站而已。”可是这个整体确实蕴含着诸多不和谐的声音。“身为外国人,你甚至都不能提‘民主’二字,否则从未参与过杀戮的年轻一辈会警告你不要低估他们的国家,现在不要,将来也不要。他们会把最近的恐怖事件说给你听:纵火;某个安哥拉人被人从东德火车上抛下来;某个人拒绝说‘向希特勒致敬!’结果差点被光头党打死。如果你说这些袭击实在可怕,实在要去谴责,但是也发生在法国、英国、瑞典。”
诺特博姆也在思考柏林墙的倒塌对德国,对欧洲究竟意味着什么。东德和西德表面上是统一了,然而精神上未必统一。当初统一时种植的热情,最后长成了法尔克广场那样歪歪斜斜不成材的小树。“你可以把柏林墙拆掉,但是这墙是不会消失的。”西德人对东德人充满敌视、猜疑和鄙视。“你还记得当时那欢天喜地的情景吗?还记得人们在查理检查站发香蕉的情景吗?欢迎东部来的弟兄姐妹?你听过他们最近的谈话没有?老是讲他们穿得如何如何,他们言谈举止如何如何。同样肤色,内里却有这些种族歧视的话语。老是在说他们什么什么不能做,或者是他们如何好吃懒做。‘战后连我们都没钱去马洛卡这些地方度假,他们倒好,成群结队地去。’‘这些人中间一半人向国安局出卖另外一半同胞,现在倒好,我们和他们所有这些人困在一起了。’‘要是照我的意思,柏林墙还是不要拆的。’‘不能就这样把两个国家捆到一起来,四十年的历史不能说没就没的,他们和我们不一样。’诸如此类,一个接着一个说法。” 而东德人“觉得自己被人忽悠了,”而两边的人都是“对统一简直一点都不懂。整个国家像装在盘子上一样端给了他们,他们却不知如何下手。”这样深深的隔阂也如一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日渐整合的欧洲之上。统一之后,一样是背负着各自的历史,一样心怀猜疑,一样相互回避,想来阿瑟与女博士的爱情,又何尝不是东西德统一,甚至整个欧洲走向共同体的一个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