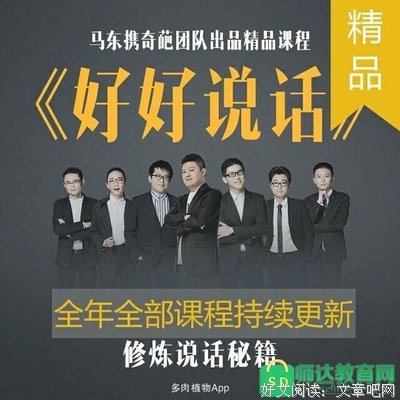《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读后感1000字
《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是一本由程美宝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80,页数:36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精选点评:
●也算看过吧,虽然在书店一瞥后,该书从此消失
●不错的地方文化史范例研究。材料和观点的新鲜度刚刚好。
●区域史至少有两种含义:制造并得到认同的历史叙述,建构这种叙述的更宏观/基层的历史过程/背景。
●不错!
●本書通過思想文化與學術成就、民系與族群、民間民俗等面向,闡述「廣東文化」自晚清到20世紀40年代之間的形成與變遷過程。透過本案例討論,希望對近現代中國地方文化觀念形成提供研究框架。「廣東文化」在此並非是一個既成或固定的概念,作者感興趣的是誰有資源和權力,為何,如何塑造與展示「廣東文化」,並形成相關的自我認同觀念。同時,地域文化、國家(中央)以及文人之間的關係也被討論。作者的重要結論是,「廣東與國家的政權和文化距離越遠,廣東的政客和文人越積極論證他們的地方文化與國家文化有著同根同源的關係,這種悖論長期貫穿了中國歷史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頁39)
●精彩,写法值得借鉴,不愧是牛津的博士
●电子版的都看完了,订购的实体书还没送到。。。。。
●看哭了。。。
●近代知识分子建构的地方文化毋宁说是在广东的中国文化,革命者借粤语构造新的国家观念,但在新的国家里却没有粤语继续发展壮大的空间。当然此书基本关注精英对文化的建构过程,下层民众的排外情绪(尤其是党治国家时期)也是一个蛮值得研究的话题
●广东人标榜国家,认同地方,越是广东的,越要证明它是中国的。
《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读后感(一):重新认识广东文化
夏日某夜,师友数人畅谈广东,言岭南一向有自己的个性,外加“山高皇帝远”,历来是国家权力难以触及之地。今日普通话与粤语的冲突,即是此看法的明证。
在旧的印象里,广东这一区域常常摇摆在国家大一统的边缘,更进一步讲——广东文化的特殊,意味着广东与中央的分离。
程美宝老师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恰恰是对这种印象的打破。
此书告诉我们,广东人在形成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时,往往借助于论证自身文化与正统的中原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无论是粤人之于中原人,或是粤语之于古音,皆是如此。历代广东人对地域文化的理解,非但不是立足于国家认同的对立面,反而从未脱离过国家一统的宏大背景。
认识到这一点,对广东文化的传统认知将有全新的改变。
以上,是阅读本书的最大收获。
(不得不说,程老师的文字浅白、舒服,读她的书就像听她讲课一般。
《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读后感(二):抓住时间、文化、人物、文本
抓住时间、文化、人物、文本
——读《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
本书确实是一本好书,对晚清到民国的历史信息包含非常丰富,非常详实。此书信息量非常大,阅读时可能抓住以下几条线索,读起来会省力些:
第一条是时间线索。此书展现的是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四十年代的发生在广东地方文化的历史。作者把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时19世纪20世纪至19世纪末,第二阶段是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第三阶段是民国时期。
全书共七章,第一章是导论,第七章是余论,主体内容在第二章至第六章,其中第五章由民俗到民族和第六章旧人新志是讲第三阶段的历史,第四章追溯岭学,分为学海堂内、学海堂外、学海堂后,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二、三阶段。第三章书写粤语,是讲粤语作为广东方言,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在各种民间文献文本和正统文本中是如何表现的,粤语在第二阶段作为革命的工具,成为受知识分子欢迎的语言,成为革命与否的标志。当革命一旦成功,知识分子又追求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追求与国家的联系,重归统一,从而追求白话与国语的统一。第二章讲述的是作为广东这个地域里的不同民族,他们是如何与国家与中央取得联系的。
第二条是文化的线索。作者认为三个阶段的广东文化随中央文化或说国家文化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第一阶段的士大夫阶层关心的文化是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否得到“教化”,这些教化的指标是学校的兴办、科举功名的兴盛、地方文人的诗词歌赋以及经学研究成就等等;第二阶段是在西学渐进的大背景下,柔和中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上述指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种族、血统等指标,是否属于汉种,成为“教化与否”之外,另一个定义读书人所认同的重要条件。而废除;第三个阶段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感觉“在西方找不着中国,他们也不愿意在旧中国里找回中国,为了建构一种新的国家意识,他们到群众中去。”,于是民俗学兴趣。文化这条线索体现的最为充分的是作者在描述岭学源流时,所展现的学海堂的历史,学海堂之内是第一阶段的文化,学海堂之外展现的是第二阶段的文化,学海堂之后展现的是民国时间的文化,学海堂的那些晚清遗民。由此又牵涉到第三条线索。
第三条是以人物为线索。书中比较详细的介绍了不同阶段的不同代表人物,有学术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不同领域、不同阶段的代表人。就学术领域来说,第一阶段有陈沣、朱次琦等人,第二阶段的容闳等人,第三阶段有温肃、陈伯陶、顾颉刚、罗香林等人。政治的,阮元、林则徐。
第四条是文本或文献类型的线索。从精英的到民间的,从经典的到俗众的,有方志、族谱、小说、民间故事、粤剧、歌谣、乡土教科书、粤语、报纸、新小说、宗教科仪书、口述故事、学术刊物。在第一阶段,民间文献里都是充斥着经典文献是所表述的地方如何的向中央靠笼看齐,如何向化中央,如何将地方秩序整合到王朝秩序之中;在第二阶段,民间文献比较活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革命了工具;在第三阶段,当革命成功后,读书人希望在中央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所以他们不停得向中央靠拢,于是代表地方特色的民间文献又屈居次要位置。
《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读后感(三):筆記
- 這本書出於2006年,當年我正於廣州工作,於學而優購得此書,當時讀來甚為費勁,好像沒有完成就把書擱下,及後輾轉送了出去。到過了幾年後想找來一讀時,竟遍尋不獲,透過二手書店的老板去找也找不到,讓人好生惋惜。
- 沒想到後來因緣巧合下,有機會與作者程教授於香港見面,更獲得她贈書一本,實在是太太幸運。話說回來,此書去年也於香港出版了繁體版,惟當時已收到程老師的贈書,故沒有再花費購入繁體版。印象中繁體版中程老師作了新序,序言中流露出些遺憾或甚麼的,大概是作為對在中山大學或國內游走的十幾年的一些回顧或懷緬吧。
- 這本書是根據程老師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主要觀點想來成於2000年以前。程老師在贈書時表示對書中有些內容/觀點不很滿意,這樣的說法對我這種沒有學術訓練的小粉絲來說自然是太過客套,但放在程老師的研究生涯中大概也能理解為何會有這樣的看法。
- 十多年前讀此書時覺得有些難讀,今次則相對容易,這或許與自己對部份議題已有所接觸有關。比如關粵語書寫有李婉薇的《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關於明清華南社會則有所謂「華南研究」的相關著作等。程老師在書中後記也提到,本書當年得到科大衛、蕭鳳霞、劉志華等一眾學者的支持。不過在後來的閱讀中,包括科大衛的書中也有引用程老師本書,當年這份博士論文應該還是去到一定高度了。
- 作者一個重要的論點,其實是談到在清末民初的「廣東文化」現像當中,地域認同與國家意識間並沒有截然而分,反而是緊密結合在一起。這與'文化'本身如何被記錄,即話語、書寫、語言體系都掌握於士大夫階層有關。
- 而正正是因為士大夫(或及後的'知識份子)的知識框架,有很強的'國家意識'或'天下意識',然後廣東的那種'中原'故事則也是普遍流傳,不管是氏族杜撰出來的家譜,還是廣府人、客家人對'中原'來源的執著,還是關於'粵音'的中古來原等,在在都反映了這種'天下'觀、以中原為正宗的文化取向。
- 關於這種文化取向,值得一提的是清末後廣東的一些'遺老們'於香港留下了他們的足跡,比如賴際熙等曾執教於皇仁書院、香港大學,他們更把廣東的重要學院學海堂移師至香港舉辦學海書樓。究竟這些舉動於香港建構了怎樣的想像、如何影響及後的香港社會,或者值得深究。
- 讀到客家認的群體在民國期間與廣府人的爭論時,也是上溯種族、中原的來歷等,也讓我想起於陳雲的論述中經常有類似的說法,而陳雲本身也是在香港的客家山村長大。這樣子的'天下/天朝'心態,著實是深埋在我們的文化意識的底層。
- 程老師的這份研究,主要著眼於清末至民初這一時期的廣東,特別是在書本的後期更多聚焦於民國年間的民俗學者(於中山大學)及高要的歷史/誌的書寫。蕭鳳霞的一些研究有與這段年代重叠,而科大衛的研究則要再往上追溯多三五百年。
- 她也提出了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這樣以行程/省別來劃分的'區域文化'的特點及限制,並提醒研究者在日後的'區域研究'中要注意的事宜;這些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應該是重要的提醒吧。
《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读后感(四):家国应如何称呼?
我想任何一个关怀过祖国命运的儿女,任何一个关怀历史中个体命运的儿女,都能明白为什么程美宝在读到《西游记》里那匹白龙马的下场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是白龙马,是陈寅恪,是《SOS,一代宗师垂垂衰竭的史学生命》,是无数的知识分子,是无数被践踏的热心。
我为什么想读这本书,是偶然读到这句“广州是岭南文化的中心,是岭南文化教育的代表”。有点生气,因为中心和代表都是好乏味的宣传用语。
然后我就去找有没有“边缘”得理直气壮、自成一派的文章,看到一个讲座名为企埋一边,朋友解释企埋一边:“通常有人,物standing in your way,配合一句唔该借歪(mead),麻烦让路给我。”我心想,挺合我意的,是我喜欢这个城市的部分:无意跟你争什么高低,什么中心啦边缘啦,市民不是很介意,揾食紧要啦。企埋一边就一边啦,一边都有自己的天地。
但是我看到这本书的开头时,就知道合我意或者合市民意都没用(不是),无数岭南精英千百年来对“企埋一边”耿耿于怀,他们试图找到自己的位置。只不过这个位置的中心总是中华文化,到近代甚至变成了中央政府。
本书的导论讲到一个展览会。1940年被展览出来的广东文化,已经是被挑选过精心策划出来的成果,但回到当时的处境中——广州沦陷一年多,正值民族危急存亡之秋,还有什么比鼓舞民族精神重要呢,重述庐山讲话都要哽咽的我,在当时怕也是看不到广府话撰写的木鱼书。细想又让人叹息:热心筹办展览会的地方精英不就可能是“白马”下场的知识分子吗。
“大抵皆中国种”
在古代,历史叙事体现着士大夫主导的书写传统所表达的天下、国家、地方。这样建立起来的广东地方历史,与其说是“地方”的历史,不如说是“国家”的存在如何在地方上得到体现的历史。
因此,无论是地方志或私人撰述,都在书写蛮荒的广东如何逐渐文明开化的历史。这其中让人无奈的是,广东内部也要为谁是“粤人”、谁是“中国种”而争吵,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皆以不同的方言去建立自己汉人的身份,而“徭、僮、平鬃、狼、黎、歧、蛋族”多被排除在外。
有亡国有亡天下
“清末,国家理论和制度的变化,迫使地方读书人重新定位乡土和国家的关系。”1903-1904年,晚清政府颁布的学堂章程中特别强调教育与国家的关系:借着教授乡土知识,激发学生爱乡爱土之情,鼓励其忠君爱国之心。各地读书人很快响应,编撰了不少乡土教材。
在乡土教材中,无论是土货还是洋货,都能表达为对现代性的追求,都能与爱乡爱国扯上关系。在这“和谐”的合唱中,也有杂音如梁启超的中国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但终究被民族主义的浪潮覆盖过去。
到近代的转变里,有这样的一点:传统的天下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主义,但演化为现代的国家观念时,民族主义取代了文化主义。从天下到国家,人民忘了有亡国有亡天下。“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亡天下是整个民族文化价值的丧失,亡国不过是一个政权的崩溃而已。”
家国应如何称呼?豆瓣看了一下评论,也明白为什么程美宝在开头,要写下:“应”一般很容易被质疑,而“是”——尤其是自以为是的“是”——却往往欠缺自省。
《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读后感(五):书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
该书的副标题为: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如作者在导论中所言“本书从这种地域文化观出发,企图进一步追寻这样一种文化观念如何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建构起来,并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展现。”(p13)作者下面一段话很好地总结了本书的主要内容:
正面地说,本研究企图以“广东文化”为例,尝试把清末以来中国的“地方文化”视为一个命题、一套表达的语言来看,探讨在不同的时代,在怎样的权力互动下,不同的内容如何被选取填进某个“地方文化”的框框。本书一开始便提出,所谓“广东文化”,视乎当时的人怎样去定义,更重要的是,在怎样的历史文化环境里,哪些人有权利和资源去定义。(p40)
在程看来,广东文化甚至很多中国的地域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体现。本书围绕三个主题展开:一是思想与学术成就;二是以中原汉人血统认同为归依的族群划分;三是民间民俗。
从思想与学术成就角度看,学术组织学海堂对广东学术传统有着深远影响,广东近代的学术名人基本上都和学海堂有联系,而清末明初的经学论著、地方志、文集、儒林列传等基本上都出自学海堂。加之,学海堂的弟子在广东的教育和文化机构中也占据了一定的位置,由此学海堂掌握了定义“广东文化”的权力和资源。如此一来,全国性的文化主流便借着学海堂的建立而在广东这偏隅之地得到巩固和发扬,并且掌握教育资源的地方读书人可以根据教育机制的变化不断调适和营造自己的生存空间。
从族群划分来角度看,如何界定“粤人”就显得非常关键。随着明代广府士大夫势力的上升,他们主动与国家意识形态和王朝政策配合,认为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只是“内化”程度的差异,而非种族的差异。通过建立起一套有关广东“内化”过程的历史叙述,“粤”或“粤人”的定义脱离了古代“百越”所含的蛮夷之意。由于掌握了话语权,广府人便将自己同潮州、客家、瑶、疍、狼、壮等人区别开来,认为自己是“中国种”或“汉种”,建构出“北人南移说”和“中原教化论”以证明自己具有正宗的汉族血统和文化渊源。
从民间民俗角度看,民国初年中国掀起了一股民俗学研究热潮,民俗学研究是为了求真,更是为了建造新中国文化寻求出路,正如顾颉刚所言“研究旧文化,创造新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去被鄙视为遗风陋俗的岭南婚姻、丧葬、节令、饮食等习俗逐步提升为“广东文化,尤其是方言文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地方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粤语实现从南蛮之音到中原古音、从口述传统到书写传统的转变。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作者认为所谓的“广东文化”只是以行政界限划分的一个范畴,至于里面填塞了什么内容,除了顺应国家文化定义的改变而更替外,也是在这个地狱范畴里人群角力的结果。随着客家人和潮州人的自我认同的意识以及文化资源日增,他们成功地在“广东文化”的框框中微自己认同的文化争取到一个席位,不让广府人专美。
到这里,“广东文化”的形成过程就被作者建构完毕,作者认为在最“地方”的文本中,处处见到“国家”的存在,其研究也是在这样的一种思路的指导下进行的,可以说将这点论述得十分透彻,这也是本书的精彩之处。然而,我以为作者在此书中有意回避或者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一些议题:为什么广府人要积极建立与国家的联系以取得成功?为什么其他族群在争夺话语权时会失败?这些问题涉及到作者所描述的现象背后更为本质的因素,对这写问题的回答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
反观现代社会,社会的集体努力转变为个人的努力,一百多万人考公务员已经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点。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不再,随着现代的“士”都纷纷进城,庶民便被撂在一边了,“士”的撤出造成了国家和庶民之间的极大的空白。接着,造就了一批没有话语权的农民工,他们的处境与那时失去话语权的其他族群又有几分类似,我相信他们终有一天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也相信不会等太久。不过这却有赖于市民社会的发育或“士”的“回归”。
如果说晚清以来的知识分子努力建构的是“广东文化”,现代的知识分子却连地方文化够懒得去建构了,心中却只有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产业的建设,文化的建设变成文化产业的建设,越走越歪! 在当前经济发展是王道的情景下,看看先辈们如何去建构文化,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