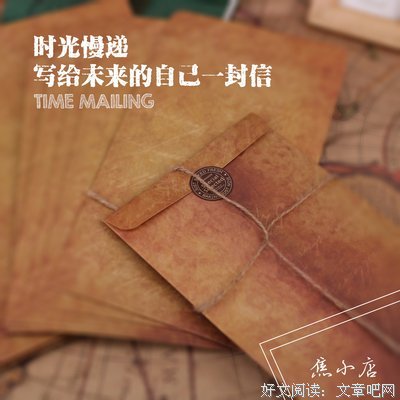《时光慢递》的观后感大全
《时光慢递》是一部由王思涵执导,孙菲 / 汪谷 / 张嘉媛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时光慢递》观后感(一):(强烈剧透!慎点!)一周时间刷完互动视频所有结局的笔记
结局A:没考上北大。上来选D:AC 结局B:平凡的世界。学霸值低,帮忙舞会后不去石舫唱歌。之后各奔前程。顺利保研进国企,生活平淡。 结局C:平行世界的你。保不上研究生 结局C2: 平行世界的你。保研后去国企,生活平淡 结局D:碌碌无为。错过了转专业,自怨自艾后抑郁,但积极走出,毕业后未保研,在各个选择浅尝辄止。 结局E:积郁成疾。错过了转专业,自怨自艾后抑郁,继续自暴自弃。严重抑郁后退学。 结局F:退学。选硬课。一路自暴自弃,挂科不签到。回家打点小卖部。 结局G:路人。成绩较好,与小雪初次会面后避免感情深化,一个人去听鱼米。毕业后去师范学校任职。 结局H:情深缘浅。没有深入发展,但两年后约她一起去听鱼米然后表白了。 结局I: 她的婚礼。转专业成为编剧,发展后感情不够。最后不表白。 结局J: 普通朋友。不去舞会,转专业后与她去听鱼米,但好感度不够。最后不告白。 结局K:未来可期。珠峰旅行后与小雪约饭一路积极发展,最后不表白。一直是最好的朋友。阿哲与沐安的婚礼上再相聚,开放式结局。 结局L: 谢谢你的喜欢。选择“小雪,我有话对你说”此后各自有喜欢的人。 结局M:学术人生。一路学习,北大读博,2022年成为博后。 大结局:时光慢递。表白小雪答应,甜蜜一段之后异地恋后分手。
《时光慢递》观后感(二):从MCPA到梅林的末班车
秋2016年毕业至今已经4年了,上周回了一趟,秋日的园子景色很美,但终究变成了使用太阳卡的校友,如孙欣师姐唱到的那样,一转身就是过往的少年。
最早接触的关于北大的电影作品,是胤祥的《此间的少年》,孙欣师姐的《转身之间》听了很多遍,耳边仿佛又回想起康敏在KTV对乔峰唱《俩俩相忘》时的深情与不舍。
后面真正到了学校,火起来的微电影是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微电影《下一站》、微电影《女生日记》、《男生日记》、《星空日记》,后来接触到北京大学影视创作协会(MCPA),去看了几次创作者见面会,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制片组小作业——《无名》,无疾而终的暗恋仿若在缅怀和解构。
隔壁的看过原创情景喜剧《作邻右舍》、校园系列短剧《爱上图书馆》等。
说回电影本身,在BiLiBiLi推出互动电影终究没赶上最好的时机,尤其是开局两道选择题劝退了很多场外观众,如果能像《隐形守护者》这样包装成为游戏或许还能传播和收益。电影剧本和镜头语言很美,其中看到了此间的少年、女生日记等的印记,也有熟悉的歌曲和回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忆与电影,这与其说是一个电影,不如说是12-17这一批北大人的毕业纪念。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沉默着的少年时光,仿佛还在昨日,未曾绽放就已枯萎的花朵,那些年生里不解与辜负的协奏。祝福大可不必,遗憾只是过往。笔走天涯的梦想,我业也遗忘。枉海阔天空,故人不曾入梦。
回来的时候在·KTV点了一首《青春大概》,只能说也许还有遗憾,甚至很多,但我相信共你,没有白活。
学习《时光慢递》观后感(三):从导演的角度记录这部学生长片的至暗时刻
在这里也把这一年里发生的故事通过文字记录下来,涉及到了这几年从本科到最后进入影视行业的心路历程。我于2018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毕业后选择北漂,承接会议广告等影视制作为主业,利用近一年的北漂时间一个人完成了电影《时光慢递》后期的剪辑,调色,发行等工作;电影于2019年4月和6月分别于北大秋林报告厅和百讲多功能厅举行放映。北漂结束后,申请到Chapman的道奇电影学院电影制作MFA,硕士就读于电影摄影专业。
对于放弃自己的本科专业从事到鱼龙混杂的影视行业,初步涉足了电影制作与发行的领域。现在回头看,这个选择放弃很多也收获很多,利弊难以简单概况,我想用《时光慢递》这部电影里的一句话来概况我做这个选择的原因——
敢去做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选择并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需要更大的勇气《时光慢递》作为一部片长近两小时拍摄取景辗转多地的学生长片电影作品,前后从拍摄到制作完成跨越了近三年,最终影片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发行,发行费用和种种努力付诸东流。或许毕业时选择一条更稳妥的路或者工作就不会有这些至暗时刻,但是生活或许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我们终将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哪怕这条路坎坷难行。这篇文章从某种程度上也是自勉,希望能在这条路上继续坚持走下去,有更多作品。
>>> 我和《时光慢递》的故事 <<<
文/王思涵
(电影《时光慢递》导演、编剧,饰演向海,并参与电影摄影,延时摄影,航拍等;完成电影初步声音处理,后期剪辑调色,电影同名主题曲及片尾曲词曲作者)
2019年8月,我的航班降落在洛杉矶。
走出海关的出口看见等我的李忠泽,一切就像我今年四月来时的模样,连互相抢着推行李的情节都是一样的。我不由再把时间往前回溯,再上一次来洛杉矶是17年的夏末,我去参加南加大电影的暑期课程,具体到达机场的情景我都已经没有了印象,倒是离开的时候我印象颇深,为了拍《末班车》的素材下决心往后改签了机票,走的时候赶紧在机场门口又补了几个镜头,生怕走得匆忙遗漏了要拍的场景。最早一次来洛杉矶是大二结束后休学参加Semester At Sea,第一次来洛杉矶大晚上银行卡取不出钱打车,幸好是飞机上坐旁边的阿姨送我到了住处,临别还给了我一碗热汤圆。
时间轻描淡写地划去了记忆的棱角,只是故事似乎是从这里开始,也似乎在这里结束。我发了一条很长的朋友圈:
飞机降落在洛杉矶机场,有点百感交集。出国这件事之前一直没下定决心,就没有和大家说。如果一切顺利,接下来三年我会在chapman走上学电影的不归路了。印象里自己每次离开北京都很匆忙,这次可能是真的离开这座生活了五年的城市了。2015年12月末从北京飞洛杉矶,前一晚和几个好友在Nova喝得倒头就睡,第二天匆匆收行李就奔机场,那时候很慌张因为觉得不知道接下来漂在海上的一年会发生什么。2018年4月再次飞洛杉矶,一边忙着联系《时光慢递》的首映,一边为了攒发行费倒着时差给甲方改了九个版本的片子,那段时间首映前两天又出了很多插曲和问题,多亏忠泽在身边不然我估计都快崩了。今天再次飞洛杉矶,在起飞前一晚还在和孟轩兄一起对接《时光慢递》的宣发事宜,半夜回到屋子里开始收拾行李。想起这些瞬间,越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虽然一路上遭遇很多碰壁和失望,但是自己一直有机会去追寻想做的事,身边也总有人愿意和我并肩同行,让我有机会去尝试新的可能性。这一年来,因为《时光慢递》自己收获了大学最珍贵的记忆,也因为《时光慢递》,我开始不得不去在现实中学会妥协与放弃,也对电影这件事失去了热情。我一直不会后悔自己做的决定,拍《时光慢递》可能是唯一一次我后悔过的决定,但是我想如果再来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还是会去这样选。每个人都想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但是为那片天空不得不放弃很多东西。向海终究会去美国学电影,小雪终究会拿到理想offer,沐安终究会找到心的归属,阿哲终究会稳健地走向属于自己的未来。我们就是故事里的他们,我们终究会成为我们的样子。希望下一个故事是一个大团圆。”百感交集,回忆上一次到LA的经历,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似乎这是一条想传达要开始新生活的标准朋友圈。只是这一句“我一直不会后悔自己做的决定,拍《时光慢递》可能是唯一一次我后悔过的决定,但是我想如果再来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还是会去这样选”,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这样写。在所有朋友的眼中,这是一部岁月静好的电影,有无数美好的回忆,有很多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似乎——我自己也很以此为骄傲。
然而,事与愿违。
走到机场出口,我停下了脚步。
李忠泽拍了拍我的肩膀,还在等谁呢。
我们俩站在机场出口的人群中,我再次转头看了一眼我来时的方向。
我知道这一切已经回不去了。身后的人群推着我们向前,我想起了电影里的台词,“我们终究是园子里的过客,时间也终究会磨平我们在这里留下的印记。我想如果时间回溯,这一切重新来过。我们又会做怎样的选择,这会不会还是同一个故事呢?”
1. 洛杉矶往事
故事的最开始要从两年前说起。2017年4月,我为学校剧星风采大赛拍摄了开场视频《相逢》,在拍摄过程中认识了黎亚东。他硕士毕业于北大经济系,已经工作了几年。拍摄完剧组散去的那天晚上,亚东说他之后要回成都了,要是我再拍片子就叫他。
《相逢》是一个概念视频,用分屏的形式做了一些创意上的混剪。朋友陈琛看了《相逢》就跟我说,咱们老是给各种活动拍视频,你有没有考虑过拍一部完全没有任何主题限制的,那种你自己想拍的片子。
2017年4月概念宣传视频《相逢》剧组我曾经因为参加游学项目休学过一年,所以在我还得多读一年才毕业的时候,那些我最熟悉的朋友们大多都即将毕业离校了。我马上要搬到新的宿舍,朋友们也都要各奔天涯。于是在2017年夏的毕业季,离别愁绪的感伤甚至胜过了一年后我自己毕业的时候。
氤氲在这种告别的忧伤气氛里,我和陈琛聊了我的构想,我想借助六月去美国洛杉矶南加大参加暑期项目的契机,去拍摄一个发生在洛杉矶和北京两个地方有关毕业季的故事。这样我可以不用什么额外成本,把剧情变成一个跨国拍摄的故事。
陈琛问我故事的内核。
说实话,那时我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故事构想,我能想到的只是一些关键词。我想拍一个介于友情和爱情之间的主题,因为我觉得在毕业季这样的故事并不鲜见。毕业后很多人面临现实的选择,而感情故事在这样的设定下会显得真实而富有戏剧张力。
在我最初的设想中,男女主会是一种暗生情愫但是彼此不去说破的关系,两人的故事因为各自之后要去往不同的未来而戛然而止。我还设计了一个场景,男女主最后的告别会是在一场五月天演唱会上。我查到那年8月五月天正好在北京有演唱会,我立马买了票,天时地利就差人和了。
很多时候剧本其实是创作者情感状态的投射,在那段时间我正陷入一种看不到未来方向的情绪,而身边在乎的朋友则在各奔西东的状态里。这种状态在5月末的十佳现场被放大为一种带有遗憾的伤感。十佳现场上石林唱了一首《鱼米》,其中有一句歌词是“同你背静夜思,睇港片,对未来没打算”。我于是在想毕业季会有多少故事和可能性因为彼此去往不同的方向而无疾而终。
最终我的拍片构想流产了,原因很直接,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预算去做准备。我没有能找到符合我预期的同学能配合我在洛杉矶拍摄。故事始终停留在一个构想的框架里,从来没能变成白纸黑字的剧本。
人们常说,生活给你关上一道门同时就会给你打开一道门。生活给了我一种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可能性,就像我在剧本里构思的——两个多年的老朋友在毕业季尾声面临最后的告别。但是现实比我的剧本还要进行得更加戏剧性一些,剧本里写的是两个人最终没有说破,而生活中两个人决定试一试毕业季前“夕阳红”一次。抱住她的瞬间,在园子里生活那么多年第一次觉得触碰到了如此温柔的记忆。回想大学几年可能大多时候都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回想总是悲伤多于快乐,以至于总是对任何生活里的惊喜和开心太过珍惜,也太过热情和敏感,太害怕失去。不得不承认,我在写的这个剧本映射的其实是当下的心理状态。女孩说,那句“同你背静夜思,睇港片,对未来没打算”就像我们自身的写照,大家都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
这段感情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我曾经以为看五月天演唱会成为现实里的桥段,但最后还是只能放在剧本中。我们分手的时候我正在USC暑期学校上课,于是整个七月我都像一个工作狂一样,把所有精力放在课程上,只有这样自己才没有伤心的时间。7月下旬我在洛杉矶的项目快要结束了,我将要回国。USC电影学院的电影棚里,教授宣布项目结束了,并说希望将来还能在这里见到大家。
或许在感情上失去了,就不希望在梦想上也失望。我那个时候想去洛杉矶学电影的愿望简直到了痴狂的程度。从USC的校园门口出来,走过这两个月里已经熟识的街道,耳机里恰好放到了五月天的《知足》。我忍不住开始想我还会再来到这里吗,我们在毕业季时所担心的未来到底是什么。站在异国的街道上,人来人往,我脑中飞速掠过了这两个月里,那些我用繁忙的安排来试图掩盖住情绪的那些美好和悲伤的故事闪回。我说不清楚里面是不是藏着对未来的担忧,或者是对过往的某些遗憾,分不清楚是友情更多一些还是喜欢更多一些。
我发消息给好友李忠泽说,我打算把回国的机票改签了,我真的想拍点什么。我找到USC暑期项目认识的几个朋友,请求他们帮助我拍一个故事,尽管我没有完整的剧本。时间已经来不及让我构思一个完整的框架了,我必须在还有人能够帮我的几天里尽量多拍一些素材。
我把这个剧本取名为《末班车》。这个概念来源于我旅行中的一次经历。休学那年在英国旅行,英弗尼斯北部有一座很孤单的城堡,因为坐落在延伸出的遥远海岸线上,很少有游客到访。我背着吉他乘公交车来到城堡,一直待到天色黑下来。我不知道怎么回去,距离最近的镇子还蛮远的,吉他背起来也不轻。这时一个好心的阿姨搭了我一段顺风车,她问你知道那是最后一班车吗。我说,我知道啊,但是呢我还是想来,因为明天我就要离开英弗尼斯了。那时候就觉得人生很多事情也是这样吧,在命运和时间都推着我们走向别处的时候,一鼓起勇气还是跑回车站坐上了那趟末班车,前往你向往很久的地方。
就像我最初写的剧本里因为彼此是最好的朋友,如果说破了可能就很难再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了。加上已经知道彼此即将异地,与其失去最好的朋友,不如就一直以朋友之名相处。而“末班车”的想法,则会给人一种未知,在时间和命运的推动下,鼓起勇气不顾结果地去尝试那种未知。既然我们都不可预知未来,又何必去为不可预知的事情而不去勇敢尝试呢。
于是我怀着一个脑中并不清晰的故事框架就开始了拍摄。一方面没有预算和拍摄团队,另外一方面我也没有几天能在洛杉矶拍摄,最大的困境是我没有合适的男演员,我于是决定自己先去演留住素材再说。后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想到在片里当演员,原因再简单不过了,因为实在找不到人只能自己上。我甚至让偶遇的路人拿着摄影机拍我过马路的场景。好在朋友们无私地给了很多帮助,几个小伙伴早上五点就起来去拍尔湾的海滩,倪雯琴陪我几天早出晚归一起搭戏,她演剧中的角色北北。这次临时召集的拍摄本身就像极了“末班车”,虽然没有能够完成一部完整的电影,但是为后来《时光慢递》能够实现埋下了伏笔。
2018年和几个伙伴在洛杉矶拍摄《末班车》2018年和几个伙伴在洛杉矶拍摄《末班车》2018年末制作的《末班车》海报2018年8月回国后,我和孙菲、沈桥、李尧去鸟巢拍摄了五月天演唱会的那场戏。孙菲演剧本里的小雪这个角色,沈桥和李尧做摄影。那天李宗盛也来了,他唱了一首《山丘》。全场白色的荧光棒轻轻挥舞,阿信唱了《知足》。这些贯穿在洛杉矶和北京,交织在现实和剧本里的故事连结在了一起。我在想,要是真的剧中的男孩和女孩在这样的场景下看着眼前挥动的一片荧光海,台上是他们最喜欢的歌手,唱着他们的青春。要是你真的真的喜欢身边那个人,在这样的场景里,你怎么可能不去告诉她呢!我于是告诉饰演剧中小雪的孙菲,我们加一个戏吧。于是才有了后来《时光慢递》里在演唱会上向海对小雪说出了那句埋藏多年的话那场戏。
后来演唱会散场,我仔细回想刚刚加上的那场戏是不是违背了我最初想表达的故事。突然想通了一件事,人生中很多时候没有所谓的最优选择。不去说破终将遗憾,但是真的在一起又得面对太多现实的问题。很多故事看似给了我们选择,但是主人公并不知道,其实不论他怎么选择,可能都不是想要的结果。但是不去尝试你又怎么知道呢,遗憾才是最让人难过的事情吧。
生活才是最高明的编剧,你以为最初的故事是这样的,但你真的身处其中,其实我们都会比自己想象的要勇敢。
2. 《时光慢递》的雏形
整个2017年的年末我都在忙着给学校拍延时摄影,延时摄影没拍多少,倒是因为这个契机认识了惠之。整个10月实在太忙,赶在10月末国外申请电影学院的最后几天DDL匆忙结束了申请季。在给学校投递申请的时候,想起了几个月前在美国的匆忙拍摄,于是又重新看了当时《末班车》拍摄的素材,只觉得问题太多完全剪不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2017年要结束的时候,惠之要去爱丁堡大学交换。临走的前几天我问惠之,“喜不喜欢,爱不爱,合不合适,在不在一起,住不住一块,有没有名分,过得过不下去,是七件事。要不要试试看咱们能走到哪一步。”
后来惠之说起这件事,她埋怨我说话总喜欢绕来绕去,那天晚上一开始她以为是因为马上异地,我发的是一封诀别信。
18年初,她乘上了飞往爱丁堡。我们处于刚确认在一起就异地的状态,我自己则处在一直等待offer的焦虑之中,没有心思构思新的剧本。2018年2月的时候学校找到我,表示看过我之前的一些校园作品,愿意扶持拍摄一些文艺原创作品。我于是连夜做了策划,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有一种强烈的表达欲,这个故事无论如何我都会去拍,有了学校的支持我就可以拍的更丰富了。北大教育基金会不仅在资金上提供了支持,还给我提供了很多北大校内场地的使用许可。因为自己参与百廿校庆的延时拍摄,北大电视台也给了很多支持帮助,让我有机会参与到很多和北大有关的大型活动拍摄中来进行取景。于是在拥有这些珍贵的资源和支持后,我决定把这个故事拍得更全面一些,不再限于向海小雪两个人之间的故事,我更希望它是一个全面立体的群像故事。
于是在2018年3月我开始重新改写剧本《末班车》。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三天没有出门,终于到第三天晚上,我把剧本初稿写了出来。这个时间点也有些奇妙,那天正好是我的好友李忠泽收到了美国Chapman电影学院的offer,他说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抱着身边学校黑人小哥保安哭。我太能理解他的心情了,我的剧本里向海最终去了USC,也是自己的一个愿望,我真的很希望能去学电影。我要是收到offer估计我也一样吧,我看了看邮箱依旧是一片寂静,但是我自己没有时间去焦虑这些了,为了在三月下旬开机,我需要尽快把剧组建起来。
我问李忠泽,我拍片了,你能来帮我么。
李忠泽说,老铁我肯定帮。他说处理完美国的事情立马飞回来,不过赶不上我们的开机日期,估计会迟几天参与进来。
我先是去询问了一些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虽然学校有资金的支持,我自己也愿意出钱,但是因为电影剧本太长,我的预算基本没有可能支付他们的酬劳,我手头资金只够付个零头。
另外拍摄周期也不短,即使从身边找同学帮忙,平时同学们也要上课,大家基本不太可能抽很长的时间出来。尤其是北大的同学平日里大多都有自己的安排,找同学跟组拍一个月是不太现实的事情。于是我开始寻求朋友们的帮助。
我想起去年和我一起拍《相逢》的黎亚东。亚东师兄知道了,二话不说立刻从成都坐火车赶到北京。我告诉亚东,这个片子可能得拍二十天,实际上后来这个片子杀青的时候已经是四月下旬,总共拍摄了四十多天。
梁元瀚是我参加“北台云大学生服务计划”认识的台大哥们儿,他知道了立刻从台北飞了过来。我的高中死党钱以骞也从云南赶了过来。惠之更是从英国爱丁堡回到北京帮我筹备,被忠泽戏称为“导演夫人”。
就这样我跟学校申请了一间拍摄使用的宿舍,在42楼117室,大家从世界各地赶过来聚在这里。我觉得这件事情给了我太多勇气和动力,我不觉得人生里还会再遇到这样一次,有这么多朋友不计代价不求任何回报地来跟着你干一个多月,一起拍一部电影。也是因为有这样一帮人的倾力相助,我们才能用不到十万的预算拍摄了一部两个小时片长的电影。因为预算非常紧张,大家的机票和火车票至今都没有报销。
《时光慢递》第一场拍摄合影新剧本《时光慢递》名称的灵感来源于我大二的时候一次任性出走。大二时我曾有一段时间心情非常糟糕,于是自己买了一张去拉萨的火车票。那段时间我脱离了学校的生活圈,看到了生活在不同地方,和我有着不同信仰,生活方式千差万别的人们。也是这次说走就走西藏的际遇,间接让我后来决定休学去航海。在西藏拉萨的一家书店里,我给一年后的自己寄了一封“时光慢递”。
一年后我完成Semester At Sea的环球航行回到学校,打开宿舍信箱,看到了一年前寄给自己的信。虽然给自己写下的话更像是一种暗示和愿望,但是在一年前我根本不会想到自己在拉萨书店写下时光慢递,一年后我会下定决心休学去坐上一艘船绕着世界环行了两万多海里。感慨这些心路历程的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着太多选择和机会,我们很难预料到自己一年后,三年后,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过着怎样一种生活。于是“时光慢递”这个概念成为电影的核心线索,它代表着一种我们自己对未来可能性的希望。把这样一个主题放在我们的大学生活里显得非常现实而戏剧性。用李忠泽的总结就是,比起那些只限于校园内的故事的青春片,他认为这部片子更应和我们这个时代,校园生活已经变了,那么多人出国交换,那么多人早作打算,并且这样的现象已经不只局限于清北两校。在现在这个背景下,剧中的几个人物,他们在这个背景下的四年是怎样的,这个故事将会非常真实。
在拍摄前调查身边同学三年后的愿望是什么,很多朋友就给我发了过来。收到的结果很有意思,还没毕业的同学愿望大多数是比较抽象的,类似“我希望我能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希望我是一个开心幸福的人”。而毕业的同学朋友写的大多数都比较具体,“我希望我结婚了”,“想要有猫”或者是“能买一套房”。
新的剧本删去了之前《末班车》里的很多设定和情节,甚至直接把北北这个人物从洛杉矶和北京这条故事线里删去了。保留在《时光慢递》正片中的素材大概只占了《末班车》拍摄总素材的5%,也就是后来正片中向海在美国的情节。《时光慢递》成为了一个新的故事,片中四个主人公向海、小雪、阿哲、沐安,故事从他们初入燕园一直讲到毕业多年后。结合之前拍摄的《末班车》素材,孙菲饰演小雪,而我继续出演向海。虽然我一直觉得自己笨拙的尬演会给电影减分,但是很多纪录片式的素材都可以不花任何额外的预算就直接在电影里呈现,这让电影拥有了很长的时间跨度。电影里最早的素材是2013年拍摄的,我在学五CBD和好友毅鹏吃烧烤聊转系的桥段。这在很多经历校园里多次拆迁学五CBD不复存在的校友来看,可以说是电影中一个亲切的彩蛋。阿哲和沐安的表演者是我之前就熟识的朋友,电影甚至没有经过选角。我们就是去全家便利店一起喝了奶茶,我问嘉媛(沐安饰演者)和汪谷(阿哲饰演者),我有个片要拍很久你们有空演吗。在拍摄沐安和阿哲的时候,我继续采用了半纪录片半剧情式的拍法,把嘉媛参加舞团三十周年演出拍摄下来,作为电影里沐安参加演出的片段。
3. 《时光慢递》的拍摄
三月末和四月初,北大校园里多了一群驾驶着电三轮扛着摄影机早出晚归的少年们。刚开始开拍的几天可以说是意外不断,因为大家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出现了不少失误操作甚至是返工。
为了体现真实感,并且解决我们找不到群演的困难,我决定使用一种特殊方式——现场拍摄。于是我们在百团大战当天去拍摄剧本里百团大战的场景,在舞团专场拍摄舞台跳舞的沐安,我们为了拍摄在十佳初赛演唱的场景,真的去报名了十佳演唱了歌曲。有意思的是当时差两分就晋级十佳复赛了,要是真的进了复赛剧本也可以跟着改了。
整个电影里除了舞会是我们自己模拟出来的大场景,其他大场景都是现场式的。这样的拍摄是没有任何容错率的,基本上拍到什么就是什么,没有重来的机会。
拍摄时三月末天气还未转暖,有时候大家穿着春夏装在寒风里瑟瑟发抖。在小西门小雪和向海的表白戏中,李忠泽发现孙菲饰演的小雪眼角有泪光,大家开玩笑八成是被冻哭的。拍石舫四人弹琴唱歌的夜戏,半夜里寒风料峭,拍完这场第二天演员就重感冒了。
Ethan和胡子阅是李忠泽在加州交换时认识的小伙伴,他们刚刚高中毕业但摄影技术不可小觑。他们在三月末加入拍摄,使得拍摄得以高效率的进行。得益于在百廿校庆活动,在与学校沟通拍摄场地时,图书馆、化学实验室、办公室都给我们开了绿灯,甚至我们还在博雅塔上完成了一段空前绝后的拍摄。我想这个片子播出,一定会有很多人说出和电影里一模一样的台词“原来博雅塔还可以上来啊”。
我们白天基本上拍摄一整天,晚上几位主创聚在117宿舍里讨论剧情。基本上大家轮流休息,总有人在醒着讨论。我不知道其他人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中是怎样的体验,我自己拍摄结束时只有110斤,后来剪辑又瘦了几斤。因为在117这个地方干了这么多疯狂的事情,以至于大家都对这个地方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离开宿舍的那天还有些不舍。
四月中旬以后,因为电影已经超出当时预想的结束时间太长,很多人都有其他安排,不得不买回程票离开了。甚至在后面几场里,我已经找不到可以来帮忙的摄影师。往常都是我自己摄影,但是很多场我要在其中演出,所以常常是我演完马上转换角色变成摄影师。在出租车戏中,由于实在没有摄影,孙菲自己都拿起相机充当一个摄影副机位来拍摄。
《时光慢递》拍摄花絮照惠之回英国本计划四月中就走,但因为拍摄延误了,她正在考虑要不要改签机票。她说投一枚硬币吧,正面走反面不走。在机场她投了硬币,我问她是正面还是反面,她说她不想看。投硬币可能不是为了知道是正面还是反面,而是想知道更希望是正面还是反面。她说,她决定留下来陪我一起拍完。我说现在可以看硬币了吧,我们打开手指,硬币是正面。
舞会场是我们最后一场杀青戏。杀青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大家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庆祝,轰轰烈烈地拍片就这样结束了。
《时光慢递》最后一场拍摄合影结束的时候忠泽和我聊天,我说真的太感谢他了,没有他这个片子拍不了。
忠泽说别整那些没用的,这次千万不要再辜负大家了。你还记得你当时出去航海的时候,我们都给你众筹了,但是你现在书都没写好。你知道大家为什么会这样来支持你,是因为你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大家在你身上看到了一种追求梦想的样子,你做的事情也许也是别人的梦想,千万不要辜负了。
回去的路上我告诉忠泽,我不久前收到了USC的拒信,我去不了美国了。电影里向海收到了USC的offer,我收到拒信的时候就在拍摄现场,我自己坐在地上平静了五分钟,然后继续拍摄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忠泽说,我马上要去Chapman念书了,你明年接着申请吧,我和Ethan在洛杉矶等你。
站在学校的小西门门口看忠泽开车离开,我竟然有些不知所措,原本以为我会出国念电影,现在突然不知道我应该去做什么。回到117宿舍收拾器材道具,一切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梦,这个故事从我从去年在加州开始,一直到此刻电影杀青身边的伙伴们都各自离开。这一切就像大梦一场。
2018年5月我开始剪辑电影,同时还得准备大学阶段的最后一个期末考试季。2018年7月7日学院毕业典礼,有一个走红毯的环节。学院在收集信息,类似每个人走红毯时,主持人会念到毕业去向和所获奖项各种title等等。我想了想,只写了两个字。于是那天走红毯的时候,前面的同学走过,主持人念出种种获奖履历和听起来很厉害的毕业去向。到我的时候,就听到学院的副院长宣读毕业去向,他似乎有些迟疑,但是还是念出了:王思涵,毕业去向——北漂。惠之和我一起走的红毯,她当场就笑炸了。谁又会想到如今忆起这个场景莫名鼻酸。
4. 你看这块硬盘,青春啊
整个电影我断断续续剪辑了好多个月。时间过去这么久我已经忘了是什么感受,只是记得剪辑的那些日子我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就觉得太阳落下又升起,累了就睡一下,睁开眼窗外下着让城市倾倒的大雨,剪完一小段再抬头,天蒙蒙亮或许晨曦里还残留些雨后的味道。如果说前期和朋友一起拍摄是体力和精力上的透支,那么剪辑除此之外还是一种孤独感的积累。就像是二十平米不到的公寓里,你和整个世界失去了联系,一切都与我无关,我只是专心地做剪辑。那时我翻了一下自己的聊天记录,和惠之了最多的词不是“晚安”也不是“哈哈哈哈”,而是“剪片”。做剪辑的三个月其实现在想想是很幸福的,也很纯粹,颇像极了多年前的高考,
——为了一个确定的目标而努力,而每一次努力后的进展都能够清晰地感知到。这比后来在《时光慢递》上花费精力却毫无收获的发行推广和后文会提到各种其他奇怪的事情相比,简直是最欢乐的时光。
很幸运的是我收养了一只流浪猫取名为栗子,栗子猫的陪伴对抗着这种漫长剪辑过程中的孤独。文件夹里粗剪的文件不断增多,栗子也从一个巴掌大小的小猫长成了一只大橘。2018年8月末的时候,我决定前往西藏补拍。之前这部分本来是剧本里比较重要的桥段,是剧情里少有的向海solo桥段,比较能突出向海的人物性格。之前李忠泽建议删去,因为这段要拍摄的话工程量实在太大了。但是在做完粗剪后,我总觉得故事差了一环,前后衔接有些突兀。
于是我决定前往西藏补拍这一段,事实上整个剧组就去了两个人。我的高中学弟吴照坤和我,我们坐着高铁前往拉萨。我们两个人完成了整个西藏部分的拍摄。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珠峰大本营的时候,在帐篷里临时拉来几个游客当群演。他们内部好像是因为车费问题在吵架,于是我们拍摄的时候,他们吵了起来。吵累了我们接着拍,拍累了他们接着吵。如今想想,萍水相逢一场,很感谢这些路上不认识的朋友,因为拍摄匆忙也没来得及留下他们的名字。拍完帐篷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在海拔五千多米空气稀薄的珠峰大本营,有两个人在帐篷外冻得瑟瑟发抖。我和吴照坤拍了一阵子延时,后来因为身体疲惫感觉有点呼吸困难回到了帐篷里躺下。我当时又庆幸又失望,一方面觉得这种像纪录片一样的拍摄方式,让西藏取景在几乎没花什么预算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方面有觉得拍出来的素材可能完全没有质量保证,自己又导又演还要负责多余的机位,在拍摄之前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可控因素,演员、场地甚至安全性都完全处于不可控的状态。幸好我和吴照坤都身体素质很好,两个人不仅承担了高负荷的剧组所有工作,在低氧条件下身体也没有出现不良反应。后来我剪辑西藏这场的时候,因为拍摄的素材质量不高只能采用比较碎的剪辑方法。
最终在经历了漫长的剪辑、历时一周的西藏补拍和大概两周左右的再剪辑后,成片的粗剪版于2018年9月17日完成。影片时长122分钟,在电脑渲染视频结束的那一刻,我激动得抱着猫在床上跳上跳下。
此时距离三月剧组建立起来已经差不多过去半年。这段时间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做长片和做短片的区别。和普通的剧组不一样,这是一个完全靠情怀和友谊维系起来的剧组。大家都不拿工资,为了这个片子从四面八方赶来。但是毕竟拍摄电影是一个对体力和精力都消耗巨大的事情。如果是拍一个星期,大家打鸡血一起努力拍完;但是拍一个月,仅靠一腔热情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如果说拍摄还能感受到是一个团队在战斗,后期剪辑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的坚持了。每天剪辑8小时,基本能剪一到两场,而影片共有102场。因为拍摄过程中不可控因素很多,杂乱的场记基本用不了,需要从多个机位里找出素材并一一合板。
《时光慢递》初期拍摄VLOG
《时光慢递》拍摄花絮
我也不记得在这其中投入了多少时间,只是觉得三个月里我就像网吧里打《文明》的少年,基本对时间失去了感知,只觉得天怎么又黑了,过一会儿又亮了。比起身体上的消耗,最难熬的可能是孤独感,因为剧组所有人都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刚开始的时候我每剪完一场就会导出来发到主创群里,大家都会给一些反馈,有时候还会打趣一下剧情。到后面我剪完新的一段传到群里,等了一阵群里已经没人说话了,于是我关上手机接着剪下一段。有时候很期待有人能随便说点什么,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地反馈都好,寂静的群里自己难免有些失落。我其实很理解剧组的大家,对大家而言《时光慢递》这个项目已经结束了,大家都有了新的生活重心,但是对我而言这一切则是刚刚开始。
于是当2018年9月17日我完成第一遍粗剪的最后一个镜头时,我是多么开心,倒不是因为这种辛勤工作后产生的成就感,而是因为自己终于可以告别剪辑过程中自我封闭的孤独状态。
5. 第一次心态的剧烈变化
我在电影粗剪完成后,写了富有仪式感的电影总结,在电影导演手记文末向身边的人征集第一批电影的观众。很快我收到了三十多份第一批观众的回馈,整理成册后近四万多字。制片李忠泽后来又发了一封很长的邮件给我,写了整整二十一页的内容,对重要的场景还做了截图说明。
那阵子每次收到新邮件都会特别感动,自己的电影终于有了第一批观众的反馈,每一封邮件都是来自大家热情的帮助。但是感动之余,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做好准备去接受这些反馈。
可能是刚刚结束剪辑,在这样一个时刻心情是很敏感的。我很难去理性地看待这些建议。
粗剪观后感,有很多观众都表达了喜欢,但也提出了很多批评和建议。很多人都指出影片的硬伤,比如电影的声音,叙事节奏等等。其中西藏这段纪录片式的影像风格则出现了两极分化,很多人很喜欢这一段,很多人觉得这段纪录片式的风格背离了故事片的叙事方式。
我一开始觉得有些委屈,很多观众们的评判标准里并不会考虑到这是一部成本不足十万的学生电影。大家并不会想到在这样的预算下去拍摄这个体量的电影本身就是很困难的。
李忠泽的邮件更是不留情面,把电影的摄影、声音、配乐和剪辑都批评了一遍,他最开始第一稿意见里觉得电影里向海小雪的平行蒙太奇可以直接去掉,西藏的部分也有些拖沓大部分都可直接删掉,这样影片结构会紧凑很多。
现在想想李忠泽说的其实有一些道理,但是在当时的心情下,我觉得这些建议是多么地过分。这意味着他否定了我剪辑时间最长精心设计的分屏桥段,还把我不计代价在西藏补拍所做的努力都否定了。强烈的自我怀疑在那个时刻开始第一次出现在《时光慢递》的制作过程中,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并没有把片子拍好。整整一个星期我几乎封闭了与外界的联系,惠之给我发消息问我还好吗。我没有回复,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终于,我还是说服了自己。在这样的拍摄条件和预算限制下,这个影片必然会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我意识如果这样的影片还有观众愿意看的话,相比观众不喜欢什么,我更应该在意的是观众喜欢什么。或许对《时观慢递》而言,我不应该从负面的评价来修改影片,而是应该从正面的回应去看我要坚持什么。有人不喜欢西藏的纪录片叙事,但是很多观众也提到最喜欢的就是这段,于是我做了保留。向海小雪的平行蒙太奇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我发消息给李忠泽,我打死都不删。后来李忠泽和我再讨论这件事时,他说后来仔细考虑了也觉得保留较好。
在短暂地修改后,2018年11月末的时候,成片已经基本定稿。我那时候在想要不要把影片放出来了。针对声音和调色上的硬伤,我决定还是尽可能通过后期的努力去挽救。而且因为初期影片使用了一些经典的电影的配乐,我担心放出来后会有版权方面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非盈利影片音乐版权一直都是一个灰色地带,经过思考后我决定还是不要去冒这个风险。因为很多剪辑是按着音乐节奏剪的,修改起来可能会增加很大的工作量,我能想到的就是去联系影片中音乐版权方争取授权。
在朋友的引荐下,我联系到了业内一家调色公司Homeboy,我预计能攒出两万左右花在调色上,在简单对接预算和预期后,对方表示近来没有档期需要在春节后再与我联系。
声音方面我打算把预算控制在一万到两万之间,朋友们也推给我很多联系方式,但是大多数都在问了片长和预算后拒绝了。最终,问了很多做声音的人后,我找到了北电学声音的王雪莹,在中关村一家星巴克咖啡厅二楼,我们戴着耳机在嘈杂的人群声里看完了整部成片。她很愉快地答应了,她觉得这部电影不错,她可以便宜一些做,并表示尽量控制预算。
考虑到调色、声音、音乐版权三方面的事情,我决定在2018年末电影已经基本定稿的情况下延期发布电影,留出时间继续跟进完善。那时候的我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整个2019年。
6.峰回路转
电影的后期调色和声音将需要一些预算,于是我在18年末做了几个影视项目希望能够获取一些利润填补到《时光慢递》的预算坑里。其中几个都比较小,大多是一些广告和简单的剪辑。给甲方做宣传片和做电影是很不一样的,虽然都是做影视,但是目的是截然不同。
18年11月末我给北大团委一二九活动拍了一个宣传片《提琴物语》。因为请的都是外面的剧组工作人员,十分钟不到的片子用了十万左右的预算。其中一天因为拍摄超时,剧组的人员要求加班费。于是这个片子最后超了预算,我只能自己拿钱垫。那几天半夜回到住处,一边写分镜一边跟猫说好几天没睡,做人难不如做猫,然后我的猫摆了下面这个无比销魂的pose。
经过一系列协商后,学校补上了这部分预算。作为这个宣传片的导演,我花了一周时间筹备,杀青后又连刷了几天夜剪辑成片,项目结束自己没拿到一分钱反而还往外垫。杀青那天临别,剧组一个大叔对我说他有一个忠告,如果要把影视作为职业,情怀可不能当饭吃。
我当时笑了笑,说只要片子能拍好,亏点钱没事的。我那时候隐约觉得《时光慢递》能拍出来是多么幸运,相比十分钟时长的《提琴物语》,前者竟然用的预算更低。如果《时光慢递》按照正式的电影剧组配置来拍摄,可能影片预算要翻十几倍才能拍下来。
《提琴物语》拍摄现场在象牙塔外与业内的剧组接触也渐渐看清了很多影视行业的现实,越是认清行业的残酷就越会觉得自己对《时光慢递》的坚持是天真的,甚至有些幼稚。可能是当时的野心并不足以支撑期待幻灭的任何一抹可能性,于是自己很希望能够通过自我感动找到做影视的理由,或者说找到继续做《时光慢递》的理由。回想起来,电影粗剪早在八月份就出来了,但是我在接下来的九月和十月,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陷入了近乎抑郁的状态。我当时在朋友圈写下了这段话:
一个创作者最可悲的事情是不能正确的剖析自我,看待作品和自己的关系。在真的想做好一个作品的时候往往是那么近乎纯粹地孤注一掷,等曲终人散却发现自己是那个不疯魔不成活的戏中人。可能这就是“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吧。
2018年初,《时光慢递》的制作暂时处于停滞。调色工作室要等到年后才有档期,饰演沐安的嘉媛要去瑞典交换,于是我赶在她离京前陪她去录音棚做了ADR,其他几个演员因为要期末考试或者已经回老家,他们的ADR我计划年后再进行。音乐版权方面我联系了多个版权方,等待他们的答复。做完这些事情后我也离开北京回家过年。
春节后我继续回到北京,往返于朝阳和海淀之间做声音后期ADR。我约好演员的时间去重新配音,一开始都挺顺利,中间出了几次小插曲,还换过音棚。比较严重的一次是当时参加配音的靳子玄师兄那阵子时间安排很紧,好不容易约到师兄一周后的一小段时间。结果去到音棚发现没人,负责录音的是王雪莹的声音系学弟,他摆弄一阵子发现设备没有调对无法开工。等音棚负责人到了之后,师兄因为有事已经走了。我很生气打电话给王雪莹怎么找这么不靠谱的音棚,她说没办法只能认倒霉,业内有时候就是有这种事情,但是倒霉归倒霉钱还是得给人家的。我说,这不是钱的事情,关键是大家都很忙,这是我老早就约好的师兄了,人好不容易来了结果录不了。
音乐版权那边也收到了一些回信,反光镜乐队比较支持,如果做非商业使用给他们鸣谢就可以了;陈光荣老师工作室回信拒绝了配乐的使用;梁翘柏老师一直没能联系上。其中让我很感动的是给《那些年》配乐的侯志坚老师,他回信说因为版权并不属于他所以他没办法给我们使用,但是他很支持学生作品,对于将来自己有版权的已完成作品不吝授权。
调色方面终于在接近三月中旬和homeboy调色工作室取得联系。对方说可以先试调一段两分钟左右的片段来确定调色风格,我满怀期待地把片段发了过去。几天后我收到了对方的回复,对方发来一段调色样片。在看我调色片段后,我只觉得所有期待都沉到了谷底。调色非常糟糕,其中甚至给已经是709的片段再套了一个709lut,整个调色可以说是很灾难。我当时有点生气,我从春节前就在等他们的档期,结果却收到的是这样的画面。和对方沟通后,我渐渐也能够理解。毕竟这是一部两小时的电影,本身因为前期拍摄涉及到不同的机器,仅仅是一级调色让画面色彩统一都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对方工作室在调色业务能力应该在业内都普遍公认,但调色是需要花时间慢慢磨的,两万的调色预算实在太低了,他们很难投入足够时间和精力去做。最后我放弃了外包调色的念头,我决定自己完成整个片子的所有调色。
在进行影片的声音配乐和调色的同时,我开始思考下一步应该怎么走。18年末片子第一版出来的时候,自己的想法很简单,这个片子在学校放一放,之后发到网上就行了。但是当时的几件事让我想法产生了改变。
我一开始以为在学校放映电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像多年前《此间的少年》一样,同学们聚在一起看看园子里的故事。但是我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先后联系了学校的多个部门,老师们都很亲切,并说这件事情需要讨论一下让我等等消息就好。等待的时间各不相同,短则几周长则几个月。最后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婉拒了,或者让我继续等消息。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其实很多部门的老师可能本身就不想介入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他们又不好直接回绝。另外就是放映的场地其实涉及到一个场地费用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部门在我多次询问后就问我场地费用谁出。关于电影首映的困难我本身早有心理预期,但是等待是一件很难熬的事情,因为你等待的规程中会不断强化自己的心理预期,等的时间越长失望就越大,更何况这件事情周而复始。
从2018年10月到2019年3月我一直在寻找校内首映的机会,但是所有努力都在等待中不知去向。如果一开始就不希望合作拒绝我就好了,而每次有老师说“我们很支持,你等我消息”,无疑给人一种希望,尽管希望最后都成了失望。在经历这些事情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决定将影片以网络电影的形式发行。7.孤掷一注
如果站在未来的时间节点回望过去,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整个下半年,也使得整件事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它有着极强的利弊性。网络电影通过发行公司进行发行,与视频平台合作扩大曝光量,出品公司和发行公司商议得出相应的合作方式和分成,视频网站按照有效点击进行分账。
之所以想到以网络电影的形式发行,其中饱含了很多无奈。我自己预设过很多可能遇到的困难,只是我没有想到这部电影连在学校放映的机会都没有。我自己也知道《时光慢递》受限于资源成本和我自己的能力,终究只是一部学生电影作品,大家共鸣点本身可能是相似的经历或者学校的印记。我挺担心网大发行牵扯进各方利益,本来单纯的事情会变得复杂,这是违背我的初衷的。在影片杀青后的半年里,自己关注的一直都是创作方面的事情,在投入了太多的精力和成本后,我真的害怕它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在洪流中沉了下去。
对于学生拍摄的长片来讲,一般去向就是电影节。但是一方面《时光慢递》本身是不是艺术导向的电影,另一方面今年的政策有些变动,长片电影参加电影节都需要拿到龙标,也就是公映许可证才能参与。对于这样一部小成本的学生电影,拿到龙标几乎没有机会。如果这是一部短片的话,我可以直接上传视频网站或者投电影节;但是长片体量的《时光慢递》在越来越严的网络政策环境下必须通过合法渠道进行发行,才能够有和观众见面的机会。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很少有创作者会轻易尝试拍摄长片,拍摄长片的剧组一般都是有充足的资金,不仅能够囊括前期的拍摄费用,而且后期宣传发行也有专门的预算和团队。
在和几个朋友聊完想法后,我权衡再三,给剧组几位主创写了一封邮件,在邮件的结尾我这样写道:
“将电影通过网大发行是我综合目解决方案里的无奈选择,我的本意是创作一部纪念大学生活的影片,没有任何对播放量或者影片观影人群的诉求;但是我必须坦诚,在为这个片子花费了无数夜晚,自己垫进去越来越多的制作费用,我很难去维持我的初衷,我太在意这个片子能够被更多人看到。交互式宣传片的推广人次仅达到了两千人,可归咎于我的推广做的太差前期没有好好策划好,但也击碎了我对自来水推广可能性的期待。我不认为以我的能力或者我们自己的途径能把这个片子推起来。假设我现在直接把片子发出来,上网搜时光慢递并不能搜到成片,只会搜出一堆不相关的搜索结果,用户都没有途径看到成片。网大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电影会有很明显的观众错位。忠泽理想的结果是,让能够感受到情怀的人去看这个片子,以网大发行就意味着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成为电影的观众。我刚开始抱着极其单纯的想法,在这件事情上哪怕学校愿意帮我一点点我都不至于这样被动。我自己的心态也多次起伏,我的心理状态一度非常糟糕,我也想早点结束这个前后搞了一年的项目。但是可能很多事情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学校不回复,平台不回复,我自己又没有能力达到我的传播预期,于是最终权衡利弊选择网大这种我一开始没有想过的形式,如果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也欢迎和我讨论。如果以网大发行,我愿意把收益分给大家,网大带来收益,带来曝光量,但这里面有明显的风险,网络的键盘侠,潜在的攻击,情怀的不单纯,如果这些是负面都是我自己的,我是可以承受的,但是片子发出整个团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也希望能听取大家的意见。”几位主创收到邮件都给了反馈。其中黎亚东比较赞同网大的发行方式,他已经从北大毕业好几年。他提到多年前《此间的少年》在学校传播的路径主要是通过人人网。因为人人网是个电脑端,点链接进去看视频是常态。如今微信是一个用户时间碎片化的信息传播渠道,这样长度的片子放在推送是没有人愿意看的。亚东觉得这是人人网消失后《此间的少年》传播模式没法复制的原因,不只是我们,几乎所有的剧都不行。所以今天视频平台成为长片能够被观众看到的唯一的渠道。随着今年网络审核越来越严格,网络发行备案是长片能上线的前提。
在网大发行上这件事上忠泽很不支持,惠之则几乎和我吵了起来。忠泽觉得这件事会很像《地球最后的夜晚》,观影人群的错位会带来诸多负面评价。惠之认为通过学校和我们自来水是最好的方式,商业公司他们不仅不buy in北大的情怀,会带来针对个人针对作品团队等等的肆意伤害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在在询问大家意见的同时,我也开始对接各种各样的影视发行公司。这些影视发行公司背景各异,很多套路极深,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乱象。在谈及细节条款和利益分配时,对方很多热情的帮助里其实都是隐藏的陷阱。后来在朋友参谋下我才知道这些其实是业内的套路。我不得不认同惠之,这些商业公司都是利益驱使的,他们并不关心这部片子,他们只在乎包装炒作后能不能赚到钱,有的公司甚至层层下套想白赚一个出品方,我其实在把一件本应该是情怀单纯的事情卷进了一场复杂的利益分配。
因为网络发行,之前争取到的所有音乐版权都失效了,为了尽量避免版权风险,我决定对于无法取得版权的音乐进行替换。电影配乐一般都价格高昂,在得知我的窘境后,朋友岳越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后来《时光慢递》大部分的配乐都是由岳越所写。整个三月除了在寻找发行事宜,我和岳越同时也在跟进配乐的替换,前后共用岳越的原创配乐替换了十多首存在版权风险的音乐。
一方面看不到电影在学校放映的希望,一方面疲于奔命和良莠不齐的发行公司斗智斗勇。我能感受到自己开始抑制不住地焦虑,这种感觉让人沮丧,曾经以为剪辑的孤独时光是最难熬的,直到一个人面对这些最不想去面对的创作之外的事情时,我才知道能把所有精力花在创作的时光是多么幸福。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发行公司说要发的话先把片子剪到六十分钟,我大概两天都没有缓过来,吃不下饭睡不了觉,情绪非常糟糕。我后来才意识到,我其实根本不用在意这样一个发行公司,我不跟他合作就行,但是我整个人的状态已经有些不对,我变得极度敏感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2019年3月末,我最终决定和一家朋友介绍的发行公司合作。我自己出资一笔钱作为宣发费用,对方公司才愿意为我发行。这笔费用接近影片的制作成本,我并没有那么多钱。为了凑够这笔钱,我于是开始疯狂接商业拍摄攒钱,三月初到四月初我几乎是夜以继日地接片子做,高负荷地工作压力下,我开始失眠。躺在床上我开始想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没有公司能看到这个片子的价值,会不会它真的确实是一部很平庸的作品呢。我不敢再往下想,要是我这个时候开始怀疑了,我可能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8. 故地重游
我已经很久没有能好好休息。
那周好朋友沈桥也在筹备他的新片《在塞万提斯》。沈桥毕业于北大13级光华管理学院,但因为热爱电影他从事了影视制作行业。先是在新片场工作,后来进入央视当编导。一年后他决定辞职筹拍自己的独立影片。我答应尽我所能帮助他一起拍摄他的新片。
拍摄沈桥独立电影《在塞万提斯》那阵子我白天去帮他拍戏累到不行,但是躺在床上我却无法入眠。
终于踌躇好多个晚上,我给发行公司回复,发行费用我想办法分期给,我接受把影片拆分成上下两部。
2019年3月的最后一天,我打开邮件看到自己收到了Chapman大学的录取信,我拿到了电影制作的硕士项目Offer。一年前,2018年4月剧组杀青回宿舍的路上,我告诉忠泽我收到了拒信,我去不了美国了。
忠泽说,我马上要去Ch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