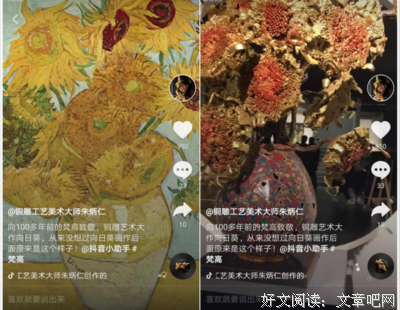《三大师》读后感1000字
《三大师》是一本由斯特凡·茨威格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0.00,页数:16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三大师》精选点评:
●茨威格的概括力相当佩服,简单的笔触就能触及一位作家的核心诉求。好像读狄更斯,看下平淡生活中的美好。
●zweig is one of the best autobiographers!
●从俄罗斯精神的母体脱胎而出。
●以后会再读
●从小对于被盖上“名著”印章的书就有种抵触感,这导致我如今对于大师们也不大熟悉,包括这本书中的三位。不过我是很喜欢茨威格的,在萨尔斯堡的几天多次问当地人以寻找他的痕迹,可惜最后没能如愿探访。通过篇幅的设置能看出茨威格很赞赏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觉得我身边还真有心性像他和他的人物的人,性格里头像是藏着岩浆,追求狂热,让激情主宰自我,渴望跨越界限让欲望挣脱束缚无节制膨胀。我最羡慕和喜欢这种人,但是自己这辈子是做不成了。我的价值观还是倾向于柏拉图的学说,个体要让理性统驭激情压制欲望,行中道对我来说还是合适些(扯远了……)。总之啊,茨威格的传记像是能钻进人物的身体里、灵魂里用小镜子窥探一样,当然,换个说法也许就是yy得很开心。即使真的是后者,把传记写得像小说,写得开心同时让人读得开心,也是很棒了。
●以为是传记 更像文艺评论 可我并没看过巴尔扎克 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不如与魔鬼作斗争精彩,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茨威格最用情的一篇,读来也不够过瘾,印象中茨威格最好的传记是写荷尔德林,而理解妥最深刻的人应是别尔嘉耶夫。
●其实也不能算完整读过,草草翻了一下巴尔扎克的部分,这个其实不是人物传记,更像是文学评论,所以如果对作品本身不够熟悉的话其实读了没什么感觉,所以也就先放下吧
●太感慨太仰视了了,没有八卦啊……
●第一,我对Zweig的文字和叙述一直无比欣赏信任;第二,Balzac和陀翁都是我心中的神,狄更斯也是神只是相比偏柔气,少了呼风唤雨的感觉;第三,文字到巅峰的时候,是可以寄寓对象身上燃烧的;最后,这三个人的并列无比合适,Zweig甘做光辉的衬托者,于是杰作诞生了。文学不需要万神殿,但需要建立万神殿的柱梁。
《三大师》读后感(一):优秀的主观流人物传记
茨威格的系列人物传记向我们展示一个进步主义者,一个人文主义的世界公民所能接受到的最好精神教养。这些传记,实际上都是这个传承的借他们而发展的故事。但是茨威格的自杀,也向我们表明这个伟大传承的脆弱。
但是这并不意味者我们要离弃这个传承,只是如同他本人所说,为了支撑这个美妙的空间,我们需要一点率真的质朴。
《三大师》读后感(二):尼采所写的三种人,在这里都有了对应了。
尼采所写的三种人,在这里都有了对应了。
最高级:他们在别人发现是毁灭的地方发现了幸福,比如在迷宫,在对自己和别人的冷酷以及在试验之中,他们就发 现了幸福。他们的快乐乃是自我征服,苦行源于他们自己的天性,并成为他们的需求和本能。最艰巨的任务,他们却认为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特权,调戏压在他人肩上的重担,对他们来说乃是一种休养……知识对他们来说同样是一种苦行的方。这种人是所有人中最值得敬重的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样是最快乐和最招人喜爱的人。
第二等级的人,他们是法律的守护者,是秩序和安全的维持者,他们是高贵的武士,特别是作为武士、法官和法律维 护者的最高形式。他们是国王。第二等级的人是第一等级的人的助手,他们是最接近第一等级、并且是属于第一等级的 人,他们是在第一等级的统治工作中担当了所有繁重任务的人,他们是第一等级的仆从,是他们的右手和最好的学生。
尼采语:再说一遍,在上述所有这些东西之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任意的,是人为的。人为的东西是和天性的东西不同的,人为的 东西只会给天性蒙羞。……阶级秩序、等级制度只是确立生活本身最高的法则,这个法则认为,要维持社会的存在,要使高以及最高等级的人成为可能,就必须区分三个等级。所以,权利的不平等乃是权利自身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权利就是特权。在权利的任何存在形式之中,也都存在着他的特权。我们同样也并不贬低平庸者的特权。生活对更高 境界的追求总是会变得越来越艰难。这时,冷酷增加了,责任也增加了。一种高级的文化就像一座金字塔,它只能够建立 在广阔的地基的基础上,它必须以广大的强大而健康的、巩固的平庸者为前提。手工业、商业、农业、科学、大部分的艺 术。所有职业性活动,总而言之。所有这些都只适合于平庸者的才能和野心。而同样这些东西对于精英们来说则是不合适 的,因为与这些东西相应的本能无论是和贵族主义还是和无政府主义都是相矛盾的。投身于大家共同关心的利益之中,成 为它的一个齿轮或一个功能,这需要一种特定的天性。正是这种各人所具有的天性,而不是社会,不是社会这种大多数人 惟一能够获得的幸福形式,把大多数人组装成一部理智的机器。对于平庸的人来说,做一个平庸的人就是他的幸福。精通 于某一件事情,也即专门化,这是基于他们的天性之中的本能。平庸本身根本就不配去发现对自己的专门化的异议,根本 就不配这种异议所需要的更深刻的精神。
如果社会要呼唤精英的出现,平庸者的存在乃是首当其冲的必要条件:一种高级的文化是以他们的存在为前提的。如 果精英们对待平庸的人比对待自己以及对待自己的同类还要体贴,这并不是出于他们内心的一种礼节,——而简直就是他的责任……(此处有人评价,尼采自负)
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价值追求
——茨威格
巴尔扎克的主人公要使世界屈服。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却要超越这个世界。
狄更斯的人物全都谦虚、谨慎。我的上帝啊,他们想要什么?一年挣一百英镑,有个漂亮老婆,一打孩子,有一桌像样的菜肴招待好朋友,他们在伦敦附近的乡间小屋,窗外一片茵绿,有个小花园和一大把幸福。因此狄更斯令人难忘的壮举其实只是:发现了市民阶级的浪漫情调,平淡无味中的诗意。
在巴尔扎克那里,要有一幢府邸,贵族院院士称号和几百万家产。
在狄更斯的著作里,所有的愿望到末了就是在绿茵丛中有一间温馨的小屋,儿女成群,活泼健康。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谁想要这些?谁也不想,他们什么地方也不想停住脚步,即使在幸福之中。他们大家都想要继续向前,他们大家都有颗折磨自己的“更高的心”。过幸福生活,他们漫不经心,心满意足,也无所谓,发财致富,与其说是他们所企望的,毋宁说是他们藐视的。这些奇怪的人,他们对于我们整个人类想要的东西,他们都不想要。他们没有人之常情,他们对于这个世界一无所求。那么他们是知足常乐者,对人生冷漠之辈,对人生兴味索然的人?正好相反,我已经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是一些新开始的人。尽管他们天资聪明,理解力如钻石一样犀利,却拥有孩子的心,孩子的欲望:他们不要这,不要那,他们想拥有一切,而且十分强烈地拥有一切。善与恶,热与冷,近与远,他们都要。他们夸大成性,毫无限制。所有的东西当中,他们就要最高级的东西,他们的感觉到处都烈焰赤红,组成的普通合金全都熔化,只留下像火焰流窜,熊熊燃烧的世界感觉;他们像马来狂人似的一头扎进人生之中,从贪欲转为悔恨,从悔恨又转为行动,从犯罪转入忏悔,从忏悔转入心醉神迷,但是(于是)跑遍他们命运的所有小巷,直到尽头,直到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或者直到别人把他们打倒在地。啊,这每个人的人生饥渴——整整一个年轻的民族,一个年轻的人类,都舔着嘴唇在渴求世界,渴求知识,渴求真理!你们给我找啊,让我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是不是有一个人,在平静地呼吸,在就地休息,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没有,一个也没有!他们都在参加这个疯狂的攀登高处,进入低谷的赛跑——因为根据阿廖沙的公式,谁若踏上了第一个台阶,必须努力登上最后一个台阶——他们向四面八方伸出手去。不论冰冻还是火烧,他们贪得无厌,这些不知餍足,没有限度的人,他们只是在寻找他们的尺度,在无限之中才找到,每个人都是一蓬躁动不宁的火焰,一蓬烈火。躁动不宁就是痛苦。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都是伟大的受苦受难的人。他们大家都面孔扭曲,大家都生活在热病之中,痉挛之中,抽搐之中。
《三大师》读后感(三):笔记:《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茨威格
__巴尔扎克
在他手里滑进滑出的金币上边,忽而是掉头国王肥头大耳的侧面头像,忽而是雅各宾式的自由帽,忽而是执政官的罗马帝国公民面孔,忽而又是黄袍加身的拿破仑。在这个时期里,道德、货币、土地、法律、等级制度等方面都发生了彻底的变革。[1]
这是他心中怀的是旨在得到整体的那种惊人抱负,是那种巨大的热烈贪欲,它轻视单个事物、外形表象和被剥离的东西,是为了抓得住在强烈震荡中旋转的世界。他从事件的混合饮料中提取纯粹的成分,从戴昂混乱的数字中得出全体的总和,从呼啸的喧闹中找到和谐,从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取得本质核心。[2]
他把世界简单化,为的是去统治它。他把所制服的世界都塞进了《人间喜剧》这么一个宏伟壮丽的监狱里。他的悲剧是冷凝出来的。[3]
巴尔扎克的主人公都像他本人一样,都有征服世界的欲望,一种向心力将他们抛到巴黎。[4]
每一个人(内心世界)都从一种氛围(周围世界)中吮吸自己的本性,一边自己能制造出一种新的氛围,巴尔扎克认为,艺术家最崇高的使命就是重视有机物在无机物中的痕迹,有生命的在概念中的迹象、社会生活中瞬间出现的精神财产的聚集、整个时代产物的描绘。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交融的。一切力量都处于悬而未决之中,无一是自由的。这种无边无际的相对论否决任何持续性,甚至否认性格的持续性。巴尔扎克总是让他的人物在重大事件中培养自己,为自己造型,就像是黏土泥团放在命运的手中那样。[5]
巴尔扎克知道,每时每刻在巴黎关闭的窗子里都有悲剧发生。这些悲剧不亚于朱丽叶之死、华伦斯坦的结局和李尔王的绝望。他一再自豪地重复,“我的市民长篇小说比他们那些悲惨的悲剧更具有悲剧性。”这是因为他的浪漫主义是向内追求的。巴尔扎克追求的不是到帷幔里,也不是到历史的或者异国的远景里,而是在极其巨大的范围里,在一种变得十分完整的,强烈的感情里。[6]
他的唯能论的基本公理是一种激情的力学。引起他的兴趣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比较完整,他们把所有精神,全身肌肉和一切思维都贯注于一种生活的幻想,即令是贯注于爱情、艺术、贪婪、献身、勇敢、懒散、政治、友谊都行,贯注于某个象征,随便哪一个象征都行,但是要贯注于那个象征的整体。[7]
路易·朗贝尔的“理论”(“第二视觉”等等)对巴尔扎克的影响。[8]
这个新宇宙的唯一的法则或许就是,所有的人——他们的不稳定的联合才构成时代——同样是时代创造的,人的道德,人的感情,也像人的自身一样,都是时代的产物。[9]
要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学者,能够用一切仪器透视时代的身体,对时代的身体进行听诊,同时又是一切事实的收藏家,一个时代的风景画家,一个时代思想的军人。巴尔扎克的野心就是成为这样一个人。正因为这样,他既要孜孜不倦地记下宏伟壮观的事物,也要孜孜不倦地记下琐细微小的事物。因此,巴尔扎克的作品,按照泰勒长期有效的话来说,就成了莎士比亚以来最大的人类文献书库。[10]
他把钱(货币价值)带进了长篇小说。自从飞出贵族特权以来,自从拉平了差别以来,货币就成了血液,变成了社会生活的动力。[11]
__狄更斯
狄更斯的作品是英国传统的具体化:狄更斯是幽默、是观察、是道德、是美学、是精神和艺术的内涵、是海峡彼岸六千万人所特有的,常常对我们是陌生的,页常常是眷恋与同情的生活感情。他不是写出了这么一部作品,而是写出了英国的传统,写出了最有力,最丰富,最奇特,因而也是最危险的现代文化。[12]
伊利莎白时代:英雄的英国;事业、意志和精力的文艺复兴的世纪;莎士比亚。
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的英国;拘谨舒适、没有气魄没有激情的国家体制的公民;狄更斯。[13]
英国传统把在默声熟睡的狄更斯(尤指他艺术家的那部分)用网缠住和紧紧绑住了,他始终是一个处于小人国的现代格列佛。[14]
他内心最深处的愿望就是为自己的(不堪的残忍的)童年时代进行报复。[15]
他伟大的、令人不能忘怀的业绩,老实说,只能是去发现资产阶级的浪漫派,没有诗意的诗。他是第一个把日常生活踅入富有诗意的东西里的人。[16]
他的作品具有卓越的民主性,但不是社会主义的,他缺乏那种激进的思想。完全是爱和同情给了他的创作以激情之火。[17]
所有的人都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敌对,都在聚集光明,或者都在聚集阴影。[18]
那是一副英国的眼睛:冷静、灰暗、敏锐、闪光,就像纯钢一样。实际上,狄更斯的天才就正是在这种独特镜头里,而不是在他有些过分市民化的思想里,他让事物从或明或暗处于神秘生长过程中的种子里发展处自己的色彩和表现形态。(与直觉不同,他是复制式的;于精神不同,他是肉体的。)[19]
他的人物是在适当温度下得立体形象,在激情中会融化,在仇恨中会僵化。他们总是毫不含糊的,要么是超群出众的英雄,要么是卑鄙无耻的无赖。[20]
英国长篇小说多愁善感的传统压制了要成为强者的意志,结局必然是一篇启示录,是末日审判,好人往上升,恶人受惩罚。狄更斯的作品即为维持作品稳定性而装配好的陀螺,不再是自由艺术家的公道,而是一个英国国教徒市民观。狄更斯对感情进行审查,而不是让感情自由发挥作用。要成为狄更斯的主人公,就必须是道德的模范,清教徒的样板。[21]
狄更斯笔下的世界是一个谦卑的市民世界,他则通过他的幽默把他的人物从沉重的现世苦难中解救出来。狄更斯的幽默是在感情的醉态,心情的狂热和嘲讽的冷淡微笑之间的一种平衡。他丝毫没有斯泰恩那样条分缕析,浸渍腐蚀的讽声,也丝毫没有菲尔丁那种高视阔步的乡间绅士诙谐的爽朗笑声,他也不像萨克雷那样尖刻伤人。[22]
那是一个处于拿破仑战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merry old England”。[23]
__陀思妥耶夫斯基
(略)
[1]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3页。
[2]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5页。
[3]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6页。
[4]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8页。
[5]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0、11页。
[6]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7]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8]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24页。
[9]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10]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11]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12]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13]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37、38页。
[14]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40、41页。
[15]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41页。
[16]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43页。
[17]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18]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19]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50页。
[20]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51页。
[21]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53、54页。
[22]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57、58页。
[23] 茨威格,《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60页。
《三大师》读后感(四):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弥赛亚情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面容、命运、作品处处充满痛苦与黑暗,面容的悲哀、命运的悲剧与作品的激情,以三位一体的方式阐述了他的真理,阐述了他的上帝,阐述了他的俄罗斯。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 面容上的苦难,先给人一种庄严悲哀的气质,而后恐惧,在然后是犹豫不决的畏缩,最后才是充满激情、不断增强的陶醉和惊叹。而这种苦难又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人生的悲剧。 贫民大院里的成长经历注定了其童年的缺失。在长期痛苦和极度兴奋中,到书中追求欢乐、力量,书中的知识铺垫了其成长的道路。由于生活的屈辱和痛苦,结合自己最大的威力即无限的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造《穷人》的时候达到了第一个人生瞬间,但上帝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考验远远没有结束。从生活的窘迫与紧张(预付款方式的创作)到写诺夫斯基广场的考验,一直到西伯利亚涤罪所生活,在从高峰到低谷的过程中,命运深深的折磨着他,但生活的经历极大扩展了他的认识,《死屋手记》惊醒了俄罗斯对麻木不仁的共同经历达到第二个人生瞬间的他成果复活。但上帝还是要继续考验他,随后的日子里,杂志被禁,债务深重,逃亡欧洲,数载地狱之旅,唯有艺术创造时他才能暂时逃脱异国他乡的艰辛,暂回故乡俄罗斯的会议。后来,上帝认为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知识足够了,让他回到俄罗斯,并完成一生最大的成就《卡拉马佐夫兄弟》,让他到达人生的第三个瞬间。 陀思妥耶夫斯基苦难的一生最终于1881年2月10日得到解脱,阶级分裂的俄罗斯因为博爱而在巨匠陨落的时候团结在一起,而三星期后的沙皇遇刺,也宣告着革命雷声滚滚而来,震撼俄罗斯古老的土地。 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苦难的人生,是一个探寻一切知识的过程。对命运的屈从,让他认识到人生苦难的必然和意义,在苦难之下,他的人生是分裂的,在幸福与痛苦、无辜与罪恶之间追求强烈的感情,以认识到幸福、荣誉的有限和内在激情、感觉的无限,由于献身于自己分裂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得感觉上的无限体验,获得了知识的真理,达到全部人性神秘的深度,成为一切苦难的伟大征服者。 艺术是人类对上帝忏悔的桥梁。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激情也来自于生活,困顿的生活条件阻碍了其创作,使他在生活之中也充满了焦躁不安,这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超越了完成工作,进而进入一种无限的状态,最终实现他的作品启示录式般的神话,成为人与人通向完善的道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知识、思想也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延伸。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时代之子,真实的反映了一个时代。19世纪的俄罗斯,在改革的时代大浪里是断了根的人,失去原有价值的俄罗斯还未找到新的方向,他们渴望世界、渴望知识、渴望真理,希望借此创建新的世界秩序。俄罗斯这种超越幸福的追求,和这片地壳最深处都饱含苦泪的俄罗斯传统在一起,在苦难、混乱、敌意的俄罗斯世界里,要在苦难中强烈的感受世界,以获得创建世界秩序的真理。 在寻求世界秩序的真理之中,俄罗斯体内孕育新的思想。但人的自尊确不愿承认这个思想,人渴望证明自己,因此不断寻求自己的界限。人在痛苦、放浪形骸、疯狂中不断将自己赶进罪恶之中,认识了自己的深度和人类的范围。在自我解放中获得拯救。 所以,作为时代之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英雄,突破了个人感情的局限,普通人的感情涌入无限之中,完成的瞬间,互相各异之人成为绝对的相似。最终在小说的结尾,产生希腊悲剧的净化,因为这种赎罪,纯洁的人诞生,普遍的人性达成,受苦受难者成为兄弟,进入真正的群体之中。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 陀思妥耶夫斯基实现了现实主义与幻想的奇妙融合。不同于其他作家进行详细的人物描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是模糊的,他是用精神来塑造人物的形象,以言语体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对读者起到一种催眠的作用,将重大的时代悲剧孕育在日常情景之中。正是这种超越普通自然的观察,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更高级的现实主义上认识到更加荒唐的真:人既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 精神描绘的人物过于真实,如预言家一般猜测命运,让人产生幻觉,以及全程都是激荡的感情,让人难以适应,这些都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实让人难以相信,也最终塑造出超越自身高度的真实。正是在内部、感情中塑造世界,在黑暗与光明的永恒斗争、平凡生活中隐藏的圣洁之美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明一切神奇清新隐藏于最低级的生活之中,寻找到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最后秘密:普遍的人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通过结构和激情的奇妙融合给人一段惊心动魄的感情旅程。尽管充满激情创作的他难以以清醒的理智从混沌的激情中提炼出永恒,但他仍旧通过一种高塔感受和雄浑气魄创造了自己的风格。 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是辛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激情中塑造他的世界,读者也需要在激情之中才能理解他的世界。为了集中情况,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一种特殊的描绘重量和描述广度来进行创造。前者指的是利用原始世界雄浑气魄的神秘重量,后者指的是建设一种金字塔般的行为规模,以一点一点的激情在内心世界击打读者的内心,为最后以闪电般的惊骇刹那间刺穿读者的心脏的喷薄激情做好铺垫,实现一种全部生活与情感挤压一处的极端感受,一种高塔感受,实现建筑艺术与激情的融合。两者的融合实现丰富多彩的挤压,导致情感的剧烈变化,高峰跌入低谷的尝试实现感情暴风雨般的净化。主人公充满激情摔倒的瞬间,小说失去叙事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现了古希腊悲剧精神,叙事文学升级为戏剧文学。 但也由于言语激情之外的种种暗示铺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旦改编成戏剧,便失去了其神秘本色。 勇敢的越界者使人类不断进入未来,作为越界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跨越了众多界限。他不但传承了时代,也推进了时代。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世界发现了俄罗斯,文化上扩展了俄罗斯的概念,让俄罗斯这片未开化之地成为笃信宗教的另一种可能;其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感情上的自我认知惊人的扩大,因癫痫病在生死不定之间不断穿越精神禁区,体验到感情统一体的分裂,在复杂、多义、乱麻的情感之中奠定了人物的一言难尽,人与人之间展现的多个世界,说明了感情的复杂性和精神的混合性;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实现了多种感情和实际互动的融合。从荷马时代单线性心理学的脸谱化人物,到莎士比亚时代内外部双重生活的自我矛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多重心理和实际的互动,显露出最底层在生命的极度兴奋中享受生活的煎熬。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爱情不是目的。感情溶解在爱情里,但爱情是升级的斗争,灵与肉的不和谐在其笔下的人物中处处可见,而其笔下人物双重的爱情,自然要面对世界的考验,在无穷的历练之中,获得更多的知识与情感。正是在无限的真实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人物们知道更多精神不朽的秘密,因更加自觉,便更加自我约束。 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追寻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和他自己,都想找到上帝,但无法达到上帝的状态。苦难的人生、分裂的思想赋予他们无限的知识,这种知识使他们怀疑上帝的存在,同时又渴望上帝的和谐统一。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人物一样,始终陷于分裂状态:作为上帝的奴仆不断自我献身,作为有知识的人不断否定上帝。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上帝的争论,既说明上帝的必要性和存在,又找不到上帝赐予的平静的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情整个世界,他体验到上帝的折磨和没有信仰的痛苦,所以他决定作为殉难者独自承担怀疑的折磨,从无信仰出发,产生对信仰的渴望,不是傲慢的宣布真理,而是创造一个信仰的谦卑谎言,为人们带来信仰。 这种信仰将宗教问题融入民族性之中,他信仰俄罗斯,俄罗斯就是上帝。俄罗斯的世界里,新基督就这样诞生了,俄罗斯的苦难,使之掌握了无限的知识和真理,正因为自己理解一切,所以俄罗斯相信自己是唯一真实、伟大、正确的信仰,所以俄罗斯便孕育了拯救一切的思想,在这种弥赛亚情怀下,俄罗斯要拯救一切,他们不惜否定欧洲一切的文化,以建立一个世界性帝国,用他们无所不知的宽容包容一切,用爱而非统治形成团结友爱的集体,来讲述上帝真言。人性的理想与征服的欲望囊括在俄罗斯和解对立的思想中,这是一种充满矛盾但又包罗万象的幸福。 作为殉难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可能获得心灵统一的平静的,他处在是和否的永恒冲突之中,为了在未来的人身上复活而进行自我毁灭,在二元分裂中期望和谐的统一体,他以囚禁自身的方式引导众人从他自己性格的终点涌进上帝,正因为熟悉一切而不惧痛苦的追寻,统一体是他这个分裂的人最后的理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追寻的统一体,最崇高的生存便是脱离世俗的烦扰,因质朴、平静、内心单纯,获得自然而然的喜悦,通过无个性,达到尘世凡人的最高幸福,因理解、博爱实现天下皆兄弟的大同。 我苦,故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畏惧生活,他通过痛苦学会热爱生活,学会理解一切。他是受苦最深的人,所以是一切人中最有智慧的,生活用苦难使伟人顺从,让伟人们宣告生活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