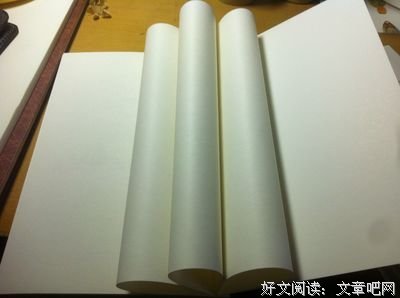博尔赫斯:最后的访谈读后感1000字
《博尔赫斯:最后的访谈》是一本由[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页数:2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博尔赫斯:最后的访谈》读后感(一):书评啊
第一次看最后的访谈系列的。也是第一次看关于博尔赫斯的作品。他并没有讨论过多的关于写作的技巧,而是谈了关于阅读的真知灼见。由这本书对博尔赫斯的作品产生了兴趣。 这里也证实了一点,好的读者也会带来更好的作者,给作者以启发。博尔赫斯说喜爱阅读胜于写作。觉得他是一个睿智,谦虚的老人。看问题的角度总和大众不太一样。总的来说,很多语句还是受益。 书摘:1.阅读对我而言是一种不亚于周游世界或是坠入情网的体验。人们常常会把现实生活同想象区分开来,前者意味着牙痛、头痛和旅行等,后者代表艺术,但在我看来这么做没什么道理,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2.我每次回忆一件事时,实际上并不是在回忆这件事本身,而是在重温上一次的回忆,是在回想我关于这件事最近的记忆。 3.我不喜欢复仇。我认为唯一可能大仇得报的方法就是去宽恕、去遗忘,那是唯一的复仇途径。 4. 我不认为作家应当聪明,或是以某种近乎机械的方式耍小聪明。
《博尔赫斯:最后的访谈》读后感(二):博尔赫斯如是说
博尔赫斯真的是读书kol。在看他的访谈过程中,疯狂被种草,比如康拉德、亨利詹姆斯哈哈哈。
博尔赫斯说,年轻的时候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世界上最好的小说家。但时隔多年再看,他感到失望。
失望在于,陀的主人公只有单一的愤怒只有经历过的事。为什么一个深陷爱情的男人,不能同时沉迷电影、艺术?
对这个观点我深有同感。有人说,在法国,深刻的对话,思想的交锋就是一种调情。只有棋逢对手,才能碰撞出火花。
我们总是试图去分清虚构与现实,但我们每个人难道不是由他所经历的事儿、所读过的书所看过的电影共同构成的吗?这是没有办法切割的。
博尔赫斯还说,有些人对文学没有感受力。我们总是试图去解构作者背后的意图。总是去升华,寻找意义。但其实对作者而言,语言或表达本身就充满乐趣,就跟音乐一样,有时候让你感到悲伤感到愉悦,这就够了。让词语回到词语本身,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
《博尔赫斯:最后的访谈》读后感(三):略有出入
让我印象深刻有以下几点。
1、博尔赫斯说他自己视力下降,看不清楚的时候,反倒能感受纯粹地活着,特别能坐两三个小时而不会心浮气躁,不再匆忙。
2、懂得越多,看的书越多,觉得自己会的越少,他一直说自己没有原创,只是把先前人物所写的换了个形式再来。
3、有些鄙弃女性对抽象思维的不感兴趣,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说他认识的一个特别聪明的女性,看哲学之类特别看不进去。博尔赫斯对形而上对时间空间的思考非常推崇,对世俗生活具象情感的小说类看不上,觉得低价值。这让我不大赞同,各有各的优略吧。整天形而上很类的。人总要活在具体的生活细节当中。而且,男女性别的大脑生理结构有所区别不能因为大脑生理所擅长的去和不擅长的比较。
4,博尔赫斯说他写作,是先有一个概念,一个想法,再围绕着概念想法去想整个故事。
《博尔赫斯:最后的访谈》读后感(四):文字本身就是谎言
整理读书笔记的时候,看到这句“文字本身就是谎言”,突然想起刚做图书编辑时看到一位作者写的散文,她在文中回忆自己的母亲,想起儿时母亲为她做心爱的茶泡饭,后来母亲去世了,从此再也没有吃到过母亲做的那个味道的茶泡饭。当时我以为她文中写的是事实,对她便多了一分怜惜,后来慢慢熟悉了,聊起这篇文章,才知道那是她编的。
虽然这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我一直认为以自己为主角时将双亲写去世,真的太过残忍了。而今看到这句话,想起曾经的自己,觉得有些可笑。只是博尔赫斯说起这句话是因为记者问他是否会撒谎,他说:“不是自愿的,但我会说谎。语言远远不足以充分表达我们的思想和感受,因此我们不得不说谎。文字本身就是谎言。”也正是因为他的谎言,能让我们享受到不一样的视觉盛宴。
在这本访谈录中,影响我的还有他对死亡的定义。他不认为广岛的遭遇要比任何其他战役惨,因为“它在一天之内终结了这场战争。很多人死于非命,跟一个人死于非命都属于同一类事实。因为每个人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死去”。死从来不是一个可以逃避的话题,而说起广岛,许多人都觉得过分惨烈,但博尔赫斯的这种说法我从未听谁说过,但仔细一想,也确实如此。广岛的惨烈,是因为牵连了无辜的平民。当然,这也是他后面提到了的。
关于死亡,他还说:“我不觉得死亡是多可怕的事。……死亡意味着你将不再存在,不再有思想或是感觉,不再有求知欲,但幸运的是你也不用再烦恼了。”这是多么幸运的事!
《博尔赫斯:最后的访谈》读后感(五):关于这本书
这本书我看了一下,是这一套里最厚的一本,所以其实读完之后会发现信息量真的超大。博尔赫斯什么都谈,谈宗教谈艺术谈哲学谈政治,从自己的作品谈到塞万提斯谈到马克·吐温,如果没有强大的知识库支撑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是囫囵吞枣地翻完的(比如我)。
总体感觉读者尽可以从这本书里获取非常多的知识,但是读起来很“难”。不如上一本海明威好读,可能这也是语言体系的问题,海明威是美国作家,博尔赫斯是阿根廷作家,植根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的语言体系,自然凝练出来的谈话风格也大相径庭。
最大的感受就是,博尔赫斯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博尔赫斯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兼心理医生,家里的藏书量很大,博尔赫斯也说他的父亲曾经想要成为一个作家但是最终没有成功所以希望博尔赫斯成为一个律师而不是作家(这个逻辑有些让人啧啧啧)。博尔赫斯小时候看的比较多的是马克·吐温,但我觉得马克·吐温对博尔赫斯的写作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
博尔赫斯也是一个很谦卑的人,虽然他本人超级反感“谦卑”这个形容词(他觉得很虚伪)。他和访谈者说他的书是不可能会放在家里的书房的书架上的,因为他认为他的书永远不能和爱默生的巨著比邻。第三篇里,访谈者说博尔赫斯现在的名望越来越大的时候,博尔赫斯有意思地反问了一句,我能怎么办呢,我的书还在出版,我还有书要出版,我总不能让大家别买我的书吧。
还挺真诚的哈哈。
《博尔赫斯:最后的访谈》读后感(六):不要把宇宙视为理所当然
记得第一次读博尔赫斯,是他最有名的《小径分岔的花园》。那是一篇带有哲学与诗的气质的短篇小说,其中关于时间的描述,使我惊叹又困惑。时间原来可以是这样的……时隔多年,看到这本访谈,对他作品的理解似乎深了一些。
很少有人去思考时间、空间、无限的问题。很少有人意识到宇宙,并为自己的存在而感到匪夷所思。绝大多数人只看到表象,把宇宙视为理所当然的,从不会奇怪自己为什么会活在这个世界上。博尔赫斯的作品引我走向那可能无解但意义重大的问题。回答不了没关系,意识到那些问题,就很好。
博尔赫斯的作品中常出现迷宫、圈套、难题,不是他有意卖弄,而是因为他总对世界充满好奇,心怀困惑,从某种程度上说,“迷宫”就是他所感受到的世界,是一种确切的象征。对刚出世不久的孩童来说,生活中感到好奇与惊讶没有什么特别,但对一位耄耋老人来说——不仅没有习惯和厌倦,还能保持惊奇之心——实在太过可贵。
啊,有时简直对他的状态感到嫉妒。一生都能好奇与惊奇地活着,如同神的馈赠——谁不嫉妒?
这本访谈让我对博尔赫斯的仰慕又深了一层。除了超群的智力与才华,他的谦逊着实令人敬佩。他的采访者说:“博尔赫斯似乎完全不需要他人对他有任何感激的表示,他总是能让你感到,他才是心怀感激的那个人。”多年后,看着他留下的东西,我心怀感激。
《博尔赫斯:最后的访谈》读后感(七):谦逊的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的访谈,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太谦逊了!如此博学,文学成就如此之高,却又如此谦卑随和,一点大师的架子和脾气都没有。像个慈祥的老爷爷,每个问题都会认认真真回答,开玩笑时也会让你知道他在开玩笑,免得对方当真。
这本访谈录的第一篇,就是一个叫理查德·伯金的美国大学生和博尔赫斯的对谈。1968年,博尔赫斯受邀来到美国剑桥做一场讲座。理查德·伯金,作为博尔赫斯的铁粉,得知消息后高兴了很久,盘算着要去见一见博尔赫斯本尊。
博尔赫斯并没有因为对方是个大学生而有任何敷衍和怠慢,反而非常在意对方的感受。访谈才开始15分钟,他们就聊到了福克纳、惠特曼、梅尔维尔、卡夫卡、亨利·詹姆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叔本华。
每隔五分钟博尔赫斯都会停下来问理查德·伯金:“不会无聊吧?不会失望吧?”
尽管博尔赫斯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但他说自己首先是个读者,其次才是个作家。他自称,自己的书房中没有一本自己写的书——“我写的东西怎么敢与托马斯·布朗爵士或是艾默生的巨著为邻呢?我只是个无名小卒而已。”“我写过的书并不能证明什么。它们是最不值一提的。”
博尔赫斯说:“上天赐予我的一大乐趣就是和他人进行关于文学和形而上学的对话(尽管我是个无神论者)。这种对话对我而言不是辩论,不是独白,更不是傲慢的说教,而是和他人一起求索真知的过程。”
在这本《最后的访谈》中,博尔赫斯从他的童年谈起,他非常坦诚地谈到他的家庭、儿时的阅读、喜欢的作家……这本书完全可以看成是他的“口述自传”。
博尔赫斯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迷宫、老虎、镜子、梦境”等主题,都被博尔赫斯一一道出原委。比如说他为什么迷恋“老虎”,是因为他失明前最后能看到的颜色就是黄色,而他生来第一眼看见的颜色就是虎皮的金黄。他曾经盯着动物园里的老虎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博尔赫斯还为理查德·伯金的访谈写了篇前言。“理查德·伯金让我重新认识自己”,他说,因为“我认为自己完成了自我表述,事实上是自我坦白,坦白的程度更甚于那些我在孤独中怀着过度的忧虑和戒备写下的文字。比起我自己独处时思考的产物,从他人那儿得到的启发往往更能让我眼前一亮”。
《博尔赫斯:最后的访谈》读后感(八):博尔赫斯微笑地向你伸出了手
坦诚、谦逊、沉迷哲学和意象,所以所作所为总是充满着一种神秘超脱的风度,讲究逻辑,追求“纯粹”。这是看完本书后我对博尔赫斯的印象。 虽然,可能是因为他研究哲学和古英语的缘故,我总是会生出一种“这个人其实有种圣人般的冷漠”的印象。 访谈看起来很快,也并没有什么很艰深的内容需要停下来体会,个人比较喜欢的,是最后一部分和有人莱库韦的私密访谈,终于(?)跳开了作品和令人头晕的作者名称,有着“不客气”的打断和涉及爱的私密部分,也谈到了他的生活。 虽然这个失明的老人是一个名声斐然拥有坎坷经历的大作家,但抛开那些玄之又玄的神话、哲学、技法和文学评论,博尔赫斯其实就是一个稍稍有点固执,坦诚又“害羞”的谦谦君子变老之后的普通人。
博尔赫斯的文章,我可,但对于这本书的内容,的确不太能提起我再看的兴趣。也可能是访谈中涉及的内容太广太杂,常有从未接触的人/作品出现,才会觉得读起来好似没读的感觉吧…看来我还是要多读书啊~ 博尔赫斯正微笑地向你伸出了手,邀请你进入这一段也许你会喜欢,也不喜欢的旅程。 (以下为阅读时随手写下的感想,不成体系,看完能一笑而过就感激不尽了) 失明让他学会忍受无所事事的生活,不会觉得无聊 形而上的,认为维系人类文明的工作已经工作的太多了,而形而上的,思考宇宙的玄妙的议题却太少——把宇宙、事物和“存在”视为想当然的,而不在乎为什么“存在”,他们源自何处。 穿着考究,是为了在人群中降低存在感,不修边幅有时只会起反作用 选择出版哪一些自己的作品,选择“大众可能更易接受”的部分,从某种方面来说,并非完全是对大众口味的让步——因为很多人,从未看过,也可能自此之后再也不会看本人的作品,选择更容易被理解的故事,至少不会吓跑读者。 而看过作品后,即使只有一个人产生继续阅读同作者作品的冲动,因而向更有深度的阅读之路进发,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且令人欣喜的事。 把博尔赫斯的观点放置其他领域,也让我对“营销”产生了新的思考:与其保持着“创作者的清高”高高在上的认为只有懂的人才配看/买我的作品,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因为虽然读者的“理解力”各有不同,但其实存在可以“培养”的空间,所谓迎合消费者,不如说是先“弯下身子”接近他们、获得信任之后慢慢提高和培养大家的鉴赏力。 这是既是创作者对自身作品的自信(大家看了更多的好作品之后可能就看不起你了),也是与观赏者之间的信任。 博尔赫斯自述生平几乎没有发过怒,并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甚至需要为其羞愧。而面对可能引起怒火的原因,他也似乎看得很淡,诚然“很少有人能真正伤到你,除了你在意的人和你自己。”也是一句挺正确的话,但我觉得这句论调中似乎透漏出了一种隐秘的自私与冷漠。 只有不关心除了“我”之外的人,才能真正做到不被无关人员伤害。我曾有段时间试图如此,但很快就破功了,这可能是因为我无法保持对世界的冷漠,也可能是因为我自私的无法放下他人对“我”的伤害。 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议题,暂且把他称之为“冷热悖论”吧。 而对于发怒这件事,如果不能做到如博尔赫斯般的不在乎,其实发怒比不发怒好。(在不冲动犯法的情况下) 吵架的原因,和因此而发生的暴力冲突结果毫无关系,分歧所在的观点是否正确并不会因为吵架的结果而改变。——恩,有道理 崇拜希特勒,和崇拜拿破仑或者任何暴力手段有什么不一样呢?当然,希特勒更快,更残忍,规模更大。但德国军队的行径,与他们脆弱伤感(?)的一面又非常的矛盾,让博尔赫斯不喜。 基督徒纪要相信灵魂永生,又要我们在短暂的有生之年里所做的任何事都是有意义的,这其实很不符合逻辑。因为若灵魂永生,在无尽的时间里,在活着的时候任何人所经历过的任何事,都可能在若干年后被自己所经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杀人犯、傻瓜和智者。“命运”一词也就没有了意义。 “如果一个人宽恕了另一个人,那他就算是改变了过去。” 当你相信了一种所谓“宽慰的说法”,那么你之前所受的困扰也就真的不会困扰你了,问题反而会迎刃而解。 对战争、冲突的看法,展示出他个性中冷漠和悲悯的矛盾性,或者说,可能是因为他喜欢哲学的缘故,从博尔赫斯的言语中总能让我感到一种如圣人般的“目空一切”的感觉。
《博尔赫斯:最后的访谈》读后感(九):一些愉快的对话
关于生活。“我首先是个梦想家,然后才是个作家,另外我最幸福的时光就是身为读者自由自在读书的那段时光。”博尔赫斯是个挺自律的人,十一点休息九点起床。曾经被失眠困扰过,“极端的偏执狂,或者说某种穷凶极恶的敌人”,改善最重要的方法是不要把失眠当成严重的问题,抛弃钟表,相信自己即使不在睡眠状态中也会有所休息。(谈论此事时他已恢复,因此说“人们很容易忘记痛苦的经历”)。从未觉得自己是伟大的人物,一心想成为“隐形人”;吐槽名誉教授头衔的无用;坦承写作收入并不能支撑生活;认为新养的猫只是“被重新打扮了一番”,并不能替代之前去世的那只;说日报的称呼“听着就让人对它的重要性产生不了多少信心”;会骑自行车,并提到“现在在中国,人们最奢侈的愿望就是有属于自己的手表和自行车”。(是啊,我们现在奢侈的愿望同那时相比又有多少不同呢。)
决定看下去的几句话关于失明他的描述很有趣,他说自己最先失去的是黑色和红色,“这意味着我再也感受不到黑夜……最后黄色也消失了。现在我看不见任何色彩,只能感受到光和动作。”与其说是失明,不如说是失暗?谈到失明的好处,他现在可以忍受无所事事,不再觉得什么都不做就是无聊,但坏处就是不能自由浏览书籍,发现自己是第三位双目失明的图书馆馆长,“手下掌管着那么多书籍,你却连读都读不了,这真是个再明显不过的反讽”。
关于快乐和悲伤,“如果一天之内我们没有同时经历悲喜两种情绪,这一天就没有真正地过去“。幸福本身是一个终点,”敞开心扉去拥抱它,而不是去深究它从何而来“,”无缘无故的快乐更难能可贵“。”对于那些你真正在乎的人,他们只要对你漠不关心,或是稍加怠慢,你就会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而失恋其实是像从马背上掉下来一样寻常,但当你亲身经历时会觉得那是件天大的事。”种种痛苦、不幸、失望、悲伤和孤独,而这些东西正是诗歌的原料“,并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悲伤的产物“。”一个深陷爱河的男人,他同时也可能对电影感兴趣,也可能正在思考数学、诗歌或政治方面的问题。“当我们回忆时,回忆得是记忆中的那个印象,重温的是上一次回忆,而不是事情本身。而最好的复仇是遗忘。
关于阅读和写作。阅读的乐趣的两种说法,一种是摆脱现有处境,进入不同的世界;另一种是阅读的世界比他所处的世界更接近他内在的自我。在一片盘根错节的文学森林中,去寻找那些你爱上的书。故事本身存在即合理,像看待音乐那样看待诗歌。“哲学溶解了现实,但由于现实并不一直都是美好的,它被溶解对你来说或许是件好事“。(kind of transitory)写作的核心是对宇宙本身的惊奇感,试图表现一种宿命感。并不存在”纯虚构“,拥抱事物的模糊不清、毫无意义;以及事物的多面性,最终都是无解的。写作最初确定的”往往只有出发点和最终的目标,这二者之间的内容就要靠我绞尽脑汁去构思、去编造“,珍惜找到你的灵感。小说与主人公融为一体,诗歌的文字自然流淌,浑然天成。推荐文章最多的合集《小径分岔的花园》。
小径分岔的花园8.9[阿根廷] 豪·路·博尔赫斯 / 2015 / 上海译文出版社《博尔赫斯:最后的访谈》读后感(十):摘
博尔赫斯 我不认为广岛的遭遇要比任何其他战役惨。 伯金 您的意思是? 博尔赫斯 它在一天之内终结了这场战争。很多人死于非命,跟一个人死于非命都属于同一类事实。因为每个人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死去。当然了,人们也不可能认识广岛原子弹事件中的所有遇难者。说到底,日本是支持武力对抗、军国主义、战争和残酷暴行的一方,他们可不是早期基督徒之类的。事实上,如果日本人手上有原子弹,他们肯定也会对美国做出同样的事。 再多说几句吧。我知道我不应该说这些话,会让别人觉得我很冷酷无情。但不知怎么回事,我从未对广岛的遭遇有过任何激烈的情绪。也许这确实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人间惨剧,但我认为如果你接受了战争,你就不得不接受它的残酷性,接受屠杀、血洗之类的暴行。归根结底,被步枪扫射而死和被人用石头砸死或是用刀捅死,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任何区别。轰炸广岛之所以特别骇人听闻,是因为牵连了太多无辜的平民,而且持续的时间又特别短。但说到底,我看不出轰炸广岛和其他战争——我这么说是为了便于讨论——或者说广岛事件和人一生的遭遇之间有什么区别。我是说发生在广岛的这一整出悲剧被压缩得无比紧凑,能让你尽收眼底,深感震撼。但一个人从长大成人,到生病,再到死亡的整个过程正像是一出延时版的广岛事件。 你懂我的意思吧?举例说,塞万提斯和克维多[插图]都发表过反对火枪的言论。他们说,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神枪手。但我是这么认为的:所有武器都很可怕,都害人不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容易习以为常,感官也越来越迟钝了,我们一点一点地接受了剑,接受了刺刀和长矛,后来是火枪。但每当下一件新型武器横空出世时,人们一开始对它总是特别畏惧,觉得它残酷无比。尽管说到底,如果你注定死于战乱,对你而言被炮弹炸死,被当头重击而死还是被刀捅死都没什么区别了。 当然了,你可以说战争、杀戮或是死亡本质上就很可怕。但我们的感官越来越迟钝了,每当有新型武器研制出来,我们都会觉得它极度残忍——在弥尔顿笔下火药和大炮都是魔鬼发明的,你还记得吗?这是因为当时大炮刚造出来不久,在人们眼中显得无比可怕。也许有朝一日当我们为某种破坏力更强、威力更大的武器而颤抖时,我们就会接受原子弹了。 伯金 您认为真正可怕的是杀死某个人这种想法。 博尔赫斯 是的,你一旦认同了这一想法,战争就不足为奇了,或者不谈战争……与他人决战从本质上来看也属于同一种想法。 伯金 您说过如果一个人真正幸福的话,他不会想要去写作或是干其他正经事,他只想活着。 博尔赫斯 是的,因为幸福本身就已是一个终点了。也许不幸的一个好处,或者说唯一好处就在于,不幸必须转化成某种东西。 伯金 所以说,您的写作生涯始于一种悲哀感。 博尔赫斯 我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悲伤的产物。我想马克·吐温在写密西西比河、写木筏的时候,心里一定也在回顾他自己的过去。他对密西西比河有一种思乡之情……当然了,当你感到快乐时,你就什么都不需要了。我仍然可以感受到快乐,但持续时间并不长。 伯金 您之前对我说,您能想象一个没有小说的世界,但不能想象一个没有传说或诗歌的世界。那么哲学呢?您能想象一个没有哲学的世界吗? 博尔赫斯 不能。我认为没有了哲学人们就会活得很可怜。因为他们对现实、对自己都太确定了。我认为哲学能让你更好地活下去。比如说,如果你把人生看作一场梦,就算它有种种黑暗丑恶之处,你仍可以把它当成是一场噩梦。但如果你把现实看作某种固若金汤的东西,你的心态只会更糟糕,不是吗?我想哲学可能给这个世界增添了几分朦胧感,但这种朦胧感是有好处的。如果你是个唯物主义者,只相信固若金汤的事物,那你就会被现实所束缚,或者说被你口中的现实所束缚。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哲学溶解了现实,但由于现实并不一直都是美好的,它被溶解对你来说或许是件好事。当然了,这些都是最浅显的思想,但浅显无损它的正确性。 我是先有了一个想法,再从中生发出一个故事或是一首诗。但我最初确定的往往只有出发点和最终的目标,这二者之间的内容就要靠我绞尽脑汁去构思、去编造。总的来说,我一旦有了这样一种灵感,总是会先尽我所能去打消它,但若是它再三侵扰我,我就不得不把它写下来。但我从不会费力去寻找主题,它们自会找上闭门造车的我。它们可能会在我快要入睡时造访,也可能是在我刚起床时。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上走着时,它们也会来找我,或是在其他任何地点,任何时刻。比方说,一个星期前我做了个梦,当我醒过来时——那其实是个噩梦——我说,噩梦本身没什么好写的,但这件事背后可能隐藏了一个故事,我想找到它。一旦我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我就会花上五到六个月来写这个故事。写一篇要花费不少时间。所以说,我用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当然了,每个匠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我应当充分尊重这一点。 博尔赫斯 可是我不喜欢洛尔迦。你看,这也是我的一个缺点,我不喜欢视觉诗。他写诗一向注重视觉效果,他还喜欢华丽的隐喻。 福克纳在我看来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顺便说一句,我不喜欢海明威——但福克纳真的很了不起,尽管他讲故事的方式有问题,叙事时间线也很混乱。 莱库韦 那只猫呢? 博尔赫斯 死了。 莱库韦 那只猫死了?什么时候的事? 博尔赫斯 大约一个月前吧。它活了十二个年头,算得上寿终正寝了。虽说我也不懂,但它显然算是一只很长寿的猫了。 莱库韦 您会想念它吗? 博尔赫斯 有时会,有时不会。我经常四处寻找它,然后才想起来它已经死了。 莱库韦 我可以送您一只新的小猫,您想要吗? 博尔赫斯 我不知道,要问问家里人,因为养猫很费事,它们要是死了你也会很难过。就算你看着新养的猫,想把它当成之前那只,但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就好像是被重新打扮了一番。所以我得问问他们,总之还是谢谢你的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