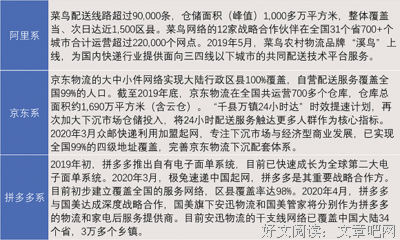碗经典读后感有感
《碗》是一本由金宇澄著作,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1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碗》精选点评:
●大雪纷飞,什么都不会埋葬
●小人物引出的一个时代。
●人生只一个回忆,还能忆什么呢,当兵的谈连队,犯罪的讲牢饭,下乡的一开口,可谓“青春无悔”,其实长夜如磐,人的一生是有悔的,然而肠子悔青,同样无人理会。
●很小一本,在图书馆一个小时看完
●一本意蕴深厚的小书,一段动荡激越的共和国史。青年女性/母亲的亡灵是承载了记忆和意义的隐喻。几十年前的苍莽青春哺育了70/80年代出生的如今的青年人。知青/纪录片青年的两层回溯,奏出那一段历史苍凉的回响。
●2019-02-26 / 注:四星半
●青春无悔,是多么的讽刺。
●繁复的场景、气味描写很精彩,让人犹如堕入作者描述的知青北上的萧瑟世界里。青春在这里是残酷的,冷峻的,和本不属于它的死亡粘连在一起。就像作者说的,美是没有的,他们都是恨的
●装帧可爱。读完第二篇,方觉得时间,空间,周围人事皆幽幽明明,影影绰绰。仿若此刻北京的冬天也无极可寻。
●3.5 小说一样的非虚构
《碗》读后感(一):短评放不下 有点长的意识流读后感
又是一个不同视角照进那个时代。不知道怎么评价,因为没经历过,也没看够多。只是觉得好悲伤、好沉重,事实的复杂程度只会比文字更胜。“特殊环境,形成了特殊内涵,从当初特殊意味的大聚集,到七八年后特殊意味的大放归,延至今日,这个人群始终富含特殊的混浊度。”嗯,特殊环境形成了特殊内涵。 我有一种感觉☝ 我读得懂的地方,是他刻意放慢规规矩矩写的,只要他没收住,一股脑倾倒出来,我就读不懂了kkkk也不是读不懂,就是没办法读很快,得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看
《碗》读后感(二):无题
喜欢这本书的装帧,这本书是在国家图书馆看完的。说实话如果是我自己平时看的话我不会选择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很薄,五万四千字却要42块钱,是真的贵!(说文景不抢钱我都不信。)说到正轨这本书包含《碗》和《苍凉纪念日》两篇小说都属于纪念老金的青春(知青时期)虽然我没有经历那个年代但是我也看了许多伤痕文学的书,大多是讲自己那破碎的青春和梦,和死亡。 看完我记得最清楚的便是死亡和坟墓"青春万岁"。 「现今的坟场,等同于坡地,分不出坟墓,分不出轮廓。他在哪里?她在哪里?他们在哪里?他们归于泥土,融入泥土,坟头平缓模糊,四周安静寡淡,年复一年野花盛开,草虫轻吟,寒风凄号,冻雪满天。这个死亡所在,集中了故事,埋葬了呼吸。」 小说以小英引出那群老知青,并且通过几个场景便将那时候的人们与时代相连。 「他们的一生都牵扯谈论这种种的复杂变数和感想,分崩离析,尔虞我诈,栏杆拍遍,引发多少家长里短,爱恨情仇,多少欢乐多少愁,无一刻无矛盾,罄竹难书,一朝放归水银泻地,在城市各阶层安身立命,引动多少汹涌琐碎的话语,多少肺腑的感慨。」
《碗》读后感(三):短评写不下了
#祭奠,是一次发呆 《碗》金宇澄。2018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定价42元。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薄薄的一本,阐发了无数久远的“青年万岁”。“广阔的北方原野,与沪西密集的棚户屋顶,都存放在你的记忆里。”金先生把他日日夜夜的心中戒惧,萌蘖日炽的悲哀,都集中了非虚构的故事里。读毕,分不清散文和小说,只记得一句“青年万岁”将东北和上海拉得很近,松嫩平原上那口30米深的北方小井里,除了失足跌落的白鸭,还有两具女人单薄的身体。她们曾经执拗,充沛,吵闹不止,纠缠,撒泼,与男友争执不休的女人的身体,再不动弹,腐烂的脸上长出细细白毛。“相逢问姓名亦存,别时无子今有孙”比尸体还年长几岁的孩子,除了谙熟烧纸钱的流程外,只剩下苍白得如北方天空一般的想象,还有抽抽的哭泣。 在那个年代,青年精力旺盛,也极易死亡。老妇在雨后采菇,发现了一具悬颈往生的男青年;两位天津青年,在地里偷瓜,被巨雷击毙,埋葬于此。一对恋爱男女,躲在麦草垛里谈情,结果被拉网收集大草堆的两部履带拖拉机拖死。“他们归于泥土,融入泥土,坟头平缓模糊,四周安静寡淡,年复一年,野花盛开,草虫轻吟,寒风凄号,冻雪满天。这个死亡所在,集中了故事,埋葬了呼吸。”青年们可以塞入棺材的物件有扑克牌,镜子,木梳,红皮语录本,这是一位17岁的上海少年,刚来几个月,即被土锅炉炸死。这是曾经的故事。 “他们一生都牵扯谈论这种种的复杂变数和感想,分崩离析,尔虞我诈,栏杆拍遍,引发多少家长里短,爱恨情仇,多少欢乐多少愁,无一刻无矛盾,罄竹难书,一朝放归,水银泻地,在城市各阶层安身立命,引发多少汹涌琐碎的话语,多少发于肺腑的感慨。” 金先生是记录他们青春,集体,艰苦回忆的人... 他时而梦呓:“我只愿你们,人神合乐,男的忘了耕,女的忘了织,安稳静好,别再念想这个世界。”对的,关于死亡和坟墓的主题就说到这...“记忆有时会使人不懂了欢喜,也不知忧伤,它只是痴痴的一种神态与表情。”
《碗》读后感(四):黑洞的世界里没有配角
■刘海涛
老井水鸭女生/辘轳天空马灯/坟墓长铺饭堂/日落日升/上海人在北方。
这是金宇澄非虚构作品《碗》和小说《苍凉纪念日》让我想到的一个场景。从远方走来,带着“断肠人在天涯”的煞气。但金宇澄突破了我直觉的窄化执念,让我去思考两篇时间相差20余年、题材相同的作品的不同之处以及其背后的隐喻。
“记忆有时使人不懂了欢喜,也不知忧伤,它只是痴痴的一种神态与表情;不饥不渴,不以物喜,不为己悲,你想一想要说什么呢?”《苍凉纪念日》这个开阔的结尾与《碗》祷祝的结尾形成一个鲜明对比,那些记忆并未真的成为作者心灵的过客,反而拉着读者一起进入记忆的隧道。
或许记忆有两种功能,一是让过往活在自己的生命里,二是让自己活在记忆的过往里。而回忆,让这两种功能合体并发芽,或滋生出新罪以解除记忆的绑架,或成长为功勋以解除记忆的拖累。显然,在这两个极端之外可能还有第三种情况,那就是金宇澄的《碗》和《苍凉纪念日》,投井的两个女人小英和阿桂,用死亡映照了当时与后来人们不同的心境。尽管蒙太奇手法的闪转腾挪尽显作者想置身事外的飘然与超然,但不经意间还是让“轻飘飘的旧时光”变得沉甸甸。
有如黑洞,记忆与回忆强大的吸引暗力错乱了经历者。那个时代,虽然很近,但对于后来人来讲,只构成一个具有代沟意义的具象(小英女儿的反应就是一个例证),一次穿越,看到了黑洞中那苍凉的远方,一群人、一片天……
同样场景的爱情、同样命运的女人和男人、同样的一口老井、同样的死亡结局,同样地被冷漠处理。
不同之处在于,同样是死亡,《碗》给出了死者的死因。这个固化了的死因,涂上了具有塑形时代的特定颜色;或者说其指向性缩减了死者的死亡意义,其“定因”之死只是让后来的我们有了物化的形式上的追祭理由。《苍凉纪念日》则不然,可以说死者是“无因”而死。正是这个“无因”之死,让我们对死因有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从特定走向寻常。之所以没有写死者的名字,是为了彰显其无名者大众化死去的普遍的“基本意义”,与寿终正寝一样,更适合大众化的死去原理。却因其轻微而反刺于我们。
作者笔下反复写到的几个意象:井、鸭、天空、碗、坟墓、女人、食堂,如散文诗,极具画面感。在所有意象中,或者说那一代人经历的过往中,作者选取了“碗”这个我们司空见惯、每天使用的物件作为小说名字,他要给我们盛的是怎样的饭呢?——“青年万岁”。
六次不同情境下的“青年万岁”,构成一首“行走”的诗、一幅流动的画。每一个情境里,都抽去历史的阴影,只留下舞台中央一群历史追光里的人,并在谢场的大幕拉起时,变得模糊。但“青年万岁”的能量与光芒,让记忆的黑洞释放其特质化的“暗物质”,并与黑洞世界里的每一个粒子——意象,发生纠缠。
这种纠缠的珍贵之处在于,它让那个年代的经历者与未经历者有了真实的链接。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虚化、弱化了时代这个底色,把亮丽的青春——人们共有的生命特质,嵌入到一段人人皆可复制的岁月里,产生超越特定年代的通性与珍视,从而在情感交融与理性认知过程中,巧妙地剔除了代沟。
《碗》和《苍凉纪念日》可以说是金宇澄的“青春文字祭”,以“碗”为载体,让我们与上一代的生命相遇。
“唯一的水井被污染……我们也都知道了早晨的圆白菜汤,是用浸泡阿桂的水做的……我们都像是吸收了阿桂的某些物质,这是很难改变的。”《苍凉纪念日》中,作者这段描写似乎隐喻了我们的灵魂在命运交错中终究会被注入一代人的基因——井是现实中的黑洞,记忆是灵魂的黑洞,二者归一于生命中相遇的主角。
正如金宇澄所说:“文学就是一只碗——记忆的这只碗插上一根筷子,作者跟它说话,让记忆安抚,让记忆平息,让记忆释放,让记忆自由。”我想这“让”的动力源应该就是黑洞世界里的那些纠缠。黑洞的世界里没有配角,我们都曾是被“黑洞”滋养过、吞噬过并最终活下来的人,而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碗》读后感(五):揣测让叙事无限诱人
(刊于《文汇报》2018年10月11日)
文/俞耕耘
在金宇澄那里,非虚构和虚构的意义分野,显得并不那么重要。《繁花》《回望》外,《碗》《轻寒》《方岛》,让我们对作家认知更为丰盈。他游走移借文类的才能,使你完全可把《碗》当第一人称小说来看。《轻寒》的故事主体前,加上“0”的序章,其中又出现了第一人称“我”。这样,故事的全知与开篇的“我”形成了吊诡。《轻寒》的情节线索朦胧隐约,在本质上是象征和印象主义气质。它被气味、光线、情绪,弥漫推动。不刻意追求明晰线索,完整故事,全用散文笔法托出抗战时江南小镇的压抑躁郁。在一个腌货铺里,错综复杂的欲望关系就像光线交汇。
七官虽名为老板“寄女”,却给老板宿夜陪侍。不断上镜的“夜壶”,反复的暗示,让故事隐而不发,“低气压”犹如台风之眼。老板和女佣阿才偷情,七官对阿才的同性忌妒,伙计寿生对七官的窥视觊觎……作家的情欲叙事相当克制。腌肉铺成了中心隐喻:它是肉的陈列堆放,与人物肉欲天然联系;腌肉的咸味、霉味,是故事挥之不去的气息。七官所恶心的,是鲜活之物被压在腌肉之下,沾染了味道。那是对生命活力的侵蚀腐败,正好暗合敌军对小镇的蚕食。
金宇澄留下的故事真空,成了小说的诱人秘境。老板和女仆的相继失踪,是否是场设计?寿生对吃了晕船药的七官,中途做了什么,为何多出一脚泥?尼姑们被镇里送给日军,因为她们没有男人。献祭的场景,哭喊散溢在平静的河道桥洞间,结局如何?小说反复提及的地藏王菩萨生日,似乎是个答案,它在超度亡魂,也在超度故事。《碗》这部非虚构作品,延续了小说的悬念,但这是真实的“限知感”。作家重述了在东北嫩江农场劳动的亲身过往,人情物事。女青年小英死于井中,生前产下一个女婴。几十年后,女孩随上海的爷叔阿姨、纪录片摄制组北上,寻访母亲墓地,作家记忆之河也开始流泻。
“青年万岁”是《碗》的一个主题“扣子”。整部作品可谓金宇澄版的“致青春”。青春总有些许苦涩悔意,无奈轻愁,否则,反倒不值记忆。金宇澄并没使用知青称谓,而始终以“小年轻”、“青年们”来看待,这避免了集合化、断代式的符号表达。其实,这也达成了另一种期待视域:追求跨时空的情感共同体,让不同代系的青年都能与作品对话。
作家有种独特的时间意识,那是一种滞留感,让过往和当下弥合了时间差。“他(她)们当年的相貌,都比眼前这个女儿更年轻……”“刻舟求剑”式的时间观,在这里恰好成了善感的艺术知觉,超越随年月俱老的物理时间,实现了不同空间的并置。所以,女儿和母辈(老人)间的隔空对话,演绎成两代青年的通感照映。
小英投井事件,是“非虚构的限知感”带来的强大能量。作家确实不晓得背后缘由。但正因如此,它看上去就像一部优秀悬疑推理的开篇,在提供一切可能。小英就是故事的岔口与回路,以她为原点,记忆就可流溢、映射、折返、凝缩。北方纪事是记忆的重返,上海与东北嫩江人事交织穿行,让整个时空都显得破碎斑驳。
“如此交叉两类人群的记忆,正是本文特点”。“让所有的内容都融入记忆好吗,上海与东北融合在一处,上海闪亮的鼻尖,耳朵背后的污垢,广阔的北方原野,与沪西密集的棚户屋顶,都存放在你的记忆里”。是记忆,就有暧昧处,犹如自带“滤镜”功效:它模糊、容易虚饰、甚至有聊以自慰的温情。无数旧面孔就像录影带浮现:教我们干农活的张某,善修烟囱及捕鱼。在音乐里意气风发的老杨,见了农场干部就立马“前倨后恭”。林德的同乡,临终前仍期待一口甘蔗水。
金宇澄的叙事总有一种迷恋,那就是“杳无音信”和“有去无回”,它就像内陆河,半路蒸发。《碗》中汇聚了很多断片儿的事,没后文的人。如果用故事类型学的眼光看,它们原本就是同一个故事。老杨被征调,曾嘱咐三个月后一定回来,完成那把手制吉他。然而,“未完成的琴,一直挂在工具房土坯墙上,老杨再也没有出现”。纪录片制作者S的小电影在中东获奖,“我给S电话,望他寄一个碟来。S抱歉说,怎么是寄过来,一定是要亲自登门,送给老师的。但至今数年过去了,杳无音信”。林德回粤探亲,上海青年让他代买荷兰式皮鞋,最后也打了水漂,老林不知所踪。
所谓的“非虚构”,并非排除想象,不能虚构,而是明确告诉你――什么时候“我在”虚构。正如太史公也在想象,项羽曾经“泪三行”。金宇澄的纪实边角是悠游补笔的“小说家言”。揣测甚至比纪事更丰腴,它颇具肉感。作家竭力幻想老林或偷渡香港,或遇了海难;或买好皮鞋,确实托人寄回,只不过受托者出了岔子。这种想象,恰是作家对老林的一片信任和追怀。
记人的简约,忆事的疏淡,往往是线描艺术,勾勒印象。这与金宇澄的“插画艺术”形成顾盼映带。插图和文本,构成意义的“增殖”与“补位”。一方面是视觉化的写作,另一面是叙述功能的图像。金宇澄并不看重色彩、造型的技术性,而是在意线条力度、构图布置背后的观念性、象征性。换言之,他追求有意味的形式,最具包孕感的时刻。因为他深谙,画面本身是一种话语,是“及物的”力量。插图里人物常常缺席,就像新小说派对客观“物世界”的兴趣,只不过画风却如此表现主义。
作家把晕染功夫放在了场景、环境的“复盘”再现上。在材料调度上,他也完全吸收纪录片的剪辑效果,“我”始终在导演监控室观看,就是暗示。“观看之道”重组了叙事意义体。《碗》的写法也是影像的拍法。1970年代,黑夜里练胆比试,手提马灯,穿行坟地的集会,以火光为主,“口味野重”。30年后,上海的老洋房大门口,巴洛克门廊、西洋水池、法式精致花园、罗马立柱,“周围同样是黑沉的夜”,“只是深重磐石般的黑暗,看不见巡游青年的身影”。
恍兮忽兮,隔世遗梦,是作品的调性色系。作家有种焦灼,那就是如何面对记忆与现实的错位不适。记忆既是确认青春的明证,也是难以承受的负重。碗里的筷子不能总直挺挺立着,该倒下就要倒下。它意味爷叔阿姨们试图解脱放下,实现“复位感”。某种不能承受,本应归于尘土。
直到故地重游时,出行方式又使“爷叔阿姨”分化出:“飞机帮”和“火车帮”。作家别有意味写出聚会的反讽――如今地位财富悬殊的人们却“共享”青春记忆。时间惩罚了那些“吃情怀吃交情”、靠记忆老本“反刍”之人。富人却想淡忘,对他们而言,记忆如“他者”。《碗》是遗忘与记忆纠缠之书。没了它,人也失了青春存在的照见;回望它,又有持久的不忍。作家想做的是安放它、叙述它,给予一种安然的遥远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