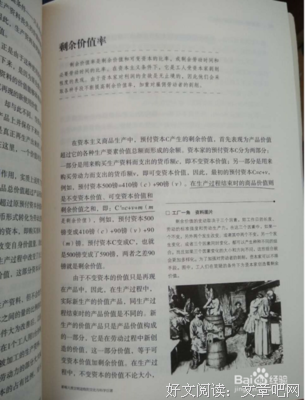《带一本书远离人群》读后感100字
《带一本书远离人群》是一本由思郁著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带一本书远离人群》读后感(一):带一本书远离人群
书名很好听。让我想起,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诗意的生活很令人向往。带一本书远离人群。那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需要远离人群。进行深刻的阅读。充满扑朔迷离,很让人臆想究竟。那是一本。指引我们旅行的书吗?还是一本励志的心灵启迪。幸福的生活,精神的丰满。能带给我们的是一场思想的进步,文明的洗礼。对生活,充满爱的自信。
《带一本书远离人群》读后感(二):轻松有趣的小书
关注思郁的各种文字至今,我的评价是:一个真诚深刻的思想者,不耽误兼任收集八卦的小能手。严肃点说,当我们多数八零九零后终日为生计前途奔波,睡前餐后的一点精力又被各路心机叵测的头条和快手分食,好在还有这样的同行者,默默守护人类智慧和文明的一点点烛光,耐心地帮我们拨开真理之路上的层层迷雾。看纽约时报的文章时我也常会有这样的感慨,这大概就是知识分子的魅力所在吧。
比起思郁以往的长篇评介,这本书里的文字多数短小,轻松有趣,文人艺术家的秘闻八卦居多,又有作者睿智的评述不时闪现其间,整本书最后部分的影评就比较深入,思辨趣味也更浓些,跟作者的给我的印象更接近。这样也好吧,先来点开胃菜轻松一下,再看烧脑长评就不会觉得太累。
不足之处大概是个别篇章别字稍多,好好校对一下应该就好了,还有个别词句也许可以再推敲。另一个感受就是书的封面封底和内容三者给我一种无法统一的感觉。看过书的内容后,强烈感觉书名好怪,虽然有扉页上的一句话连接了书名,但是跟书的内容并没有什么连接啊,真想带着这本书远离人群的读者可能要失望了。还有封底上提到的大时代,是什么大时代呢?是书里各类人物生活的时代?还是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
《带一本书远离人群》读后感(三):来自粉丝
关注思郁很久,见识他“想读”书目之多之广,一直作为读书方面的向导。在我标记的仅400多本已读里,有300多个共同喜好,看起来同步率还蛮高的。但是翻阅过后,还是阵阵冷汗,我知道的真是太少了。
不得不说,这本书对读者的要求颇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是对读者阅读量的检验。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本书拉近了我们与作家、与文学、艺术和影视作品的距离。要想参透这样一本书,也确实能达到书名“远离人群”的目的。对于我而言,遇见自己看过的片段会欣然称道,未接触过的也能从中略知一二,也算有所收获。可能是碍于出版篇幅所限,对于自己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又觉得不过瘾。所以整个阅读体验就是针对作品各抒己见的交流,也会常常感叹为什么生活中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虽然打着“猎奇”的名号(“关于作家和书记的古怪记录),但作者为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提供了另一种更全面的视角。即使是身为贪得无厌的读者,也深深清楚精力有限,并不是每本书都能亲自阅读。对于像乔伊斯的天书、或对厚部头的《追忆似水年华》望而却步的读者而言,可以从这些趣事和评论入手窥得一二。
有时也会很困惑,对待文学/影视作品,如何看待创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一个有着出色作品的人,可能在生活中并不道德,比如王尔德;一个喜欢掉书袋折磨读者并自鸣得意的人,可能生活中喜欢抖机灵,比如艾柯。这些趣闻轶事除了充当谈资,对研究作品本身是否有真正的意义?还是评论本身也是作品的一部分?
思郁真的很低调,整本书一丝不苟地配上插图,却没有公布自己的照片。
直到读完《后记》,我原谅了作者和这本书。天知道从网络文字到一本书要经历哪些,他做到了我只是想想但从未付诸行动的事。
:虽然英文书名<Gone with the book>会让人想到《飘》,私以为换成<Gone with a book>可能会更贴近中文名。
:从作者阅读的数目来看,其实有更高的期待,虽说已经很了不起了,但这样的阅读量写这样的评论可以说是“高射炮打蚊子”了。期待以后更有深度的作品。
《带一本书远离人群》读后感(四):当我们谈论阅读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带一本书远离人群》文/文小妖
不知不觉,在豆瓣上关注思郁老师很长时间了。有时候,闹书荒,会点开他的豆瓣页面,小坐一会儿,看看书评,顺便去寻一寻能勾起阅读兴趣的书,然后,买之,再沉浸其中。
得知思郁老师的新书《带一本书远离人群》出来时,真是让人期待。
爱书之人谈书事,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水到渠成。《带一本书远离人群》亦是一本关于书事的集子,全书总共分为三辑,前面二辑记录了关于书与作家的种种,第三辑则是书与电影相辅相成的记录。里面谈论书,谈论作家,谈论那些环环相扣的书事,几乎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围绕着书籍展开的。
众所周知,“一百个人读《红楼梦》,会有一百种观点”。每个人对书的解析和感受亦是如此。读思郁老师的文章最大的感受就是,他可以对一本书或一个作家的评论做到纵深拓展,往往让读者能从中读到更多的知识点和信息,对该作家及作品产生极大的兴趣,勾起阅读欲。
曾有人提出过,读书最好去读原版书,何必去看别人的评论和观点呢。话虽如此,但在我看来,原版书必然要读,可是也别人的观点和评论也是可以看一看的。因为,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收获到另一种解读方式的同时,也可以加深对本书的一些理解。更何况,某些眼光特“毒”的读书人,总能在书中看到很多一般读者所看不到的内容和暗语。我想,思郁老师,大概就属于这类眼光比较“毒”的读书人吧!
《带一本书远离人群》里的文章,可读性极强的背后隐藏着思郁老师的阅读量之广博和多年来的思想凝结。他熟悉西方文学,谈及许多文学大师的事迹如数家珍。尤其第二辑《藏书家与偷书贼》中的文章,人与书之间的爱恨情仇跃然于纸上。比如,被书贩子骗去买了一批色情书籍的藏书家迈克尔·津曼先生,捐赠了这批数量可观的色情书籍后,因祸得福,反而拥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藏书室;再如,我们都知道泰坦尼克号事件,却不知道在这次灾难中,还有一个令人动容的藏书家的故事;再如,人们都知道书是人类的灵魂导师,大多都是引人向上的,然而,有的人却为书而痴狂,干起了杀人越货的勾当,西班牙藏书爱好者唐·文森特为了一本心仪已久的孤本书,不惜杀人放火,伤害无辜生命……这些关于书的故事,若然不是在《带一本书远离人群》里看到,我想我大概不会了解到这么多有关书籍的新鲜事儿,真是让人涨知识了。
书中,思郁老师曾写道,“我们读过某个作家,然后按图索骥,晋升到了更高级的阅读阶段,进入了一个更为澄明的阅读境界,阅读的熏陶让我们成为一个贪得无厌的读者。我们所有的欲望只有在阅读中才能光明正大地伸展和膨胀开来,阅读是一种名正言顺的贪婪,喜新厌旧是阅读的合法诉求。”这段话戳入内心,引发共鸣,大概这些就是爱书人之间的小小暗号吧!读完全书,意犹未尽。反而期待还能再看到思郁老师带来更多的书事,供我们选择和提炼自己喜欢的书籍。
《带一本书远离人群》读后感(五):不必自命清高,但求怡然自得
想起十几年前,余秋雨在《山居笔记》的自序中曾说:对于探寻中华文明,写作的最大困难,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烦,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淬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这种焐化晦涩之冰的温度,从浩瀚繁多的典籍中一一捡拾并记录灵光一闪瞬间的执着,多年后我在思郁的专栏评论集《带一本书远离人群》中尤为可感。
因为是专栏的合集,所以篇幅都不长,但思郁以自己广博、循次渐进的阅读为线索,从欧洲到美洲,从西方到东方,快活地游弋在外国文学的版图上,搜罗着作家们的奇闻逸事和八卦怪谈,或如本书封面所称“关于作家和书籍的古怪记录”。总之,跟随思郁游弋而收获乐趣的过程,我们可以过足一个普通人对于俗世谈资的瘾:“社交名媛”奥斯卡·王尔德秉持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的信念,不断通过冒犯社会名流为自己制造上头条的话题;法国著名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在自传《来日方长》中,巧妙得利用受害者无知无畏的角度,为自己无缘无故勒死妻子的罪行用抑郁症开脱;而我们熟知的说故事的高手毛姆,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更惊人的是,与其说毛姆是为了说服自己,不如说是为了欺骗自己,而偷偷去找了一个女人,之后不幸地染上了病;还有纳博科夫背后伟大的女人薇拉,诗人里尔克靠女性资助的一生,等等。
作品和书籍之外的作家,当脱离了文学光环和奖杯头衔的美化之后,也可能会真实得暴露出一个普通人不为人知的癖性。不过,大作家也是人,历史既然已经演变发展至今,单从人性的缺憾来说,再多的苛责也无济于事。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更愿意和思郁一样,在无穷无尽的史料典籍之海,在世人约定俗成的意识理念之外,捡拾被主流价值观轻易遗弃、显得不那么登得上大雅之堂的片羽碎金,自由得发掘出一个不再束之高阁,更有人性温度的作家世界。
不过,“片羽碎金”只是一个作家完整真实的一生里一块不可或缺的利于评价的金石,它不是目的,也不是结果,更不是因了这片羽碎金的琐碎就可以否定掉一个大作家一生的文学成就。说到底,它其实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更为完善和全面的视角,去洞彻一幅如蒙娜丽莎般只能远观不可亵渎的画像背后,种种不为人知的秘密,秘密发现之后是惊喜是失望,是多加一份向往还是徒添一份烦恼,在你自己的书籍和思想堆砌的围墙之中,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在这一方面,说书人思郁的探寻,不敢谓之完美,似乎也不免有缺憾之处,但的确是不失偏颇的。纵使一件奇闻逸事背后暴露出的是怎样的让人不舒服的现状和人性,思郁的笔下也始终没有没有莽撞的批判和讽刺,反而是敏锐的看法和评论不时闪现其间,丢弃了掉书袋式的故作深沉,有时还夹杂着有趣的调皮。总之就是地简简单单表明,这是我的评论,就是我想与作家或者读者的对话,这一幕在《作家给总理荐书》中尤其应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作者扬·马特尔为了让当时的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重塑对阅读重要性的认知,每隔一周都要寄一本书给他,然而四年过去了,这个在公开场合表示最喜欢的书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总理,几乎没有亲自回信给马特尔。阅读的重要性,一个国家总理尚无一丁点看好,更何况城墙外的普通人呢。思郁在这里无可奈何,却也是克制得评论道:
阅读并不能改变什么,阅读对生活最大的改变只有那些真正喜欢读书的人才能领会,而且这种心领神会往往无法成功分享给没有这种阅读体验的人,与其这么多好书分享给一个丝毫不懂得阅读的人,不如分享给更多的读者。所以这个寂寞的读书会在四年之后无奈封存,也在意料之中。
相比于思郁分享给我们的读书会,明显我们眼前书本里的读书会就热闹多了—东西方作家怪癖大碰撞,知名作家小众作家奇闻相交融。但是这个热闹的读书会,可能是因为篇幅所限,好几次让我大呼不过瘾。为什么著作等身的马尔克斯,思郁以一句“就算他写了再多的作品,人名津津乐道的,还是《百年孤独》”,就草草了事了马尔克斯传奇的一生?在《毛姆是几流作家》,思郁不惜笔墨得赞同和认可了毛姆的写作天赋和适时的成功,但是对于毛姆在作品中常常表露出来的“毒舌”有趣的一面,却只字未提,让我深觉遗憾。
诚然,如果联想到我在文章开头所述,也如为此书作序的曹亚瑟所言:当我拿起一本书,有时候只是为了彻底读懂其中某一章节,甚至还得同时翻阅其他二十本书才行。那么《带一本书远离人群》让人轻松愉快的背后,是作者翻阅、消化多少古今史料才呈现在我们读者眼前,可想而知。其中的艰辛和执着,值得每一个愿意走进阅读的世界,并且愿意长久得与阅读为伴的人学习。
《带一本书远离人群》读后感(六):《带一本书远离人群》后记
2013年,我在媒体上新开了一个专栏叫“妩书媚影”,最初的构想是以当时的阅读为线索,以观影为辅助,写写文坛和影史八卦。专栏文字都不长,千字左右的篇幅,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多,也积累了十多万字。这本书的原型就是出自这个专栏。
专栏写作有它自己的特点,比如迅疾的语速,零散的思想,匆忙的判断,流于表面的抒情,短暂的时效性,等等,这些都容易为人所诟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专栏写作同样不可或缺,我们不但需要某种精神上的指引,还需要分享某种阅读经验,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思想并不孤独,需要在这种媒体平台上完成某种阅读和写作对话。这就是我专栏写作的初衷。
时隔几年之后,我打算把专栏文章集结出版,重新翻阅那些短小而不精悍的文字,突然发现了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几乎每一篇都有可以扩展的空间。当文字脱离了篇幅的限制,发表时候的语境,几乎所有的短板都暴露了出来,恨不得重写大部分篇章。大概这种分裂的心态在这本书中有很清晰地体现:一部分文章保持了专栏文章的原貌,另外一部分文章进行了大刀阔斧地修订——我希望这种修订不是画蛇添足,狗尾续貂,不是多余的饶舌,不是废话提炼机。最理想的情况,我希望它能满足不同阅读层面和阅读需求的读者,这大概是每个写作者都奢望达到的完美情况。
这才是我的第一本书。严格来说,它只能说是我阶段性写作的一个总结。而且这种总结有时候很让我觉得很尴尬。比如,翻看以前的文章,我们总会有不同的态度,有时候觉得以前的文章写得太糟糕了,还不如不出版,有时候会恍惚觉得现在还不如以前写得好,这只能说明我们没有丝毫的进步,还停留在顾影自怜的阶段,这种情况就更糟糕了。所以最好的状态就是不要总结,继续写作。瓦尔特·本雅明有句话就让我很赞同,他说,绝不要停止写作,因为那样一来你就再也不会忽然想起什么了。只有不断地写作才能保持我们对语言的敏感,对经验的提炼,以及对写作本身的敬畏之心。
但是,我还会为自己的这本书做一个简单的辩护。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写作者都有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源自瞬息万变的环境,也源自我们内心对外界变化的某种不适应。这个时代除了变化是不变的,几乎没有什么是恒定不变的,我们被裹挟着,踉跄着行走在变化的途中,还来不及细细体味这种变化的细节,就被拖着观看下一幕的场景。我们的经验来不及总结和梳理,更不用说提炼出某种文字可以恰如其分地概括这个时代的精神。
十几年前,我拥有了第一部手机,可以打电话、发短信,就觉得是步入了智能化时代,现如今谁还记得自己的第一部手机什么样子?不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是想象力限制了我们的未来。现在的生活基本已经数字化,我们的阅读体验更是如此。试想不远的将来,我们说起家藏万卷书,邀请同好者去参观的时候,打开房间,最尴尬的一幕出现了,空荡荡的书架上只有一台kindle电子书。我们现在的写作带着一种紧迫感,把自身视作最后一代纸质书的爱好者,无论我们买书,读书,写书,夸张点说,都多少带有这种虚妄的责任心。出版一部纸质书,就能留下一点阅读的印记,仿佛就可以让纸质书的消亡延缓一些,再延缓一些。我们不想被裹挟成时代的人质,梦想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者,用写作的形式,留下几行文字,几本书,可以记录和描慕一个匆忙而未定型的大时代的幕景。
一本书出来,我们只能看到作者的名字占据书页的中间,好像他是唯一的付出者。实际上除了作者,还有更多为这本书作出贡献的人,照理应该感谢他们的付出。先是要感谢我的好友曹亚瑟为这本小书作序。亚瑟君是我的老大哥,在报社担任要职,公务缠身,却从未放弃他的阅读兴趣,家中藏书两万余册,业余研究《金瓶梅》,一手美食,一手美色,擅长双手互搏,多年来勤奋如是,已经出版了不少专著。我在郑州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几年,如果说有好友可以对谈畅饮,自然非他莫属。他自然是为我的书作序的不二人选。
感谢我的编辑罗丹,感谢她不断地督促,细致地帮我修订文稿,给了我很多良好的建议。要说起来,我们也是老朋友,旧相识,早些年她在北京做出版,后来她南下到了广州,仍然从事出版行业,我们也一直保持着联系。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缘分,每位写作者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都想找一位可靠、熟悉、值得信任,可以托付的好编辑。我很荣幸第一本书就能找到这样好的合作者。
最后,要感谢自己的父母。很惭愧,三十多年来,我大概是家中最不省心的孩子,从来不按部就班地工作,结婚,生子,过稳定踏实的生活。我很讨厌被安置好的生活,总想跳出常规,按照自己内心的意愿选择。我的任性即使没有伤害到他们,也总会让他们担忧我的未来。幸好,他们的包容,给了我继续下的勇气。这本书如果能献给他们,我希望这是最好的礼物。
还有其他为这本书付出的朋友,我会一一铭记于心,恕不赘言。
思郁
2017/11/24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