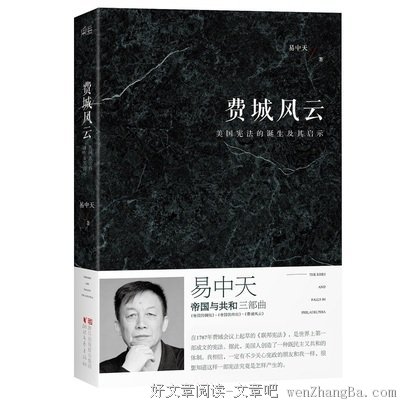《费城风云》经典读后感10篇
《费城风云》是一本由易中天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2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费城风云》读后感(一):没有统一的合众国政府是不行的
最早推荐这本书的人是毅鸿,他说易中天最值得推崇的就是这本书了,他看了足足好几遍。听完这样的推荐,对于百家讲坛向来有偏见的我来说,拿起易中天的书来看,实属不易,自从推荐以后至今,已经过去了两三年。
当然,松散的结果是,一个组织分崩离析,无法长期运作。而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各个邦联松散存在的结果就是,一来,无法应对战争,二来,外交上没有话语权,不被承认,三来,无法面对债务问题,更无法征税。易中天在书中就举了无法面对债务问题这一点。
美国要打独立战争,打仗就需要钱,虽然有了一个临时政府,能够向外借钱,但毕竟也只是临时的,战争结束了,也就没啥用了。但钱不能不还啊,可是,没有统一的政府,谁来组织大家还钱?谁该对债务负责,如果没有负责,无法信守承诺,那么如何让下面的每一个债务人相信呢?
想要一个统一的政府,说来简单,但具体应该怎么做,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倒推的办法,看看怎么办。
司法权、行政权、立法权,说起来容易,但人家《联邦条例》明明规定了,不要设立法庭,不要总统(行政官员),那如何设立司法、行政权呢?当然,在今天,很难想象,不设立法庭会是何等景象。但在当时,大家觉得,既然是松散的依靠契约建立的邦联,要什么司法权呢?来去自由嘛。于是,问题还是出在《联邦条例》上面,必须修改联邦条例。
修改条例,说起来简单,但这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制宪人,凭什么有权力修改,如果他们有权力修改的话,人人都有权擅自篡改条例了。于是乎,问题就出在,到底应不应该有一个立法机构?好吧,那就设立一个立法机构吧。但是每一个邦联有一个自己的立法机构,你联邦政府凭什么高于我们,凭什么我们要服从你呢?
总之,松散甚至无政府状态是不行的,唯有统一的全国政府,才行。
《费城风云》读后感(二):碎了一地的契约精神,不也创造了奇迹吗!
佩特森指出,召开本次会议,是根据邦联议会的一项决议和各邦议会的授权,而邦联议会的决议和各邦的授权态度都很明确,就是修补和完善邦联。因此,《邦联条例》是本次会议全部议程的适当基础。我们应该恪守这种限度,否则我们的选民就会指责我们篡权。最后,佩特森义正言辞地指出:美利坚人民正拭目以待,不容欺骗!——费城风云
《费城风云》读后感(三):【笔记】弄明白了,再说怎么学
谦抑
富兰克林:活的时间越长,就越相信是上帝在主宰着人间的事务;而会议的进程则证明,人的悟性绝非完美。
理想是有的,但不宏伟;主张也是有的,但不绝对。不宏伟,就能务实;不绝对,就好商量。
总统是美国人的发明,英文为President,和俱乐部主任是同一个词,意思是主管(参议院议长也叫President,意思是“主持人”;众议院议长则叫Speaker,意思是“发言人”)。
建国领袖都是些务实的人,不是书呆子。因为这些人不但没有坚持“必也正名乎”,而且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的做法。比方说,为了提高效率,先讨论大家感兴趣或者有可能取得共识的问题。讨论够了,就表决。成熟一个表决一个。如果不能取得共识,就先搁置起来,以后再说;而一旦得到共识,则表决存档,并作为下次讨论的先决前提。也就是说,摸到了石头,就跨过去;碰到了暗礁,就绕着走。先易后难,先求同后存异,一步步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 正因为他们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理论”,反倒比他们有文化的同胞(英国人)和有理论的朋友(法国人)干得更出色。
一个职务,如果既体面荣耀,又大权在握,还有利可图,那就足以让天上地下的人都趋之若鹜。这会是些胆大妄为、无所顾忌、为追求私利而百折不挠的人。
程序
会议过程中改变观点是常有的事,一旦这些证据公诸于众,会议就会显得矛盾百出。
妥协并不一定消极,也有可能产生积极的结果。 妥协并不等于放弃原则,更不等于没有责任感。政治妥协的原则底线。 这个底线有三条:第一,制宪会议不能一事无成;第二,国家不能分裂,必须联合和统一;第三,联合和统一不能通过战争,只能通过谈判。而在梅森等人那里还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尽管为了国家的统一,必须建立一个“全国最高政府”,但决不能因此而侵犯和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梅森他们看来,这是比前面三条底线更基本也更重要的底线。
简单的东西未必简单。而且,唯其简单,才是真理;也唯其简单,才可坚持。真理从来就不是什么天花乱坠或者高深莫测的东西。它应该是人人都能明白,人人都能掌握的。同样,唯其简单,才是底线;也唯其简单,才可坚守。底线弄复杂了,就弄不清,也守不住,最后只能是不再成其为底线,或者不再有底线。相反,如果底线简单朴素,大家都明白,也都能守住,剩下的事情也就都好商量,都可以放到实践中去检验和调整。即便有错误,有瑕疵,也顶多只是走些弯路,惹些麻烦,不至于动摇根本,酿成大祸。
承认各邦主权平等,起源于将契约和条约混为一谈。条约是一些特定的义务,契约则创造一种授权。
尽管费城会议的分歧表现为修约与制宪之争、邦权与民权之争、集权与分权之争,但归根结底,其实是席位之争。 分配席位的尺度是人而不是财产。全国议会的席位分配问题,影响到大邦和小邦的关系,最后很可能还是需要相互让步。所以,费城会议前一阶段的争论,也可以说是大邦与小邦之争。 态度微妙的是那些中等邦。
要使一个政府有效,就必须赋予它捍卫自己的能力。要使组成政府的各个部门有效,每个部门也必须能够自我捍卫。
把权力授予少数人,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受多数人摧残。
议会两院,一院代表人民,一院代表各邦。
绝对的权力必定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专制,哪怕这一权力来自人民群众,或者掌握在正人君子手里。民主和道德并不绝对可靠。民主完全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道德则很有可能导致“理想的暴政”,由理想中的“人间天堂”变成实际上的“人间地狱”。靠得住的只有法治和宪政。
人民的权利并不等于公民的权利,尽管人民是公民的集合体。但正因为人民是公民的集合体,所以,人民的权利是整体性的,公民的权利却是分散的,属于每个个人的。整体的权利并不难得到保障。因为总统毕竟在名义上是人民选举的,议会在理论上也是“民意机关”。公民的权利就难讲了。立法机关作为“人民代表”,完全有可能以人民的名义侵犯和剥夺公民个人的权利。
国土
邦联如此不像国家,议会如此没有威望,不成体统倒在其次,没人负责却是麻烦。
争论的焦点不但在于权力的基础究竟是邦权还是民权,也在国家的体制应该是共和国联盟还是单一共和国。或者说,是邦联(confederation)、联邦(union),还是单一制民族国家(nation)。
“全国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这个称谓,改为“合众国政府”(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这不是文字游戏,也不是偷换概念,而是建国理念的重大变化。它意味着国权主义和邦权主义心照不宣的暗中妥协。因为几乎所有的代表都意识到,邦联制和单一制恐怕都行不通。他们为未来的美利坚合众国设计的,将是一种新的国家制度── 联邦。
为了控制立法部门,你得把立法机构分解;为了控制行政部门,你得把它合一。因为一个人会比三个人负责得多。三个人就会彼此争雄,直到一个人主宰另外两个人为止。
制宪代表是既要防腐败,又要选人才,因此两难。也因此,舍曼说,最好是既有足够的吸引力,使人们愿意担任公职,又不能让这个职务变成诱惑。
国力
一个人的生命比一百吨炸弹更珍贵,这就是美国的战争理念。美国人有着“一贯珍惜生命的传统”,即对人尤其是对人的生命的态度,在历次战争中都是人员伤亡最少的。伊拉克败给了美英联军,其实也就是以苏联为首的武装集团败给了以美国为首的武装集团,美国的战争理念战胜了苏联(也包括苏式的)战争理念。
人权也是国力。对人权的尊重,对生命的珍惜,都将直接转化为创造力、生产力和战斗力。“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
对中国人来说,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是臣民的义务;而对于美国人来说,则是个人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当然,不是说你想当什么就能当什么。但,第一,你有权去想;第二,如果被任命了,你有权去当。你可以放弃这个权利(辞职),也可能因为玩忽职守等原因失去这个权利(撤职),但不能稀里糊涂被剥夺这个权利。
民主制国家主权在民,国家主权的拥有者── 人民,永远不会缺位,也永远无可更换。所以,真正的民主制国家只有“换届”,没有“换代”。换届是和平的,换代则不一定。
直话直说未必容易,既直白又深刻就更难。稍有学术训练并且诚实的人都知道,用大白话讲出深刻的道理是最难的。同样,有些话看起来很白,实际上很深。说话既直白又深刻并不容易一样。在这里,真正难的还不是深刻,而是直白;不是雅,而是俗。因为媚俗的结果一不小心就是恶俗,正如直白一不小心就是浅薄。所以,俗而不恶难,俗而能大更难,由大俗而大雅,那就难上加难。
美国既然由一群土得掉渣的乡巴佬在一片蛮荒大陆上建立,则其人民的血液中就难免积淀着野性和蛮劲,甚至引以为荣。美国的那些治国精英不能以精英自居,更不能以精英自傲。他们必须找到精英和草根之间的结合点,使自己既精英又草根,是“草根精英”或“精英草根”,或者虽骨子里精英,看起来还是“加油站的修车伙计”。
权衡
一个国家,如果当真有什么“秤杆子”来“挑江山”,那“秤砣”就绝不可能是老百姓,也不应该是老百姓。实际上,秤砣叫“权”,秤杆叫“衡”(这是“权衡”一词的本义)。秤砣之重不在于个头大、数量多。恰恰相反,秤砣只有一个。它的个头是很小的,自身的分量也是很轻的。它之所以能够衡定天下,仅仅在于它是“权”。这就叫“秤砣虽小压千斤”。
公民作为个人,虽然个头小,分量轻,权重却不大,也不能大。而作为公民集合体的人民,做秤砣就更不行,那等于是把秤砣和秤盘掉了个,岂能平衡?这也正是早期民主制国家的问题。早期民主制国家由于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秤砣,便只好让“僭主”来代行其事。结果是“僭主”变成了“君主”,民主制国家也就变成了君主制国家。
秤砣是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大难题。对于民主制国家来说,难就难在不知道该由谁来充当原先由君主担任的那个角色。公民或人民是不行的,理由已如前述;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不行,因为那等于制造了一个“僭主”甚至“君主”,一个“无冕之王”。由国会来当秤砣同样有问题。国会既是民意机关又是立法机关,因此权重虽大,个头却不小,自身的分量也不轻,怎么能做秤砣?所以秤砣是个难题。由最高法院来当秤砣是再合适不过,因为它完全符合“个头小,分量轻,权重大”的要求。
《费城风云》读后感(四):民主的基石
《费城风云》读后感(五):值得静心一看的书
这本是工作多年后第一次静心下来要求自己一周看完的书,老实说前面部分还有一点难以进入,不过毕竟是本好书,越来越不错。个人觉得好在两点:
一、书要描述的仅仅是一次会议,而且是依次历史三个月的会议。会议本身没有指望达到今天这样的历史地位。一个会议,本身就不想小说故事那样的曲折性和故事性,要写好确实难,更不说是一部关于法律的会议,涉及参会人员的外国名字就一大堆,不好记。但是易中天做到了,让很多读者能深入地了解这次的会议,不是学术的枯燥。
二、关于法治。法治提了很久,个人也思索了一些时候。书中很多提法都甚是和我意。喜欢“防官如防贼、防权如如火、防全力的滥用如防洪”的权力观,更加佩服美国人对于幸福保障的深刻认识,一是要把权力分开,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二是保护人民不受转瞬即逝的思想有货;更感到于对民主和道德的认识:“民主和道德并不绝对可靠。民主完全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道德则很有可能导致”理想的暴政“”,这是多么的深刻,我们历史中的庸众破坏、多数暴政难道不是教训么?
通过费城风云,仿佛看到了美国成长的根基,权力的相互制衡、权利的不懈追求,法治的根深蒂固,也许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未来。
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法律改革要进行下去,当然需要体制外的有识之士摇旗呐喊、批评指正。但是说说就好,最好别添乱,不然就成了纽约州那帮民主共和党的代表,胡闹不解决问题而只是增加改革的成本。并非“肉食者”的人们提意见当然也应该被欢迎。这是一艘驶向希望的航船,所有甲板上的乘客都要帮着看看那个新大陆在哪里。可是这不代表乘客可以抢船长手里的舵,因为乘客对于暗礁、鲸鱼群、非法海域的位置毫无了解。
话又说回来了,这样的制宪会议能够有大量的折冲讨论和抗议争辩,靠的就是英美商业文化环境培养出来的精英。在中国土壤上长出来的精英们,能不能有这个参政议政的水平,还是非常令人怀疑的。所以也许即使看懂了人家立法的这一整套故事,要完全复制这样的传奇,也是很困难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