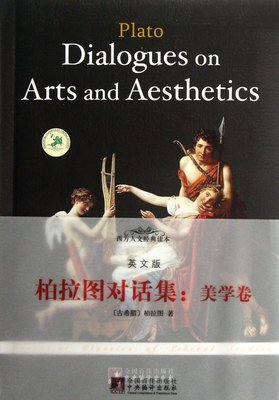柏拉图对话集经典读后感10篇
《柏拉图对话集》是一本由(古希腊)柏拉图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78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看这本书时,音响里传来一首很优美的钢琴曲,Fantasy in F minor Op.103 D.940 Franz Schubert;Schiff András;Rohmann Imre - Piano Duets , 这是只活了31岁的作曲家舒伯特的四手联弹作品,人类双钢琴曲中翘楚。舒伯特虽然短命,不过却比任何其他伟大的作曲家都留下了更多的四手联弹钢琴曲。这张CD录制发行于1994年,由匈牙利钢琴家Schiff和Rohmann合奏。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和教育理论家怀特海说过,西方哲学的发展,无非是对柏拉图对话的注解。根据本书后的“柏拉图传记”,柏拉图总共写了56篇对话,其中《理想国》《会饮篇》等等脍炙人口,我之前的文章也有单独介绍过。可惜的是,本书并不是柏拉图对话的全集,而且在本书摘录的这些对话中,也有几篇没有译全。
该书一共选录了12篇对话。《欧悌甫戎篇》写的是苏格拉底质疑欧悌甫戎关于什么是虔诚的看似确凿的判断。通过类比、推理一步步向他展示了他的坚信的荒诞;甚至开起了玩笑:“虔诚就是和神灵做交易。”
《申辩篇》写的是苏格拉底被告后在法庭上自己给自己的辩解词。他针对对他的指控:破坏社会风气和不虔诚、带坏青年分别作出了反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己这个智慧打假者是因为太聪明了招人恨,而且戳穿了太多假冒智慧的人而得罪了众人,而自己实际上是雅典的良心和牛虻,因为“未经审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最后的辩词显示了为真理就义的决心与自豪。
《格黎东篇》是苏格拉底临死前与劝他逃走的格黎东一番对话,驳斥了“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歪理,说明了真理、正义、法律的永恒价值。
《卡尔弥德篇》探讨的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明智。先是反驳了明智是沉着、明智就是谦逊,然后通过“明智就是做自己的事”到“明智就是有自知之明”上,然而这个结论也被推翻了。最后没有定论,只是说真理难以追求。这里的“明智”,跟“智慧”或“真理”有什么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柏拉图极其注重精神生活,指出爱情的终极目的是在对方身上找到自己没有的美好以及通过繁衍实现唯一的不朽的可能,后世甚至有“柏拉图式恋爱”(以精神而不是肉体、物质为主的恋爱关系)的说法,这一篇里他却描写了苏格拉底对美少年的爱(“你胆怯的小鹿啊,不要往狮子眼前跑,那样会成为它的口中食”),而且当时雅典男风甚盛,可见柏拉图自己也不排斥同性恋,况且,此篇推论的结局,甚至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苏格拉底之所以把辩论对方绕迷糊,只是为了把那个美少年留在自己身边。
《拉刻篇》是有关勇敢的,柏拉图在这里又捎带黑了一把智者,然后过渡到讨论美德。我个人认为,勇敢当然和知识、智慧分不开,但它首先是一种明知道危险但为了某种更崇高的目的和追求而不管危险的品质。
《吕锡篇》谈论的是友情,没有译完。
《枚农篇》讲的是品德,不过提出了“相”或“型”的概念,也提出并用几何学的例子证明了知识其实只是对不灭灵魂的经验的回忆的说法。
《裴洞篇》即是之前介绍过的、杨绛先生翻译过的《斐多篇》。
《会饮篇》也是之前介绍过的、朱光潜先生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
《治国篇》就是之前专文介绍过的,大名鼎鼎的《理想国》。
《巴门尼德篇》,说的是存在、型、一、是、有与无的互相否定、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论证的有些云里雾里。
“你必须考虑从这个前提中可以推出什么样的结论,即涉及相似和不相似这两个假定的术语,又涉及其他事物,即涉及它们自身的关系,又涉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你还可以假设不相似存在或不存在,还有静止、变化、灭亡,以及存在与非存在本身,简单言之,无论你假设任何事物存在或不存在,或拥有其他性质,你必须考虑从前提 中可以推出什么样的结论,即涉及与自身的关系,也涉及与你选择的其他事物中的任何一个事物的关系,或者与你选择的其他事物中的若干事物中的若干事物的关系,或者与你选择的所有事物的关系。”
《智者篇》,基本上是在用二分法揭穿智者Sophists的不懂装懂并以此谋生的本来面目。文中提到了语言是思想的基础这一观点。
书后附录先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传记,然后是柏拉图的徒弟亚里士多德“爱吾师更爱真理”的对柏拉图的批判,之后是译者王太庆先生对柏拉图思想发展和西方哲学“是”论的分析和总结(这个总结非常透彻易懂,不可错过),其中对中国翻译做了个精彩的回顾,最后是王太庆的翻译观点,主张信达雅,翻译必须重视,以及对一些术语要认真对待。
总的来说这书是名著名译,是了解柏拉图思想的很好的一本著作;其对话的深入浅出的形式也较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晦涩著作易懂的多,柏拉图辩论的技巧也值得学习,很多思想即使今天仍能发人深省,让人获益。推荐阅读。
最后以本书最后一篇王太庆先生的文章《学和思》里的片段结束,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学和思是哲学研究的两个必要的环节。所谓学,就是取得经验,经验就是知晓各种信息。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如果一无所知,像刚刚落地的胎儿一样,当然谈不上任何认识;一个没有任何认识的人,当然不会得到任何深入的学问,更不用说哲学这种参透世界和人生的智慧了。哲学家首先要有丰富的经验。经验不会自动产生,必须亲自通过实践去取得,无法假冒。而且经验必须丰富,不能稍尝辄止,又必须全面,不能止于一隅。我们从降生的一刻起就在不断地取得经验,只是有时不自觉,有时自觉,然而尽管如此,还是不能说到什么时候就有足够的经验了。个人的亲身的、直接的经验总是有限的,必须扩大,扩大经验的办法就是向别人学,首先通过语言吸取别人的、前人的经验,使它成为自己的间接经验。一个人的间接经验要比他的直接经验多得多,学历高的人又比学历低的人多得多。但是不管间接经验有多少,它必须连在亲身的直接经验上;缺少直接经验的人纵然学富五车也不能成为真正有知识的人。
加拿大读书会微信号:careaders
《柏拉图对话集》读后感(二):仅限于菲德罗篇的精神对话
菲德罗篇前篇是对爱情的讨论,属于精神范畴,后篇便转述到修辞术,以及如何做好一篇文章的讨论上,通篇读来,确实受益匪浅。
开篇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最差劲的作家也不会一无是处,确实如此,即使最差劲的作家,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在研究做学问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秉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传统,虚心求教。
而对于如何做一篇研究性论文,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启迪。首先,在做一篇论文之前,如果想完备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得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否则的话一定会说的不着边际”,这也就是要求我们在做一篇研究性论文之前,要最先弄清楚自己在想什么,自己想表达的是什么,否则,连你自己都不明白,如何能作出一篇条理清晰的文章去说服他人。
其次是关于下定义的准则。苏格拉底认为,“现在大多数人都不明白自己并不知道事物的本质,因此在讨论时,他们把人们一致赞同的关于某个事物的定义搁在一边,还以为自己知道这个事物,而在耗费精力进行讨论之后,他们最终当然就会发现自己的看法既相互矛盾,又自相矛盾。因此,你和我一定要避免再犯这种我们指责别人的错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一个人是更应该陪伴有爱情的人还是没有爱情的人?我们必须先对爱情的定义取得一致看法,这个定义要显示爱情的本质及其效果,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讨论爱情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这一段话中,苏格拉底是在告诉我们,在对一个事物进行讨论之前,首先要对这件事物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且这个定义要能显示事物的本质及其效果,才是最完备的定义,才会有接下来进一步的讨论。只有建立在明确、完善的定义之上,讨论才能有根基的得以发散。
苏格拉底认为,演讲术是一门使用语言的技艺,这种技艺是一种用词语来影响人心的技艺,不仅在法庭或其他公共场所,而且在私人场合也是如此。同时,他认为任何一个人想要误导他人而自己并不迷惑,他必须要能够精确的把握事物之间的相似程度和差异。因为人们普遍在面对两件事物的时候,通常是在他们差别很小的情况下容易被误导,所以,假设我们一点一点地改变立场,而不是一步到位,走向对立面,这样就更不容易被他人看出破绽。在这一论断中,我们可以明确的发现一种有效的传播理论,我虽然不知道它确切的名字,但是可以把它姑且理解为“相似理论”。因此,在传播过程中,相似论可以更好的帮助人们一点一点渗透他人的思想,虽不是一步到位,却可以潜移默化的达到自己传播的目的,颇有一点偷梁换柱的味道。而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想要准确的掌握修辞学,“首先要对词语做系统的划分,把握区分两类不同语词的标准,知道民众对那些词语的看法动摇不定,对那些词语的看法是确定的,掌握了这种差别就有了很好的洞察力。其次要做的是,碰到某个具体的语词,必须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要能敏锐地察觉他提出来加以讨论的事物属于两类事物的哪一类。”这是修辞学中对词语掌握的要求,他要求我们掌握词语的属性,换而言之,是要求传播者区分词语的类别,那一类词语受众听起来完全不能接受,哪一类词语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的,受众听起来却容易被迷惑觉得可以接受。这是由面及点的划分,它要求我们把全面的词语系统进行划分。同时,他也对我们提出了由点到面的要求,也就是要求我们对每一个词语进行分析,明白它所分属的种类。但归根结底,这都是对词语系统的划分。
苏格拉底在它的修辞术探讨中中,除了要求我们对词语有准确的把握,同时也在告诉我们,结构很重要。苏格拉底认为,“每篇文章的结构都应该像一个有机体,有它的特有的身体,有躯干和四肢,也不能缺头少尾,每个部分都要与整体相适应。”因此,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结构的安排,需要找到一个无法驳斥的理由,表明下一段话或者任何一段话必须摆在现在这个位置上,也就是说,要遵循一定的写作原则。因此,要遵循一定的步骤才能更好的实现这种原则。苏格拉底便给出了这样的步骤,他认为首先是要把各种纷繁杂乱、但又相互关联的事物置于一个类型之夏,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目的是使被选为叙述主题的东西清楚的显示出来,而第二步恰恰相反,顺应自然的关系把整体划分为部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自己一篇文章的结构,因此,这便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脉络使你明白自己所要讲述的东西分为几大块,同时,哪些部分又是紧密相联的,承上启下的。最终实现几部分各要素成为一个整体,使各部分相互之间以及与整体都和谐一致。
而对于文章的结构安排,苏格拉底也给出了明确的划分,首先开头要有绪论,接下来是陈述,需要伴有直接的证据,第三是间接的证据,第四是讲述的可能性。在论证过程中会用到的有引证和佐证,用于起诉和辩护的正驳和附驳,以及暗讽和侧褒。最后便是总结。
除了对如何做一篇论文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苏格拉底也提到了一些有效的演讲术的技艺,包括研究前的科学考察,以及在研究过程中要重视揭示事物的本性,并且对受众进行细分,同时考虑到传播效果,作出一些迎合受众的“受众本位”的思考。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些文字传播的弊端,诸如无法附带感情色彩的区分如何对好人说话和对坏人说话等论断。
《柏拉图对话集》读后感(三):哲人与城邦能否相容(2014.12.18)
(2014年第一学期西方政治学说史五分钟课堂发言。篇目涉及《游叙弗伦》、《申辩》、《克里同》和《理想国》。)
哲人与城邦是否相容,也就是哲学与政治是否相容。柏拉图在对话集的一开始,就用类似一部三联剧的方式展现了这一核心问题。
从游叙弗伦到申辩到克里同篇,从衙门口到法庭再到牢房,哲人在城邦面前似乎是无能为力的,城邦一步步在把哲人逼向绝境。
这种思绪在斐洞篇达到一个高潮。哲学向左,政治向右。苏格拉底之死似乎昭示了哲人与城邦之间无可弥补的断裂,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悲剧是无可避免的,而英雄只有在悲剧中才真正完成了自己。苏格拉底必须死,就像普鲁塔克写吕库古时说的,用死来维护着城邦的幸福。
这里牵涉到苏格拉底是否节制的问题,哲学要求自由的追问,要求不断打破终极,但哲人在城邦的言行是否应该有节制?诚如施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中所言,柏拉图把哲学比作疯狂——恰恰是清醒或者节制的对立面;思想必须要做的不是节制,而是无畏,更不用说无耻了。但节制是一种控制哲人言辞的德性。
苏格拉底的诘问法常常受到怀疑和诟病,这一点也是我们在阅读时所能感受到的。针对这一问题,柏拉图在他的对话集中进行了反思和补救,从而也使他对话中产生了早期苏格拉底和中期苏格拉底之分。
在对话集的开头《游叙弗伦》篇中,我们看到的苏格拉底似乎更多是破坏性的批评者而非建设性的建构者,他的诘问成功驳倒了真正不虔敬的游叙弗伦,但对方显然是不服气的。这篇对话也可以看成是苏格拉底之前与所谓诗人、智者多次交谈的缩影,在与人们的对话中,他的诘问往往成功迫使对方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同时无法达到正面结论而以“无通路”告终。
这种苏格拉底式的诘问对哲学的思辨是有益的,但却会惊扰洞穴世界的秩序。节制不是哲学世界的美德,却是政治世界的德性。无节制的追问会破坏城邦现有的信仰和价值体系,使人人陷入怀疑。由此,城邦对于苏格拉底的审判有其正当性。
那么柏拉图的意思是否是要以苏格拉底之死警示哲人不应惊扰城邦呢?我认为并非如此。
留在洞穴中的人无法承受地上世界的阳光,但走出洞穴的哲人却可以而且必须返回洞穴。柏拉图的对话充满了戏剧性的暗示,《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在玻勒马霍斯带有胁迫意味的挽留下来到他家里,这里用的一个词“下行”katabaino和第一个走出洞穴的人的“返回”以及再后来提到的哲学王要在轮值中下降都是同一个词。苏格拉底与公民的交谈正是一种哲人的下行。
现实政治对于哲人来说是一件苦事,苏格拉底通过和城邦公民交谈影响政治,本人却视政治为畏途。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更进一步,指出惟有哲人做王,城邦才能得到拯救。这对只愿永远停留在永恒的真实之境的哲人是不公平的,但柏拉图说,立法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
哲人要净化城邦,但为此他必须介入政治,也就意味着要先把自己弄脏。现实的政治世界是晦暗不明的洞穴,和光明纯净的地上世界不可同日而语。政治指向的是利益,讨论的是适当而非正义,而这恰恰是哲学家所要蔑视和抛弃的。
哲学家始终对城邦怀有一种温柔与尊重,也负有不可推卸的牛虻之责。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我看到的哲人具有英雄的意义,就像俄狄浦斯王和《苍蝇》中的俄瑞斯特斯一样,勇敢地承担起城邦这个洞穴,也即政治世界的原罪,引导人们回转过来关怀自己的灵魂,无论在此世还是彼岸,能够永远走向上的路。
其他参考:
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
余纪元:《<理想国>讲演录》
顾丽玲:《苏格拉底的敬神——柏拉图<游叙弗伦>疏解》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
(2014.12.18)
《柏拉图对话集》读后感(四):受苏格拉底精神感召的柏拉图
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年)被后人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苏格拉底常说:“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我像一只猎犬一样追寻真理的足迹”,“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他曾自问:什么是哲学?他自答: “认识你自己!(know yourself)” 苏格拉底在2000年前提出了“知识即美德”的神圣思想,他的思想中心是探讨人生的目的和善德。他强调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各种有益的或有害的目的和道德规范都是相对的,只有探求普遍的、绝对的善的概念,把握概念的真知识,才是人们最高的生活目的和至善的美德。他提倡人们认识做人的道理,过有道德的生活。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要有道德就必须有道德的知识,一切不道德的行为都是无知的结果。人们只有摆脱物欲的诱惑和后天经验的局限,获得概念的知识,才会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等美德。他认为道德只能凭心灵和神的安排,道德教育就是使人认识心灵和神,听从神灵的训示。苏格拉底提出肉体易逝,灵魂不朽,认为天上和地上各种事物的生存、发展和毁灭都是神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
苏格拉底在白天闹市中就常会进入到深深的禅定中,在他身上常有神迹现象出现。在古希腊,有一回,有位叫凯勒丰的来到以准确的预言而闻名的德尔斐神庙,向神提出问题,求神谕告诉他谁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女祭司传下神谕说,没有人更智慧了。苏格拉底并不认为自己是最有智慧的人,他造访了一个又一个享有智慧声誉的人,发现这些自认为聪明的人,最不聪明之处就是以自己所不知者为知。于是他终于明白,神谕通过苏格拉底告诫人类,最聪明的人是意识到自己的智慧微不足道的人。
柏拉图自二十岁起师事苏氏,前后八年,苏格拉底亡故时,柏氏才二十八岁,老师的死,使他受刺激很大,因此他看清了雅典的民主本质,明白了群众的无知,柏氏受苏格拉底的精神感召,变成一个酷爱智慧的青年,自柏拉图开始,人类开始有大学制度了。柏拉图非常敬爱他的老师,他常说:“我感谢上帝赐我生命,······;但是我尤其要感谢上帝赐我生在苏格拉底的时代”。 苏格拉底还被称为是西方的孔子,因为他们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是靠政治的力量来成就,而是透过理性,对人的生命作透彻的了解,从而引导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柏拉图对话集》读后感(五):翻译得不好
王太庆的译本好像被评价很高,但我对照英文读下来,发现不行。跟王晓朝的那个,不相上下。
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评论短了吗
《柏拉图对话集》读后感(六):关于儒家的虚无
今天,我们为什么跟着西方屁股学哲学、学制度、学民主、学自由、学辨证主义?因为早在苏格拉底时代已经开始探讨辨证的理性公民思维。而我们那时候有什么?只有庄孔孟老道不可言式的神秘主义与虚无主义?
这也许就是几千年之后的我们依然沉迷于虚无、复制、歪曲、欺骗,沉迷于乌托邦式的自我迷局的冲突中,而不断委屈求全。像商禽的火鸡一样,只有向着虚无示威。大家都好像了解它的存在,却无法实现这种理想。说到底,孔孟黄老思想的局限是建立在人治思维的基础上,它是人治里的理想乌托邦,如何执行取决于专职君主个人的道德修为。
因而,孔子之后二千来,儒家思想到底带给我们什么(当然你可以说一堆它影响我们的习惯和思维,以及随之而来的成果)?几千年王权专制,和士大夫的中庸自保,孔子所的倡“德治”“礼治”“仁政”于他们不过用来维护王权和自身参政合法性,是一种自我迷思式的精神麻醉,于民众仅止于政治福利的恩施,其局限终无所突破,也就是缺乏一种实质的约束性,仁与德的取决于上层的道德修养和政治觉悟,这种人治的思维,终是飘忽不定的,这也是为何农民起义不断原因之一。毕竟理论上,在没有制度与法定的约束下,上层与下层处于一种无限索取和有限施舍的不平等关系,只要任何一方打破,这个“仁德”维持的临界秩序都会被打破。
但谁又能捉得准个平衡黄金分割点呢?它会具体参照到能影响平衡的赋税兵役、土地分配、法典的奖罚公正,当然,还会牵涉到天时地理等因素。而仁政德治,在这些因素其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像一个影子,一面镜子,也叨叨不休,常常后知后觉,但具体做了什么,对行动对意志有多大约束性,事前完全取决自我意志的博弈,难以界定,对行动结果的认识取决于道行的深浅而缺乏具体的参照。
于此,假如无西方文化闯进来,或者启蒙,而今我们又在想什么呢?还是之乎者也,道不可言?在王权下,士大夫君子的自我阉割的“君子之道”精神修行?对人民的嗟来之食,近似一张空头支票。当然这个“假设”本来是不成立的,因为世界毕竟往前走的。但此前毕竟可考的王朝轮换了二千多年,也止于王朝轮换,和赋税土地制的改良。这样的局面难道是孔子“仁德”所追求的吗?我想不是,但那又是什么呢?
当然你也可以说它不虚无,因为它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和国人的纲常伦理,维护了封建王朝的合法性,也起到了一定限制王权作用。但是,实际上和它的初衷对比,显然是不足够、不彻底和被破坏的,因为它总是少了一样东西来保全它本身的神圣。假如说儒家不虚无,那它一定是一个被改造、为封建王朝量身定做的披着儒家思想皮毛的伪儒家,被一批犬儒乡愿的文人所掌控。
《柏拉图对话集》读后感(七):Plato《会饮篇(symposium),论情爱或论向善》小摘要
【按语:《会饮篇》思想的雏形其实在《吕西斯篇(Lysis)》中已经出现了(即将爱界定为缺乏者对绝对美善的渴慕和追寻),只是现在以优美瑰丽得多的形式呈现出来,不仅仅是哲学论著,而且是伟大的戏剧作品:在其中,Phaedrus, Pausanias, Eryximachus, Aristophanes和Agathon等都发表了对爱神Eros的赞颂,而以Socrates的灵魂走向美善本身的超越之旅为顶峰,最后又补充了Alcibiades对Socrates的赞美为结束。
阅读中使用了王太庆译本、王晓朝译本,Cooper校译本。刘小枫先生的《柏拉图的<会饮>》据认为中文较好的译本,只有等以后再仔细研读了。】
Apollodorus向朋友讲述他从Aristodemus那儿听来的,有关Socrates和Agathon等人在会饮中谈论爱,这故事Apollodurus也向Glaucon讲述过。那个谈话发生在很久以前,Agathon第一部悲剧获奖后举行庆祝酒会的时候。
Aristodemus路上碰到Socrates去Agathon家赴宴,也跟了去。路上Socrates却出了半天神才进去。席间医生Eryximachus提议颂赞爱神来消遣时光,因为他刚好听Phaedrus抱怨,“各种神道都引起过诗人们作歌作颂,只有爱若(Eros)除外,从来没有一位诗人写诗颂赞他,尽管他那样伟大。”【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95页,下同】于是席间诸位同意依次做一篇颂扬爱神的讲话。
首先发言的是Phaedrus,他认为爱若是一位伟大的神,引用赫西俄德的诗歌表明爱神最古老,而且带来幸福。爱的原则“厌恶丑恶的,爱慕美好的(a sense of shame at acting shamefully, and a sense of pride in acting well)”【297】能够给城邦带来美好正当的生活。接着Phaedrus举了Alcestis,Orpheus和Achilles等人的故事作为例证来说明因爱蒙诸神赐福。在其中,Achilles在对Patroclus的关系中界定为被爱者(the beloved),而被爱者向情人(the lover)的爱更博得诸神赞赏,因为情人的爱常常是为神所激发的。总归就是,“爱神在诸神中是最古老,最荣耀的,而且对于人类,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他也是最能导致品德和幸福的。”【299】
第二个发言的是Pausanias,他说应该首先精确界定赞颂的对象,其实是更细致地区分了善恶。因为有两个Aphrodite(美和爱之神),一位是较年长的天上的Aphrodite,是Uranus之女,没有母亲;另一位是较年轻的,凡间的Aphrodite,是Zeus和Dione的女儿。相应地,Aphrodite的女儿Eros也有两位,“一个称为天上的爱神,一个称为凡间的爱神。”【300】凡间的爱只限于下等人,“所眷恋的是肉体而不是灵魂”【300】,这是因为其所源发的那位年轻的女爱神同时出身于男女。而天上的爱神只为男子所生,其引发的爱情对象也只是少年男子,又因年纪较大,不至于荒淫,而渴慕理性。Pausanias说,蛮族把钟爱少年男子、爱智慧和爱体育都看为丑事,这不过是不愿意被统治者高尚、有牢固友谊和亲密的交往而已,反应了统治者的专横和被统治者的懦弱;而在希腊尤其雅典,追求爱情被看做光荣,负面的反应往往是源于凡俗的爱,而“为了美德(virtue)而眷恋一个爱者是很美的事。这种爱情是天上的Aphrodite所激发的,本身也就是属于天上的,对国家和个人都非常可贵,因为它在爱者和被爱者心里激起砥砺美德的热情。”【305】对于爱者与被爱者的情感Pausanias给出了几条建议:迅速接受爱者是可耻的、受金钱和利益考虑是可耻的;应该将爱情和学问美德的追求合而为一。
因为Aristophanes在打嗝,Erixymachus就先讲,他认同Pausanias对两种爱的区分,却超出人性范围,从宇宙结构中寻获一种普遍的爱:“除了把人的灵魂吸引到人的美上去以外,爱还有其他许多爱的主动者和爱的对象,爱的影响既可以追溯到动物的生殖,也可以追溯到植物的生长。我可以说,存在于神圣或世俗的各种活动中的爱的威力适用于一切类型的存在物,爱的威力伟大得不可思议,支配着全部神的事情和人的事情(it is that Love does not occur only in the human soul; it is not simply the attraction we feel toward human beauty: it is a significantly broader phenomenon. It certainly occurs within the animal kingdom, and even in the world of plants. In fact, it occurs everywhere in the universe. Love is a deity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he directs everything that occurs, not only in the human domain, but also in that of the gods)。”【306;王晓朝译本卷二,页223】Erixymachus说,在音乐、医学以及其他一切人的事情和神的事情上,都要尽力区分两种爱。“仅当爱,无论是天上的爱还是人间的爱,它的运作是公正的、节制的,以善为目的的时候,爱才能成为最伟大的力量。”【王晓朝译本,二225】
喜剧家Aristophanes的发言或许是最著名的片段。他用神话的方式来歌颂爱神,这是一个有关人的真正本性及其变迁的优美或凄美故事:最早的时候,人有三种性别:由太阳生成的男人,由大地生成的女人,由月亮生成的阴阳人。那时候人的形体是圆的,有四只手、四只脚,圆颈项上安着圆头。体力非凡,想要造诸神的反。宙斯就把人剖为两半,然后让阿波罗疗伤,并赐予媾合生殖的功能。“那些被劈成两本的人都非常想念自己的另一半,他们奔跑着来到一起,互相用胳膊搂着对方的脖子,不肯分开。他们什么都不想吃,也什么都不想做,因为他们不愿离开自己的另一半。”【王晓朝译二228】因此,“我们每人都是人的一半,是一种合起来才成为全体的东西。所以每个人都经常在寻求自己的另一半。”【312】这种种寻找另一半的过程中,仍然是男人对男人的爱较为高尚。Aristophanes说,“我们本来是个整体,这种成为整体的希冀和追求就叫做爱。…全人类只有一条幸福之路,就是实现自己的爱,找到恰好和自己配合的爱人,总之,还原到自己的本来面目。…爱神就是成就这种功德的神。”【313-314】我们也应该敬畏神灵,免得再叛逆的时候被宙斯劈得只能用一只脚跳来跳去的。
接下来是诗人和筵席的少年主人Agathon的发言,他说前面的几位都颂赞了从神那儿得来的幸福,却没有说明爱神的本性。“所以颂扬爱神也要先说他是什么,后说他给予的恩惠。”【315】首先,爱神是最幸福、最美的神:爱神最年轻,永远年轻,远古诸神纷争与爱神无关,诸神中有了爱神后就会只有彼此相爱;爱神最娇嫩,“在世上最柔软的东西上溜达,并且住在哪里。他寓居在神和人的心灵里,灵魂里。”【317】;爱神容貌秀美,与丑恶水火不容。其次,爱神具有一切美德:不害人,无暴力,爱情都是出于自愿的;爱神公正、节制而勇敢、而且智慧,“一切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都是由于受到爱神的启发。…一切技艺,凡是奉爱神为师的艺人都有光辉的成就,凡是不曾受教于爱神大都黯然无光。”【318】Agathon总结说,“自从爱神降生了,人们就有了美的爱好,从美的爱好就产生了人和神所享受的一切幸福(once this god was born, all goods came to gods and men alike through love of beauty)。”【318】
Agathon的发言赢得大家的赞许,Socrates却暗讽Agathon不辨真假,只顾“把一切最优美的品质一齐堆在所颂扬的对象上”【320】,然后质询Agathon得出:爱总是对某某的爱(love desire that of which it is the love),而爱总意味着某种缺乏。“爱首先是对某某东西的爱,其次是对他所欠缺的东西的爱。”【323】而爱所爱的就是美,那么,爱就缺乏美、没有美的东西。因此“主张爱神是美”是不对的。
接下来Socrates的讲论借助于回忆女祭司Diotima对Socrates的一番教导。爱神不美也不丑,正如“在智慧与无知之间有一个中间状态…正确的意见(correct judgment)就是介于智慧和无知之间的东西”【325】一样,Eros介于美和丑之间,“爱神正由于缺乏美的东西和好的东西,所以才盼望这种东西。”【326】因为欠缺美的东西和好的东西,所以爱神不是神,也不是凡人,而是介于会死的人和不死的神之间的精灵(Spirit)。Eros是丰饶神Poros(富裕,善意的忠告之子)与匮乏神Penia(贫穷)的孩子,在爱与美的女神Aphrodite的生日在天国怀下了。所以,“Eros也成了Aphrodite的随从和仆人,因为他是在Aphrodite的生日投胎,生性爱美的东西。”【327】Eros像母亲一样贫乏,却又具有父亲的一切品质,渴求美善的东西,他处在智慧和无知之间,“因为智慧属于最美的东西,而爱神是爱美的东西的,所以爱神必定是爱智慧的,他作为爱智者介乎有智慧者和无知者之间。”【328】
那么为何要爱美和爱善呢?为了拥有美和善,为了幸福。这种爱是人人具有的。在各种渴求中,我们只说“对于好东西,对于幸福的企盼,是每个人心中最大的、强烈的爱。”【330】人们所爱的只是好的东西。这种爱的活动表现为“在美里面生育,即在身体中,又在灵魂中(give birth in beauty, whether in body or in soul)。”【331】肉体而言,只能在美的东西里生育,“为什么要企盼生育呢?因为在会死的凡人身上正是生育可以达到永恒的、不朽的东西。”【332】因而,爱也是对不朽的企盼。这不仅仅涉及肉体,甚至知识和研究也是一种维系和企盼不朽的方式,人们也盼望流芳百世。
在灵魂方面,生育则孕育智慧之类的美德。这些美德中最大最美的是安排国家事务和家庭事务的,即正义和节制。“那从幼年就在灵魂中孕育着这些美德的人是近于神明的,到了一定年龄就有繁殖、生育的欲望。”【335】这样的例子有Lycurgus之于斯巴达、Solon之于雅典等,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作品和制度。
接下来Diotima讲述了爱的最后和最高的密仪(mystery):从幼年起追求某个美的身体;进而追溯哪个具有类型意义的美者;“再则,他必须把灵魂的美看得大大优于形体的美”【336】;从各种行动向前更进一步,达到知识,这样就见到知识的美;最后见到美的终极启示或美本身:“它首先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那个在自身上,在自身里的永远是唯一类型的东西,其他一切美的东西都是以某种方式分沾着它,当别的东西产生消灭的时候,它却无得亦无失,始终如一。”【337-338】相比于这神圣的、纯一的美本身,钱财、首饰、美少年统统不值得一顾。
ocrates讲完后,大家都赞美,这时喝得醉醺醺的Alcibiades(曾受Socrates教育,从事政治,后来背叛雅典)突然跑进来。他发表了一通赞美Socrates而不是歌颂Eros的话:Alcibiades在Socrates面前感到自己很羞愧,“他有多么蔑视它们,以及大多数人羡慕的财富和各种荣誉。他把我们看得一文不值,做出愤世嫉俗的样子,一辈子都再讥嘲世人。可是当他认真地推心置腹的时候,谁都看见他肚子里的那些神像(figures)。”【345】Alcibiades迷恋Socrates,他也以为Socrates迷上了自己的年轻美貌。Alcibiades似乎有一次试图勾引Socrates或者说回报Socrates,结果发现事实上Socrates对他的年轻美貌加以蔑视和讥嘲,只是试图在他灵魂中播散美善的种子。另外Alcibiades还回忆了Socrates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和出神的事情。“这个人十分奇特,无论在为人还是在言论方面,都找不出任何今天的人或古代的人来跟他相比,除非像我那样,不拿他和人比,而拿他比西勒诺们和森林仙子们。…所用的字眼和说话是外面包的一层皮,就像林中仙子脸上刻得一团傻气一样…可是一个开通人一看,往里头一照,就立即发现这些话里面包含着思想,是十分圣洁的,其中充满着美德的形象,引向最崇高的目标,有助于追求美和高尚的人进行研究。”【350,这似乎也适合于柏拉图的对话录】最后,Alcibiades说Socrates表面上看是个爱者(the lover),实际上是个被爱者(the beloved)。
然后继续饮酒,到黎明的时候,只有Agathon, Aristophanes和Socrates还是醒的,而天大亮时,其他人都睡了,Socrates就走了。
江绪林 2012年7月21日星期六
《柏拉图对话集》读后感(八):苏格拉底霸气十足啊!
读了三章,吐槽以纪念之。
1.苏格拉底真能把人问趴下,当他的聊天对象真是辛苦。但这也就是他的质疑精神所在了,值得学习。
2.当时的人熟读《荷马史诗》,时不时就拿出史诗里面的句子作为论证的材料,就差来几句“荷马曰”了。
3.某人一本正经地论证道:“宙斯都灭了他老爹克洛诺斯,所以我状告我爹是虔诚的”神话迷信,害人不浅那。
4.“凡人哪,你们中间那个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是最智慧的,他承认自己在智慧方面毫无价值。”明白自己无知的人最聪明。
5.“现在我们各走各路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这两条路哪一条比较好,谁也不清楚,只有神灵知道。”面对死亡能有这等魄力,苏格拉底霸气十足啊!
6.让相爱的人上战场,他们就会为了维护对方英勇奋斗,这样的军队将无往不利!……好想法。
《柏拉图对话集》读后感(九):柏拉图对话集
有时候觉得世上之事真是不可思议,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内,中外同时出现两个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苏格拉底。而他们都不仅仅留传下伟大深邃的思想,并且都有一群杰出的弟子,孟子、柏拉图。而且他们的思想主要都是由对话体或者语录体记载下来的。另外他们也大都采用启发式方法传授的思想给周围的人。 当然区别还是有的,此书虽然柏拉图大多记载的是苏格拉底与他人的交谈,但似乎更多是表现自己的思想。所以他笔下的苏格拉底与苏格拉底另一弟子色诺芬又有微妙的不同。 不过我觉得内容颇有诡辩的感觉,著名的“助产术”讨论的许多的概念是没办法下定义的,换句话说苏格拉底足够聪明并且反应快,所以辩赢了对手而已。当然这种方式也确实有助于头脑以及思想训练。至于其哲学内涵如何,由读者自己汲取吧。
《柏拉图对话集》读后感(十):欧悌甫戎篇:非学术型读书笔记
两个都是有麻烦在身的人在官府门口遇见了。欧悌甫戎跟苏格拉底寒暄了起来,问他说你怎么不去吕各苑跟人讨论问题跑来官府干嘛?估计那时候社交媒体不发达,苏格拉底摊上了违法的大事欧悌甫戎居然不知道。连苏格拉底自己都说他摊上的可不是一般的官司,而是案子。告他的人有三个,其中最让他纳闷的是有一个年轻人叫梅雷多。不过必须要说苏格拉底对自己这档子事还是相当冷静的,在他向欧悌甫戎描述’他到底被告了什么事’的过程中,他正好借由这个说明的机会精辟的点出了几件事情:
你要告我’毒害青年’,首先你自己必须先知道年轻人是怎么学坏的,因为你这样才得以判断我是如何毒害青年的
‘孩子禀告母亲’这个形容特别向班干部跟老师打小报告的行为
政治家应该关心青年就像农夫要关心’秧苗’(这个年轻人虽年纪轻但是有政治野心)
如果你心态很支持苏格拉底这个人的话,你也可以从这段话中读出很浓的讽刺的味道,如果你支持的是理,那么在最后苏格拉底也说出了关心青年的重要性。并且苏格拉底还来了一段自我评价:生性爱人。同时在与欧悌甫戎对话的过程中,发现欧悌甫戎是一个认为人家不理解他是来源于嫉妒的人,在苏格拉底顺着他的话说’只有你这样的先知才能知道结果如何’的时候,欧悌甫戎就飘飘然了,并且很笼统的下了结论,同时把话题转到了自己身上。
欧悌甫戎提告父亲一案
‘我告的那个人,你听了会说我疯了’:告父亲这件事欧悌甫戎自己对民间舆论自己是有sense的,并且还没有等苏格拉底回答就自己先下结论对方会认为自己疯狂,再对比之后他非常强调自己从公正的角度出发,可见他应该是很以自己的行为为荣而去做的。
而苏格拉底也是个逗逼,他回的更妙’你告的这人会飞吗?’一来一回的对谈就看出了对于告一个什么样的人是疯狂的两方标准不一,苏格拉底认为你今天无论告谁,只要你告的有理,为理而来,你都不是疯子,但是如果你告一个会飞的人,你才疯了,因为这才配的上疯的标准。’是人就不会飞,飞的就不是人’,自相矛盾才是疯。
接下来为了增加两人的对立感,请允许我把苏格拉底描写成一个极尽赞美之能事的马屁精(在我心中苏格拉底是很天真的哦),不过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衬托欧悌甫戎的自负心理(增强一点戏剧感)
一句‘只有高度只会的人才能做到这样的公正’踩中了欧悌甫戎的下怀,欧悌甫戎把自己看成了公正的化身,自称已把虔诚和不虔诚分辨得一清二楚,并且强调把这类事情了解清楚才能和别人区别开来,自负的人最大的特点,以追求与众不同为目的(以为是自己成就一切事情,而不是自己不过是事情的经历者),然后自负的人要干的第二件事就是’好为人师’,苏格拉底就继续演他得马屁精戏码,想要借拜师为名来请教他自己关心的问题,进入正题’虔诚是什么?‘
欧与苏关于虔诚的讨论
欧悌甫戎相信神话故事发生的事情vs苏格拉底不相信神话故事发生的事情(大家可以掂量一下这两种人的区别)
苏格拉底不满足于欧悌甫戎只是用事例来说明虔诚,他希望欧悌甫戎从虔诚的事——跳到给出’虔诚的’型or相本身上来
欧悌甫戎给出了第一个说法:“神灵喜爱的就是虔诚的,神灵不喜爱的就是不虔诚的”
苏格拉底要求欧悌甫戎给出证明,所以开始了他对第一个说法的审查过程,他审查的过程从第一个词开刀“神灵”,神灵显然是个名词,它作为主语具有一定的决定权,那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到底是个单数还是个复数啊,鉴于他们俩已经讨论过神与神之间本来就有分歧,说明神是个复数(当然是顺着欧悌甫戎的思路下去),而谈到了分歧如果只是关于’量‘上面的分歧好解决,而如果是质上面的事呢(是非,善恶)很难取得一致,不然怎么叫不一样的神呢?所以就可以得出了同样的事情有的神灵认为对,有的神灵认为不对的情况,于是在苏格拉底的循循善诱下,欧悌甫戎有了第二个说法“所有的神灵都厌恶的,就是不虔诚的,所有的神灵都喜爱的,就是虔诚的”。(苏格拉底给欧悌甫戎一个台阶下,自负的人自尊心都很强,但是显然欧悌甫戎因为自满并没有从第一轮回合里面学到任何的东西,而是拿到一个改正版的时候就立马肯定自己,虽然口口声声说是要钻研,但是他根本不知道钻研是怎么一回事,就说这一个更改版一定是正确的)
接下来苏格拉底就以自己的追问和分析作为活生生的例子来展示什么叫做“钻研”(白话就是’认真思考’):开始衡量’是’两边之间的关系,所以’虔诚的事是因为虔诚所以被神灵们所爱呢,还是它被神灵们所爱所以虔诚’,而且还说明了不同说法的来历。而且在说明来历的过程中又是从最具体走到最抽象概括的过程。
由于这一个脑力激荡的过程所以需要详细展示一下:
a. 事发起因是苏格拉底想请欧悌甫戎说出“虔诚的”的型or相,给虔诚下个定义,那么你给出的定义就要起到一个作用就是对事情能够做出判断,有了这个定义我就可以去判断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是不是虔诚的。
. 现在欧悌甫戎给出了一个说法“所有的神灵都喜爱的是虔诚的”,如果把’是’的左右两边分开来看(对句子进行拆解),一边是所有的神灵都喜爱的,另一边是虔诚的,那么如果要对事情或人做一个判断的话,再进行一次拆分,因为牵涉到动词“喜爱”,所以就有一个’能动’和’被动’的问题。例如我喜欢你,我就是能动的,你就是被动的。能动的存在不是因为被动,但是被动的存在是因为能动,那么能动就是能动,可是欧悌甫戎说被所有神灵喜欢是因为虔诚,所以他得出来的是他被喜欢是因为虔诚,虔诚这时候变成能动,当然虔诚就当然的’并不是因为它被喜爱’,那么虔诚并不是因为被喜欢而虔诚,是因为虔诚本身,虔诚直至之中都是能动不是被动的存在,而有如果神灵喜欢的和虔诚是一回事,那么就会发生对立的情况。
接下来提出了关于虔诚的第三种说法:“凡是虔诚的都是公正的”,这回放在’是’两边的都是形容词,这样就比范围,苏格拉底拿恐惧和羞耻做了类比。他认为恐惧的范围比羞耻大,所以是凡是羞耻的就一定是恐惧的。那么同等类比虔诚就是公正的一部分,并且欧悌甫戎认为虔诚是’对待‘神灵那部分的公正。苏格拉底纠结于’对待’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针对某个对象的艺术,例如牧牛就是对待牛的艺术,是对象收益。而欧悌甫戎强调对待上帝的虔诚是以仆人对待主人得那一种。这种对待叫“侍奉”,并由此延伸出两种行为“祈祷”和“祭祀”。苏格拉底点出:祭祀就是向神灵送点礼,祈祷就是向神灵索取,那虔诚是跟神做买卖的筹码吗?你送给神的无非就是崇敬。
最后欧悌甫戎只是一直在尝试更换词汇,而并说不出虔诚到底是什么?最后以闪躲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