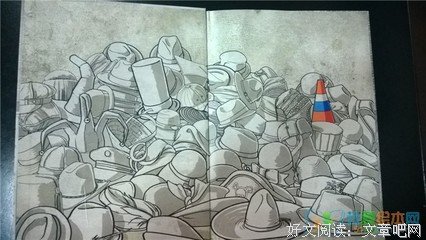《重访灰色地带》读后感精选10篇
《重访灰色地带》是一本由刘海龙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2.00,页数:207,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重访灰色地带》读后感(一):传播学术史——反思与重构
这是一篇早期的书评文章,由于最近在重读书中的几个章节,因此将书评发表在豆瓣上。
反思与重构是学术史研究得以螺旋发展的莫比乌斯环,刘海龙在著作中对传播研究的元叙事展开剖析,通过考察灰色地带中的典型事件与代表人物对传播学术史进行一定程度的重塑。本评论首先从认知角度解读传播学术史中的误读缘由,将中国学界对西方传播研究的偏狭认知归咎于种族假象;将存在结构性缺失的中国内地传播理论演绎归因于洞穴假象,其中的经验养成又主要受制于政治权力及功利主义;其次,从学术史重构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出发,强调方法的继承与重访的精髓;最后进行否定之否定的思考,提出的建议包括:对新学术史话语保持谨慎的态度,并积极创造合理的学术史考察方法。
自古迄今,人们通常站在当下的立场来反观历史,我们现在所遵循的、所依赖的,是现代人的一些观念。因此,辉格史观、现代主义叙事的出现便具备浅层次上的合理性,鲜有学者对这种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宏大叙事之后的痼疾予以反思。刘海龙的《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以下简称为“《灰色地带》”)延伸自知识社会学视角,关注断裂叙事中的绵延和既有叙事中的缝隙,致力于解构现存的不合理元叙事,发掘意识形态遮蔽下的问题,进而推及整个学术史话语系统,并结合中国传播学科发展的困境提出建议。
福柯在考察“性话语实践”的过程中曾提出:“我力图绕道压抑假说及其引发的禁忌事实或排斥事实的背后,从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实出发,让这些运动系统地呈现出来”。刘海龙同样使用类似的知识考古法,聚焦学术史中的灰色地带,这些暧昧且晦涩的灰色地带就是学术史上“连续之中的断裂之处与断裂之中的连续之处”,对于这些地带的陌生化考察与持续性注视往往能够回归传播思想流变过程中的偶然性与复杂性,为被神话包裹的主流宏大叙事所造成的思想板结带来一丝滋润,这种新的想象空间是基于对灰色地带中标志性事件、被忽略人物的细致解读才得以开辟的。若以传播学的想象力关照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庶几能摆脱“既缺少在自身经验内部寻求关联和统一解释的努力,也缺少将西方知识体系还原到自身历史语境下的意识”的窘境。愿景来临之前,令人警醒的现实仍是主要矛盾,因此有必要根据刘海龙引介的视角对传播学术史现状进行多向度反思,并从特定的切入点论证重构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一、 反思的焦点:认知局限与理论演绎
正确的认知基于对经验事实的科学考察,且无法离开批判思考的辅助。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Novum Organum)一书中提出四种阻碍我们清晰思考的假象:种族的假象、洞穴的假象、市场的假象以及剧场的假象。尽管培根的论断以个体认知作为出发点,但依然对于本文的分析路径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结合时代变迁的不同政治经济环境,可以大致将中国传播研究者对西方传播研究的认知视为受“种族的假象”所影响的不全面建构,而中国传播学术研究本身的理论演绎则囿于“洞穴的假象”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缺失。
(一) 种族假象的诱导与迷思
种族的假象意指过分依赖根植于思维深处的直觉或者所谓的常识。传播学作为与意识形态贴近的舶来学科,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始终是面貌残缺的,学者的常识与直觉的形成根植于这种非平衡的环境中。1982年施拉姆访华“与其说给中国带来了传播研究,不如说给中国带来了传播研究的学科观念”。施拉姆在反复宣扬自己建构的传播学起源神话同时,通过四大奠基人、与新闻学接轨、统摄性学科等理念孜孜不倦地证明传播学科本身的合法性,且施拉姆与其高足余也鲁合作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也成为“中国早期研究者想象‘传播学’的主要参照”。
可惜之处在于,有一批中国研究者往往“想当然”而未知其所以然。譬如直接给拉斯韦尔的思想贴上“5W”的标签,误把拉斯韦尔模式与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划等号,而《社会传播》中的宏观要义与核心论点却长久地处于沉睡状态。研究者往往在管窥蠡测间自以为已获要义,却只是抓住皮毛,在“被误解的口号式的概念片段”中难以自拔,略过前人鲜活的思想与真正值得批判的失误。这一谬误的根源可以归结于一种粗糙的学术风气,这往往带来空洞的能指游戏和一系列畸形后果:概念脱离文本,文本抽离语境,而对概念的运用又难以表达出创始人的原意。
对于丰富的哥伦比亚学派丰富学说的简化与抨击同样体现一种非常依赖直觉的高度形式化特征。黄宗智认为:现代化进程中,伴随思想的世俗化,“理性和科学被建构为绝对的、普适的、超历史的”,科学实践无法脱离演绎逻辑和经验归纳的支持,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代主义自始便具有强烈的偏向演绎逻辑的倾向,也就是后来在各知识领域中被称为‘形式主义’或‘形式化’的理论传统”。首先,哥伦比亚学派的自身建构表现为高度的形式化,其传承血脉的断代亦已被证明为学术历史记忆中的“伪叙事”;其次,批判领域学者思虑巩固自身地位,为建立一套系统化的流派通约纷纷把哥伦比亚学派的经验和实证信仰视作攻击对象。国内传播学教科书中以“派系之争”为主体的叙事方式,与其说再现学术史上的难断公案,不如说是双方学术话语权的争夺及其本体论分野的现代呈现。《灰色地带》充分论述哥伦比亚学派的多元面向,将哥伦比亚学派思想简单归结为几个单纯的概念或者理论教条不啻为一种天真的思考逻辑。
书中将哥伦比亚学派学术成果进行全面呈现是超越有限效果论的有力之举,其中又特别侧重对帕克的思想进行重新发掘。詹姆斯·凯瑞在建构芝加哥学派神话时对于帕克的“屏蔽”处理源自于他自己的精心意图。遵照知识社会学的路径,知识社会学不仅必须处理人类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经验“知识”,而且必须处理所有“知识”被社会地建构为一种“现实”的各种过程。凯瑞坚定反驳的传递观里难以容忍帕克的功能主义思维与贴近于哥伦比亚学派的研究方法论,致使他在建构美国文化研究“现实”的道路上必须将其模糊化。在知识社会学传统谱系中,尼采提出“人类的思想是求取生存与争夺权力斗争的工具”,凯瑞的努力正是建立与标准历史相对冲的叙事结构,其目的是为美国的文化研究争取生存空间。近年来,关于芝加哥学派神话已有不少质疑声音,体现出治学的严谨精神与一定的理论自觉性。可国内尚有不少传播研究者禁锢在这一学术史黑洞中,仿佛芝加哥学派就是铁板一块,难以割裂,因此在对芝加哥学派缤纷多元的研究探讨上依旧犯下常识性错误。
同样因为学科既定规则的常识,使伯内斯及其著作《宣传》一直处于传播学者关注视角的边缘。华勒斯坦认为:学科创立的信念是“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而学科发展作为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实践,又“进一步建构并合法化这样的划分”。鉴于思想史、学术史、学科史之间的分野,重新检视伯内斯的宣传观念对于当下社会现实的贡献意义是思想史研究的必要选择,而传播学科对《宣传》这一代表进步主义逻辑崩溃的宣言书进行审视有助于反思宣传在本土语境下的正当性,且能将思想史的生命力汇聚进学术史中进而延展学术史的关注视域。
“举凡思想史不能烛照之处,便是各种神话与偏见的肆虐之地”,在基本围绕神话进行证伪时,很容易令读者联想到“迷思”(Myth)。迷思来自于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田野考察,之后法国结构主义学者罗兰·巴特将迷思移植到信息传播中,将传播过程中内涵意义的运作称之为“神话”。文森特·莫斯可[14]将迷思定义为:不仅是“与人类价值等同的人类学范畴,也是一个通过意识形态扭曲人类价值的政治范畴,通过否认政治完整性,迷思将它的叙事自然化,并将之提升为一种凡夫俗子无法挑战的近乎坚不可摧的堡垒”。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学术史中的迷思作为神话的胚胎,通过收编与遮掩,将叙事自然化的同时赋予自我以神圣地位。关于对西方(尤其是美国)传播研究认知迷思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国内传播学科启蒙时期形成的惯性思维,这种直觉或常识限制了其他话语的进入可能,而刘海龙的角色恰如率先跳出牢笼的人。
(二) 洞穴假象之后的政治与功利
如果将传播学在内地的发展比作是外来学科的缓释过程,那么传播学科中有些思想很好地在本土环境中溶解,而其余思想或多或少地水土不服。洞穴的假象描述的是政治体制、经济环境、文化习俗的影响后果,简言之就是我们的生活经验决定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独特的环境培植出独特的经验已毋庸置疑,但对中国内地的学术史分析远不可止于此,应该深入讨论其后的基于功利主义的逻辑演绎以及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互构关系。
20世纪西方传播研究进入中国的两个传统:社会学与新闻学,曾于50年代之后出现停滞。这两种学术传统的断裂可以归因于美国传播研究范式转变、中国传播产业不发达、学术建制、政治干预之故,而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又是典型的方向性与合理性关系,因此关键论点要化约为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如接受一种前设:政治涉及到社会生活过程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它在本质上是权力),即通过任何的手段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那么政治权力的确无微弗至,无远弗届。在严格区别政治路数的威权主义国家体制内,社会科学受政治权力的影响大于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强烈倾向普适主义和纯粹的客观主义,但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到意识形态,赵鼎新曾经细致对比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异同,这些对比能对社会科学知识所受的意识形态影响进行合理的回答。首先,社会科学研究中以人为主体,人本身就会运用意识形态和价值来论述自己的行为正确性,换言之,结构与功能的联系是羸弱的,人们在认知心理意义上容易出现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使得学科史建构能选择性遗忘一些非线性事件,最后导致集体失忆。尽管如此,这些合理或不合理的存在都拥有它的维系势力,使既有的解读被特定的价值观、企图和潜意识所支撑;其次,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机制都是正反馈机制,对于权力的强烈追求成为社会变迁的最大原动力。这一特点在政治体制较为封闭的国家内尤为明显,譬如书中提及的建国后学科整改过程中,社会学被视为“提倡孔德的改良主义”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而遭受取缔;1978年作为分界线的时间意识弥散至历史书写中[19],此处不妨进行一次合理推测:权力的合法化形成于各方支持的舆论建构,权力的延续更依赖于集体意识形态的稳固。在双方的博弈中,思想作为权力安定的动力,其断代与政治分期间的逻辑关系不言自明。
以上论述突显学术史的内在逻辑性与天然非线性受到被动干扰的一面,实际上缺乏主体性反思的书写和甘愿沦为政治附庸的抱憾也有其主动的缘由。关于第一层面的主动刘海龙已给予详述,早期在图绘传播学科之际,新进入学术场域者面临着双重选择:标新立异,抑或采取模仿策略,知识分子结合过去的际遇与如今的形势,往往会做出一个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如果这一层面侧重于生物性,那么第二个层面则携带鲜明的经济色彩,而经济又与政治紧密勾连,马克思主义者在较深层次上认为“政治权力源于阶级制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汪晖也早已提出:在一个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中国虽然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但“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尽管这一判断包含作者所受学科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当“文化产业”悄然替代“文化工业”概念并在学术场内受追捧后,羞愧的自治性与经济权力对符号资本的改造功效的确显露无疑。尤其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媒介“双轨制”进一步解放市场的力量,在一场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权力精英掌控多数资本的格局并未被消解,资本独立的格局反而日渐缥缈。经济改革使中国传媒的权力性质由简单的政治权力走向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重叠。业界作为学界知识的应用场域,其生态变化引发的只能是连锁效应,业界的经济资本游戏带动学界符号资本的竞相角逐,因此“行动者围绕何为关键资本、何为场域行动规则等问题进行斗争,争夺的焦点是符号的正当性问题”,当然更为精辟的论述是刘海龙的另一句总结,可以借用来印证学术史研究正面临的严峻问题:国家需要将自己的政策正当化,媒介文化的研究者需要通过社会资本的投入进一步巩固其学术地位或兑换更多的经济资本,这种不适当性使得学术史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路径依赖困局。
关于学术史理论演绎瑕疵的进一步阐释将从功利主义展开。与经验证据归纳不同,理论演绎试图将西方传播学理论镶嵌于本土,并基于逻辑恒等原则追求普世化与绝对化。黄宗智举出舒尔茨的案例说明将所谓“公理”放在多元性与复杂性并存的人类社会中的荒谬与不切实际,造成的后果很可能是“所谓的经验证据,说到底只是一种修饰;演绎逻辑才是一切的关键”。这一点在批判学派引介过程中非常明显,20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占据政治和日常生活的主导地位,一切的问题似乎都可以用一种单一的思想来解释,批判学派的观点被看作“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和阶级分析的老一套”情有可原,实证研究也被视为与马克思主义一致的理论未发挥应有之义。无论是对客观经验主义还是批判主义的吸收上,新闻学术场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栖息地,都秉持着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功利主义是“基于主体的目的性实践,满足主体功利的需求是认知和实践行为的基本出发点……所关注的往往都是特定条件下的功利性目标实现,而不去反思其双向或反向的结果。”施拉姆版本的传播学很大程度上以实然逻辑部分置换传统新闻理论中的应然逻辑,适应经济改革潮流,能够为解决权力机构遇到的现实问题提供策略,给学界带来一丝新意,因此国内学界对其青眼有加。不仅如此,中国传播学者往往对批判理论也抱有“实用理性态度”,因此某些话语的生命力只有被召唤出来,却难以拥有恒常性。
回到书中的导言部分,传播理论教材中的学术史建构是一种“被中介的经验”,如今依然存在“传播学 = 传播理论 = 大众传播理论 = 传播实证研究”的不成立等式。虽然传播研究的主导范式近年来一直在追求价值无涉的意识形态,但所有社会思想都无法脱离现实生活境况,在理想追求与无奈现实的双重困顿下学术史正深陷于曼海姆悖论中,只能通过收编吸纳与建立霸权来维护叙事自洽。
二、 学术史的重构:何以可能?何以为能?
检查辉格史的叙事弊病是学科发展的必然阶段。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肯定的是知识生产并没有严格轴心,多个学派在运用多元视角对社会现实予以分析或阐述,“较之中心化,离散性是其(知识生产)更具经常性的特征。”面对学术史的重构,应当如布尔迪厄所述:外化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使之成为我们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笔者认为,刘海龙的“连续与断裂辩证法”和“内部反思”为重构学术史提供可能性,此外中国传播研究者提供的许多有价值工作揭橥了学术史重构的可行性。
(一) 可能性的预示:两种思索方法
齐格蒙特·鲍曼在利用后现代性来定义现代性的尝试中,提出:现代性表现为对秩序的一种永无止境的建构,现代性的最显著特征是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因此等级严明的系统、大写的存在都是虚无的。连续与断裂的史学考证方式之所以较传统的编年式结构、里程碑演进式结构、大师主导式结构、学派冲突式结构和观念统领式结构而言更具效力,正是因为它符合库恩所说的范式转换带来的难以避免的阵痛与遗留。库恩在总结自然科学研究史的基础上提炼出范式革命概念,传播学科作为社会科学的一脉分支,难以断定绝对的主导范式,反而是范式理论中的相对主义得到了社会研究者们的重视。《灰色地带》特意强调此类相对性,注意到连续与断裂不是泾渭分明而是相互缠绕的,因此连续与断裂的辩证法在肯定思想史发展内在连贯性的同时也关照了跌宕起伏之处。其次是如何正确认识知识与权力的问题,刘海龙将哈贝马斯的意义合法化问题与福柯的微观权力问题整合进自我研究中,对既有学术史的准确性进行科学的研判,得以在学术主体性的凝视下,独立于政治、市场的影响,跳出官方意识形态的原野,超越某个流派或某种思想的话语体系。这样的好处是:既不臣服于连续的叙事,也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根基,致使注意力没有被偶然性事件全部带走。学术史作为一种知识类型在书中的考证是相对纯粹的,是一种独立的、自由的、富有活力的娓娓道来。
如果说“连续与断裂的辩证法”侧重描绘知识形态,那么“内在反思”的思考策略就是重访知识形态的考察工具。一系列已有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案例通常是从外向内看,其缺陷是浅尝辄止,没有学术逻辑的思辨实践;而从内向外看注重反思习以为常的惯例与潜意识,折射出更明显的进步色彩。在日积月累的学术熏陶中,潜意识被掩盖在重重关卡内,学术史通过反复强调、内在协同、排他性等方式不断堆砌出虚拟环境,使得研究者难以察觉繁荣景象下究竟有何不妥。一旦平心静气从本体论和认识论开始切入并保持深思,那么攻破一个常识观点就有可能揭露背后一连串的“别有用心”。学者潘忠党曾提出:“(我)反对将理论——或者某种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无论是传播学中的哪一类流派,对防范意识形态对其的收编或防止坠入按照权力意志进行循环论证的陷阱而言,内在反思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 可行性的证明:观点与成果
在《灰色地带》精彩的文字界面之后贯穿的是学者从自发到自觉的知识消化逻辑,但《灰色地带》的重构学术史是一则个案?还是可供借鉴的样本?如果时间倒推至10年前,这似乎是无定论问题,但如今学者的理论自觉修养和学科的独特发展模式业已证明了可行性,且有不少优秀的工作成果为这一观点增添了注脚。
20世纪的哲学大师德勒兹提出“虚拟”的概念,认为虚拟比现实更加真实。恰如人眼感知光速时形成视觉上的当下现实,但真实的光束本身却指向当下现实之外的无穷可能,新(the New)出现的时刻,就是一个作品克服并越出关于它的各种既有的历史性理解的时刻。虚拟前方有着无穷的契机,即使是再熟悉不过的文本,如果忠实于文本写作发生时的语境进行解读,对同一时期的平行思想予以关注,也会从旧意中升华出新知,因此学术史的建立不必完全仰赖于推陈出新,转向温故而知新或许会柳暗花明。
笔者在书评写作过程中曾与同好交流阅读心得,一位阅读者提出:“《灰色地带》笔法极好,但论述的都是些边角料。”需要辩驳的是,正是所谓的“边角料”被不断去伪存真、层层剥笋,才使得传播学术史具有更多“正史”的意味。史学研究强调在范式和想象之间建立起关联,杨念群建议采用经验功能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默顿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中层理论,即“通过经验的方式提出一些相对的概念丛,不断地积累一些中层的概念,来回避大的叙事对历史进程的干预,同时又避免那种绝对的琐碎方式或状态。”中国的传播学术研究场中,已有类似表现的踪迹,譬如胡翼青针对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中西二元框架”的认识论悖论作出分析,号召多元化的学术自觉与中西对话里培养的批判意识;孙玮紧扣“新技术”与“旧范式”对社会与媒介的关系进行精彩的论述。此类研究日益呈现繁荣之势,一系列学者踊跃地发乎内而游于外,为学术史的真实面貌贡献智慧。
可行性的论证不过是吹响集结号角,如果承认知识社会学的相对观点,那么传播研究者们的探索视角都离不开对应的意识形态。尽管如此,即便是在一些小问题上形成真诚而关切的论争,对于实力尚弱的中国传播学而言已经是善莫大焉。更重要的是,史实不会发言,重要的是研究者对它们做出的解释,只要把习以为常或者难辨雌雄的知识作为问题,那么传播学科自身的发展轨迹就可以作为知识社会学的考察对象,经过若干次的知识考古与文本细读,就一定可以对史实做出公正合理的解释,使学术史具备良好的信度。
三、 余论:否定之否定的思考
相较于其他社会学科而言,传播学科面临理论匮乏、历史积累有限等诸多挑战,长久以来深受学科正当性赤字的困扰。其原因很可能是威力强大的元叙事隔绝其他可能性,令学术思想处在凝滞迷津之中难寻新途。当致力于反思现状的努力开始萌芽时,会走向一个新的学术空间向度,一系列事实与概念将被还原并锚定在合理的位置上。但是这种尝试得出的结论一定正确吗?已有学者表达出冷静的思考。纵然修正过后的学术史如何看似准确,如何阐幽发微,尚需要其他研究予以证实。刘海龙的努力是一种“证伪”,通过论证一个反例来推翻已有定论是较为容易的,《灰色地带》更深刻的意义在于曲径通幽,研究者必须遵循光亮深入内里,对推翻定论后的结论予以证实,尽管这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但能有效防止被新的学术史神话所裹挟。
第二点思考是:书中使用的方法是否是重构学术史的最优解,是否存在超越“连续与断裂辩证法”或与之并驾齐驱的新思索方式?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不能止步于口头论争,唯有尝试、笃行、互议才能启迪新知,浇铸出更好状态的传播学术史。
参考文献
[1]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载《读书》第5页,2003年第1期。
[2][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第10页,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3][6][7][8][13][18][19][20][24][25][27][29]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第14、104、122、34、75、99、105、128、143、163、128、1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王维佳,赵月枝:《重现乌托邦:中国传播研究的想象力》,载《现代传播》第25页,2010年第5期。
[5][美]皮廷格:《行为研究的设计与分析》第5-9页,马广斌译,[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
[9]黄宗智:《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载《开放时代》第11页,2007年第4期。
[10][11][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第3、6页,汪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2]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第9页,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14][加]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第28页,黄典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5][21]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第16、17页,张立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6][26]黄宗智,高原:《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载《开放时代》第159、163-164页,2015年第2期。
[17]赵鼎新:《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载《社会学评论》第8-9页,2015年第4期。
[22]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文艺争鸣》第7页,1998年第6期。
[23]陈卫星,徐桂权:《权力衍续与媒介寻租:中国与俄罗斯的比较制度分析》,载《国际新闻界》第52页,2010年第7期。
[28]吴予敏:《功能主义及其对传播研究的影响之审思》,载《新闻大学》第25页,2012年第2期。
[30]刘海龙:《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载《国际新闻界》第5-10页,2006年第5期。
[31]王金礼:《传播思想史的反思性书写——兼论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的写法》,载《新闻记者》第76页,2016年第3期。
[32]Pierre Bourdieu: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 转引自潘忠党:《反思、思维的独立和研究真问题》,载《新闻大学》第31-33页,2008年第2期。
[33]郑莉:《鲍曼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94页,2004年第1期。
[34]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第7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5]潘忠党:《反思、思维的独立和研究真问题》,载《新闻大学》第31-32页,2008年第2期。
[36]吴冠军:《像德勒兹一样阅读》,载《社会科学报》第006版,2015年4月30日。
[37]葛兆光,杨念群,徐杰舜,范可:《研究范式与学科意识的自觉》,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页,2005年第4期。
[38]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载《现代传播》第34-39页,2011年第4期。
[39]孙玮:《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载《新闻记者》第50-58页,2014年第12期。
[40]刘利刚:《温故而知新——评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载《全球传媒学刊》第146页,2015年第4期。
《重访灰色地带》读后感(二):建构中的学科历史
在导言中,作者提出了全书重要的几个概念,包括“灰色地带”、主流叙事结构和反讽的叙事等。简而言之,作者力图在本书呈现的即是,通过运用反讽的叙事,借以审视所谓传播思想史中间的“灰色地带”,从而证明有关传播思想史的主流叙事结构的“虚伪性”。
作者指出,由于传播研究的实践与应用特性,使其与权力的场域、与知识的场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因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传播学,比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更深切地感受到“学科自治”的威胁,于是,身处其中的学者们便更有动力去“建构”一套有关传播研究历史的话语体系。
在阐明了这一有关理论历史建构的冲动后,作者进而指明并评价了当前在传播思想史研究中的5种主流叙事结构:编年式结构、里程碑演进式结构、大师主导式结构、学派冲突式结构和观念统领式结构。作者认为,这五种主流叙事结构所致力营造的是一种思想“连续体”的“幻象”,而真实的理论演进则是充满着断裂的,也就是充满着“灰色地带”的。
作者指出,主流叙事背后是对秩序感的强调,“秩序感的获得常常建立在武断的分类体系和线性的过程描述之上”。在这种思想的左右下,主流叙事或者说宏大叙事,通过“有意省略或遮蔽”思想史上那些模糊之处,将“灰色地带”拒斥于外。
本书所要做的恰恰是通过发掘连续之中的断裂和断裂之中的连续,从而更为“真实”地还原理论的谱系。
【导言基本上规定了(或阐明了)全书的某种价值取向,即对历史采取一种建构主义的视角,也就是说,整个传播思想史是基于在该学术场域中的人们所采取某种话语策略而建构出来的。】
《重访灰色地带》读后感(三):如何避免被“灰色”
在我们学院的午餐会上有幸目睹男神风采,非常专心地听完了他的每一页PPT(以至于连我导的到来都没注意到),还当了第一个提问的人,奖励就是这本签名版的《灰色地带》,哈哈哈哈当时心里那个暗爽。
借用国庆假期仔细翻看了一遍。拉斯韦尔作为被误读的传播学“奠基人”,其所开创的学术传统被传播研究的“无形学院”逐渐抛弃;以拉扎斯菲尔德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的经验分析法长期以来成为“众矢之的”;芝加哥学派尽管创造了传播研究神话,却忽视了帕克从知识社会学与现实社会建构的角度去理解的传播与新闻现象;伯内斯前瞻性的《宣传》却一再被冠以“精英主义”的头衔……一直以为传播学术史短短几十年的进展历程不过是简单的“魔弹论——有限效果论——新强效果论”,而这本《重返灰色地带》让我脱离了平面观点,重新站在了三维的立体角度上去审视传播学上这一段曲折的发展史。
这门年轻的学科在百年不到的发展历程中到底经历了哪些曲折与误会,书里已经详尽描述,我个人受到的启发则在于为何会出现这些“灰色地带”,又该如何在将来的学术领域和实际生活中避免被“灰色”。
首先,作为一名创新者,即书中所说“卡里斯玛”式的开创人,拥有前瞻性的想法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如何能让自己的想法得到流传与继承,经历后人的阐发与衍化,最终在不断修正和重新建构中葆有生命力,这就需要来自外部与内部的竞争与挑战。这也是拉斯韦尔被“灰色”的主要原因。他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传播观念,想尽力使其变得完美和逻辑缜密,却也剥夺了其他人参与的兴趣,最终人们不得不将他的观念简化为“漏洞百出”的“拉斯韦尔5W模式”,才能得以进一步的“修正”。因此开拓者最需要做的事情不是亲力亲为地查漏补缺,而是如何提出一个具有足够吸引力的谜题,从而诱惑更多人的参与。
其次,大众都喜欢追逐“新鲜”的事物,从而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被学术主流拥抱的是施拉姆新颖的“范式革命”而非席勒用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和阶级分析对于政治经济批判的“老生常谈”。这也是为什么哥伦比亚学派为了凸显自己的“突破性”以及迅速获得大众的注意力而简单粗暴地树立起了一个“魔弹论”的靶子(尽管随后他们也成为了“有限效果论”的稻草人,并被人忽视了其他更为丰富的理论贡献)。
最后,成功的宣传营销并不是直接暴露出自己的目的,而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实现其目的的环境。这一点可以从伯内斯的《宣传》一书中习得:传统的宣传不过是就事论事,简单粗暴地把劝说性信息硬塞给受众——我国目前大多数硬广告和新闻发布会仍在采用这种做法;而新的宣传则是创造促进某种行为的环境,让接受宣传者自愿地产生某种行为(比如口香糖有助于口腔卫生,钢琴厂商鼓吹起居室应该留出“钢琴角”等)。这种近一百年前的宣传理念在当前的互联网扁平化宣传语境下看竟仍有超前之处。
总有人错误地把传播学与新闻学画等号,甚至担心新闻客观主义是否会受到宣传的影响。而在这一点,我引用海龙老师的观点:对传播学的研究其实更多地应该落在对人的思想史和观念史的研究上。
(本文系原创,如需转载请联系本人 微信号:shidaostorm)
《重访灰色地带》读后感(四):冯建三教授书评——《进步的颜色:评介<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冯建三教授书评——《进步的颜色:评介<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载《传播、文化与政治》,2016年6月,第三期,P149-158.
《重訪灰色地帶:傳播研究史的書寫與記憶》引述了一篇書評,讓人眼神一亮(頁 14)。
1940、50 年代,「結構功能學派」的聲勢如日中天。它有健將墨頓(Robert K. Merton),卻在此時為書商撰寫深度評論,推薦《資本主義發展論》(Sweezy, 1942/陳觀烈、秦亞男譯,1997)在美國出版,該書作者是史威濟,是美國最 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之一。
不過,墨頓其後出版論文集《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從「研究主題與問題界定......」等四個面向,討論歐洲的「知識社會學」及美國的「大眾傳播研究」之差異時,完全未曾著墨馬克思主義(Merton, 1949)。我們因此也許應該推論,七十多年前的大西洋兩岸,其左右政治在反法西斯的脈絡中, 可能對於歐美的相關知識及研究的進行,並無影響;或說,若有影響,也還不怎麼明顯。
當年似乎因為冷戰還沒開始,兩岸傳播研究的差異,並沒有人想從左右之別給予詮釋,惟最慢在1950至1970年代,成形於英國的媒體研究,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其後,一直到冷戰結束後的現在,歐洲與美國的主流傳播研究,政治的差別已很明顯。在歐洲,若以英國為例,不太有人想要用「傳播學」這個概念,作為區辨人我群己的界線或判准,原因之一,或許是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英倫研究者,傾向於採取全觀的、整體的論事角度,「寧願把與傳播和媒體相關的問題及現象看做一個值得研究的領域,讓來自不同學科、不同知識背景的學者帶著各自的問題設置、理論視角和方法路徑進入這個領域。」(曹書樂 2013,頁 3)
相較於歐洲,台灣領受美國的影響,在1960年代開始顯現,代表作是 《大眾傳播理論》(徐佳士,1966),但至1970年代中後期,隨著留美學人返台,泛稱為效果研究的美國主流,才算穩定站立腳跟。值得注意的是,將書名冠以「傳播學」的人,是未曾留洋的作者(李茂政,1981)。李金銓(1982) 以美國為主,但已旁及歐洲(英國)文獻的介紹與評論,最初的書名雖是「大眾傳播學」,兩年後則改成「大眾傳播理論」。晚近,台灣另有集體作品,納進更廣的傳播研究成果,使之分門別類而冠以「傳播學」之名,並且突出了在地的關懷(翁秀琪,2004)。
對於「傳播學」的用法,本書作者似乎存有戒心,因此出現在副標題的是「傳播研究」;對於「本土化」的修辭與實踐,作者好像也是評價不高。
一來本土的界定可能變成套套邏輯,於是本土化之說,就成了「研究中國傳播問題」、「服務於中國傳播實踐」。但是,關鍵之處在於,「誰」來界定問題是些什麼、為「誰」而實踐?
由於「誰」的缺位,作者遂有一個看法:在官商的引領及界定之下,中國的傳播研究早就已經本土化,並且具有「輕理論、重應用,輕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之色彩;如果進而注意,察覺這個本土化的呼聲,重新在本世紀前十年快要結束、中國的政經與國際力量增長之際,「又被重新提出」, 那麼箇中所「摻雜的政治動機」是不是「反映了中國傳播學界......的迷茫狀態」?若然,這樣的本土化,對於學術是否反而成為戕害,未必是貢獻?
其次,中國如同任何國家,都有各自的特殊歷史與社會性質,表現在傳播研究的中國特徵,變成了對西方商業傳媒的「超越前進」。因此,公共關係本來是西方資產文明的商業產物,即便在西方也經常因為背離新聞的(專 業)要求,致令結合二者的作為,流於遮掩而不好公然擁抱。名義上,中國的憲法上是要奉行社會主義,卻無須批判就熱情接納、新聞媒體成為公關的「積極提倡者」,新華社開辦了中國第一個公關公司!很多號稱傳播的研究,變成是「媒介經營管理的研究」;到了《政府資訊公開條例》施行、新聞發言人培訓蔚為風尚而想要「設計民意」以「引導民意」時,不少傳播研究的訴求對象,又變成是以「政府......為最重要的聽眾。」
總結,作者的重要見解是,198年代以來的中國傳播研究,動力與西方同行無關,「而是本土的政治與經濟實踐」,美國等等「西方的傳播理論非但沒有主導中國的傳播研究,反而被整合進了中國的傳播研究」。因此,作者希望強調與凸顯一個認知:重點不是本土或西方的爭論,畢竟中國與西方都「不是一個整體」,其「內部(各有)差異」;與此同時,學人也不宜只是擁抱「文化多元論與相對主義」,多元及相對之說,未必帶來解放與自由,反而可能淪於保守反動,乃至於種族主義的壓迫陷阱。(頁 170-4, 180-3, 186, 189, 201)
劉海龍能夠注意「誰」這個問題,據此而與「本土化」及「西化」開展對話,來自於他考察傳播研究歷史的心得。
本書的第五章探討〈中國傳播研究的史前史〉,第六章問津〈孫本文與 20 世紀初的中國傳播研究〉。前者提及杜威(John Dewey)60 歲時,抵華講演2百多場,並由當時北京《晨報》編印演講集,一年內印行 13 次、各次印量都超過 1 萬本。那麼,以杜威對美國傳播研究的重要性,這個遺產何以在華人社會消失了?同理,孫本文在1925年完成紐約大學的博士論文,《美國媒體上的中國:美國媒體對華公眾意見的基礎及趨勢研究》,堪稱今日中國有關國家形象研究的「濫觴」,怎麼也不存在於後來中國傳播研究者的「集體記憶」?孫返國後積極引入社會學,著作《社會學原理》在 1949 年前重印 11 次,1953年社會系消失於中國,但孫仍在南京大學任教,何以其早年的傳播研究,遲至 2004/05 年才見學人提及,但未申論?孫的博論通過內容分析,以兩家日報、三份週刊與四份月刊為對象,解1897 至 1922 年間, 它們對排華條約、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與華盛頓會議等四項問題的言論。 劉海龍在閱讀後表示,若以今日眼光視之,孫的研究固然「方法和理論都顯得很原始,結論也平淡無奇」,惟若考量該書完成90年前,則不但值得「刮目相看」,並且反襯當前大陸的這個類型研究,「思路還停留在這個層次」、「絕大部分仍停留在該文的框架」,則當前「理論的粗糙和學術創新能力的不足」,顯露無遺。(頁 90, 95, 98, 106-10)
若說杜威與孫本文的水過無痕,是因年歲久遠、「自然消逝」;那麼, 1979-1989 年間,中國學人在引入海外傳播研究的成果時,按理還是當前的「往事」,卻怎麼也禁不起考驗,直至近年才告有人重新發掘?
作者認為,文革後的第一個十年,新聞與傳播學術在內的中國學人,「有一種多極而非單極化的想像......出於政治敏感,有意地與美國保持距離」, 表現在《國際新聞界》引入了不少歐洲乃至於美國的批判研究。但是,何以 1990 年代以來,很少人提出那段歷程,中國學者在論及傳播研究的時候,反而是集中在展現宣韋伯(Wilbur Schramm)等美國主流範疇在中土的散播? 特別是,何以學者又將宣氏的《人、訊息與傳媒》(Men, Messages and Media) 以及英文的「傳播理論」通通翻譯為「傳播學」?對於這些問題,作者似乎有兩或三個觀點,解釋何以在那段時間進入的「批判」研究,長時間不見蹤跡。一是「知識份子的驕傲」,引進的人,是在「從事否定的批判而不是做學科推銷員」。二則這類批判研究所使用的理論資源、概念與術語,在中共建政後,早就為官方揚左、形左壓右的「言說」所挪用,至於實踐則在左右夾雜的同時,顯現為對左的早熟催生,致使果實生澀,成為眾矢之的,於是 「擺脫左傾思想」之名,成為主線,對於資本體制的批判也就「顯得不合時宜」。另外,引進批判理論的人多屬年長而身有同感的「左翼民族主義者」 (如,林珊),則其聲音隨世代的轉換,轉趨低迷沈寂,似可理解。與此有關,「傳播學」這個名稱的出現,可能是引進的人,要以媒介是「中性」的 說法與概念,取代「新聞學」,當時這個詞在中國具有強烈、狹隘的政治屬性,一說到新聞,歷來強調的是媒介的「階級性」。(頁 124-5, 127-8,132-3, 137, 170)
手筆至此,作者又提醒讀者,「批判」的內涵,在中國大陸已有變化。早年,中國傳播領域的學人引入批判資源時,「沒有(深刻理解)其批判精神內核」,沒有用以「返照中國當下問題」,致使批判的論說,因為表面上與官方修辭相同,早年是遭到見棄。時至今日,中國政經文化等各方面的變化, 無復往昔,「新一代批判學者也不再與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同步,相反對國家與資本的勾結常常持否定態度」。如今,洞若觀火的事實是,中國傳媒的主要性質是「向城市中心化......廣告目標......中產階級化」靠攏(頁 135-7, 173),批判者固然對此早有所見,任何誠實的人又能視而不見嗎?
果真如此,那麼,本世紀初很多人的主張,指中國傳媒「市場化程度並不高」,是以必須「防止把批判理論直接用於」分析「我國傳播現狀」的說法(頁 138),當時已很可疑,遑論當前?事實上,該認知重複了作者反對的二分法,是將「國家」與「市場」對立,而不是評估,「自由經濟」是否其實出自「強勢國家」的打造,亦即二者可以並不互斥,甚至另有可能是相互構成(參考 Gamble, 1994)?再者,即便是主流的經濟學理,仍然承認,若要通過市場機制,調配傳媒內容的生產與使用,勢必造成失靈(最佳的英語分析,參見 Baker, 2002);政治哲學家更曾主張,市場機制若要運作良好, 重要的前提就在,不但傳媒內容、並且是所有形式的文化,其提供(生產) 與使用(消費),都必須先行協調與節制市場機制的運作(Keat, 2000)。這些學理的討論,對於「市場化程度不高」之後的歇後語(因此要有更多的市場化),一定沒有啟發嗎?非得堅持國情特殊,中國與西方涇渭分明,學理不能相通嗎?
同理,作者認為,1990 年代的中國,「還沒真正建立起阿多諾所說的文 化工業」,卻出現了「對文化工業的批判十分熱鬧」的景象。與此對照,本 世紀以來,中國日趨以行政力量推動傳媒的商業走向、同時各地首長儘量想 要割地自雄(雖然多少受到衛星電視與網路的突破),並且不肯對表意、而 特別是政治表意尺度有所放鬆,僅存民生、情色、體育運動......等等題材的 空間之有限增長。此時,法蘭克福學派所要批判的對象業已長成,但「批判 者卻已經成為文化工業(或文化產業、創意產業等)的學術顧問或者推動者。」 (頁 162)那麼,我們似乎應該說,與其指霍克海默與阿多諾的論述流於特 殊,不能用在中國,不如說,這是因為有些學者「揠苗助長」在先,「變節 求榮」在後。
前述的觀察與阿多諾的反思,可以相通。阿多諾試圖在「法蘭克福學派 及『接受世界現狀的』美國傳播社會學家『之間』,刻畫自己的位置時」,曾 經在 1960 年代對艾科(Umberto Eco)說,當年若是在戰後的德國寫作《啟蒙的辯證》而不是在 1940 年代的美國,並且是「分析電視,那麼,他的判 斷就會比較不是那麼悲觀,也不會那麼激進」。(Gripsrud, 1995, p.7)事實上, 關於《啟蒙的辯證》而特別是其中的〈文化工業:作為大眾欺騙的啟蒙〉, 依據彼德斯(John Durham Peters)信心飽滿的精細解讀,不能僅是讀成、定調為是菁英的悲鳴與悲觀,是無視於大眾通過娛樂得到的解放乃至於反抗; 不是的,彼德斯認為,該篇宏論與「哥倫比亞傳統、使用與滿足,甚至是英國文化研究並無二致......。」(唐士哲譯,2013,頁 69)
劉海龍的反省精神,類似彼德斯,他檢視中國大陸的傳播研究,同時也「對中國傳播研究影響更大」的美國(頁17),重新予以解讀,而其要旨, 應該是要對中國的現實,致意發聲。他所聚焦的對象,是四位(或說四組) 美利堅學人,依序是拉斯威爾(Harold D. Lasswell)、拉紮斯菲爾德(Paul F. Lazarsfeld)作為代表人物的哥倫比亞學派、派克(Robert E. Park)作為重心的芝加哥學派,以及「公關之父」,但在傳播研究中,很少得到重視的伯內斯(Edward Bernays)。
拉斯威爾曾經憂慮「黨政宣傳國家」(party propaganda state)演變成「駐防國家」(garrison state)。若是這樣,暴力專家將會掌握軍政及經濟與文化大權。因此,拉斯威爾在二戰之後,努力從事社會改造運動,希望「提高公民素養」以「促進民主」,劉海龍鼓勵讀者,不要將這個目標「簡單」地「批判」為是「灌輸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頁 29-31)。
由於研究旨趣的轉變,以及早年未曾培育博士生,拉斯威爾在美國的傳 播研究陣營,知名度及影響力,落在哥倫比亞大學之後,但這不是重點,作者在這裡重視的是,哥大研究群的成員,存在不同的立場與取向,而拉紮斯菲爾德與法蘭克福學派諸子的關係,並非總是「行政與批判」的二元對立關係。(頁 14-15, 36-40)
這裡可以補充的是,拉氏在 1941 年發表的〈論行政與批判傳播研究〉, 不但沒有詆毀批判研究,他還以允稱認同的方式表明,「從事批判的學子, 在分析了現代的傳播媒體......之後,還得追問下列的問題:這些傳媒是怎麼 被納入組織與控制的?在它們成為機構,納入制度之後,其走向中央化與標準化的趨勢,以及其所承受的促銷功能與壓力,又是怎麼表現在傳媒的?無 論是怎麼掩飾,這些傳媒威脅各種人文價值的形式,又是些什麼?」接著, 拉氏還舉了一個例子,表示理解批判的價值。他說,第一次歐戰期間,(假使)有幅廣告,顯示啤酒廠商的促銷手法,就是讓某位仁兄,厭惡地丟掉整版報導歐戰的報紙,然後在該幅圖片下方,寫著在這種戰亂時刻,「唯一讓 你還有平和、力量與勇氣的感覺,就是坐在爐火旁邊,喝些啤酒。這會造成 什麼後果呢?假使人們渴望和平的基本欲求,在符號上,錯誤地成為私人慰 藉與舒適的表達......?假使人們喝口新品牌的啤酒,就能完成相同的目標, 他們何必還要通過行動與犧牲,解決他們面對的各種社會問題?......這就變成促銷文化所可能搞成的狀態,相當危險......」(Lazarsfeld,1941, pp.161-2)
當然,理解與欣賞批判的意義,這是一事。置資源有無於事外,穩定從事或長年投身批判,又是另一回事。在美國,傳播批判雖有傳統(Hardt, 1992),但可能因為不是主流,對外傳散也就比較慢些,因此,(比如,)它進入台灣已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進入中土雖然早在文革之後,但隱而不顯直至本世紀才告重來,前已述及。
可能是有見於此,即便美國文化與傳播研究大家凱里(James Carey)認為,哥大傳播研究與芝加哥大學不同,劉海龍並不同意,他沒有跟進這個建構出來的說法。反之,他看到的是兩個傳統相近、甚至傳承之處。因此,作者提請讀者注意,撰寫《移民報刊及其控制》的派克,其研究目的正是標準、典型的行政研究,是一種基於演化論、進化論、功能主義及「美國中心的民族主義」所寫就的觀點,想要消除移民文化帶來的社會不安定因素。總之, 派克崇拜一元秩序,使其在移民問題,「喪失了對個人自由或社會正義的基本敏感」。從以上視角所做的比較,不會凸顯哥大與芝大的差異,反而會是指認,派克其實開啟了拉氏在哥大「發揚光大的管理研究的大門」(頁 64-65)。文革後的中國,歷經舉世最大規模的城鄉人口移動,雖然與派克所研究的不同國度之間的移民,並不相同,惟離鄉背井所牽動的適應、排斥、 格格不入與(不)融合、辛酸、苦楚、希望的上升與挫折的浮現......等等過程,仍有相通的地方。
為管理者謀,派克與拉紮斯菲爾德都已用心,伯內斯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作者先行還原他應有的地位,指出伯內斯出版於1928年《宣傳》,具有「思想觀念的原創性、影響力」,但後人卻以該書「不夠學術」為由,未曾將他列入傳播研究之林。然而,劉海龍並沒有說「原創」本身,就能讓人肯定其主張。這是因為,伯內斯流於認定,凡是存在,就是正道理;在他看來, 公眾是無能的,因此,問題必須交由專家處理,而宣傳就是一種教育,並且不僅只是促銷商品,舉凡政治教育及婦女運動......等等,都可以是宣傳能夠奏效之處。作者認為這是一種不問「權力的主體」的立場,流於將人當成是「大機器的一個組成」,對於這種無端擁護現狀的姿態,劉海龍欠難同意(頁 74-77, 83)。
在新聞傳播領域、在人文社會領域,「行政」(「管理」)與「批判」研究; 「在地化」與「國際化」(或「全球化」);「東方」與「西方」;「普遍性」與 「特殊性」;「質化」與「量化」;甚至「(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劃分與二元對立的思維慣性及語彙,經常可見。《重訪灰色地帶》的作者不肯遷就,努力走出黑與白的二元窠臼,遂讓「灰色」不是黯淡無光, 而是進步的表徵,豐富了讀者對中國及美國傳播研究的瞭解。
参考文献从略,原文链接:http://ccp.twmedia.org/
《重访灰色地带》读后感(五):论国内新闻学院名称之争:兼论新闻学传播学与社会学之学术关系
读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厘清了新闻学、传播学与社会学的相互之间几个问题。
传播研究起源于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尤其以社会学在传播研究上的耕耘贡献最大。最先进行传播学研究的是芝加哥大学的杜威、库利、帕克等人,后来随着芝加哥学派的式微,社会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哥伦比亚学派,但是哥伦比亚学派的社会学家对传播功能失去了研究的兴趣,转向了工具性的题目、以民意调查、市场调查为代表的注重短期效果的应用性研究取代了纯学术研究,新闻学科接管传播研究后将其学科化与体制化,排除了其他学科的介入。也就是说,传播学研究的范式进行了革命,范式的转向使得传播研究与新闻传媒界紧密结合,不再关注社会学领域。新闻学进入传播学研究,取代了社会学对传播学研究的地位。
80年代,施拉姆来华推销传播学,也是用新闻进行了包装,他主要在新闻系活动,不再关注社会学领域,于是传播学在中国和新闻学进行了结合。其实,本来中国传播学的研究在民国时代已经有了自己的社会学学术传统,只是在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下,社会学被认为是孔德的改良主义,被无情取缔,社会学领域的传播研究被边缘化。文革后,从美而来的传播学已经是脱离社会学、将新闻院系当作垦殖目标的传播学,这时候传播学已是改头换面的传播学。另外,中国的传播产业不发达,中国社会学学者关注的领域转向其他问题,如城市底层、农村问题等。于是,传播问题被划入新闻学的势力范围,这样就加重了传播学和社会学的断裂。
所以,正是第一,美国社会学和传播学的断裂,新闻学介入传播学后对其他学科的排斥性;第二,文革后传播学进入中国后,已经不是社会学领域的传播学,第三,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社会学被当成“非马克思主义”学说受到猛烈批判,社会学关注下的传播研究只是处于暗流涌动的状态,并不入流。
有个值得大家注意的问题,当下国内大学新闻学院的有“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院“等名称之争,看似是”新闻“与”传播“之争,其实是新闻和传播之间断裂的学术传统所造成的。因为一直以来,传播在社会学和新闻学之间还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准确位置,而且中国传播研究的传统断裂,而民国历史记忆尚未完全挖掘,使得新闻、传播之间纷扰不断。灰色地带过于狭长。这也算是”社会唆使下的遗忘症“的一种表现吧。
《重访灰色地带》读后感(六):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一些新看法
刘海龙老师的《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和记忆》这本书是笔者在图书馆偶然遇到的,从书架上取出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对作者刘海龙的向往让这本小书承载了更多的期待。事实证明,读完之后,这本小书带来了更多的惊喜。
从整体结构来看,本书以中西为线,在西方传播研究史方面,对中国传播研究史中广泛重视的西方传播研究经典奠基人及学派如,拉斯韦尔、哥伦比亚学派、芝加哥学派、公共关系起源,指出这些“理所应当”的个性化、标签化人物或学派中与主流叙述相矛盾的地方,或者某些让我们有意无意被忽略的地方;在中国传播研究史方面,先是把中国传播研究起源追溯到20世纪初那段被主流叙事忽视的时间段。再是1978年中国传播学研究对西方理论的跨文化解读、想象与改造。包括对批判学派集体被遗忘现象的必然因素的分析,对“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变迁中学者态度的前后戏剧性变化的背后工具性使用理论的实质。最后是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的问题,从受众研究角度证实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的过度。在此基础上,作者辨析了中国传播研究本土话语,提出发展多元竞争合作的本土化,推进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进程。
本书虽出版于2015年,但正如书中后记中写到,作者从思考、酝酿到出版这本书跨越了近十年的时间,书中很多观点来自于作者平时的教学研究中困惑,还有学术交流中的新研究、新问题。本书的研究也是基于进入21世纪后,尤其在近几年,传播学界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反思,对批判学派的重新认知和理解,西方传播学理论研究进入新的阶段,研究者们除了意识到传播学研究的学术语境,还愈加看重学术理论的社会语境。
对于本学科的发展来说,本书的研究视角较新颖,整体理论构建在连续和断裂的辩证法之上,从“连续”中寻找“断裂”,从特殊的“断裂”看学科发展的“连续”,重新看到学术研究发展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此外,本书不是为了打破主流叙事而打破,在笔者看来,本书也有一定程度上的要求争取学术研究独立的意味。书中对学科主流叙事结构的挑战,对权力和市场等外力因素、对研究者工具化研究理论的因素的批判,都是隐含地要追求某种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独立。从更广泛的背景下来看,本书还反映了20世纪以来中西方传播研究的内在逻辑,为知识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
总而言之,正如书名,作者刘海龙从传播研究史中的“灰色地带”入手,结合新发现材料或被搁置的历史“碎片”,重新诠释西方传播学经典文本,反思当下中国传播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以求解构主流传播研究史中的宏大叙事,寻找传播研究的另一个可能的书写和记忆的视角,尝试解放传播研究的想象力。
在作者的西方传播研究史部分中,重点放在对中国传播研究史中不得不提到的传播学研究“四大奠基人”和学派的刻板印象的解构上。作者通过挖掘细节上的传播研究史料,树立了一批相互矛盾的形象,从而试图颠覆对这些人物及学科的单一性认知。其中,笔者原有认知受冲击最大的是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学术研究认知。自从从接触传播学以来,受传播学教材类的书籍影响,拉扎斯菲尔德自然是传播研究史中尤其受重视的一位人物,他是“两级传播”理论的提出者,他和卡兹等人进行了“伊里调查”,并出版了《人民的选择》,是“有限效果论”传统的开创者,他的研究方法是经验式的抽样调查和量化分析。 随着之后笔者对批判学派的了解,对拉扎斯菲尔德式的经验研究产生了怀疑。之前柯泽老师的论文中也有对拉扎斯菲尔德更为详细的介绍,让笔者从个人经历方面对他增加了新的认知 ,而刘海龙老师这本书从学术研究方面让笔者对拉扎斯菲尔德有了全新的看法。
这种新看法的一方面来自拉扎斯菲尔德并非完全赞同有限效果论。从拉扎斯菲尔德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他和默顿合著的《大众传播、流行品味和有组织的社会活动》这篇文章提出了我们熟知的大众传播的三个功能:低位赋予、社会规范强制功能和麻醉负功能。作者提到这篇文章,是为了证明哥伦比亚学派是不能完全等同于有限效果论,这篇论文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文本,对该论文是否有限效果论的解读是作者给芝加哥学派和有限效果论之间重新界定关系的一个切入点。作者先是指出了文中前后两部分的矛盾之处:前半部分“批判大众媒体的保守性,强调大众媒体影响,后半部分为大众媒体辩护,认为媒体的影响有限。”写文章一般都是一脉相承,后来作者推测,像这样自我矛盾的文章同时也说明了当时两位学者关于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问题的复杂性达成了某种共识,这篇文章一定程度上也是两位学者相互妥协的结果。既然文中两位学者都没有确定“有限效果理论”的结论,芝加哥学派也并不完全等同于“有限效果论”,同理,那拉扎斯菲尔德也不可能是“有限效果论”的完全赞同者。
此外,作者还认为拉扎斯菲尔德的经典代表作《人民的选择》中“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了大众传播强化既有政治倾向,却没有说过强化等于无影响。它的前提假设仍旧是大众传播学的强效果理论。”作者之后还列举到《人际影响》中与有限效果论相互矛盾之处:“当证明人际传播的效果大于大众传播效果时,同时也间接证明了大众传播的强大影响力——因为人际影响所传递的意见正是大众传播的内容。”而且“大众传播作为一种社会体制或权力,不能简单地和自发性的人际传播相提并论。”
在个人层面,拉扎斯菲尔德对效果定义也不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狭隘。作者指出1948年,拉扎斯菲尔德在论文中提到媒体效果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及两个维度交叉形成的16个单元构成效果矩阵。关于广受诟病的效果研究,作者以卡茨为例,如卡茨转向媒介仪式、叙事符号、受众意义解读和文化影响方面,但还是离不开拉扎斯菲尔德的“效果地图”。事实上,所有的媒介研究都不可避免的涉及对效果产生影响的结构因素。
这种新看法的另一方面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研究方法。拉扎斯菲尔德研究方法并非单一的抽象经验主义。客观上来说,拉扎斯菲尔德确实使“抽象经验主义”发扬光大,作者指出,拉扎斯菲尔德并非只把实证研究奉为唯一可行研究路径。作者首先提到拉扎斯菲尔德研究传统,他继承了欧洲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传统,对这些研究手法肯定也是熟悉并且认可的。
作者书中以阿多诺例子表明,拉扎斯菲尔德最初邀请阿多诺到应用社会研究局来,除了回报霍克海默之外,更大程度是因为看中阿多诺的独特视角与思维方法。此外,拉扎斯菲尔德还曾为阿多诺辩护,作为“中间人”调停。作者还指出,两人冲突后,拉扎斯菲尔德发表的《评管理的与批判的传播研究》一文中表明了对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的尊重。阿多诺离开研究所之后采用的实证与批判结合的手法完成的威权人格研究大获成功后,拉扎斯菲尔德因此在回忆录中有深刻的自责。接着,作者进一步根据拉扎斯菲尔德的社会主义者身份,他对两个人合作之前的期待,还有一封给阿多诺的信对拉扎斯菲尔德的态度进行再推论,表示拉扎斯菲尔德并不反对批判视角,两人之间争议主要集中在论证的逻辑之上,拉扎斯菲尔德坚持形式逻辑“应该以一定的规制和程序为基础”,阿多诺则采用主观性较强的思维方式。但之后作者提到了拉扎斯菲尔德对《人民的选择》文末有从受众角度暗示,间接指出拉扎斯菲尔德研究方法的多样。
不同于书中作者对拉斯韦尔、帕克、伯纳斯明显的偏爱,同属于西方传播研究四大奠基人的拉扎斯菲尔德的名字并没有占据某个章节,但作者并非真的就此遗忘了他,在对哥伦比亚学派及其批评者的重审后,以整体学派为依托,以一种细腻的方式再塑拉扎斯菲尔德本人学术研究的丰富性。
笔者读完这本书之后,以“拉扎斯菲尔德”为关键词查阅了国内几篇相关的论文,并大致翻看了罗杰斯的《传播学术史》 和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
发现这些文章和书籍对于拉扎斯菲尔德的观点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强调拉扎斯菲尔德对传播学的学术贡献;对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范式的批判;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关于“广播项目研究”的分歧及启示;对拉扎斯菲尔德学术研究的重新解读。
无论是对拉扎斯菲尔德的学术研究成果还是对其研究方法甚至个人层面的解读,不管这些解读是批判还是赞扬,不可否认,拉扎斯菲尔德在传播学术史中的确是位不可忽略的人物,他本人及其研究所带来的学术争议将会始终伴随接下来传播研究。在宏大主流传播学术史叙事传播学术史“应然”书写的背后,像拉扎斯菲尔德这样有些自我矛盾的学术人物并不少见,他们研究范式和成果在中国传播研究发展中都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刘海龙老师及胡翼青老师的传播史研究中,是对传统西方主流学术人物形象的结构,更是对之前单一刻板的形象的塑造的反思与批判,我们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学子,是否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找寻一条独特、新颖的传播史研究书写和记忆的途径呢?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2版。
2.柯泽:《社会心理学家参与美国传播学建设的历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9期。
3.[美] E•M•罗杰斯:《传播学史——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4.[美] 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最近读《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和《人民的选择》,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学术研究会有更多认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