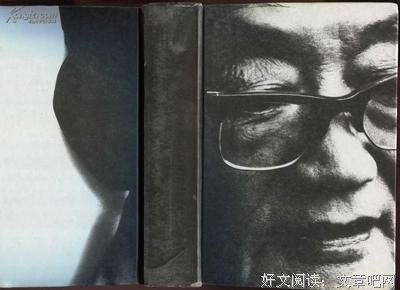父亲徐开垒与我 l 徐问
在著名作家、编辑,现代文学研究者徐开垒先生离去6年,由徐问、徐容编的《重读徐开垒》新近出版之际,开垒先生爱子徐问为“朝花”撰文。他笔触细腻的回忆中,开垒先生是一个慈父,一个一辈子一丝不苟地做好生活中小事的人。隔着纸面,我们犹能感觉到开垒先生为人的温度。
徐开垒在新华路寓所与儿子徐问、孙子徐承棠合影
父亲徐开垒虽然离开我们六年了,每每想起他对我的好,仍黯然神伤。人世间最揪心的事情,是他走了,我却记得他为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最伤感的事,是等我明白了他的眷眷之意,他却走了。父亲对我的养育教诲之恩,萦绕心际,历历在目……
记得父亲最早给我买书,是在我小学一年级下学期。他带着我到南京路新华书店帮我亲选三本:《西汉故事》《东汉故事》《银河漫游》。每逢星期天,只要没采访任务,父亲都会给我们讲书中故事,他讲得神采飞扬,抑扬顿挫,再加上自由发挥,常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父亲讲到动情处如岳飞被秦桧害死,我们会为之流下眼泪。他先挑一本书中的几个精彩片段讲,等我们对故事的前因后果感兴趣了,却戛然而止,让我们迫不及待自觉去读书。《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便是在我小学三年级读完的。继而,他又给我介绍了不少外国书籍,诸如 《基督山伯爵》《牛虻》《居里夫人》《爱的教育》等等,它们伴我读完了小学。我如今也习惯了像父亲一样,一有空就去逛新华书店,每一次都收获满满,还经常把许多书空运到美国。喜欢读书,为我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1965年徐问10岁时与父亲合影
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在我读小学一年级第二学期的一天,父亲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每天要记日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下班回家再晚,也要天天检查我的日记。有一天我贪玩,忘记记日记就睡了,父亲把我从被窝里拖出来,说写好再睡。从此我再也没落下过日记。父亲常常给我的日记打分、写评语,改正错别字和语法错误。有个暑假,我几乎天天重复报流水账,写来写去不是“吃妈妈买来的西瓜”,就是“和邻居同学下棋”。父亲的评语是,徐问小朋友,你最近的日记天天写吃西瓜和下棋,有什么意义?能不能写点有意义的事情?
徐问与父母亲合影
除了在学业上是我的启蒙老师,生活上父亲对我们的关怀和影响也是细致入微的。小时候早餐是吃粥,待母亲烧好盛到碗里,我们急着上学,常吃得肠子都觉得烫,也易得胃病。父亲就教我们,吃粥要先吃表面,再喝四周,然后吃中间,一层吃好再吃下面一层。按这个次序喝粥,果然感觉不那么烫了,同时节省了时间。又比如过马路,父亲要我们左看右看,如果身边有停靠车辆挡住视线,则一定要先将头探出去看,再过马路。他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比安全更重要的事情了。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教会我们一些生活细节,希望我们一生都能养成良好习惯。
当然,对于做好生活中的小事,向来严谨的父亲是身体力行的。尽管家里藏书多,他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他的书橱里,每一本书都有固定的位置。他去世后我们整理遗物,发现书桌抽屉的每一层都异常干净整洁,最让人惊叹的,是他集纳了从他幼年到去世前的上万张照片。从135、120相机到后来的傻瓜相机,他拍了巨量照片,使用的照相簿则有30多本,按黑白、彩色、年代、工作、亲友、家人等类别排列,每一张照片都被妥妥地安插在不同相簿里,每张后面都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左边是谁,中间是谁,右边是谁。
父亲的作品手稿,除了《巴金传》等已捐出外,都很好地保存了下来。看着方格子里清秀的字体,我们心中油然而生的是敬佩,更难忘父亲写作时的一幕幕。父亲从66岁起应上海文艺出版社邀请开始撰写54万字的 《巴金传》,历时四年。那时家里没有空调,冬天里,他半夜两三点钟便起床,穿着厚棉袄和棉鞋伏案写作;夏天则摇着蒲扇,汗流浃背趴在桌前,汗水常常把稿纸打湿。
徐开垒与巴金先生合影
我小时候兴趣广泛,喜欢“折腾”。父亲对我的爱好却总是给予无条件支持。读小学时我喜欢集邮,每天晚上盼着父亲回家,他再忙也不会忘记将寄给自己的信封上已盖过戳的邮票剪下带给我;我对做船模产生了兴趣,父亲就慷慨解囊,让我到南京西路船模店买材料回家组装;我又对做木工活来了兴致,他就买锯子、刨子,让我用它们做出此生中唯一一只木箱子,多少年来这只箱子一直被父亲保管着,舍不得丢掉……尽管我“花样”不断,兴趣多又易变,有时候颇有点离谱,但父亲义无反顾做我的后盾。记得有一次我被单位选派去当了一次陪审员,因感触良多、心血来潮,写下一篇一万字短篇小说《陪审员》,父亲便鼓励我把它投给筹备中的《宁波文艺》杂志社,未料想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尽管略有遗憾地把我的名字错刊成了“徐向”,但这毕竟是我唯一一篇公开发表过的小说。
徐问与父母亲在外滩合影
1986年,我参加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律师资格统考,拿到了律师执照,并在市政府机关工作。父亲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你的责任重大,业务水平必须好好提高。他联系我的大伯、民法专家徐开墅教授,让我一有空就到大伯家,旁听他给研究生的讲课。1988年,我去职考托福,申请自费留学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法学硕士,父亲知道后又是全力支持,鼓励我趁年轻到外面去看一看、闯一闯,他还用自己的稿费给我买了去旧金山的机票。我到美国后面临很多困难,父亲一直关注我,不断来信给予安慰鼓励。我在美创业后,父母亲四次到美探访,最长的一次居住了约一年,我陪父亲游历了许多城市,在一起谈论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在美国硅谷从事了近20年高科技风投基金的工作。父亲鼓励我说,你兼具中西方文化教育背景,了解中美法律,又熟悉中美两国的经济环境,如果把外国的先进技术引进来,对国家和个人都是好事情。在他支持下,我夜以继日工作,几乎每月都在中美之间当“空中飞人”。按理说,与父亲距离更近了,我们交流时间应该更多了,可是往往我的工作一展开就收不住。我一有时间就会去看父亲,最难忘2012年1月14日,临近春节,我和父亲一起吃饭,帮他解决一些家务事。临走时,父亲对我说:“徐问,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我当时并没有反应过来,想着忙完这一阵,一定好好陪陪父亲。想不到1月19日父亲竟撒手离我们而去,他再也看不到我在事业上点点滴滴的进取和进步,每念及此,我痛心不已……
父子聚少离多,但牵挂是一直的
徐开垒在旧金山与儿子徐问一家合影,(左起)分别为徐开垒、徐问、王玲娣、徐承棠、徐婕妮
徐开垒先生
(刊于2018年2月4日解放日报朝花版)
点击下面链接,可读部分“朝花时文”上月热读文章:
告诉你一群真实的芳华 l 窦芒
记忆中的“锦园”,是否还是原来的样子?l 曹可凡
《风筝》辩证三题 l 李建强
霜落天下 | 高明昌
今天,我们应该记起一个名字 l 章慧敏
《妖猫传》:有佳句,无佳篇 | 钟菡
《金瓶梅》写过的鲥鱼,在时间的长河里洄游 l 刘早生
冬夜之伤 | 唐吉慧
这是“朝花时文”第1467期。请直接点右下角“写评论”发表对这篇文章的高见。投稿邮箱wbb037@jfdaily.com。 投稿类型:散文随笔,尤喜有思想有观点有干货不无病呻吟;当下热点文化现象、热门影视剧评论、热门舞台演出评论、热门长篇小说评论,尤喜针对热点、切中时弊、抓住创作倾向趋势者;请特别注意:不接受诗歌投稿。也许你可以在这里见到有你自己出现的一期,特优者也有可能被选入全新上线的上海观察“朝花时文”栏目或解放日报“朝花”版。来稿请务必注明地址邮编身份证号。
“朝花时文”上可查询曾为解放日报“朝花”写作的从80岁到八零后的200多位作家、评论家、艺术家和媒体名作者的力作,猜猜他们是谁,把你想要的姓名回复在首页对话框,如果我们已建这位作者目录,你就可静待发送过来该作者为本副刊或微信撰写的文章。你也可回到上页,看屏幕下方的三个子目录,阅读近期力作。
苹果用户请长按并识别二维码,向编辑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