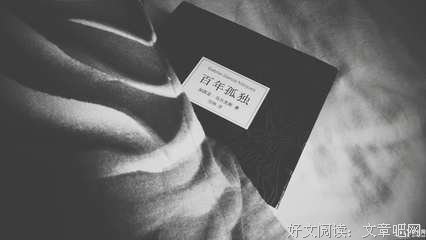放言有忌经典读后感10篇
《放言有忌》是一本由虞云国著作,华夏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放言有忌》读后感(一):听来的历史
也曾读诗书,也曾看古籍,却不曾有着那份由自己亲身经历而带来的感觉。看别人随心所欲的谈古论、引经用典,那是一种羡慕是一种期待。某天,我看到有人说着放言有忌,便不由的被吸引。我也知道历史是很久前的东西了。读史,读书,读世,那都是一种站在高处的博学。
读史,能指点古今政治文化的得失;读书,能探寻走出显示困惑的蹊径;读世,冷眼几率亲历世界的感情。领悟了三者,便是当成通透之人。看到读史里面作者说的毛泽东与水浒传的故事。那是一种能把平民化的书籍看成政治化的能力。那是一种能把历史的故事变成现实活学活用的过程,是一种任然或者现在之中的过去。而读书,读好书经典之书,追本溯源直截根本才能探骊得珠。官场制度,深宫闱史,无论哪种都不是想想就能明了的。而最让人在意的是现在,当下的生活,那是有着和历史密切因果关系,又一直会影响未来的关系。关爱现在就更不能忘记历史, 不敢那是怎样的存在。
有时候记忆是残酷的,而有时候记忆是温暖的,关键是你必须记忆。历史里的很多故事有的要学习,有的要反省,有的要感恩。作者写的有关高考的文章很是让人深思。独到的见解和对当时的解说很是让我赞同。对于高开1977我只是听说过,而作为有着经验的长者来说,那是难以忘记的日子。回复高考是感恩,那么想想为何高考会停止是不是更应该反思。一件事情,一个时代,有着偶然和必然的因素。再看到历史两个字的时候,就不会仅仅当成一个过去式来看。要知道失去记忆的人是悲凉的,失误记忆的民族是悲伤的。而在前行的道路上,就更该多借鉴多学习。中国的历史,上下五千的智慧,而后的世界大国变成了被侵略。再想想德国的分列和崛起,几次的世界大战,朝鲜半岛的现在的生活和格局,似乎会更加的明白当下我国该如何去做去说。看作者有说着现带文人的悲哀:不敢说,看见领导时的谄媚。如此下还有什么会给以后留下来呢。本书里面跟随作者的脚步能看到很多学到很多。他了广博的知识,信手拈来的史诗名著、诗歌文学都会让人不由的折服。他敢说,他会在权力和义务的统一下放言,为前行助力。历史的浅与杂难免,了解感触再说来便是个人的选择了。
听着作者的放言有忌,享受着一场历史盛宴,真好。
《放言有忌》读后感(二):有话好好说,有话更要不“忌”的说
(1025字)古之“放言”与今之“放言”完全是两个概念,也许是时代发展致文明之故,在封建时代,孔子说虞仲、夷逸“隐居放言”,即隐居不再说世事之意;而今之“放言”则是放纵其言,不受拘束,虽说言论自由,但也不能逾越法律的限度。故如此书名《放言有忌》,有忌,而不是全无禁忌。
这本虞云国所著《放言有忌》分三辑而成,从史、书、世三个方面,用三十八篇短文表达出对中国与世界重大政治、文化事件的真实想法,也并非全是歌颂之辞,多的是对社会现实清醒的认识。
三十八个短篇道尽人生百态社会万象,求取成功或是实现梦想者都可以细读其观点。李敖恣肆,言辞犀利,而虞云国则洒脱,多几分接地气。《高考1977:不应该仅仅是感恩》此书,表达了对1977年高考的感恩之心。这一年的高考,不仅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而是改变了数代人的人生轨迹,求取上进的读书人,唯有读者才得偿心愿。
《晚明的体制性贪腐》一文中,淡到晚清的病灶:贪腐。晚明官场以贪贿为得意,笑清廉为无能,官场是非已完全颠倒,可怕的价值观的全面沦丧。虞国云分析,“整个社会创造的财富,已经失去了相对合理的分配机制,而是最大限度地流入了掌控从中央政权到地方权力的各级官员与胥吏们的私囊。”“体制性贪腐遵循着按官等分红利的潜规则,把他们中最大多数成员拖入了腐败的磁力场,成为大大小小的实际受益者,欲为君子而已无可能。与此同时,体制性贪腐逼使卷入其中的每个官员在向上送贿与向下贪赃的两极之间恶性循环,饮鸩止渴而欲壑难填。这种恶性循环的必然结果,就是把不断扩大的送贿负担转嫁给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彻底崩溃,把广大民众逼上“穷且盗以死”的绝境。这种体制性贪腐的必然结果,最终把明王朝送上不归路。”
有话好好说,有话更要不“忌”的说,虽然是说史,但直指现实。
史学家虞国云在《放言有忌》中也谈到在大时代之中个人的立身处世方式。“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的人生境界与高度,是所有读书人究源的根本。虞国云从历史上敢于直言,政权从来是强者才具发言权;从个人素养上探骊得珠,不可否认个人努力对成功有极大影响;从世事而言,个体从来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而存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前进的脚步一旦停下便会遭遇社会无情的淘汰,桃花源式的悠然也需强大的支持才能实现,没有实力的镜花水月终是虚梦一场。
吴晗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读《放言有忌》并不觉得隔膜,如此以史明鉴,让人深思和警省,虞先生的真言真语真性格可见一斑。
《放言有忌》读后感(三):《放言有忌》:我们需要怎样的真实
作为一本由作者发表在各式刊物上的文章结集而成的文集,《放言有忌》中所容纳的文章难免让读者看来有参差不齐之感,但由于作者本身所具备的史学素养,加上对文字的敏感和坚守,仍使得这部文集值得一看。
本书的作者虞云国先生是一位知名的历史学者,主攻宋史。著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细说宋朝》、《宋光宗宋宁宗》等专著,同时还主持编撰了《宋代文化大辞典》、《中国文化史年表》,整理标校《文献通考•四裔考》、《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菿汉三言》等古籍十余种,可谓是著作颇丰。
这本《放言有忌》总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一“读史”,将作者几年来闲读史书的体会与感悟娓娓道来;之后“读书”,侧重谈论作者于读史之外的读书拾余;而在文末的“读世”,尽管仍旧立足文坛,但其眼光,显然已放之于学术之外。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虞云国认为,“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一个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下仍然活在现在之中的过去。”,因而在这本文集的第一篇,作者便以《历史的通感》为题,谈论了自己的历史观念。在他看来,历史的通感与“影射”显然是要区别对待的观点,前者由历史观察为根基,所谈论的也仅仅是有关历史的观点与规律性的升华;而后者所强调的,乃是历史,在非历史层面的应用。尽管这一方面的探索显得颇具诱惑,但对于读者和“单纯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方向,显然背离了学术的本来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虞云国先生其实是一个纯粹的“学人”,他所致力的,只是自己热衷的学问。他的名字或许因此而令人感到陌生,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有良心的书写者”,也并不妨碍你在闲暇之余,选择这样一本作品来充实自己。
“强调常识”是本作的一大特点,而这必然又要牵连出作者在写作上“平实无华”的另一特色。对于有一定史学基础的读者,这样的特点显然意味着这样一部作品是“可以被绕过的”,但正如作者曾在作品中表达的观点,“常识性的作品”应当被普及,既可悲却又是幸事,可悲的是大众本身对知识的缺失,会妨碍他们在社会活动中的角色扮演,而幸运地,是“亡羊补牢”,即这样的作品不断涌现,还可以对不甚乐观的现状,达成某种程度的弥补。
这显然便是作者这部文集出版的初衷了。事实上关于所谓“放言”,作者也曾在前言中做了探究,即关于中心动词“放”,既可解释为“放置、放任”,也可认为是“放任”之意。此中便隐含了“一出一入”的处世观,而作者的选择,显然是后者。
我们曾对历史,或者对文字书写下来之事深信不疑,但随着阅历的加深,我们开始倾心于“历史是胜利者的清单”这样的观点。其实信与不信仅在一念之间,而真实与虚妄,大概并无关于个体的认知,而只与信仰有关吧。无论你坚信怎样的故事,倘若信念为真,一切或许,仍是美好。
《放言有忌》读后感(四):何以“放言有忌”
何以“放言有忌”
“放肆其言”与“放纵其言”的唯一尺度,就是宪法规定的阈限。著名宋史专家虞云国在“光明鸟·主见文丛”《放言有忌》(华夏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一书中说,尽管书名“放言”,然而,“放言”的现代内涵,远比古典涵义更为复杂微妙。每一个世代,总“有某些说之不宜的话题负面清单,放言还是有忌的……”
纵观国际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任何一个开放的、民主的社会,无不将言论自由作为实现和健全民主制度的重要一环。但是,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差别,“言论自由”的“度”也各有差别。即便是在“最自由”的美国,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在1918年被禁,直到1966年最高法院才撤销禁令。1938年,亨利·米勒的小说《北回归线》也被禁止引进,直到1961年才解除禁令。其中,对不同思想迫害最严酷的时期是上世纪50年代初,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主导成立的“非美调查委员会”对异己分子进行调查听证,甚至列出了一份好莱坞黑名单。卓别林等名人都曾接受过美国国会的审查,一些大学教授还因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被解职。其现状,就像马克思所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宪法“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
从历史及各国的立法看,言论自由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但是,言论自由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它必须接受法律的限制。在历史及实践中,围绕言论自由究竟是相对自由还是绝对自由这一问题,各国思想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纵观历史,“相对来说,在中国古代,宋代文人具有相对较高的自由度,其关键在于对知识分子的基本国策。用今天的话说,宋朝制度的顶层设计远比明朝来得宽松……”由此,作者在书中认为,由制度顶层设计建构起来的历史大环境,无疑是文人能否相对自由的首要条件。
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一个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活在现在之中的过去。近日读史,发现不仅是现代社会与民主政治条件下的行政权利运作需要接受舆论监督和批评,就是在封建社会,那些开创了一朝盛世与和谐社会的开明君主,也是广开言路,勇于纳谏,主动接受舆论监督并鼓励公开批评的。据汉代王符《潜夫论·明暗》所载,“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虞云国的《放言有忌》分为三辑:读史,回溯中国和世界的重大政治、文化事件,多维度看待历史事件,评点古今历史政治文化的得失;读书,遍寻中外名家、经典,汲取智识,从书中探寻走出现实困惑的蹊径;读世,既有对“盛世修典”等热门事件的述评,又有对故人的追忆,冷眼记录亲历世事的感悟。尽管作者自谦“浅与杂,是难免的”,但现实既然构成将来的历史,某种意义上,不妨将《放言有忌》当作当代史来读,至于在读的过程中,是否又诠释出哪些历史的通感,那是读者个人的修为和境界。因为一个人的修为和境界,决定着他看待问题的高度或深度。
《检察日报》10月17日第06版:纵横
《放言有忌》读后感(五):“放言有忌”还是“读书有得”?
翻一翻文章后面的“本文原载”的各路书刊报纸专栏名目,就会发现原来书中所收录多是些作者的书评或读后感之类的文章。这其中既有作者对他人的书评,亦有作者对自家著作的评述,还有一些讨论了与书相关的话题。私以为,比起书名所用的“放言有忌”,明显该书“读书偶得”的成分倒要更大一些。其实,书中的内容写得太学术写得太学术也还好,觉着看得费劲儿的地方大不了跳过,但真正讨嫌的却是,那股子无论什么都不能就事论事,一概要向上求索,非得上纲上线到思想的觉悟,民众的素质,物质的昌盛,……时时处处总要攀扯上些大道理,非得要象征什么、代表什么才好的劲头儿,实在是让人消受不起。
大抵全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这此段话了,“格拉斯说得很实在:要找借口的话,唾手可得。然而,他最终反思道:自称当初无知并不能掩盖我的认知: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及时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责任’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P.086)读来令人深感震撼,话说这种深刻反省的精神,不独是我们的近邻需要认真学习,国内许多的“公知”身上也是严重匮乏的。让我们再次重温作为篇末结束语的这句话,——向格拉斯学习,向格拉斯致敬!
对后来这篇《且听海客放谈》的内容姑且不予置评。但读过后明显能够看出,作者对“公知”这个词,是极有感情的,不知是否源自于“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这个引进版的词源的关系?估摸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可能在作者看来“公知”所代表的是群有良心,社会责任感,有道德意识的特出的人,自然形容格拉斯这样的人物也是要冠以“公知”一类的头衔。但相较之下,我倒是更倾向于对该人使用“学者”这个更加中性化的称谓的,就像我对专业的素养、独立的思考、道德洁癖式的公平和正直这类的形容好感还会更多点,试问,一个真的有思想、有见地的人可能会去自诩自家的道德水准层次是有多么的超尘脱俗吗?
至少若是真的“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固然是不惮于说真话的,但他们从来也不是随意开口的,在对别人发表意见之前,他们更多的倒是先自省谦卑,自我批判了。私以为,正是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哲学塑造了当今东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认知方式,西方人一早便从宗教中接受了“原罪”的存在,所以他们能够更加理性地接受自己自私甚至卑鄙的一面。反之,我们的国人就不同了,潜在的认知差异直接导致了普遍性的缺乏一种最重要的勇气:剖析自己内心的黑暗面。于是,总想否定自身负面的一部分,不再自我反省,也没法安下心来思考。
除了盲目自大的认为唯有“公职群体”方能真正的济民于水火,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更加严重的集体缺陷,往往就是不知民间疾苦和不懂经济理论了!这些人成日里多动嘴说闲话,少动手干实事,莫非只是为了躲懒图闲不成?更加让人难忍的是,越是这样的“公知群体”就越热衷于代表别人,而被代表的人但凡表现出一点不乐意的样子来,便会被抨击攻讦是“缺乏独立精神”。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务实主义者,从很早开始我就不再喜欢给自己的行为找什么光明正大的理由了,是以对着时下意见多到泛滥了的“公知群体”,不免亦是抱持着和普罗大众一样的烦腻感的。
他们真应当回头看看梁实秋当年是怎样写的,——“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素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的发表一点‘不满于现实’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实’的药方。”这么多年下来,从来就没见这些人有丁点儿改变,他们一贯就只负责看不惯,是不负责解决实际问题的。还信口提出各种未经验证的“良策”,既不怕西风东渐后的水土不服,更不惮于拿着国民的生计来做实验一地鸡毛。是啊,他们怕啥,好了自然是万事大吉,不好了也大可以一推四六五,反倒怨怪别人把他的话当了真。别觉得不可能,这种事发生过的还少么。
记得在同书系的某本书上读到的话,深以为然,在此愿与诸君共勉:“一个人30岁以前不是左派,就没有良心;30岁以后仍是左派,就没有大脑。”上网查过后发现,这句话虽然是台湾的李某某最先说出来的,究其来源却是一战时期的法国总理克里蒙梭。一战时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刚上台,他的儿子就在街头参加左倾政治活动,有记者问,“如何看待你自己年青时的‘左’,以及你儿子现在的‘左’?”克里蒙梭从容对答,语出惊人:“一个人年青时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到中年时还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别怪我说得刻薄,可再多的抱怨不满,除了快活快活嘴皮子,还真没见改变了世界分毫,有这个闲时间,干点啥不比忙活这种“务虚”的事儿来得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