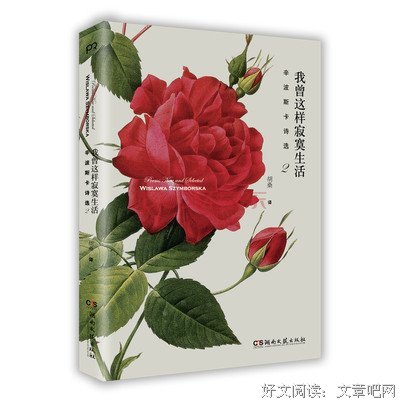《我曾这样寂寞生活》经典读后感有感
《我曾这样寂寞生活》是一本由[波兰]维斯拉瓦·辛波斯卡著作,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018-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我们这个喧嚣的时代,比起认清自己的优点,承认自己的缺点显得更为容易,因为缺点总被装扮得十分华丽,优点却隐藏得更深,而你自己从未深信它们就存在于你内部。
●记一次不存在的阅读之旅。
●精装版。修订本。
●我们都是时代之子
●断断续续读完的,依旧没有《万物》那种根本不想放下书的惊艳。标记了几首喜欢的小诗,闲来随手翻看它的西语译本。
●读诗的感受是挺私密的,所以觉得还好吧。(和万物静默重复了好多首)
●坦然承认,太破碎了,看不懂,找不到共鸣。 但是不打分无法Mark,所以给了现在已有的分数。 可能诗歌真的太私人了。
●诗人的生活
《我曾这样寂寞生活》读后感(一):我不知道
关于大多数,关于少部分,我不知道,
我看到的都很表面,我喜欢的都很直接,太过委婉深奥的那些,我不知道,
诗人有他特有的浪漫,跟不上他的想象节奏,这是我肤浅的借口,我不知道。
说实在话,看完辛波斯卡这本《我曾这样寂寞生活》,灵魂共鸣的地方并不多。翻译多少有些影响,但是本质上,辛波斯卡无疑是“真实世界的信仰者”。
她的目光多聚焦具体现实,崇尚确定:“我们的二十世纪本应超越其他世纪,如今,却并未改善,剩下的年月屈指可数,它步履摇晃,呼吸短促。”“爱吸引着我们,是的,但必须是,兑现承诺的爱。”
相比较而言,我更偏爱阿多尼斯浓郁的忧愁与深情,更偏爱海子燃烧的激情,赤子之纯朴与多重意象,更偏爱托卡尔丘克的梦与脑洞。
然而,我的偏爱并不影响辛波斯卡的魅力。如另一个自己所说:诗人在用不用的视角观看世界。辛波斯卡客观、冷静带着嘲讽或幽默,同样自成一格。 ———————————————————
当我说出“未来”这个词,第一个音节就已属过去。当我说出“寂静”这个词,我已破坏了它。当我说出“虚无”这个词,我已创造了虚无自身无所不能把握的事物。
第一次看到辛波斯卡的诗句,是在唐宁书店的诗歌夜晚。我们一起读了她的,我曾这样寂寞生活的长诗。正是这本诗集的名字,也是她的诗句的典型。
不宏大,不激烈,不涉及个人事情,只叙说细小的静默的事物的平凡,静默之中有隐约可见其中的深情。
她是冷静的。她并不想激烈的大声尖叫,只想做一朵优雅的带刺的玫瑰。她描写身边的细小之事,好像并不涉及个人情感。可对她来说,没有一块石头是寻常的,在诗歌语言中,没有一个存在是寻常的。
她偏爱写诗的荒谬,偏爱种种可能性,偏爱所未说之物。诺贝尔文学奖给她的授奖辞说到:通过精确的反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示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
她相信个体的、日常而微弱的、对雄辩具有天然抵抗力的声音,是人类获得自由的隐秘小径,尽管它曲折而漫长。
《我曾这样寂寞生活》读后感(四):青年时报对译者的采访
问:请回忆下您与辛波斯卡第一次相遇。
胡桑:最早接触她应该是2000年获2001年,具体日子已经既不真切了。当时我在西安上大学,在师大路邮局二楼的邮政书店,我买到了一册非常厚的《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歌金库》(人民日报出版社),将近1200页。这本砖头一样的诗选收录的最后一个诗人就是辛波斯卡。当然,那时候,她被译作“希姆博尔斯卡”,只有18首,译者是波兰文学专家林洪亮先生,以及当代诗人和翻译家黄灿然先生,这些是很不错的译本,但我当时更关注的其实是波兰诗人米沃什,对辛波斯卡没有足够重视,只留下一个粗略的阅读印象,觉得容易阅读,但结构感似乎不是很强,先锋性也不够,那时候,也许出于青春激情,对先锋性是比较热衷的。过了不久,我就在西安钟楼旁的万邦书城找到了辛波斯卡的单行本诗集《呼唤雪人》,译者林洪亮,几乎收录了辛波斯卡全部重要的诗歌,使我对她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又过了一两年,万邦书城里又出现了一本《诗人与世界》,译者张振辉,是辛波斯卡自选集,这本诗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为中文版的题词:“诗歌只有一个职责:把自己和人们沟通起来。”这三本诗集从西安跟随我到上海,不过,我一直没有像米沃什的诗集那样反复地找出来阅读。直到后来在网上流传见到台湾诗人和翻译家夫妇陈黎、张芬龄的译本电子版(那时候,《万物静默如迷》还尚未在大陆出版),我才重新发现了辛波斯卡,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译本,经过陈黎和张芬龄的翻译,我被她对生活的精微感受力所吸引了。然后才去翻出前三本来重新读。而且,我个人生活的变化,经验的拓展也可能是一个原因,才能逐渐接受辛波斯卡这样的书写日常生活的诗人。
问:您最早是哪一年开始翻译辛波斯卡的诗歌的?
胡桑:我是从2012年下半年才开始译她的。这之前一两年我在北京的叶壹堂外文书店买到一本辛波斯卡英文诗选:Poems:New and Collected.是美国著名女翻译家和东欧文学学者克莱尔·卡瓦娜(Clare Cavanagh)和波兰诗人斯坦尼斯拉夫·巴兰恰克(Stanisław Barańczak)合作翻译的。克莱尔·卡瓦娜是辛波斯卡在英语世界的主要译者,这个译本值得信赖。而且在书店粗略读了一些,和我在汉语中对辛波斯卡的感受很不一样,她的语言简洁、精确,很有质感。但我并没有想到译她,因为她的译本已经不少。后来,我的好友余西从台湾引进了陈黎和张芬龄译的《辛波斯卡诗选》,很意外地畅销,于是让我将Poems:New and Collected这本诗集中陈黎和张芬龄未译的部分译出来,我欣然应允,因为我自以为对她还挺熟悉,而且她的诗风我也挺喜欢。2012年的年底,我去德国波恩大学做访问学者,于是将辛波斯卡的这本英文诗选放入了行李箱,在德国继续翻译。德国和波兰是邻国,地理上的切近使我的翻译更具有了在场感,我的德国房东祖籍就在波兰的格但斯克,经常会聊起他父母在波兰的经历,而且,她父母和辛波斯卡的年龄相仿,经历过的历史时代也十分相似。他书架上还有波兰语-德语词典,也成为了我翻译的工具书之一。德国的生活十分安静,那时候我成天沉浸在辛波斯卡的诗里。
问:您是从波兰语直接翻译成汉语的吗?《万物静默如谜:辛波斯卡诗选》的翻译者陈黎:他有几十年透过原版唱片聆赏西洋歌剧和艺术歌曲的经验,翻译方式是以原文为本,参酌手中字典、各种语言译本、网络上翻译引擎及相关资讯,逐行逐句推敲、斟酌字意、诗意而成。不知道您的翻译方式是如何的?
胡桑:这两本辛波斯卡诗选都是浦睿文化出品的,他们购买的版权是我前面提到过的Poems:New and Collected.我是从这个英文底本翻译的。有时候我也会参照黄灿然、林洪亮、张振辉、陈黎等人的译本,但是,又怕会受到他们太多的影响,所以,基本还是忠实于英译本,以它为准。有时候,我也会找到波兰语原文进行对照,但是我只是初学了波兰语,对波兰语的理解只能起到解答某些难词、难句的作用,我要做到的是译文文本的样态尽量是贴近英译本。况且,辛波斯卡有修改诗歌的习惯,她的诗在波兰语中也有很多版本,我经常会发现同一首诗的波兰语本和英译本相差甚远,甚至只有几行相似,这种情况下我只能以英译本为准。
一首诗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词都是具有其特殊位置的,所以,我也会去推敲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词。但是,我首先想做的是从整体上熟悉一首诗,读透它,捕捉它整体的语调、结构和立意,在我和它完全像老友一样熟悉之后,我再逐词逐句推敲翻译,这样每一个词就是一个完整身体上的一些相互协调的局部特征。
当然,翻译期间,我也在阅读很多关于辛波斯卡的相关资料,尽管她的传记资料不多,但是仅有的一些我得做到熟悉,才能使她在诗中所排布的一些个人生活细节得到贴切地呈现。比如她有一个比她大六岁的姐姐玛丽亚·诺沃耶卡,她有一首诗叫《赞颂我姐姐》,诗题有人译作姐姐,有人译作姐妹,有人译作妹妹,如果没有传记资料的协助,就无法断定。比如他和丈夫之间的感情会大量入诗,虽然是隐晦的方式,我找来她的很多照片,熟悉她的一些生活片段和场景,解读她和亲人、朋友们的表情、服饰等等。这期间也读了不少关于她的评论和访谈,比如米沃什等人的评论,许多段落我都译了出来,安插在我为诗集写的序言里了。有位德国Dörte Lütvgot写了一本研究《辛波斯卡诗歌研究》读我也有所帮助。
另外很有用处的是Youtube上的一些视频(可惜国内打不开),我可以听她的诺奖演说,听她和朋友们聚会念诗、聊天。她生活中是一个很随和很幽默的人,气质非凡,翻译她的过程和阅读过程是一个不一样的享受。翻译引导你进入一个人更深的生活褶皱和内心的角落里。
我自己也写诗,我希望翻译的时候有一种写的姿态,就是在准确的前提下,试图做到每一首译作像是一个人在用汉语写诗。所以,对辛波斯卡的翻译必定融入了不少我自己对于诗歌和诗歌语言的理解。我希望每一首诗可以在当代汉语里成为一首具有质感的诗,一个词一句话在当代汉语里也需要有诗的质感。当然这只是我的预期,也许差距还很大,但我译的时候的确是这么想的。
问:你的这个翻译过程顺利吗?
胡桑:挺顺利。辛波斯卡的诗相对来说不是太难。而且在德国期间,除了学德语在波恩大学听课之外,我的空余时间不少,而且这是第一次到欧洲,我处在兴奋状态,生活也没有压力,译的时候状态还不错。当然,个别处也会遇到难以理解的时候,这也许和我的翻译能力和理解力有关,尽管我认为准确是翻译第一要务,但是我相信这个译本还是会存在问题,这有待时间的改变。过一段时间,我对诗对生活对语言的感受变化了,大概会对译本做一定修改。
问:《我曾这样寂寞生活》一书在国内三个月的印数已达10万册,估计这个数字还会被突破,作为诗集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观的,除了出版方推销有力以外,您认为,辛波斯卡诗歌最主要的魅力是什么?
胡桑:这本书应该还没有印到10万册吧,是前一本《万物静默如谜》销量已超过了十万册。
与很多现代主义诗人不一样的是,辛波斯卡的诗很少进行形式实验,她的诗平易,好读。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好友米沃什在诺顿讲稿《诗的见证》中为诗歌下过一个也许会令人困惑的定义:“诗歌不过是一句碎语,一个迅速消失的笑声。”辛波斯卡的诗歌大概就是对这个定义的完美演绎,她在《眼镜猴》中写道:“我如此轻盈。”她善于以微小的事物书写真理。那首《一粒沙看世界》就是这方面的宣言诗。在她看来,细节才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异的部分,而诗人的职责就是呈现这些细节,用语言赞美持续震撼我们的事物。
作为一名生活和平凡事物的歌者,作为向大问题提供小答案的思想者,辛波斯卡的诗歌明晰、简洁,能在顷刻之间深入人心,让她得以在全世界征服了大量读者,这都要归因于她精湛的诗艺,她不屑于让诗歌仅仅成为修辞练习或者米沃什所谓的“小小的孤独练习”。辛波斯卡不仅以其轻盈的诗风而独树一帜,更重要的是,她坚持不懈地试图用诗歌展现对事物的好奇,探索人类生活的严峻问题,她“把诗歌当做生命的回答,当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和责任的语言工作的方式”,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所说的,正是这样一种天然的融合,她的诗成为了“完美的语言客体”,这种完美的语言织体的确犹如音乐,而莫扎特的音乐就是以音符编织的完美的诗,不同于贝多芬的宏大,莫扎特的诗以轻盈取胜。在这个意义上,“诗界莫扎特”这个称号对于辛波斯卡当之无愧。
米沃什在《纽约书评》曾这样评价辛波斯卡:“辛波斯卡的诗探索着私人境遇,然而有时相当具有普遍性,这样,她才能避免独白。……对于我而言,辛波斯卡首先是一名知觉诗人。这意味着她面向我们说话,与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作为我们的一员,为她自己储存私人事务,以一定的距离经营它们,而且,涉及每个人从自己的生活中得知的一切。”这一评价十分准确。这也验证了辛波斯卡自己的愿望,我前面提到过的那句话:“诗歌只有一个职责:把自己和人们沟通起来。”
当然,辛波斯卡的诗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能力,就是反讽。她能够将板结的生活、话语和文字推到边界,使其流动起来。能够揭穿装扮成真理的宏大谎言。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天才般的能力。诺奖授奖词中也是这么突出辛波斯卡的反讽能力的。这样的反讽能力使读者在阅读她时,既能够享受她对生活感受的精确把握,同时又能将读者带入到一个新的处境,或者使读者获得一种大量生活的新的目光,她让读者的内心和生活流动起来。
《青年时报》2014年3月23日
《我曾这样寂寞生活》读后感(五):这个译本新译了84首《万物静默如谜》中未收的诗
我们同情那些并不相爱的人
——答《都市快报》记者戴小贝问
胡桑
1、作为一个过世了的女诗人,辛波丝卡在中国的影响力已经跨出诗歌爱好者的小众圈子,而被更多人广泛地接受。你认为她的诗歌有何与众不同的魅力?真的就像瑞典文学院赠予她的称号“诗界莫扎特”一样吗?
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好友米沃什在诺顿讲稿《诗的见证》中为诗歌下过一个也许会令人困惑的定义:“诗歌不过是一句碎语,一个迅速消失的笑声。”辛波斯卡的诗歌大概就是对这个定义的完美演绎,她在《眼镜猴》中写道:“我如此轻盈。”她善于以微小的事物书写真理。那首《一粒沙看世界》就是这方面的宣言诗。在她看来,细节才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异的部分,而诗人的职责就是呈现这些细节,用语言赞美持续震撼我们的事物。
辛波斯卡曾经回忆,八九岁时,她刚移居克拉科夫,和班上同学去参观一个反酗酒的展览会。然而,她对那些图表和数字无动于衷,记得最清楚的却是一块牌子,上面每两分钟就亮一下红灯,解说词是:“每两分钟,世界上就有一个人死于酒精。”她的一位女同学用手表测验红灯的准确性,并以优美的动作画着十字,念诵祝愿死者安息的祷告。这一细节感动了辛波斯卡。正是与真理具有沟通能力的、令人惊异的微小事物将世界从平庸的抽象中拯救了出来,这是辛波斯卡写诗的核心任务。她能够通过对细节的敏感,记录“日常的奇迹”。她的许多诗都呈现了对平凡事物的惊异感,比如《奇异》《奇迹市场》《一见钟情》等。
作为一名生活和平凡事物的歌者,作为向大问题提供小答案的思想者,辛波斯卡的诗歌明晰、简洁,能在顷刻之间深入人心,让她得以在全世界征服了大量读者,这都要归因于她精湛的诗艺,用她自己的诗句来说,“她拥有狙击手的敏锐视力/而且毫不畏缩地凝视未来。”(《仇恨》)德国当代诗人格仁拜因曾写过:“何为诗?诱人深入古老的智慧。”在这里,古老的智慧是去追寻“真正的绝对的真实”。辛波斯卡无疑也会同意这个观点。她不屑于让诗歌仅仅成为修辞练习或者米沃什所谓的“小小的孤独练习”。辛波斯卡不仅以其轻盈的诗风而独树一帜,更重要的是,她坚持不懈地试图用诗歌展现对事物的好奇,探索人类生活的严峻问题,她“把诗歌当做生命的回答,当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和责任的语言工作的方式”,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所说的,正是这样一种天然的融合,她的诗成为了“完美的语言客体”,这种完美的语言织体的确犹如音乐,而莫扎特的音乐就是以音符编织的完美的诗,不同于贝多芬的宏大,莫扎特的诗以轻盈取胜。在这个意义上,“诗界莫扎特”这个称号对于辛波斯卡当之无愧。
2、《我曾这样寂寞生活》这本集子和上一本《万物静默如谜》有何不同?为什么这本不先出呢?
《万物静默如谜》和《我曾这样静默生活》可以称为姊妹篇,它们都是由浦睿文化策划出版。辛波斯卡一生写作量不大,只有两三百首诗歌,她自己所珍视的不到两百首。陈黎译本《万物静默如谜》收录70首,不到一半。《万物》的成功让这本书的策划我的好友、诗人余西想再做一本辛波斯卡诗选,挑选部分陈黎未译的诗歌结集出版,他找到了我,于是才有了这本《我曾这样寂寞生活》。我新译了84首陈黎没有译过的诗,这样两本合在一起基本就涵盖了辛波斯卡的代表作。另外,考虑到有些读者并不一定会两本都买,所以余西又建议我,我又从《万物静默如谜》中挑选了14首代表作进行重新翻译,如《记一次不存在的喜马拉雅山之行》、《一见钟情》、《在一颗小星星下》、《植物的静默》等。所以两本书尽管有小部分重合,但基本上是前集和续集的关系。
3、诗歌是不可译的,你在翻译辛波丝卡时对这句话有何领悟?如果说翻译必然是丢失的过程,那么辛波丝卡诗中不可逆转的丢失部分,无法用中文传递的部分,你认为是什么?
翻译必定会丢失什么,辛波斯卡的英语译者克莱尔·卡瓦娜(Clare Cavanagh)曾将翻译称为“失去的艺术”,丢失几乎是翻译这项工作无法回避的宿命。因为翻译这个工作已经表明两门语言之间的差异,而每一门语言都有其非常精妙的表达(在诗歌中尤其如此),往往是很难通过翻译来再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可以说,诗歌是不可译的。但是,我同意本雅明的说法,每一部作品在翻译中才完成了自己,好的作品都是在召唤翻译的,也经得起翻译的。翻译就是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所谓的“创造形式的渴望”。或者说,翻译使原作获得了新生。因为每个时代对语言的运用和理解都在变化,语言是流动的,翻译捕捉到了这种流动的痕迹。随着时间的展开,我们不断地需要翻译。翻译不仅是共时的交流,也是当下与过去的交流。
翻译不是搬运,而是在另一门语言中找到合适的形式。另一方面,这种合适的形式并不意味着最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有时候尽量保留原语言别致的表达方式可能为为汉语带来陌生的令人惊喜的东西,这是翻译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也是翻译忠诚于原语言带来的收获,尽管这收获必定来得艰难。本雅明说,翻译就是母语诞生时的阵痛。当我们找不到对应形式去翻译时,正事母语正在诞生时刻。辛波斯卡的英语译者克莱尔·卡瓦娜说过:“我所看到的诗人和译者之间最主要的亲密关系是欢乐的挫折。”当我译下这样的句子:“燕子,你这锋利的寂静”,“它们的队列安闲地漫游于你的全部生活之上”,“移动大海,旋转每一颗星辰”,“他们承受着潮湿的希望,/一朵火焰燃烧于自己的颤抖之中。”我内心产生了抑制不住的激动,这正是翻译才能带来的语言,因为我们在日常汉语中不这样说话。
翻译有时候是一种发明。最近一个世纪,我们已经目睹了翻译如何丰富、拓展了汉语(我甚至认为我们在阅读古汉语典籍时内心也在默默地翻译)。遗憾的是,尽管我在开始学波兰语,但这是门很难的语言,我进步迟缓。我只能从英译本翻译。我根据的底本是美国著名翻译家和学者克莱尔·卡瓦娜和波兰诗人斯坦尼斯拉夫•巴朗恰克(Stanislaw Baranczak)合作翻译的,卡瓦娜的研究领域集中在东欧诗歌。她的翻译十分忠实于波兰文。而且英语和波兰语之间肯定要比汉语和波兰语之间更加亲近。我也在学习波兰语,可以从波兰语中做一些简单的校对。我曾经在纪录片和视频里听过辛波斯卡朗诵,那种抑扬顿挫的音韵和节律是汉语很难再现的。汉语只能通过另一种节奏使译文在汉语里成为一首诗。但很难说这种节奏是辛波斯卡诗歌在波兰语中所具有的。听辛波斯卡朗读,你可以在语音上感觉到一种幽默、智慧、轻盈,这在汉语里很难做到。好在我们可以在整体的气息上接近辛波斯卡,我在翻译中也是这么做的。
4、如同这本书的封面,大红的玫瑰,里面有大量爱情诗,比如《一见钟情》,《金婚纪念日》。但不同于以往女诗人的风格,比如疯狂,脆弱,辛波丝卡奉献了一个睿智、谦逊、隐忍的形象,她强调承诺,强调家庭之美,“爱吸引着我们,是的,但必须是兑现承诺的爱”。这是否是她在当下更深入人心的一个原因?
《万物静默如谜》做得很成功,得力于译者陈黎和张芬龄的出色翻译。诗歌并不必然是圈子的东西,越多的人去读优秀的诗歌,这是好事。优秀的诗歌书写的都是我们生活的秘密和处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和我们的世界。好的诗歌应该像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每天站立的大地,平凡而伟大。辛波斯卡自己的诗也是面向每个人写作的,正如米沃什评价辛波斯卡:“她面向我们说话,与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作为我们的一员,为她自己储存私人事务,以一定的距离经营它们,而且,涉及每个人从自己的生活中得知的一切。”
辛波斯卡曾说过,诗歌的职责就是将自己和人们沟通起来。在早年的诗歌《爱侣》中,她写道:“我们同情那些并不相爱的人。”(林洪亮译)她的诗歌才能体现在优异的反讽能力,在细小与伟大、短暂与永恒、切近与渺远、偶然与必然的事物之间取得巧妙的沟通,使每一样事物随时可能走入另一个未知的空间。在一篇书评中,她写过:“在那个时代的平凡与伟大之间得到真正的平衡。”这句话仿佛是她对自己写作的总结。她的诗并不封闭,而是向生活开放,向每一个人开放。
辛波斯卡写的爱情诗其实并不多,不过,仅有的几首却都深得读者喜爱,大概是因为她写出了人们在恋爱过程中的普遍感受,才引起了共鸣。不错,她的诗里充满对承诺的渴望,以及那种相遇的偶然性,突出表现在《一见钟情》中,然而正是这种偶然使承诺变得可贵,正如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所说的,爱就是忠诚于相遇。她的爱情诗里也是经过真实经验的浸润的,许多时候,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他与第二位丈夫科尔内尔·费利波维奇之间的爱。费利波维奇1990年去世。辛波斯卡1993年的诗集《结束与开始》中就充满了她对丈夫的思念。
5、你去探访过辛波丝卡生活的城市、居住的小屋、拥有的藏书,能否告诉我们,她吸引人的地方还有哪些?
翻译辛波斯卡的时候我正在德国波恩大学访学。而波兰是邻国,于是就有了波兰之行。当然我只选择了一个城市,南方古城克拉科夫。我在微博上看到《世界文学》副主编高兴先生也在波兰渡假,于是相约在克拉科夫见面。这次见面很美好,我们都对东欧文学兴趣浓厚,高兴先生新近还主编了“蓝色东欧”书丛。我们一起逛了古城,这是中欧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波兰文化的发源地。当然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它是诗人辛波斯卡居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也是另一名诺奖诗人米沃什晚年定居的地方。我们听说有辛波斯卡纪念馆,于是在街上问当地当人。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说没听过。但是我们继续前行搜索时,他却又骑车赶上我们,说他问到了,没有辛波斯卡纪念馆,但是有一个辛波斯卡纪念展览,就旁边的国家历史博物馆。他还推车带我们到了博物馆前。这个意外发现令我很高兴。这次展览名叫“辛波斯卡的抽屉”,展览的是辛波斯卡一生所收集的明信片、小摆设还有书籍,甚至有诺奖证书,身份证。之后我又寻访了她的故居,拜谒她在火车站北面墓园内的墓。
但是,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她的那些抽屉。只有在看过这些抽屉之后,我才理解了她在《种种可能》中所写的:“我偏爱桌子的抽屉。”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家里有几百个抽屉!另一名波兰诺奖诗人甚至送了她一个抽屉作为礼物。她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与爱的人。
另外,在展览现场还在播放一个纪录片,是伍迪·艾伦为她制作的。她每到一个城市都会收集一些小玩意,这是她在生活中的可爱之处。而且,她说话风趣幽默,经常会开玩笑逗人。这一点是在她的诗歌中不太能够读出来的。我想,与辛波斯卡交往一定是很愉快的,她是一个以生活为上的诗人,诗歌是生活的产物,她不会让诗歌来压迫生活。她是一个十足的美女,举止和着装都十分优雅,她的很多照片在网上流传很广,比如阅读、采蘑菇、抽烟等等,大概许多人有过深刻的印象。她不喜欢抛头露面,对出入记者云集的公众场合不感兴趣。至于她所喜欢的事物,我们可以仔细阅读《种种可能》这首诗来获知:“我偏爱电影。/我偏爱猫。/我偏爱瓦塔河边的橡树。/我偏爱狄更斯,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面记录了很多她真实的爱好。不过有一个她并未写出,就是拳击。她热爱拳击。在《我曾这样寂寞生活》的新书发布会上,波兰驻华文化参赞梅西亚讲过一个故事,辛波斯卡十分喜欢波兰拳王戈洛塔,由于时差,常在深夜看戈洛塔在美国的比赛,不过由于她讨厌媒体(作为诺奖得主,她也是名人),于是错过了唯一一次与戈洛塔的机会。她一直感到遗憾。她去世以后,戈洛塔写了一首诗献给辛波斯卡的诗,而且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写诗。我在“辛波斯卡的抽屉”展览上,就看到辛波斯卡双手举起戴着拳击手套的照片,显示出老太太很萌的一面,有一张还被放大到真人大小挂在墙上。
2014年0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