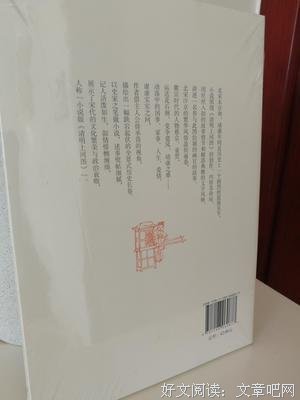汴京残梦经典读后感有感
《汴京残梦》是一本由[美]黄仁宇著作,三辉图书/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014-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汴京残梦》精选点评:
●不错的历史小说,但这版校对实在太差了
●很喜欢这种略为掉书袋的文字,又有史家的关怀,但是作为小说,风格叙述太分裂,清明上河图部分看得很有滋味,柔福一出场马上大跌眼镜,语言情节都很狗血,后面只要一提及两人的感情都有强烈的砸场感。
●该版本错漏字很多,顿时打消了入手毛边本的念头。历史学者毕竟在史籍中浸淫已久,文笔简省信息量却很大,不似某些小说家过分沉溺于对静态或细节的铺陈。如果黄仁宇“讲故事”的能力更强一点,或许就能把万历十五年改写成POV小说了吧。
●完美的嵌入,以假乱真,所谓小说家言,而能令二者混淆,此即高妙处。查史实,柔福遭际不确,可叹乱世浮生,纵连彼际显贵,亦未全身而退。
●“凌烟自绘,匠意英姿,两无差。”。清明上河图和李纲抗金的年代,黄仁宇幻想中画师和公主的爱情故事。
●写得好,但此版错漏太多。
●原来错字是真错字不是通假字 啊
●亂世中身不由己的無力感啊。歷史學的魅力就是從短短幾十字的史料裡去推測古人一生的故事吧。
●省图#文人写诗什么的真是看不进去 想起拨号网络还有聊天室那会 误入某吟诗作赋的房间 一群人在合辙押韵就差把酒言欢。虽然还没见过大千世界 却忽然明白所处的渺小
●从图书馆抽来的轻薄一本。历史学家写历史小说真心不敢恭维人物刻画,谋篇不错但措辞略呆硬,但是渗透其中的史实背景及对于历史对于人事的一些体悟却写得颇有见地,开卷生涩但确是精巧有益的小书。
《汴京残梦》读后感(一):作者也很尴尬
不建议阅读,浪费时间。从文学性来讲我至多只能给他打7分,本来只给6分,后来想他一个史学家也不容易多一分鼓励和宽容吧。全书两个线索,一个画《清明上河图》,另一条是和柔福帝姬的爱情故事,两个故事写的都很差。清明上河图的铺垫很多,但吧唧一下就结束了。虎头蛇尾。徐赵二人的爱情开始的莫名其妙,结束的倒是不拖泥带水……作者费尽心思插入一些宋朝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知识,然并卵,插入的很僵硬。我又不是来看历史书,我不需要在小说里看你把王安石变法每一条都写出来……
《汴京残梦》读后感(二):最是人间寂寞事,来世莫生帝王家
作者虚构了一个历史小人物,徐承茵,从他进京赶考开始把北宋末年的政治制度变化,皇帝的昏庸,吏治的腐败,官员的低效率,部队上下欺瞒人人只为私利一一反应在故事中。徐承茵因“画壶”好阴差阳错成为宫里画师,参与制作清明上河图与柔福相见,从而发展了一段与柔福帝姬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三份诗书笺文词优美契合,作者诗词功力可见一斑。读罢令人回味,深感此书还可以继续写下去:北上的徐承茵为了柔福帝姬靠着自己曾经的老本行在金人谋得一官半职,改名徐还。以期待日后能和柔福一起回到故国,回到家乡杭州。柔福却早已被金人糟蹋,因是年纪最大的未出嫁公主而进献金太宗,天性倔强不受宠,后来送去妓院。徐还动用他所有的金钱能量,终于把柔福带回自己身边。柔福早已不能接受破碎的自己,不能接受眼前这个为金人卖命的曾经的心上人,虽然徐还从没有以武职伤害大宋军民。于是她独自了结了自己的一生,时年绍兴十一年,三十一岁。徐还在北风呼啸中,感到半生业已成空,独往佛门而去。
《汴京残梦》读后感(三):历史小说不是借口
简介写得荡气回肠,让人的阅读欲陡增,读来却软绵无力,不尽兴。
连上尾声全书共二十一章,第九章女主人公才出现,见第二面徐承茵就主动亲了柔福帝姬。一个画图的小臣子敢唐突帝姬,努力调和身心想象置身于封建社会的读者看到这里,“啪”地一下脑袋空白了徐承茵的忐忑、激动以及后来仕途上的跃跃欲试,似乎都是为了配上帝姬身份,跃出自己的阶层。能得帝姬另眼相看,宠辱若惊,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早已落了下乘。
人物塑造的无力与情节的缺失不消说,因为作者在前言已提点读者,这是本“历史小说”。所以清明上河图一幅画而已,提升到影响朝政的高度。文中屡屡提及绍述,恕我功力浅薄,看不出作者想交待怎样一种历史观。
开篇与结尾写得反而好一些,仆人将徐承茵一人扔在荒郊野外逃跑,徐那种等待的焦灼与无望,国破、前途黯淡、爱人离散,人生到此凄凉否?耳边回响着徐母絮絮叨叨念着:“他们都不叫他徐老爷和徐相公了……”家庭的败落,个人处境的窘迫,齐上心头。
无论如何,黄先生想到以一种小说的方式追述远去的历史,终究有一位史家的热情在里面。历史学家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勤奋型,一种是天才加勤奋型。豆瓣读书的历史分类里,翻了一页又一页,张荫麟张先生的中国史纲堪堪在第七页找到。可惜先生英年早逝,可叹由他撰述的宋史该是如何引人入胜。所以说,寿命也是实力的一种。
《汴京残梦》读后感(四):皇帝老儿用金砖擦屁股否?
这本书放在书架好久了,冲着黄仁宇的名字买的,不知为何第一次没有读进去,许是因为该书和《万历十五年》风格迥异,让持有刻板印象的我一时接受不了。
第二次读起来却感觉颇为惊艳,不禁奇怪为何第一次竟读不下去。
历史学家写历史小说,当真叫人读得放心又满怀钦佩,可惜我历史学的不好,不知道文中哪一段依傍的是哪段史实,或是出自哪个典故,很希望黄先生能在书后出个“参考书目”,我可以照着列表读下来,后来想想,先别好大喜功,能把《宋史》读过一遍再说其他吧。
奇怪豆瓣评分竟然只有7.7,我是想给五星的,起码四星。作为小说,这篇的风格实属难得,文字风格有古韵,达意且流畅;依托史实,算是另一种史学科普;对世态人情的刻画,又往往让读者感同身受。唯一的缺憾是主人公的感情生活,真是让我出戏,不禁没有被感动,反而觉得有损主人公形象,落了俗套。大抵小说必得有感情戏来贯穿么?
作者对《清明上河图》的描写,细致生动,但我之前看了冶文彪的《清明上河图密码》,所以对这段并没有特别惊艳。但黄仁宇和冶文彪的风格不同,黄更像是解画,冶文彪注重在情节上天马行空。
摘录一些原文,当做书摘记录吧。
读过就忘,很是困扰。
4 人穷则思父母,这话是说得不错的。
7 说到这里陆澹园又用一只手指着承茵:“你们那里怎样?画卷有标题作交代没有?”
16陆澹园此时已经微醉,他用手指点着承茵面上说:“可不要忘了,下次不许推托!”(读到这略有不舒服,为什么这个人说话一直用手指着别人?作者是故意这样写?读到后来发现,作者对人物刻画极细。)
15他所填词固然按集韵,但如以南腔调唱出,更能表态所叙之扭捏味道,比如“子”和“似”,少带“紫、缁”之浊音,“与”读如“吕”,“美”读如“米”,也就更够劲了。(试着读了一下,仿佛可以想见当时的趣味)
17这东京到底有多少人口?……此口数之内妓女不可能少过一万人,尚可能在两三万以上。再加假母仆佣之类靠青楼乐籍为生的人数,应在三五万之间,承茵想着早已如此。不然来京应试的学子一次即一万七千多人。他们一方面竞取功名,一方面也随船带来各地方物在京出卖。漏付关税所得盈余趁此名士风流一番。虽不每人如此,很少的能例外。若无众多的妓女,如何能容纳如是许多的五陵年少? P19今人生在大宋,婚姻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行,没有古人桑间濮上自寻配偶的自由,所以偶尔在花丛中寻欢,也为时下谅解。
57 此时承茵不免在嫉妒之中掺杂着许多无名的情绪。再因着澹园更觉得对不起自家的小妹。他的妹夫尚未成亲即有这样的外欢,则他日徐苏青的空闺独守也可想像了。
(当时的京都风气,狎妓合法且属于名士风流。漏付关税那个算是当时的“代购”么?)
18夫钱者泉也,总要川流不息,你既不许人兼并聚敛,则要使之发散流通。蔡太师论国家财富,“和足以广众,富足以备礼”,务须多出多进也是这个道理。
29 这事之成为争端则是很多人,也包括朝中上下认为“劳民伤财”蔡攸的训话承接着父亲“丰亨豫大”的宗旨,务从大处着眼,劳民并不见得伤财。国都内外很多人民愁苦,主要的原因就是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京城内财货堆积如东汉之西园唐之琼林,不使之流通,莫非愚不可及?他又引用《孟子》讲及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和文王以民力凿为沼,而民欢乐。再用《诗经》所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要把皇室之事做好,然后利之所在也泽润到老百姓头上了。
41王荆公是对的,蔡太师的基本方案也是对的,国库既有盈余就当下放,所以修京城,筑宝宫,造艮岳,运花石纲都可以使民就业,本身都不失为善政。并不是朝廷有任何举动即是与民争利。”(经济理论)
19可是词又与诗不同,它上一句可能修饰得极尽其华美,下一句又可以不嫌俚俗,好像以口语道出。(作者说“诗”和“词”的差异)
28什么星变会影响朝中政局?不是四十多年前的王安石王荆公即说此种天象经常发生,也与人世间之有德与无德全不相干?徐承茵即及此事曾受好友李功敏的指点,他要承茵不可造次。李剀切说及国家大事看来全是朝廷作主,其实不然。朝令也要透过各地府尹县令才能下达闾阎里巷,各地方官也不能全不顾及下情。迄至今日四海之内都知道天子奉昊天诰命办事。所以天象失常,天子避殿减膳,诏求直言,已千百年如此。如果天子而不畏天,则全国上下也失去了听命于朝廷的根据了。(天子的无奈)
47 至于方腊所部之被肃清,还是由于山东剧盗宋江的反正。他们这一伙人被龙图阁学士知济南府的张叔夜诱至海滨决战。该处无山泽水沼可以置奇设伏这群绿林好汉一见无计可施,也只得俯首贴耳就降。至此他们仍不过打算暂时偃旗息鼓,来日再图大举。而这张叔夜也并非心无城府等闲之辈。他早已与各方布置妥当:宋江降张后第一件任务即是往江南征方腊以期待罪图功。初时官方还允许诸强人保存着“替天行道”的杏黄色旌旗标号,只是一登过江船只,这批人才发觉自家兄弟已是两百人一队、三百人一营的分割配属于童贯的各军中。又加以方言不同,土地习惯迥异,也无从与南方的叛军聚合,自此别无他法只得在官军中打先锋。这边方腊乌合之众,也并非真有手下的本领,而不过由于官军畏怯才致坐大。此刻听说连山东好汉都已降宋,此后还要打硬仗,也就无斗志了。所以以毒攻毒之计奏功,不到年底方腊授首,他手下伪丞相太子等一并成擒。(狡猾张叔夜)
53只是专注着自家愿讲愿听之事而不及旁人之嗦乃人之常情。
53这画卷已定名为“清明上河图”,取其“清明在躬”之意,只表示城中一种意态,并不一定所画限于清明节那天的情事。
56 徐承茵多时希望姻弟来京可以抵掌作长夜谈。至此一顿饭之后不免失望。一方面看来陆澹园慷慨直言的形貌依稀如旧,另一方面则显有新来的隔阂。他也不知不和谐的地方究在何处。(恰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感觉就是如此微妙不可言)
56 大凡男女间之事,最是要得专心。如果两方存着一片痴心,将人世间任何纵横曲直,全部置诸度外,也不分你我,则灵肉相通, 身心如一,彼此同进入海上仙山的神妙境界。若是当中有任何阻隔,有如听到不悦耳的声音,闻及不愿入鼻的味觉,则此类事物立即将当事人打归尘世,此时一个人骑驾在另一人身躯之上,不仅猥亵,而且尴尬。(趣,对)
57 如果没有几件分心之事,徐承茵甚可能与她倾情尽欢。不幸花枝又因着她自己对楼华月的嫉妒做了勾栏之人不应做之事,在顾客前议论自家姊妹之长短。
92 可是此际茂德与承茵彼此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则是女子的地位,已正走向下坡。先从皇室说起:国初自杜太后强令太祖传位于太宗,立弟不立子以来后嗣而参政,实为大宋传国之特色。不料哲宗以冲年践祚,太皇垂帘听政,功成身故事历三朝,只因近日党争,臣下犹敢追罪于她,请追废她为庶人。哲宗身后刘皇后虽加衔为太后,最后被逼自尽,此皆千古未有之事。再说国家之下层:民间生有女子,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备士大夫采拾娱侍,以后皇都汴京妓馆林立,最近则缠足之风气逼近上下。(作者多次为女子发声)
104 他提起画笔,自此随兴所至无往不利,笔下之帝姬,注视有神,唇吻微长,面颊浑圆,双手柔软。柔福虽不是国色天姿,只是一团利落明快,惹人注视引人爱慕的形像已跃然出现纸上,自己过来看着也点头认可。
(Are you kidding me?)105 他已经再四压抑自己,只是禁不起最后一问,她之一问,在转瞬之间把他间成一只脱缰之马。他抛弃了所有画具,两手合围放在我她肩背上向着她狂吻过去……(太突兀了,吓到我了。至此方发觉,真的是“小说”。男主一副孟浪轻浮状,哪有之前的种种君子作态?感觉作者写到与公主谈恋爱种种,还是离真实的公主有距离,虽然我也不知道真实的公主是什么样的,但总感觉作者的描写太过于贴近凡人的想象,不禁让我想起那个关于皇帝用金砖擦屁股的比喻。)
107 谁也知道翰林院有职无权,只是衙中官员待命于中枢,交游泛,常有职权以外的声势。如果得罪了他们,可以影响到层峰,因之商税务的人员不得不谨慎行事。
112 承茵被他说得哑口无言。这白庆文将一切归咎于京官,初听来人感到不平,可是再一付思,自已何尝不有同感?朝延既有旧章又有新政,即以描画汴京景物为例:先说体顺民情,据实直书,前后罗致了十来人,换了三个主持。费时两年余,今日说楼台亭阁不画,明日又说骆驼要画。一个主张舟车房舍按实际尺寸比例画:一个又主张不能完全放弃朝霞与暮雾。再一想来连他徐承茵自己也没有把这问题简化,他也主张侍婢用宫装,也为画幅生出无端是非。
118 他又习得三纸大字楷书,可是看来总不如意,也仍是眼高手低。自是他又付思:此等事到底是雕虫小技,只是一入文士之手,才借此写作大块文章,道传真伪,播弄是非,什么君子小人,良臣贼子,作陈情表,镌党人碑,一切都来了。太史公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也就始自此处。倒不如原始初民结绳记事,免去了这套颜柳苏黄,来得爽快利落。
179 同到旅邸的途中他心中忖想:那宣和元年底他和陆李一共三人以杭州府举子的身份来京会试早逾六载,倏忽将近七年。于今落得他们两人都为亡犯,自己虽逢主官被黜,比着他们却又远胜矣。可是自家心头烦恼,也为他们所无。
微信公众号:ligaoxing
《汴京残梦》读后感(五):一篇旧书评
来自: 还有我,是一头狮子 2007-08-02 22:00:25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823912/
传统历史小说的叙事方式,常以人物,特别是传奇性的人物为中心,从罗贯中以降,到现代的高阳、二月河莫不如此。当史家黄仁宇试图以小说家李尉昂之眼看历史时,他是在哪里看见了小说的可能?
历史学家黄仁宇生前,曾以笔名李尉昂发表两部历史小说作品:《长沙白茉莉》与《汴京残梦》。前者写三○年代的上海,后者则是靖康之难前的北宋京城。两部作品各自书写一个不稳定的年代,一座繁华的城市。
小说家李尉昂与历史学家黄仁宇,这同一个人的两种叙事身分,毕竟是分不开的。从《万历十五年》已经可以看出作者在历史叙事上破格的尝试。然而小说写作与历史叙事有所不同,尤其传统历史小说的叙事方式,常以人物--特别是传奇性的人物--为中心,从罗贯中以降,到现代的高阳、二月河,基本上都不脱这样一种以人物为中心的书写方式。史家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点,是否体现在小说家李尉昂的历史小说当中?而传统上以人物为主的历史小说文类,在现代史学训练与历史观影响下,是不是能出现新的书写可能?
历史与历史小说
在明清历史小说论述中,理想的作品必须具备通俗的阅读乐趣,并且不严重违背正史。也就要小说家在正史的文本真实之下,作叙事的发明(通俗化、浅显化),而非故事的发明。李尉昂的历史小说,基本上也承继了这样一种传统。
首先让我们回头看看明清以来的历史小说论述。
在中国的文史传统中,历史向来被赋予「以古鉴今」的现实功用。历史在求真纪实的担子之外,还有一副更沉重的、影响现实的责任。历史既是政治正统解释的来源,而历史人物的忠奸贤愚,又关系个人行为伦理的殷鉴,可以说历代官方的正史文本,等于是一套正统政治与伦理学的解释系统。
相对的,小说作为一种通俗的文类,少了这些肩头重担,伸展的空间本来应该是大得多。然而历史小说的情况比较特殊,处在中国文人对「历史」与「小说」两种文类不同的想象之间,历史小说的处境似乎显得左右困难。主要是历史在中国文史传统中的神圣光环,对历史小说文类形成一道紧箍咒:如果往通俗小说的那一端稍稍靠拢,便要小心流于「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的责难;虚构的成份多了,也要落入「重诬古人」的抨击。
因此,明清以来诸多为历史小说请命者,举出历史小说足堪称道之处,如明代庸愚子称《三国演义》:「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 言下之意,这考诸国史、事纪其实的实证工夫,得以使小说不同于「失之于野」的瞽者之言。
尽管许多明清文人把历史小说读得这样严肃认真,却不时仍有一二人,迂回地承认他们爱读小说胜过爱读历史。「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 对照于令人昏昏欲睡的正史,历史小说等于将他们从读史的昏倦中拯救出来。因此历史小说的价值在于逼近于历史,但却用一种较为通俗的方式呈现,使「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在历史与小说之间,明清文人有意识地将历史小说向历史的天平这一端拉,藉以替历史小说正名,同时更要强调,历史小说也具有史册阐述盛衰治乱、臧否人物的伦理学功能。
逼近于真实仍是历史小说不可不备的要素,以便借着真实的权柄(authority),引导读者进入正统的政治伦理教训系统。然而小说毕竟不免虚构。被评为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的《三国演义》,其实也在不少地方改写了史实,或是借着小说家丰沛的想象力,将角色膨胀出正史记录所没有的丰富性。相形之下,明清文人们强调历史小说真实性的话语,有些像是在对历史过于神圣的想象之前,为自己嗜读小说寻找着合理化的借口。不过整体而言,历史小说与正史的对应关系,仍是被强调的。 综上所述,在明清历史小说论述中,理想的作品必须具备通俗的阅读乐趣,并且不严重违背正史。也就要小说家在正史的文本真实之下,作叙事的发明(通俗化、浅显化),而非故事的发明。李尉昂的历史小说,基本上也承继了这样一种传统。
至于历来的历史小说,如何在对应正史的架构下,去作叙事的发明,是值得深究细绎的问题。把水浒、西厢列为六才子书的金圣叹,论及他心目中的演义时,即是偏重不将历史真实多做穿凿改造的写法:他盛赞《三国演义》「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而且无所事于穿凿,第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而已无之不奇」 ,也就是以原汁原味的历史材料,事实始末无所穿凿,而能写出其中之「奇」,为最高境界了。以下我们也将讨论李尉昂的小说,在历史框架下作了什么样的叙事发明。
再进一步思考,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以「庶几乎史」而获称道,这里的「史」,不是历史,而是史册;指的不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所辐辏出来的历史真实,而是「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的正史。
换句话说,明清文人担心冒犯的,不仅是历史上的真实,更是正史文本中的真实,以及藉由这个文本真实而开展的历史、政治、伦理教训系统。为了维护这个教训系统,正史文本的真实性因而不可更易、不可唐突。这也就是明清文人面对历史小说中的虚构,最大的焦虑之所在。
正史文本的神圣性,在现代中文文学世界里显然已被打破。然而历史小说与历史真实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不能断离,只不过历史真实的形状,不再如前述明清历史小说论述,为正史文本所规范。高阳的历史小说,可看作是正史的紧箍咒突破后,历史小说家以大量的笔记史料渗透正史,在考证与笔记两种传统上吸取小说叙述的养分。
而黄仁宇在现代史学训练之下,面对历史的态度,便不仅是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考证、翻案出新的历史真实,而是整个问题意识的转移。现代史学的问题意识,与大历史的史观,如何影响到李尉昂的历史小说写作?这是我们接下来要问的问题。
当史家黄仁宇,试图以小说家李尉昂之眼看历史时,他是在哪里看见了小说的可能?
如何画下流动中的汴梁城?
如何画下流动中的汴京城?这既是李尉昂笔下的角色张择端等人,在小说中面临的问题,也是李尉昂作为小说家,必须思考的问题。历史小说家面对的汴京城就是历史真实──庞杂错综,无所不包,几乎不可能作为知识的对象。然而在历史真实之外,还存在另一个历史:经过史家或小说家选择、裁切、解释的历史。最后才是历史小说家以当代读者能够理解的形式,再现出来的作品。
倘若史家的工作,如布洛克的主张,包括判断何者为真,何者为伪,及何为可能(identifying the true, the false and the probable)。则小说家越过真、伪,更偏重寻找的是最末的那个选项:「可能」。那么,当史家黄仁宇,试图以小说家李尉昂之眼看历史时,他是在哪里看见了小说的可能?
也许《汴京残梦》的故事题材本身,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汴京残梦》描写北宋徽宗年间,一名参与绘制「清明上河图」的画官的故事。在其中,我们也可窥见作者的历史小说观。
清明上河图绘制的时代与动机,在学界很有一番争议。这幅名画,有不少摹本存世。其中公认艺术成就最高,且为一般人所习知的,应是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图。这幅图并非北宋年间的作品,而是清宫画院里的五位画家,于干隆元年合绘的画卷。虽然仿自宋代张择端的画卷,却在成就上超越了原图。
《汴京残梦》书中所指的清明上河图,显然不是清院本,而是宋清明上河图。问题是宋代清明上河图的身世极为模糊,作者张择端传世的记载不多,关于他的生平,留下的不过是幼读书、游学京师等笼统的叙述。甚至他是宋人还是金人,也有一番讨论。非仅如此,存世的本子当中,何者为真?何者为伪?真本是创作于北宋,还是南宋人因思念故都而作?这些都是尚无定见的疑问。在清明上河图一片「汴京富丽天下无」的景致中,隐藏的只是无数历史的可能性。
这种种历史的可能当中,作者李尉昂选择了其中一种可能性,当作小说作品中的真实。在李尉昂的笔下,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徽宗下诏,令画院画师们绘出京城汴梁的景物与民间生活。由于历史真实难以断定,相关的事件在史料中湮没于无形,它们和《汴京残梦》小说中的真实,两者间的对应关系也就无法得知。《汴京残梦》等于是抓紧着这一种可能性,在史料的缝隙间建构起来的。李尉昂既然选择了将清明上河图视为北宋徽宗年间,下诏绘制的一幅画作,由此便引伸出整本小说中,关于清明上河图绘制过程的描述。而徽宗时代的人物如蔡京、童贯;史实如运送花石纲、党争遗风、靖康之难等,则纷纷取得相对位置,次第落座。历史小说家的叙事发明,便是在这些历史事件与时间错落的相对位置间,展开布局。
在李尉昂虚构发明的情节当中,有关于三任画学主持不同的绘画观点,很可以当作他的历史小说观来解读。
在《汴京残梦》中,这清明上河图的绘制,带有帝王欲藉以了解京城民生百态的用意,要将一座繁华喧嚣的东京汴梁,加载平面的画卷中,成为知识的对象。然而偌大个京城,究竟什么应该入画,什么不该入画?这其中牵涉到主其事者的选择。在李尉昂笔下,主导清明上河图绘制工程的画学主持,先后换过三任。第一任要画中景物样样出自实录,要求画官们写生街上风景,完全得「我笔画我眼」地照实写生,不得隐瞒扭曲。第二任主持和第一任大不相同,以为画之可贵在于近乎神仙仙品,不可出自强求,于是这位画学主持喝酒的时间,倒比作画的时候多。
第三任主持,也就是最后与清明上河图一起留名的张择端。在史料中仅找得到聊聊数行记载的张择端,在这里便由李尉昂的小说家之笔来为他赋生血肉,成了一位处事有条不紊的翰林学士。这个小说角色张择端的主张,介于前两任之间。他认为画作既不能脱离现实,也不能一砖一瓦照单全收,无论如何,要将一城的景物,画进二十尺的画幅内,就不能不透过画家之眼,加以「选择」。(「选择,选择──选择。我的名字不就叫做张择端吗?」小说中的角色张择端如是说。)
小说中这历任主持的三个角色,正象征了三种艺术态度。也可说相当程度地反应了李尉昂的历史小说观。在小说中李尉昂为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加上一道来自帝王的最高指令:写实──写京城之实,于是清明上河图之于当年汴京的现实景况,遂构成一种再现的关系(representation)。正如李尉昂的历史小说,之于历史真实情境,同样是一种再现;至于再现的方法,李尉昂藉张择端这个角色写出的,可以说正是他的历史小说观:既不应是一成不变的临摹,也不应是天马行空造起空中楼阁,而是考实与想象相互衬托。在这再现的过程中,「选择」尤其必要。
由此便可对应到李尉昂在《汴京残梦》篇首的〈楔子〉里,以后设的笔法,自问自答的问题:「你写的是历史,还是小说?」他给自己的回答是:历史只注意现实如何展开,历史小说虽不偏离现实,却是在顾及当代读者心理的基础上,去做那再现的工夫。
如何画下流动中的汴京城?这既是李尉昂笔下的角色张择端等人,在小说中面临的问题,也是李尉昂作为小说家,必须思考的问题。历史小说家面对的汴京城就是历史真实──庞杂错综,无所不包,几乎不可能作为知识的对象。然而在历史真实之外,还存在另一个历史:经过史家或小说家选择、裁切、解释的历史。最后才是历史小说家以当代读者能够理解的形式,再现出来的作品。
于是,我们似乎在李尉昂的历史小说观里,嗅到一丝与前述明清文人的历史小说论述相近似的气味。李尉昂的历史小说,同样预设一道写实的界限,在这界限内虚构。但他的历史小说不去背离的真实,不是明清文人眼中的正史。在这里,作「选择」的人,是受过现代史学训练的黄仁宇/李尉昂。
问题是,受现代史学训练,经常从财税等制度面思考历史问题的黄仁宇,他所关照的历史面貌,有可能写入传统上以人物、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小说吗?在黄人宇的大历史史观影响下,历史小说中的人物,会呈现出什么样貌?
历史中的人与小说中的人
黄仁宇大历史的角度观照下,历史上非事件性的因素受到重视。相形之下,历史上的人,均不免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常人。在这种史观影响下,李尉昂小说中的重点不在人物的传奇。相反地,读者经常被引导去看主角所处的时代背景。小说中的主角,反而像是被过于抢眼的舞台背景给掩盖住了。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李尉昂的小说里,背景才是主角。
问题是,受现代史学训练,经常从财税等制度面思考历史问题的黄仁宇,他所关照的历史面貌,有可能写入传统上以人物、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小说吗?在黄人宇的大历史史观影响下,历史小说中的人物,会呈现出什么样貌?
在真正动手尝试写作历史小说之前,黄仁宇曾说写历史小说必须要有闯进紫禁城戏谑慈禧太后的本事 。历史小说叙事的活泼性,无疑是黄仁宇作为史家而一向心向往之的,因此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蒋介石、毛泽东等人物而说道:「我希望将来写历史传记的人,在叙述这八十年间的人物时,不妨以《三国演义》的方式写出。「三国」非正史,内中也有孔明祭东风,替刘备留下锦囊妙计等等想入非非的传说。可是作者始终以笔下人物为非常之人,所记之事为非常之事。因之不被俗套拘束,而能将各人生龙活虎的姿态描写出来。」
然而在黄仁宇以小说家李尉昂身分发表的两部作品里,对人物的描摹却不至于如此「想入非非」、「生龙活虎」。事实上,李尉昂笔下的角色很少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生命力。这些主角们,整体而言,缺乏前述清代文人金圣叹所深为吸引的「奇」。
在李尉昂的小说中,稍稍有潜力发展成「奇」的一个角色,应是《长沙白茉莉》当中的胡琼芳。胡琼芳是长沙的交际花,后来成了上海清帮领袖杜大耳的情妇。在小说的开头几章,我们遭遇这个角色不符合社会常规的行径,与她对赵克明的大胆戏弄,似乎隐约感觉到有一个奇女子的原型,在这个角色中呼之欲出。然而随着故事开展,我们终于还是错失了这个奇女子。她的面目很快地模糊了,至多不过在杜大耳身边显得机灵。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汴京残梦》的柔福帝姬这个角色身上。帝姬贵为公主,对笼中鸟般的命运有反抗之意,然而她所能采取最激烈的手段,也不过是要求被画入清明上河图罢了。
相对于两位女性角色,李尉昂的两位男主角,从一开始进入故事时的位置,便都极为被动。随着故事开展,他们对自己命运的掌握程度,也十分有限。
《长沙白茉莉》的男主角赵克明,虽然在小说的开头,带着几分慷慨激昂地宣称:「别搞错。我仍是共产党员。就算你用手枪抵着我的脑袋问我同一句话,我也还是这么说。」这样一个开头,可能会让读者误以为以下要讲的是一个为主义奉献的热血青年的故事。然而读者很快在下文中发现,关于这位主角「怎么会卷入这一切是非之中」,竟然和主义或信仰完全扯不上关系。赵克明加入共党的原因,不过是因为一位他所心仪的一个同班女子,带了他去参加「马克斯主义研习营」,由此一步一步,卷入掌控整个上海的帮会势力。
《汴京残梦》的男主角徐承茵亦然。徐承茵原本与天下学子一般,入塾读书,等着考取功名,入朝为官。不料遇上王安石变法,学制也整个改变,应举的学子可选择参加字法、画笔、算数、医理四项专长的甄别考试。徐承茵因为常在读书无聊时画茶壶玩,竟因而进了画学,走上一条始料未及之路。
赵克明与徐承茵都不是被理念引导着向前走的人。他们都不是史家黄仁宇口中的「非常之人」。正相反地,他们可能都是历史上的「常人」。这两位常人对自己的处境,能够掌握的范围很小,他们都是如法国史家布劳岱所说「被命运所决定,而又只有极微力量去改变的人」。只不过,相对于布劳岱曾被批评为「没有人的历史」,赵克明与徐承茵所处的世界毋宁更是「太多人的历史」。无论是上海还是汴京,有太多人在各种位置、为各种利益,发展成错综复杂却稳定的规则。在这太多人彼此牵制的棋局中,赵克明与徐承茵遂都成了「只有极微力量去改变的人」。
倘若明清文人眼中的历史小说,在以人物为中心的史观之下,着重「摹圣贤心事,如道子写生,面面逼肖」 ,那么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影响下,《长沙白茉莉》与《汴京残梦》两部小说的人物都退居次要地位,反而是夹带了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情况的叙述,占据了相当重的篇幅。
黄仁宇大历史的角度观照下,历史上非事件性的因素受到重视。相形之下,历史上的人,均不免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常人。
在这种史观影响下,李尉昂小说中的重点不在人物的传奇。相反地,读者经常被引导去看主角所处的时代背景。小说中的主角,反而像是被过于抢眼的舞台背景给掩盖住了。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李尉昂的小说里,背景才是主角。
《长沙白茉莉》与《汴京残梦》虽是小说,仍不脱黄仁宇对大历史的关怀,我们在里面可以辨认出《万历十五年》式的企图。
角色的历史观景窗
倘若我们将两部小说中发生在主角身上的具体事件,汇集在一起,大约几句话就可以写完。可是作者更大的努力,是放在描写角色身后,故事发生时的舞台背景。甚至可以说主角在小说中的种种遭遇,都是作者为了让我们看见历史时代的面貌,而刻意做下的安排。
在《万历十五年》中,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位史学家一次历史叙事的尝试。黄仁宇选择万历十五年这平静无事的一年来写,重大事件的阙如,不等于意义、影响的缺席。相反地,黄仁宇有意用这平静无事的一年,让读者感受到政治、经济力量的板块,在历史事件面的平静当中,逐渐卡榫平衡,影响未来两三百年的政治经济结构于焉成形。
《长沙白茉莉》与《汴京残梦》虽是小说,仍不脱黄仁宇对大历史的关怀,我们在里面可以辨认出《万历十五年》式的企图:在历史之流的横切面中呈现北宋末年的汴梁、三○年代的上海,以及拉扯着这两个历史特定时空的种种力量。
让我们再回到《汴京残梦》里的清明上河图。
在宋徽宗旨意下画一幅清明上河图,不是描摹写生就可以了事的。清明上河图的绘制又从一开始就负担着以画叙民情的用心,画官也就成了史官。要加载画卷,成为知识对象的,实际上是一整座在时间中流动的、为各种政治经济势力拉扯的北宋京城。小说中安排徐承茵无意间批评汴京对违章建筑住户(棚户)处置不当,而被遣返原籍数月,一方面当然是作者有意藉徐承茵这个京官返乡,将叙事带到北宋天子脚下的汴梁以外,看一看汴梁的繁华是由什么样的社经结构支撑着;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画家作画对象的京城汴梁,原是充斥着种种政治的禁忌,画家也无法自外其中。
小说中的高潮发生在徽宗之女柔福帝姬出现,要求画家将她画成清明上河图中的一个丫嬛时。画官徐承茵起初强烈反弹,直到了解柔福帝姬对自己的婚姻与将来皆无法自主,因此要借着化身入画,表明「她庸可为丫嬛女使,一则不愿缠足,二则不能为他人的利禄而择婿就婚。」
在这里,柔福帝姬与徐承茵在帝姬入画这件事上呈现了短暂的对立:一方面是徐承茵以为清明上河图应当专注于主题(民情)的客观表现,另一方面是柔福帝姬认为她可以在画卷中传达一己思想。
而徐承茵向柔福帝姬的要求妥协,等于是画家认知了画作所要再现的汴京城,原不是完全客观、静态的存在。换句话说,即使徐承茵能如前述第一任画学主持的主张,将全汴京的景物复制到画纸上,也未必就能表现整个京城。一位帝姬身不由己的心情,与贩夫走卒的日常争端一样,也是京城生活的一部份。
而小说家李尉昂,与他笔下的画家角色徐承茵,面对着同样的课题─如何将动态的、变化中的历史,再现为知识的对象。
小说家虽然看出这个任务的难度,但他所采取的叙事策略,却相当简化。前述不带传奇色彩的主角,以其「常人」的姿态,正构成最好的历史观景窗。小说家以叙述再现的,便是角色在小说家设定的时空、身分之内,能够合理地经历、看见的事物。
《汴京残梦》不仅借着主角徐承茵参与清明上河图绘制,交代了东京汴梁内内外外的情景,前述徐承茵失言而遭遣返,一趟南归之旅,也给作者开出大量篇幅来描绘南方社会经济情况。至于北宋军队无法从数字上管理、花石纲与地方赋税制度的失控,这些黄仁宇史学研究上关注的主题,小说家李尉昂当然细加描写。
同样的,《长沙白茉莉》也借着赵克明这双外来者的眼睛,打探杜月笙清帮势力支配下的上海。李尉昂甚至让赵克明替读者读当时上海的报纸,交代了从黄金荣到杜月笙的清帮权力转移;让赵克明打探出在上海摆个书报摊,需要和帮会人物打交道;更多着墨的是帮会势力在上海罢工运动中的角色。
倘若我们将两部小说中发生在主角身上的具体事件,汇集在一起,大约几句话就可以写完。可是作者更大的努力,是放在描写角色身后,故事发生时的舞台背景。甚至可以说主角在小说中的种种遭遇,都是作者为了让我们看见历史时代的面貌,而刻意做下的安排。
当小说成了清明上河图
当小说成了清明上河图,小说中的人,也就如清明上河图画卷上的任一贩夫走卒般,成为具现作者眼中大历史的角色。个人生命的微观历史,成为时代历史的一个断面。角色的经验,或是角色所处的环境--无论是《汴京残梦》中的开封,或是《长沙白茉莉》中的上海,同样成为史家/小说家拼凑时代面貌的入手式。
在史家黄仁宇史观的影响下,小说家李尉昂特意着重历史横切面式的书写,等于是将小说写成了《汴京残梦》中所说的清明上河图了。
当小说成了清明上河图,小说中的人,也就如清明上河图画卷上的任一贩夫走卒般,成为具现作者眼中大历史的角色。个人生命的微观历史,成为时代历史的一个断面。角色的经验,或是角色所处的环境--无论是《汴京残梦》中的开封,或是《长沙白茉莉》中的上海,同样成为史家/小说家拼凑时代面貌的入手式。
然而,为了表现非事件性的历史,传统历史小说书写中,最引人入胜的人物描摹,与传「奇」的故事,在李尉昂的小说里成了失落的传统。当然小说的写法并无定规,李尉昂的小说所作的尝试亦十分可贵。李尉昂小说面临的困难,其实很接近昆德拉所说,当人们倾向将世界视为单纯的知识客体,人(大写的人)便被一股化约的漩涡力量(whirlpool of reduction)给攫获 。李尉昂面对小说中的世界,太接近史家黄仁宇面对他知识的对象,因此小说中的角色都不可免地经历昆德拉所说的「化约的漩涡」,而成了那些历史上非事件性因素的棋子,而成了读者的观景窗,而失落了他们独立的生命力。这也是一切在现代史学训练影响下的历史小说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尽管从小说的角度,《长沙白茉莉》与《汴京残梦》的艺术成就可能有限,但其中揭示出历史小说的可能性却值得深入思考。现代史学训练下的史观与思考方式,如何能够被带入历史小说的叙述中,而又能使历史小说不只是历史时代的观景展示?李尉昂的两部历史小说已提示了一种可能,我们愿以历史小说的丰富传统,与在现代史学中开展的可能性期待来者。
注释:
1.(明)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丁锡根编着《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2.(清)吴沃尧〈两晋演义序〉,同上书p.942。
3.同注 1。
4.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同上书p.888。
5.金圣叹〈三国志演义序〉,同上书pp 898-899。
6.杨照〈历史小说与历史民族志──高阳作品中的传承与创新〉,收入张宝琴主编《高阳小说研究》(联合文学出版社,1991)
7.C. Fink,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8.参考那志良《清明上河图》(国立故宫博物院,民66年)、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图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9.李尉昂《汴京残梦》(联经,1997)p. 72。
10.吴齐仁〈历史小说与历史叙述〉,《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92.6.8。
11.黄仁宇〈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收在《近代中国的出入》(联经,1995),页64。
12.Peter Burk,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89,中译本江政宽译《法国史学革命》(麦田,1997)
13.(明)吉衣主人〈隋史遗文序〉,《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p. 356。
14.《汴京残梦》p. 110。
15.Milan Kundera, The Art of the Novel (1986),英译文为:"Man is caught in a veritable whirlpool ofreduction where Husserl's 'world of life' is fatally obscured and being is forgotten." 斜体字在英译本中即为斜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