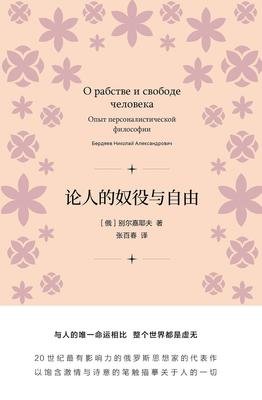《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读后感锦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是一本由尼·别尔嘉耶夫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40页,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甚好!!买一本收起来
●好书。
●语言有些绕啊,不过正文的结构和论述都很赞,不知为何觉得这本和对迅哥儿的一些评论感觉类似。很喜欢人 自由 恶 俄罗斯 大法官 斯塔夫罗金
●太了不起了。别尔嘉耶夫是真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也是懂俄罗斯的。
●存在两种自由:最初的自由(选择善恶的自由、非理性的自由)、最后的自由(在善之中的自由、理性的自由)。第二种是精神自由的最高成就,苏格拉底只知道这种自由,基督则同时给予和要求两种自由。人不能被强制从善,必然的善已经不是善,自由的善是唯一的善,善以自由为前提。自由的悲剧和悖论即在于此:拥有选择善恶的自由,可能选择恶,从而吞噬和消灭自由。即便如此,人必须和只能在这样的危险和困难中走向自由,这是唯一的道路。因此自由之路必定是苦难之路,而钉在十字架的耶稣是上帝的爱的隐喻,上帝给予途中人的爱不是强迫的恩赐,是与人同在、同受苦的爱,是对每个个体的尊重和相信的爱,是对人的软弱和泪水的爱。(人必须一个上帝。但是,为什么祂叫“上帝”,以及如何相信“言成肉身”、而不仅仅是言说和思维方式,此书未涉及)
●陀氏的哲学,其本质是真正的人学。走近他是非常痛苦的,但痛苦本身也就包蕴着莫大的幸福,这正是陀氏的魅力。别尔嘉耶夫也是足够伟大的对话者,他们的灵魂是相通的,但别氏又跳得出陀氏的自相纠缠,真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读后感(一):关于俄罗斯思想的随感
今日通读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耿海英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名家眼中的名家,经典注释的经典。其实对陀氏理解的先行因素是对陀氏作品的预先理解,然而陀氏著作本人一本未读,应当对此演绎文字理解不佳,然而此书文字晓畅,未尝感觉有十分的阻碍。
全书贯穿大量的神学探讨——并非是具体神学问题的——而是“世界观”意义上的神人关系。别尔嘉耶夫评述的陀氏作品,比如《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死屋》《马塔拉佐夫兄弟》,一统而论,核心在“人”,并无他物。一种寻求自救之答案的人类中心主义贯穿陀氏执笔的始终,“人神”还是“神人”?“人神”的希冀将会导致人类的毁灭,毕竟人类终究无法步入神的境地;而“神人”是安分守己的,是“神性的人”,中心语仍在“人”之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别尔嘉耶夫的世界观中,尼采的“超人”是无路可行的:“上帝死了”,然而人类却不能舍弃上帝而独在,上帝的死亡意味者人类的死亡。而“自由对他来说,即是人正论,又是神正论,应该在自由中找到为人的辩护,也要找到为神的辩护。”人的自由的要义不是“欧几里德的智慧”所能解决的,那呼唤一种实践的哲学与神学,其中应该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
别尔嘉耶夫以为俄罗斯精神并非西方精神,亦非东方精神,而是东—西方。俄罗斯精神融合希腊—基督教世界与东方神秘主义,但整体而言已经被纳入希腊—基督教世界,其民族精神与东正教的渊源不可不察。信仰之外,俄国皇帝自冠“沙”字,其实即是“凯撒”之音变,俄罗斯国旗中间尚镶有罗马双头战鹰。我辈可于此今日瞻仰昔日罗马的荣光。俄罗斯大地盛产思想家,据说“知识分子”一词即是来自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勃洛克等等星光闪耀,灵性逼人。其中勃洛克的《知识分子与革命》思想深刻,文风犀利而不失狡黠,着实让人读后难忘。
一个盛产思想家的民族往往是专制主义的天下,俄罗斯的专制主义从未消减。乱世出英雄,平世存庸才。然而“一将功成万骨枯”,英雄的代价是他人的牺牲,我厌恶种种英雄的时代,我也不愿成为英雄时代的俄罗斯人。牺牲者或者殉道者,皆非我求,无论在昔日俄罗斯还是文革时期的中华。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读后感(二):托尔斯泰谈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斯特拉霍夫的信四封)
一
这几天我身体不好,在读《死屋手记》。有许多地方忘记了,重读了一遍,我不知道现代文学之中,包括普希金在内,有哪一部作品写得比它更好。
不是它那种调子,而是它的视角叫人称奇——真诚,自然,基督教徒式的。是一本富有教育意义的好书。昨天我一天都觉得很满意,好久没有得到这样的享受了。您如能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请告诉他我喜欢他。
二
我非常希望向你和盘托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您说了您的感想,其中有一部分我也有同感。我从没有见过他,也从没有直接同他打过交道,当他死去以后,我突然发觉他是我最最亲近的人,他对我来说十分宝贵,我需要他。
我是作家,凡是作家都有虚荣心,都喜欢妒忌别人,至少我也是这样的作家,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同他比个高低,从来没有。凡是他所写的(他写的好的、真正的作品),我都喜欢。他写得越多,我觉得越好。他的艺术手法,还有他的智慧,使我羡慕不已;他的心理分析,使我感到惊喜。因此我就把他当成自己的朋友,除了认为同他有可能相见但需要等待机会之外,没有别的想法。
不过这只是我的感觉。而突然之间在吃饭的时候(我一个人吃饭,时间也迟了)读到报上的消息:他死了。我的一根支柱倒下了。我昏昏沉沉的,后来才开始明白过来,他对我是多么的宝贵啊,我哭了一场,现在也在流着眼泪。
他去世之前那几天,我读了他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深受感动。 凭我的直觉,我知道葬礼上无论怎么议论……这些报纸,都是真实的感受。
三
他是令人感动的,引人注意的,但是他全身充满斗争,不可能把这样一个人放在纪念碑的顶上教育子孙后代。从您的大作我第一次了解到他的智慧的分量。非常聪明,真正的智慧。我至今仍然深感遗憾,我没有能够认识他。
屠格涅夫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可是会活得更长久。不是因为艺术的功力,而是由于脚下没有闪失。真诚地拥抱您。
四
您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笔下的人物描写自己,并认为所有人都是这种模样。那又算什么!他笔下的人物,即使是非常特别的人物,说到最后,不但与他同一族类的我们,甚至是异族人,都会从中认出自己的面貌,认出自己的灵魂的。开掘得越深,大家会觉得越有共同点,越熟悉,越亲切。
不但艺术作品是如此,科学的哲学著作也一样,无论如何努力想写得客观再客观,即使是康德、斯宾诺莎,我们所看到的、我所看到的仍然是作者本人的灵魂、智慧和性格。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读后感(三):别尔嘉耶夫的世界观
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之所以能称之为伟大并超越时代,就是他们从不闭门造车,凭空捏造一些空泛的哲学理论,而是深刻的洞察人生和现实的意义和规律,运用理性这一工具在生活观感和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从而解释和影响世界的现实,引导人类社会的走向。
俄国20世纪最伟大(没有之一)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别氏的思想涵盖极其广泛,包罗万象。其独到之处,在于拜托形而上学数千年的本体论传统(当然尼采更是先驱),开创了新的形而上学思路。试以自己的理解来把握他的思想核心。
其一,客体化。他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传统,指出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所追思的本体实在,实际上推动了人类走向世界客体化的道路。以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的思想为极致,他甚至将精神世界客体化为实体,而个人精神必须为此而牺牲,为极权统治提供了哲学根据。客体化在人类历史上的危害巨大。在政治上会导致专政甚至极权(无论是对忠君爱国还是集体主义的推崇和鼓吹都是把普通人民客体化为棋子,他们生杀予夺的权力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在经济上,表现为人的异化(专业分工和经济物欲的膨胀使得人成为商业生产机器的固定零件和追逐利益和名声的经济动物);在基督教信仰上,会导致教会从世俗角度曲解神,因此导致更多的罪恶(错误把上帝曲解为统治者,则藐视信徒的自由,而信者得救、不信灭亡这种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宣教方式无异于威逼引诱,违背了基督救赎的本意)。总而言之,客体化使人丧失自由,而自由本是幸福之源。
其二,恶的由来。这是饱受遭受天灾人祸的人类永恒的追问,也是基督教思想的核心问题。恶和苦难从何而来?假如有一位全能至善的神,它创造的世界为什么会允许有恶的存在?别尔嘉耶夫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在于自由,尤其是精神(灵魂)的自由。没有自由,则神所造的人只会是傀儡或木偶,失去自由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自由是人生的意义所在,而意义高于幸福,也带来幸福。然而,个体是有限的,至善又是无限的,自由意味着个体要选择,恶(奥古斯丁对恶的定义:善的缺乏)是有限的人选择的一个必然结果。面对撒旦满足个人私欲的诱惑人自甘堕落,甘愿牺牲自由以换取私利,便是一种摧毁自由的恶。如此看来,自由会带来恶,但是恶却会摧毁自由。如果要完全消除恶带来的苦难,就要消除自由。面对这种二律背反,只有通过基督的救赎才能真正恶和恶带来的苦难(主要是人祸,而非天灾,天灾前人另有解释)。
其三,客体化与自由的关系。客体化会剥夺人之自由,进而带来更多的恶和苦难,更多的恶又促进了客体化(看到万物为刍狗,自然会觉得天地不仁,把思想客体化;看到人祸连连,只好构建越来越复杂的制度来制约,把社会客体化)。可见,恶是通过客体化来消除自由,出路所在只能是神的救赎。但客体化甚至使救赎者基督也被客体化为主宰一切的统治者,信徒只是谋求利益和幸福,为此甘愿抛弃自由,使教会客体化,背离了基督的救赎的本义——基督来要人与神建立个体的自由的关系,以救赎消灭恶,以自由的本质去趋向神的至善。
为了阐述自由和客体化等命题,别尔嘉耶夫写了四十几部书,不计其数的文章,令人咋舌。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读后感(四):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关于“自由”的思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地下室手记》中写道:“人毕竟是人,而不是钢琴上的琴键。”、“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了。”其中,地下人对于“二二得四”、“石墙”、“科学的蒸馏罐”的控诉就是陀氏对于人类理性的批判。
理性是人定的,是强制的。所以理性拒绝理解自由,它否定自由,避开自由的重负。这“欧几里得的智慧”企图营造一种强制的和谐,其中没有了自由,人在其中也只能是理智的机器。
理性的对立面是非理性,陀氏借地下人之口肯定了非理性的合理性——“理性的确是个好东西,愿望却是整个生命的表现”,因为“愿望”保留了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这个“愿望”指向非理性,到个体层面就是“人格和个性”。而非理性隐藏着自由的秘密——它正视理性害怕的“无限”。而真正的、最终的自由是以“无限”为前提,即“无限”是最初的自由、非理性的自由,人只有在这个自由中能够选择善恶,用肉身的命运来体验、探索、验证真正的自由之路。
陀氏的所有作品都在考察自由中人的命运。无论是杀了人的拉斯科尔尼科夫还是丧失信仰的地下人,陀氏选择考察的是各种卸下自由重负的人的途径。他所有的悲剧小说都是人的自由的体验,他们狂妄地寻找自由最后的界限,最后用虚假的自由杀死了真正的自由。陀氏确实“残酷”,他拒绝卸下自由的重负,他必须要揭示真正的自由之路。
奥古斯丁曾指出有两种自由,一个是低级的小自由,一个是高级的大自由(神的自由)。前者是最初、最原始、非理性的自由。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经过觉醒和赎罪之路才能到达的最终的自由。
陀氏在奥古斯丁的基础上为我们指出他的真正自由之路。在最初的自由上人可以选择善恶。要注意的是,“恶”在自由(善)之路上被选择是合理的。首先,善的自由以恶的自由为前提。因为如果绝对免除恶和苦难,世界就会被强制的善和幸福所奴役,自由就被否定了。其次,恶是人深度的标志。因为。恶的自由证明了“人格和个性”的存在——后者让恶可以被创造和被负责。最后,恶元素在陀氏的作品中和“复调”模式是相生的。特别是《马拉卡佐夫兄弟》中的复调让权威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冲突和对话的思维。有了善恶的选择后,如果选择了善,那么就是自由的善,人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如果受到恶的诱惑,往往会犯下罪,受到良心的折磨。于是一些人(面向“神人”的人)走上了苦难与赎罪之路。这些人体验着从恶走向善的过程,承受着灵肉的净化,最终达到真正的自由,回归神的自由。
但正如陀氏所说:“地下室的原因是丧失了一般准则的信仰。”陀氏的主人公总是悲剧的命运,是因为他们超出了真正的自由之路。他们虽然察觉并力图反对“强制”建立的社会幸福,但是他们的自由之路和反抗之路是灾难性的,因为他们企图穿过人性的界限——“一切都被许可了”。他们在迷狂的自我意志中走向“人神”,极端的自由意志瓦解了个性,消解了自身,杀死了自由。自由被自由消灭了!所以自由不能丧失内容、目的,必须走向高于人本身的东西。陀氏正是看到了“人神”的诱惑,批判“无限度的自由”,他发现“神人”之光——神和人同在,只有“神人”才可以解决人的问题。
别尔嘉耶夫曾说:虚假的自由的目的断送了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出处于被强迫之中,处于外部规律调节的绝对统治之中。他们的毁灭照亮了我们,他们的悲剧是自由的颂歌!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读后感(五):在破立之间
鲁迅会喜欢别尔嘉耶夫的。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鲁迅主张的立人,和别氏的人格主义(personalism)不谋而合。在《奴役与自由》中,别氏很清楚地说明,人的自由意味着人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也可以成为自己的奴隶。而往往人们误把后者当成值得追求的自由,因为成为自己的奴隶是容易的,是寻求感官给予生命的方向。而成为自己的主人,也就是要培养自己的人格,也就是要抗拒感官对生命的统治,却是困难的。因为如果没有超越自身感官的原则和人性,人又有什么动力与方向去成为自己的主人呢?那种“拔剑四顾心茫然”之感,或许是在世纪末思潮中,在传统的极速衰微而何为现代又悬而未决的时刻,人们能普遍感到的。
“人性的原则是以神性为原则,杀死上帝,你就杀死了人。“(p.94).
在这句话中别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代与传统断裂时,人对自我理解的无处安放。传统思想对于人是什么的见解和构建在漫长的现代之前的岁月里是传统社会的定海神针,它帮助统治者建立社会,帮助个体安生立命。而上帝已死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则表达着旧世界之破坏而新世界之未建立。陀氏的文学正是在追问处在断裂中的俄国社会,人是什么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立人”这个概念在鲁迅的时代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为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已经被“吃人”这个标签而定性为不合时宜。而值得注意的是,‘立人‘恰恰是孔子提出的重要概念。换而言之,新文化运动时期与孔子当年一样都面对同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与孔子所提出“克己复礼”以为仁,以仁立人的方式不同,鲁迅和其他新文化运动的探索者们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陀氏,也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中,但基于俄罗斯东正教的文化语境,走上了基督教的存在主义道路。
别氏就是基督教存在主义者。这个思潮或许可以被类比为民国早年的新儒家。但陀氏是一个文学家,写的是小说,是民族的秘史。而新儒家则没有产生什么小说家,只有思想家在试图解决问题,却没有时代的见证者能够把问题的本质表达出来。这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遗憾,没有人,把时代的问题深刻地描写出来。陀氏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不仅仅是俄国的意义则是如此。作为一个提问者,他把失去标准答案后的人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再次提了出来:人是自由的,但人要怎么生活?
自由作为一个问题,在西方长期被基督教世界的伦理而回答,而在中国是儒道释三家试图把这个问题解决。别氏把自由当成陀氏的作品中最为核心的命题,从《地下室手记》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宗教大法官”,一次次经由不同的角色从不同的角度问相同的问题:上帝死了,什么事都可以做了吗?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别氏的解读呼应着萨特的名言:“存在先于本质。”所谓的存在,就是选择的自由。所谓本质,就是做选择的理由和原则。我们拥有着选择的自由,卻失去了过去选择的原则和依靠,如初出社会的大学生,要在体制外选择自己的生活。
或许要判断一个作品的深刻程度,我们要看是否这个作品向读者提供了解答。别氏指出陀氏的深刻在于他尖锐地提出问题,而不像是托尔斯泰有自己的解答。相对于自由主义的胡适,和社会主义的陈独秀,也许鲁迅的深刻正是在于他不断批判,没有终极答案。这对于读者反而是好事,因为有启发性的思想往往留读者自己去思考的空间,太过圆满的解答只能让读者被动地接受,而不能感到是自身思想的结果。苏格拉底把哲学家的工作比作接生婆也是同样的道理,哲学应该让学生感到他们自己的思想能通过哲学学习更流畅地成形而表达,而不是接受别人的什么普遍真理。柏拉图说教育不是把景象放在一个盲人的眼睛里,而是把一个灵魂的双眼从黑暗指向光明。
而就像尼采所说:“人就像一棵树,当他想向高处、向光明生长,他的根就会愈发强壮地向下、向着大地的方向生长,向着黑暗、深沉,向着邪恶。” 无论是杀死上帝的基督教世界还是打倒孔家店的儒家世界,现代性体现了人的不断反省着传统的深厚土壤,正如一棵树不断扎根更厚的土壤,难免又要戳穿一层泥土。但这挣扎的深刻,这反传统,正是他想向高处生长的理想,是从传统到现代以来没有变动的。这也是为什么,春秋战国时,孔子呼吁立人,新文化运动的鲁迅,也呼吁立人。传统和现代也是两种立人的方式,或许南辕北辙,或许两不相融,但在这场斗争中的精神界战士都在提醒着来者,他们是为了同样的理想。
别氏认为陀氏对于人类的恶,有着深刻的理解而非判断。陀氏相信恶的存在是神存在的证明。自由的用意是人最后可以选择善。也就是说,上帝作为人类的答案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人类向自己提出了问题:我的自由是什么?我该怎么活着?我也觉得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值得我们阅读的原因:他向我们指出,在考虑什么是我们人生的答案之前,我们要好好思考什么才是人生的问题。悲哀的是,中文世界里缺少对于恶的深刻描写,也缺少深刻的追问者。中文世界里有伟大的回答者,思想家,革命者,学者,卻少有问者。如何在现代世界中,有一个敏感的问题意识,如何不急于找到答案,而观察人们是如何犯错的,我们则不得不一次次重返杀死上帝和打到孔家店的犯罪现场,这也是我阅读陀氏和鲁迅的重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