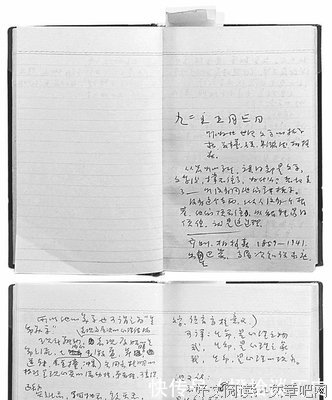涉渡之舟读后感1000字
《涉渡之舟》是一本由戴锦华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8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涉渡之舟》精选点评:
●词汇很繁复,形容词以及一些专业词汇很多,读起来颇费力。不出声感觉读不到点子上去。评论的色彩更多的是一种再解读,包含着太多批评者自身的语意和语言习惯,也许与作者本人想展示的文本不同。阅读的快感不是通过咀嚼剩下之物,更多地应该是去寻找本文中富含的意义色彩。当然戴爷的逻辑分析还是无与伦比。
●最感兴趣的是刘索拉 林白陈染好像没有看到
●戴老师的书读起来总是畅快淋漓~
●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和西方文批评理论,从女性的角度解读中国重要的女作家的创作。
●只看了绪论和尾声,中间的作家论全部跳过了…张洁的评价,在当时是《沉重的翅膀》更受好评,但日后文学史书写多以《爱是不能忘记的》为其代表作,也是文学的现场与评价之间的矛盾。王安忆铁凝等等,自己一直较着劲不看的。
●愧,当时只顾着毕业论文找资料了,得再读过。
●仔细读了绪论和后记 戴锦华在文化研究上的路子是我可以参照的
●戴錦華這個名字終於不再是記憶中高考作文的引言了 不由覺得這告別了十八歲前記憶的人物及文字 如果進入十八歲之後的現場 多少帶著點非庸常的傳奇感
●张洁、戴厚英、宗璞、谌容、张抗抗、张辛欣、王安忆、铁凝、刘索拉、残雪、刘西鸿,方方、池莉
●毕论的别名叫做:把戴爷的一句话扩展到一万字
《涉渡之舟》读后感(一):小记
看到这本专著的即刻,我和小谢就交流过。一个显然的共同观点是,中国的女权主义很混乱,这个混乱的表现在于: 第一、女权主义的诉求是什么?第二、如何达到这种诉求? “男女都一样”在颠覆性别歧视的社会体制与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对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性别群体进行了否认。“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一样能做到”在完成了对女性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消除的同时,也让女性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看似性别平等,实际男性规范成为了绝对规范。 如果我们对中国文学进行回溯考查,可以视见两种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女性镜像,受苦、遭劫、蒙耻的旧女性(秦香莲),作为准男性的战士(花木兰)。 稍加考查,我们可以说,花木兰这个僭越了性别秩序的故事,是在中国文化秩序的意义上获得了特许和恩准的,那就是一个女人对家与国的认同,即孝与忠。“木兰从军”的全称应该是“木兰代父从军”。《木兰辞》一直被关注的详略布局问题其实也可以做这方面的深入思考。木兰是作为一个典型端庄的女性形象出现在开头的,对十二年从军经历做了省略处理仅以寥寥几句代过,它省略的是一个女性在军旅中可能遭遇的由性别带来的尴尬甚至危险。 这里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在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家、国不同于现代意义的家、国。古代的家非以“男权”为核心而以“父权”为中心。阴阳观的性别秩序下,尊者阳,卑者阴,主者阳,奴者阴。因此,男性也可能被置于“阴/女性”的文化位置上。这样就可以对《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一类男子的处境作出解释,他们常常需要屈服在父权下(有时是代行父权的母亲)。 最后这个问题指出的目的在于表达我对前述问题的曲线回答。女权主义的诉求应该在于平权,而这个呼告目前在国内太不够力道了。轻易指责男子对应的男权中心反而会召来剧烈的排斥。 我在此尽量以学理的态度看待问题,不对任何主义进行呼告,所以请一定不要给我贴上某种主义的标签。没有一种主义能够大过生活。 实际上,我不认为有任一种主义能在中国产生效力。
《涉渡之舟》读后感(二):女性为何拒斥女权主义?(笔记之一)
谈到新时期女作家抗拒女权主义的现象,作者说:
“一个有趣而颇具深义的现象是,新时期的女性写作十分自觉地拒斥女性反抗的姿态,几乎每个重要的女作家都发表过“我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声明。尽管此间除了某种策略性的选择之外,无疑有着极为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成因,但它作为一种“单纯”的表象已然传达出十分丰富的信息。在新时期的女性写作(尤其是其佼佼者)之中,女性的声音不再是反抗或控诉的声音;如果它仍然表现为一种反抗或控诉,那么它的对象更多的不是朝向男性而是朝向社会权力机器。”(P37)
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不但是号称敏锐的女作家,就是普通女性,拒斥女权主义的人依然大有人在。这又如何解释呢?
我觉得作者将这一拒斥姿态的缘由理解为惧怕被扣上“反社会”的帽子,恐怕是不太充分的。事实上,作为一种声音论调,反抗社会比反抗男性,从来都更简单更轻松得多。如果说是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时期,任何负面的声音都被解读为抗议社会的话,那还算有一定合理性;但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实践论”发表之后,批判之声上至官方,下至民间,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是一种忌讳。这时候把拒斥女权主义理解为惧怕被视为抗议社会,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我认为,或许可以以女性获取自身利益的主要方式为依据,对其历史背景做一简单划分:一、帝制时代;二、五四时期;三、社会主义时期;四、改革开放以后
帝制时代,女性获取自身利益的主要方式便是依赖男性,这自不必说;
五四时期算是最激进了,女性获取自身利益的方式开始天翻地覆,那就是:向社会寻求自立机会,而不是依赖男性。所以这个时期,不但女性独身一时成为风潮,更有许多富家子女主动与家庭割裂,寻求自立谋生的出路。当然,这也仅仅限于城市妇女,或部分流向城市工厂的农村妇女,能够自立的女性是极少数。所以整体上,女性谋取自身利益的方式并未有太大改观,但却是历史之先声。
社会主义时期又是另一番情景:外出工作已经不是个人自主的选择,而是国家命令。所以这时不管女性自己是否乐意,都必须成为集体主义劳动者大家庭的一个成员。这一时期,女性是否彻底摆脱了对男性的依赖,似乎很难回答。有一点比较明确的是:形式上的男女平等漠视了文化上性别歧视,男性霸权在文化场域中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甚至以男女平等的形式为依据,更加明目张胆地在国家权力场域之外继续变本加厉地实施。
也许是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权力过大,使得一部分不愿参加劳动的女性感到传统的女性气质受损;于是,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回家”的声浪逐渐高涨。在“女性回家”主张的背后,是对所谓女性气质(女人味)的再度体认和重构,这种重构不是简单地回到贤妻良母的角色上,而是借助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话语,以西方资产阶级女性气质为模板,建构一种新的、能够带来自豪感的女性身份。而这份自豪感的来源,一方面是经济上的自立,一方面是性魅力的彰显,某种程度上,性魅力是经济地位的证明。此时,女性究竟主要是向社会还是向男性谋求权利和利益?事实上,在此刻,男权与资本主义已开始融合为一体,难分难解。由于男权文化并未消解,男权结构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融合,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女性要谋求自身利益,必须同时迎合男权文化。
之所以做这一划分,是想说明,对男性的依赖程度与对女权主义的抗拒是正比关系。新时期女性作家必然要迎合男权文化,对女权主义的拒斥态度,不是由于害怕被冠以反社会之名,而是担心丧失男权文化对她的承认,从而丧失在社会上谋生自立的机会,同时丧失受男性保护的机会。如果说女性作家可以代表一部分女性的话,恐怕也是以(城市)小资产阶级或小知识分子女性为主。这部分女性深陷传统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融合而成的社会结构当中,而从某个个体(一个疼爱自己的男人)那里获得保护比从社会获得保护可能性更大一些。
所以时至今日,尽管通过在社会上自立谋生的女性越来越多(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赐),但对于丧失男权文化的承认,很大一部分女性是深怀恐惧的。我想这是今天许多女性依然拒斥女权主义的根本原因吧。
同时,也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经济自立,给了许多人“男女已经平等”的理由,在这样的认知下,女权主义似乎更是多余的了,或者说,更能够理智气壮地指责女权主义者了——尽管大部分实际上对女权主义根本谈不上了解,甚至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有的也只是误解和猜测而已。但在言论自由的逻辑面前,谁能有权制止被人猜测和误解呢?
《涉渡之舟》读后感(三):研究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全面”之作
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的研究专著,非常彻底而全面地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对新时期代表性女性作家作品进行了富有创新的研究。张洁、戴厚英、宗璞、谌容、张抗抗、张辛欣、王安忆、铁凝、刘索拉、残雪、刘西鸿,方方、池莉等重要作家。发现女作家作品中时隐时现的女性视点与立场的流露,提出了女性写作的“花木兰式境遇”——化妆为超越性别的“人”而写作的追求,在撞击男性文化与写作规范的同时,难免与女性成为文化、话语主体的机遇失之交臂,并在有意无意间放弃了女性经验的丰富庞杂及这些经验自身可能构成的对男权文化的颠覆与冲击。本书是国内研究新时期女性写作的奠基性著作。本书作者戴锦华最早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和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成功地再解读中国重要女作家的创作,成为今天的一种范式。 戴锦华的强大和缜密超越了简单的女性立场。她有理论,但保着敏感和热情。她有视野与深度,不流于一声叹息。序言很长,但是很精彩,面面俱到的分析,企图把所有当代的重要的女性作家,都分析的透彻明白,野心是很大,但是读起来其实是有些太密太拖沓,写论文的时候又仔细做了铁凝部分的笔记,有所收获。但是在往后读,尤其是自己对于一些文本本是没有进行精读,可能就会有阅读障碍。不如《浮出历史地表》震撼,也可能是我更喜欢现代部分的缘故吧。之后在找这本书读的话,可能是又要写哪个女性作家的论文了吧?字典式的全面和细密、深刻犀利,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笔记:
秦香莲与花木兰
家国之内
女人与个人的天空
家国之间
书写性别
“女性文学” 表达女性体验、颠覆男权文化的女性主义文学成为缺席者
空洞的能指 典型的类型化特征 一个女人的故事和命运,来象喻知识分子的道路,便成为一种恰当而得体的选择。《青春之歌》中,女性命运与知识分子道路,在意义层面上作为象征的不断置换,成为小说最为重要的文本策略之一。
杨沫的《青春之歌》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主流写作范本,这一特定的政治修辞学方式,在不期然之间揭示了女性与知识分子相类似的文化边缘地位。《青春之歌》为我们展现了一处被成功地组织于中心之间的边缘叙述,是某种边缘处的中心叙事。
历史的怪圈
再次凭借女性形象的“复位”来完成秩序的重建,来实现其“拨乱反正”的过程。
中心与边缘
《人啊,人》人道主义反思与忏悔的主题
1. 在赢得“做女人”的权利之后,是虽女性自我身份茫然的困窘
2. 匮乏与迷惘
类似女性形象指称着自我与历史的“他者”,一种历史的、来自历史之外的拯救力
男性作家通过书写类似“真女人”,重新构造了历史与记忆的清单,以个人生命史的记录对抗、取代,同时遮蔽了原有的历史文本与历史记忆。
代价论之后
主体与主体性
无法告别的19世纪所提供的文化资源与记忆清单 “丰富的痛苦”
抹去自己的性别身份,丧失了相当部分的行为空间与表述可能
女性主体性的发现与展示
反道德的道德主义表述
文化/政治修辞方式
理想爱情与现实 “被理想话语所充满的时代”
解构爱情神话 告别理想主义或解构理想话语
女人的成长过程
《玫瑰门》是一部结构十分繁复、意义复沓回旋的小说,成了小说中最重要的叙事线索
书写绝望,始终是勇者的行为,书写女性的生命经验,无疑将伴随着巨大深切的痛感。
历史、寓言与女人
历史暴力与身体暴力 寻母过程
张洁:“世纪”的终结
同行者与涉渡之筏
“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书写、悬置与等待 爱、记忆与梦之谷
80年代的社会现实被描述成一个中间过程,一个此岸到彼岸的涉渡,一个由湮灭到浮现,死亡到再生之间的期待。
彼岸降临、破茧而出之前的痛苦、绝望的过程
精英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型”的思考者
关于“爱”——记忆与回忆、救赎与归属的表达由是而呈现为一个经典的乌托邦话语
关于女性的话语
别致的诗意与温情
性别、写作与罗网 世纪的终结与时代的坠落
戴厚英:空中的足迹
《涉渡之舟》读后感(四):女性意识源自何处?
首先,这是一本好书。该书梳理了八九十年代主要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将分析视角嵌入时代背景/话语当中,提出了一个至今仍被广泛沿用的概念:花木兰式境遇。这一概念的意思是:女性作家的创作经常是(不可避免或不自觉地)采用男性的视角和口吻,从而使得女性身份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
从作者细致的梳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女性作家的写作经历了一个从有意无意地否定自己的性别身份、忽略自己的性别经验到开始有意识地呈现性别经验、建构女性视角的曲折历程;然而直到九十年代末,按照作者的说法,“关于女性的话语与女性的社会及个人生存始终是一片‘雾中风景’”(P378)。如今已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一“雾中风景”的迷局是否有所改观,依然难以回答。
但有一点比较清晰可见的是,坚称“我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女性作家依然大有人在(如“少女”作家春树http://book.qq.com/a/20130311/000023_1.htm),其中有些人的写作大约的确沾不上女权主义的边;但不排除其中有些人难免受了女权主义的影响而或多或少写了一点女权主义色彩的作品,但她依然不能认同女权主义。
其实,我想说,一个女人不愿成为女权主义者已经足够奇怪,何况还是“女作家”。
按照作者的说法,1993年之后,商业大潮以前所未有的汹涌势头席卷中国。如果以此为时间点,我不禁要问:为何在消费主义盛行之前和之后,(某些)女作家的声音总是那么一致?为何都自觉地站在了“我不是女权主义者”的行列中?甚至连其中的逻辑都未曾改变: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女人。
事实上,社会变迁必然带来语境的变化,而在这变化背后,坚持抗拒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姿态和逻辑竟保持了惊人的一致,这实在令人好奇。我想,在社会语境变化的背后,必定有什么东西始终未曾改变,正是它支撑了(某些)女作家们对成为女权主义者的抗拒姿态。
在本书中,作者对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新时期”,约指改革开放以后)的女作家们“拒斥”女权主义的原因给予了解释,认为“如果它(指“女性的声音”)仍然表现为一种反抗或控诉,那么它的对象更多的不是朝向男性而是朝向社会权力机器。”
这一解释是十分矛盾的。作为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组成部分,彼时不少女性作家的写作本身就是带着“反思”与“批判”社会的色彩;反过来说,正是对社会的控诉,才成就了所谓“伤痕文学”。事实上,作者本人在行文中也不止一次清晰地确认了女性作家的创作所带有的“控诉社会”的特征,在张洁、戴厚英、宗璞等人身上,这一特征都表露无遗。
正如我在上一篇笔记中指出的,并不是由于担心被冠以反社会的罪名,而是担忧不能被男权文化认同,才是女性作家们拒斥女权主义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一担忧,表现在新时期女作家的创作中,是努力与当时的男性作家、知识分子保持一致,跻身“启蒙者”“救赎者”的行列,以社会主人翁的姿态表达某种文人式的忧心,或者说“胸怀”。
正是与男性一道控诉社会,对身为女性的个人经验予以主动的漠视,才导致了作者所说的女性身份沦为“空洞的能指”。
是什么导致了一个时期的女性作家对个人性别经验保持缄默,又是什么原因在1993年之后,女性经验得以大张旗鼓地表达——其中不乏性、欲望等的大胆表述?
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探究的问题,我想把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聚焦在“经验”与“言说”的关系上:是先有可以言说的话语,还是先有经验的表达?
这一分析思路显然是“被后现代洗脑”的后果,但也不妨尝试一下。
从作者所列举的女性作家中,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初,人们刚刚从“文哥”中走出来,惊魂未定的人们对“斗争”心怀疑惧,而反思过去、以“人道主义”大旗重建理性与秩序大约是时人(知识分子)的共识。事实上,在时人的反思中,五四话语常常是被借用的,包括民国旧事也时常成为创作源泉;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四五时期的女权主义遗产却似乎被全然遗忘,抑或是主动抛弃。这也许是由于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话语取代了五四时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式的“女权”主张,而妇女解放话语被新时期知识分子视为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而讳于提及,同时也许是由于“男女平等”以“国策”形式出现而否定了妇女抗议之声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身处知识界营造的“启蒙”氛围中的女性作家,已然失去了言说女性经验的合理途径。
按照作者的划分,王安忆和铁凝可以作为一个分水岭,从她们开始,女性作家开始触及个人性别经验的话题。但真正激发女性言说性别经验的时机,却是九十年代中期张爱玲在大陆的被发掘,正如作者所说:“在当代中国女性写作中,张爱玲、苏青则成为女性文化的‘寻母’之途上新的发现和可能。”尽管包括王安忆在内的许多女性作家否定张爱玲对其产生的影响,但在我看来,张爱玲直露的女性经验的表述和清晰的女性视角,尤其当它们置身商业化和消费主义浪潮带来的“解构崇高”语境中时,无疑为试图讲述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人化女性经验的女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前左翼女作家如萧红等事实上早已提供过具有鲜明女性视角的写作路径,然而,左翼女作家置身战火纷飞中的女性经验的表述却与身处现代都市中、试图表达琐屑的个人化经验的女作家们的诉求无法达成一致,倒是西方白人资产阶级女性对“女性的奥秘”的揭示或许才更能与之契合。显然,与战乱中的萧红相比,“沦陷区”张爱玲的女性经验更接近“女性的奥秘”。对此,我甚至认为,如果没有张爱玲,恐怕不会有日后铺天盖地的个人化女性经验写作的繁荣场景。
张爱玲来的也正是时候。90年代中期,以王朔为代表的“解构崇高”的声音甚嚣尘上,以迎合“大众文化”为旨趣,而与之针锋相对的“人文精神”派亦不甘示弱,演绎了一场煞是热闹的文化大论战。我读大学时,也算是远远围观了这场论战的尾声。如今,显而易见的事实无疑宣告了人文精神派的最终败落,然而,个人化女性经验的写作却从中遇到了绝佳契机,这一契机很快演化为商机,或者说,正是商机成就了这一契机旷日持久的延续。正如作者所分析的那样,在商机制造的女性写作中,我们已经很难辨别究竟是女性在主动发声,还是在被商家利用,成为可消费的卖点。
然而,不论是张爱玲没有出现之前的王安忆与铁凝,还是深受张爱玲影响后的女作家,女性作家或多或少、或朦胧或清醒表达出的女性经验,却十分一致地主要围绕着爱情、婚姻、欲望等展开。如果说女性“(性)欲望”的表达算是由张爱玲开拓的一个崭新话题,但爱情、婚姻的女性视角和经验,在中国其实却是有着最悠久的传统的。这些话题或许在社会主义时期曾一度被遮蔽,但时至今日,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面前,女性经验的表述却未能“与时俱进”,依然囿于这些最传统的领域,不能不说是令人失望的。
造成这一令人失望的局面的出现,我想与女性作家个人经验的同质化不无关系。首先,假如女性经验必须寄托于“个人化”,那么它可能反过来说明,非个人化的女性经验是不存在的,或者说,非个人化的经验便不是女性经验,又或者,没有对非个人化女性经验进行表述的话语资源,也可能这样的话语资源是有的,但已被有意无意地抛弃或遮蔽。非个人化,不是一定意味着集体主义,但恐怕恰恰是由来已久的对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抗拒,使女性经验的表述聚焦于“个人”/“自我”。其次,特定时期出现的左翼女作家群体,正是藉由战乱背景才得以拥有不那么个人化的性别经验;而今天的女性作家大约多数身处都市,共同分享着商业大潮和消费主义的经验,尽管各人处境终究有所不同,但整体上所处的背景却并无二致。是故,我们见证了评论家们所预言的“个人化写作”的结局必将是创作资源枯竭的一个个例子:九十年代颇负盛名的陈染已销声匿迹,层出不穷以“身体写作”为骄傲的美女作家们也因为受众的审美疲劳而一个个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与女性作家个人经验同质化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今天网络上大量异彩纷呈的女性个人经验的畅快表达。网络显然比纸媒更利于话语的传播,一个女性的性别经验表达出来,拥有类似经验的女性必能很快分享并延伸这些经验,某种程度上,网络就是一个经验共享之地。而这或许正是九十年代精英们大肆批判的“大众文化”之一种。更为有趣的是,当越来越多的“大众”加入了以女性经验发出抗议之声的行列当中之时,包括女性作家在内的不少精英女性却日益表现出对这种抗议之声的抗拒和反感。我相信经验之谈是真切的,尽管当经验转移成表述时或许会遭遇话语的扭曲,但不可否认大众之声是强有力的,在这强有力的大众之声面前,试图保持优雅姿态的女性写作恐怕再难为“弱势性别的抗争”提供什么有效的资源了。
说到这里,可以重点来谈谈那些拒斥女权主义的女性作家们是怎么回事了。
首先,认为女性身份不具有优先性,应该先将自己视作“人”而不是女人。这样的论调历史悠久,自从女性意识到自己的性别弱势之后,它总是一而再地被“觉醒”了的女性表达出来。就连九十年代被视为典型的“女性写作”的陈染,也清楚地说过“超性别意识”这样的话。
这一逻辑,是认为性别视角将限制其观察世界的广度。这一认识,首先将“女性”本质化,放在了“妻子”“女儿”“母亲”的角色上,持有这种论调的女性认为,女性不应仅仅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
因此,澄清“女性意识”的本意,实在太重要了。所谓女性意识,意指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女性因为“性别”而获得的经验,这些经验不止体现在爱情、婚姻和性上,事实上,生活中无时无处不有性别。书应该读到什么程度,有性别;应该读什么书,有性别;做什么工作合适,有性别;应该有什么样的姿态和打扮,有性别……这都是极细微的例子,而所谓“性别意识”,便是指意识到这些极细微当中亦有因性别而引发的差异对待。简单说,性别意识便是体认因性别而拥有的经验。这就是前面说了大篇的“女性经验”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而所谓“超性别意识”,这样的提法本身已经显示了“性别”的意义,因为这多是由女性提出的一种说法,男性不需要超性别,因为他们便是性别真理的标准。
其次,认为男女平等早已实现,甚至认为该需要“男权主义”了。这些论调,将由深嵌于整个父权制社会结构男女权力关系简单地理解为男女个体之间交往的形式,似乎女权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求男性要怎样怎样。又有很大一部分人将女权主义视为与男性争权夺利。这都是对女权主义的误解。事实上,女权主义的根本目标是针对整个性别结构,以及建立在性别结构基础上的社会结构,改变这一结构意味着性别不再是一种结构,性别是灵活的,于此同时,社会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巨大改变,那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拒斥女权主义的理由太多,在此也不必一一驳斥。回到本书中,当前需要正视的是父权结构与资本主义的融合,而建立在对女性经验的体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只是改变性别结构的第一步。
几乎可以说,清醒地觉察到性别经验,拥有清晰的女性意识,可以讲述它,这就是女权主义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