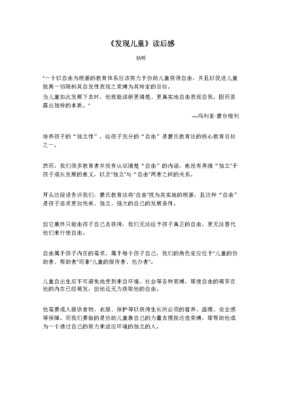《六论自发性》读后感1000字
《六论自发性》是一本由[美] 詹姆斯·C·斯科特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3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六论自发性》读后感(一):自发性的缺失
书中观点、精要繁多,吸收其中之八九,已有足够的快乐和烦恼,知识爆炸的年代,读书也越来越不是一件能让人心旷神怡的事情了,除非,看一些不疼不痒的书,也就是看过即忘的书。
《六论自发性》读后感(二):《六论自发性》(作者:詹姆斯·C·斯科特)
新京报书评周刊-2019年5月18日-书情 罗东
在人类近现代史上,国家(state)是思考一切政治经济社会行动无法绕开的关键性概念。说它是这些议题的中心概念也并不为过。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或范式,看待“国家”的方式和态度也不尽相同,它们以此也形成了纷乱复杂的意识形态光谱。而在这些光谱中,无政府主义长期以来都是最具争议的光谱之一。
美国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就阴差阳错地被人归类到了“无政府主义者”。这大概源于他在《国家的视角》《弱者的武器》等学术著作中对社会下层自发秩序的描述。这些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等版本在各地学术界传播。斯科特也因此获得较高的学术声望。他的确表现出了对社会自发秩序的理解、同情和信心,在建制未到达的地方,人们也呈现着合作和交流的能力。然而,如果要因此说斯科特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那只能是一种误会。他的这本《六论自发性》以学术随笔的形式为自己作了一次辩护。他从未否定国家或政府在近世以来的价值和作用,而只是与其保持距离,在这一视角之外去理解人们的自发秩序,而这种自发秩序有一套自己的实践逻辑。
《六论自发性》读后感(三):闪着独立的光
《六论自发性》读后感(四):《六论自发性》VIP私享段落
(加粗部分)
碎片二十九 历史误读的政治
清理、简化、浓缩历史事件的习惯不仅是人类的自然癖性,也是编历史教科书的必然要求,但这是一种高度利益攸关的政治争夺。
1917年俄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一样,许多背景各异的局中人并不知道事情最后的结果如何。研究过俄国革命的细节的人可以确信几件事。他们一致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革命的发动上并不扮演重要角色;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布尔什维克只是发现了躺在大街上的权力,把它捡了起来”【4】。1917年10月底的事件具有高度的混乱和自发性。学者通常认为沙皇军队在奥地利前线的崩溃,以及溃散士兵迅速返乡参与农村的自发土地抢夺,对打破沙皇在农村的统治具有决定性作用。研究者认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工人阶级确实怀有不满情绪,并拥有武装,但他们并没有寻求占领工厂。最后他们还认定,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革命前夜对工人拥有一点宝贵的影响力,但是与农村没有任何联系。
然而,当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他们开始在历史叙事中消除事件的偶然性、复杂关系、自发性,以及其他一些革命团体的影响。【138】新的“大势所趋”的故事重视事件的明晰性、决定性和先锋政党的力量。列宁在《怎么办?》中展望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历史角色,布尔什维克党人相应地把自己视为革命所成结果的主要推动力。1917年至1921年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不稳 ,布尔什维克尤其感兴趣把革命尽快清出街巷,搬进博物馆和教科书,避免局势再度动荡。革命进程是历史必然性的“自然”产物,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合法性。
革命的“官方故事”在真正的革命还没有完成时就已经成型了。在列宁的理论中,国家(另外还有革命)应该像一台流畅运转的机器,由上层操作,并且和军队一样的严整,所以后续的革命“重演”便在这一轨道上进行。早期布尔什维克的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设计了一个巨大的城市公共剧院,其中曾上演描绘十月革命的戏剧,剧中用了4000名演员(由军人担任群演)、道具火炮、河上的军舰、东方升起的红太阳(用灯光特效来模拟),给35000位观众讲解了革命的历程。在公共剧院、文学、电影和历史中,布尔什维克都表现出“包装”革命历史的强烈兴趣,消除真实事件中存在的偶然性、多样性和目的差异。当亲身经历革命并且可以把历史记载和自己的真实经历相比较的那一代人成为过去,官方的史观就成了主流。
革命和社会运动中通常存在着多样的行动者:怀着千差万别的目标、强烈的愤怒与不满的人,【139】除了身边事物之外不理解任何状况的人,受偶然事件(一阵暴雨、一条流言、一声枪响)驱动的人——不过这万千事件的嘈杂之声,虽方向迥异,但矢量相加可能就形成了我们回望之际称之为“革命”的大事件。它们很少如布尔什维主义史观描述的那样,是协调的组织机构领导着它们的“队伍”迈向确定的方向。【5】
这种大型表演大有来历。20世纪早期,不论左翼还是右翼的政党都曾在大体育场中组织过“大众体操”,以展示社会的力量和纪律。成千上万穿着统一服装的体操表演者做着协调一致的动作,如同以密集队形行进的军队,展示着集体协同的力量和整齐的编排,这都少不了那幕后指挥整场演出的导演。
许许多多这样的象征工程的目的,其实都是想要用如同台球表面一样光滑的秩序、慎重、理性和控制之幕,遮起政治权力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困惑、混乱、差错、临时性和任意性。我认为这是“秩序的模型化”。玩具世界的这种做法我们都很熟悉。外面更大的世界中的战争、家庭生活、机器和荒野自然是危险的现实,超出了孩子的控制范围。玩具的世界里有塑料士兵、娃娃屋、玩具飞机坦克、模型铁路和小花园。同样的逻辑应用到了模范村、示范项目、示范住房计划和模范集体农场。当然,小规模的实验是社会创新的一种谨慎策略,即便是失败了后果也并不严重。不过,我怀疑有时这种模范演示的目的【141】单纯就是展示,它们代替了更具实质性的变革,展示一个精心布置的微秩序,用一种波将金式的布景媚上欺下。这种小的“秩序岛”越是扩大化,越会引发人们的怀疑:策划它们正是为了防止其背后非官方的、超出统治精英控制能力的社会秩序被人看到。
《六论自发性》读后感(五):从碎片化历史和现实中,阐述无政府主义观念
无政府主义的几个突出观念,斯科特基本都加以了阐述, 佐证。有一点疑问,自发互惠的行动是否能在大范围铺展开(=无政府主义能否在大群体存在)。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一个关注人的塑造,一个关注环境的秩序,关注点不同。作者论证肯定了无政府主义在人的塑造上的价值,指出了国家的问题,但无法充分说明无政府社群相比国家在现实存在 社会组织上的优势。除非是在一个前提下——社会中人的塑造远比集体秩序更为重要。不同的关注点,不同的优势,我们很自然地想,国家主义代表的大集体和无政府主义下的小社群能否和谐共存呢?这点就难倒自己了。从国家主义代表的集权,制度秩序化的要求来看,小社群的范围多可能压缩限制在一定安全范围内,处于被监视被限制的情境,而非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