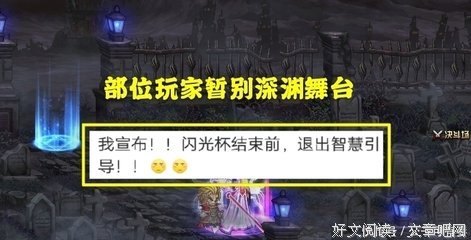闪光,成全
每个人沙滩上发光的沙子还有蚌壳,我们的时代喜欢传播金钱,还有分数的故事,都以为拼着某个阶段的努力,进入某所学校就可以改变人生,甚至还有人生。
不知道为什么想起苏霍姆林斯基的一则故事,女教师退休以后修理电视机的是她当年极力打击讽刺挖苦的孩子。而他只要简单的几下就把电视机修好了,女教师还是明智的,她那时终于羞愧不已。更多的时候一个教师需要一种眼界,肯定和激励是给予孩子生命最好的滋养,记得作家黄蓓佳写过一篇文章《画在生命里红双圈》写自己高中时代因为作文不错被老师画了十八个红双圈,静静的午后,她一个人悄悄地看着那些圈圈,居然忍不住数起来。这一篇文章我看过不知道为什么印象深刻,所以从那以后,她感觉自己读书很有潜力,因此最终爱上了文学,走向了创作的道路。
但是记得去年管建刚老师说他们曾经一起参加一个活动,原来安排一个小时的黄倍佳的讲座,谁知她对于气场的控制能力不够,所以半小时后草草收场。诚然,他不是要否定黄蓓佳,而是意在从另外角度说明每个人长处不同,作家可能善于把握文字,但是未必可以演讲那么流畅,受欢迎。
而现在的学校太多时候看见的是分数,而很多孩子因为家中比较重视所以,小学阶段考试分数也越来越高。导致很多家长产生误差:自己孩子可以走学习地方道路,其实不然,看看社会上真正跟文化有关的工作其实不多。
昨日遇见一个熟人,她是一个单身母亲,而她却给自己孩子找了一对一补课,可是她自己却要用做月嫂的钱支付。“我就是看不得她考得那么少,你说怎么搞呢?小学我要给她冲一下,也许后面就好了。”
“我倒是以为培养孩子独自生活的能力才是第一位的,因为孩子将来未必走读书的道路,却一直要好好地生活。”我只是委婉地提醒。
“哎呀,现在找了一个一对一老师辅导数学,现在已经进步了,应用题会做了……”看着她那么兴奋的脸我真的不忍心继续打断。
“哎,就是经常还得搞到十二点,太累了。”一声叹息,打断我的思绪,这样的孩子在学业上花去那么大经济力量确实也真的没有必要,况且孩子睡眠都不能保证还谈什么呢?
而后,我又忍不住啰嗦几句,妈妈倒也坦白:“我也不想让她那么累,可是就是看不得她那么少的分数。”
我所知道,她早出晚归,一个孩子中午自己在家吃饭,然后放学后去游泳,不回家去作业班写作业,要是没有写完,她就会回家继续……
这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悲催的故事,一个孩子也许因为没有读书的天资却被迫走在这样的一群人中去追求分数。也许他们以为有了分数才有人生的意义。
当然,我们太喜说成功的故事,传播天才,发财的故事,大家似乎都对此乐此不疲。
可是,有时候孩子差异真的巨大,即使同样的老师也无法教出一样的学生,记得两年前,我有学生因为在二中中考第一名,有人就来祝贺。我淡然一笑:“这孩子我是教过,你可知道我班上以前同样有一个孩子天天考试三四分呢?”非我矫情,而是实事求是地表达。
少年班的故事也是人们喜欢津津乐道的,任何事情在传播中往往会有主观的因素叠加,因而变得诡异起来。其实宁柏出家的故事大家也是略知一二。无论在哪里学习,关键是不是有兴趣,还有一种天然的热爱。
传播挣钱的故事同样如此,其实恰如股市,盈利者自然会津津乐道,可是真正的规律确实亏者众多。
记得牛顿有一句话,人们常常引用却不知道当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真实用意:其实我就是海边随便玩玩就可以发现这些,别跟我比!可能他一辈子因为太孤傲所以终身未婚,那么聪明的人必然也是跟俗人差异巨大。
一个人一辈子遇上肯成全他的人,就很好了,据说李安的夫人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支持他拍电影,可是李安差点就要放弃了,要是没有人成全,困难他已经淹没在世俗之中了。
早上吴修志带来一本书,是关于铜镜的专业书。而且作者就是吴修志爷爷的哥哥,并且因为父亲的爱好,家中三个孩子也是收藏铜镜的爱好者,可谓家学渊源。
当我举起那本书,请孩子说自己思考时,却发现不少孩子哑然无声。孔哲回答倒是很流畅:“没有想到这样一本关于铜镜的书,还有那么厚,我想一定是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
季雨晨回答也是不错,剩下的孩子站起来茫茫然之感。
孩子晚归,问及原因:“给同学报听写。”此孩乃一学霸。遂问:“你为何要报听写呢?”
“我是课代表啊!”那一刻倒是还那么简单。后来,我得知一些孩子进入初三担心自己经常给同学服务耽误自己时间,所以不干了,这孩子乐呵呵也傻乎乎地接受了,我想,孩子还是简单些,乐于做事总是好的。
网上关于毕福剑的传言文章也多,最近的事情让我联想到有关东厂西厂的事情,所以人性之恶有时候可以意想不到。所谓朋友一定要扎起利益之外,要是处于同样一个统一的利益结构之下,那么可能你会受到你预想不到的伤害,所以毕福剑之人,还算是一个正常情况。人性的弱点真的无处不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