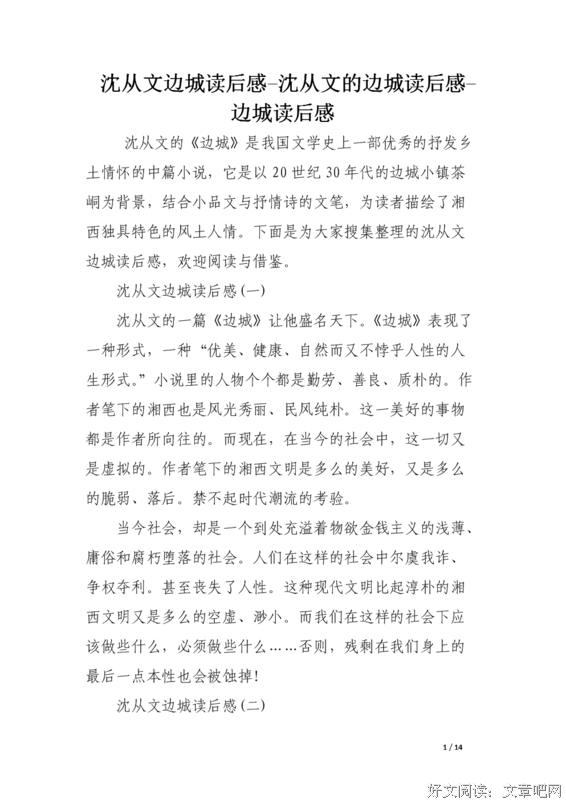《沈从文晚年口述》读后感锦集
《沈从文晚年口述》是一本由王亚蓉 编著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页数:26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沈从文晚年口述》精选点评:
●居然是“饭饭”编的
●乡音无改鬓毛衰。更多是沈从文晚年事业,于文学所涉不多了。
●还是很喜欢沈从文先生的
●附带的光盘,沈老的口诉录音是亮点。
●还不错,虽然所说的未必有多少是出自真心,但毕竟是沈从文本人的口述会议,有助于我们了解作家晚年的生活细节,以及一些当年的恩怨纠葛,认清部分被修饰过的人的真实面目。比如丁玲、范曾等人,以沈从文如此敦厚的人,尚且免不了在晚年不满埋怨。不过,要从此书中看出历史的苦难,或许是要失望了。历史的风波,几乎没在沈从文的口述中留下多少痕迹。倒是口述所提及的80年代的生活,以及那时候人们的思想认识,在近三十年后回头看去,会有意料不到的趣味。比如,沈从文对美国养老制度、后现代艺术的认识,在今天看来充满了吐槽的乐趣。另外,该书还附有一张CD,是沈从文几次报告的录音,殊为难得。
●前半生与后半生,外人看来或是传奇,却是一种那个时代的造化弄人
●沈从文的声音很难忘。
●亲切的口音
●“我听别人讲她(丁玲)写的东西和她本人一样,只是放荡。”这样的句子出现在书里我希望不是先生本意。
●沈從文轉向文物研究,不是他個人的損失,而是文學界的一大損失
《沈从文晚年口述》读后感(一):听沈从文说话
听沈从文说话
从一位朋友的《读书看碟笔记》里知道,国内新近出版了一部《沈从文晚年口述》,是沈从文晚年在公开和非公开场合的几次谈话的录音整理本,所谈“谈到文学的不多,他说:‘我的写作应该说是失败了。’”大约主要涉及的是四九年之后的经历。
我客居国外,暂时无法得见此书,遗憾是免不了的。无论将来人们对他的一切会有怎样的评价,沈从文的一生都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传奇。有关这个传奇的点点滴滴,自然都是珍贵的。人们常常感叹,人生苦短,事业难成,一辈子把一件事做得比较像样已经很不容易。可是在沈从文这里,尽管其一生经历也远非平顺,却能在前半辈子以文学名家,后半辈子以文物泰斗名世,单是从立言立功的角度看,也已经足以在《文苑传》中占据一个较大的篇幅。更何况从这些年的沈从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在整体硗薄的当代文化土壤上,后人首先应该为他编写一部《德行录》。
关于沈从文的德行,人们已经做了很好的总结,曰“赤子”。写起来只是简单的两个字,解说起来,也还是以他的妻妹张充和为他写的挽辞中的“不折不从,亦慈亦让”八个字最为贴切。可是真的要了解这几个字怎样成就和铸写了一个人,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位朋友在她的笔记里摘引原文说,沈从文说到下放的时候,一个人住在一个大教室里,“看着窗子上有几个大蜘蛛慢慢地长大了”,“这面窗子还可以每天看见一只大母牛,每天早晨还可以看见牛,那个大牛、小牛都庄严极了,那个地方的牛都大极了,是花牛,美极了,一步一步带着小牛吃饭去。间或还能看见一些小女孩子梳着两个小辫辫,抬砖头拣树叶子。”这样的“风景的发现”,没有胸中的神明所铸造的容受空间是做不到的。尽管沈从文一生也并不总是这样从容淡定,可是这样的从容淡定却总是能够帮助他安度诸般危机,从而成就人生的传奇。
我起意要写这样一篇小文,并不是为了说这些不咸不淡的话,而是因为被上引《读书看碟笔记》中透露的另一个消息所激动:“这本书还附一张CD,是(沈)当时说话的录音。说话慢慢的,南方口音,也还听得明白。”这实在太好了,好到无法想象。传奇逝去了,声音留下来,在自己的书房里,回响着包含了老者全部生命信息的细说从头的语音,一个书本上的沈从文,变成了仿佛在与你促膝共话的老先生:这该是怎样不可思议的事情。
汪曾祺记晚年的沈从文,说到他在家乡听古调犹存的弋阳腔傩戏,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对年轻人打鼓失去旧范很不以为然:“沈先生听了,说:‘这是楚声,楚声!’他动情地听着‘楚声’,泪流满面。”这些曾经令他泪流满面的“真的楚声”,经由生命的转换保留在沈从文自己的声音里,本来也已经随着他的逝去而逝去,现在竟能借助现代科技和商业复活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无论如何,对此我们都应该心存感激。不管人们怎样诟病科技和商业戕害人文,我都要说,至少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到的是相反的例子。
2003-11-10,于汉城
《沈从文晚年口述》读后感(二):从文素描
相由心生,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看沈从文十八九岁的时候的照片,竖起的短发,警觉的眼神,一副紧张的正经样----大概该每个少年都曾经用这样的对抗姿态对待过自己尚不熟悉的外部世界。彼时他是军队里小秘书般的角色,不爱说话,多数时间里是一个人看书,一个人练字,一个人爬到山崖上对着下面的流水发呆。猜想着自己以后的生活,为此而茫然愁苦---生活没有目标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宛如双脚踏空踩在虚无里,也不知下一秒要滑到哪里。他在这样的惶惑里度过青春期,直到被一个“细眉白脸”的女人骗过,才下了决心到北京靠一支笔谋生活。
《从文自传》有一个小细节,我觉得非常可爱-----他准备出宿舍吃饭的时候,发现自己唯一的一件衣服洗了还没有干,想到赤身去吃饭的不雅,他干脆放弃吃饭,一个人锁在屋里过了一个下午,直到衣服干了,才出去随便找了点东西填肚子。他的这种羞涩感的背景是什么?是一些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抽大烟,嫖妓的大兵们。这个底色与他太不相合,虽然他曾经用温暖的笔调写过这些人,那也不过是对与己完全不同的某种生活状态远距离的审视,他可以理解,可以尊重,不过肯定是无法融入。这种对底层生活尊重的态度让他的小说有一些悲天悯人的味道。
到了三十多岁,他眉目间柔和了许多。我看到的照片是他和张兆和,都笑得满足。他是她的老师,追了她八年,八年时间写过无数的信,被拒绝了无数次,还千方百计要讨她欢心。那句“我行过许多地方的路,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华的人”就是写给她的,她终于成为他的妻子。
在博物馆的工作照片我也看了,从文老矣,在黑白照片里慈祥地笑着,很平常的一个人,看不出他生活的波澜。他被罚去扫厕所,自嘲“至少别人还是相信我的品质的,让我扫女厕所。”真是有韧性,就此放弃写作,埋头在锦灰堆里,整出了一部服装史。
前段看《从文晚年口述》,突然看到一句:“我这样很狼狈地活下来,是很可笑的。”的确,现实有时候很荒谬,象个大大的愚蠢的笑话。我到凤凰去,在他的故居停留很久,隔着玻璃,用手指触摸他的笔迹,在他的床边放着一个旧式碟机,碟片居然是《难忘今宵》。我在他家屋前傻呼呼照了很多照片,又想把他写的字也照下来,把他的小床也照下来,为了把保证自己和身后高挂的“从文故居”同时入镜而且好看,我摆了不少姿势---直到旅行团的其他成员都走完了,导游到最后折回这个地方喊我-----可糟糕的是这些个照片最后被同事不小心删掉了。
《从文晚年口述》这个书里夹着一张CD,是先生的部分演讲实录。我打开来听的时候,笑了起来。我想他在大学讲课不那么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口音,湘西话谁都不懂,我对着书仔细地分辨他的话,刚听懂一点儿,就完了-----想当初对张兆和示爱,用湘西话说我爱你是多么有趣的事。
他朴素,沉默而又倔强,有一种柔软的力量,如他妻妹所说“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沈从文晚年口述》读后感(三):就像一个串联电路:《沈从文晚年口述》
书的前半部分,是几次演讲。虽然是正儿八经的演讲,读来,却有浓浓的冷幽默。比如81年两次演讲——
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题目叫《自己来支配自己的命运》(也不知道这题目是沈自己取的,还是作者放入书稿时拟的)。不由自主的人生,虽是“耐得烦”的扎实路子,但要说是自己支配的,这就有几分悲壮、几分Game over重新来过的喜剧感。
在湖南省博物馆演讲时,标题叫做《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用文物经验去修补bug,把“迷信”一词用得如此可乐。简直是对一个一直惊讶于乡村魔术团的少年,轻轻一点,把底都亮了。提取几个bug——
比如: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沈先生讲个“叉手示敬”(宋元做法)就把成画年代五代(南唐)给否定了。
孔子没有胡子。因为下巴乃系冠部位,怎会自我厮杀。
中间部分,是沈先生与金介甫对话,也有意思,一个小开关摁下去,前面的就亮起来了,跟串联电路似的。比如:在《沈从文家事》一书中,知沈从文先生写《湘行散记》时就已沿途拍照了。50年代分期付款买相机。
在此书,对话中,得知:原来,沈母就会用照相机。
一个出色的散文小说大家,是不是同时就是一个摄影画画高手?比如萧红就擅长画画,在哈尔滨经常带着画板出去。
1922年到北京。北大附近住的十分之三以上,为非北大学子。附近公寓里可以赊账,是前清做法的遗留,真是好啊。
沈先生“开始想学摄影,交不起学费去不成。考取了中法大学”,“你一进去只要交学费,毕业后即刻就可以到发过去。可是我交不出学费。”穷学生之间互相助学,但是学英文、日文,先生自己觉得很不开窍。
这不开窍的背后,我估摸是生存压力。如果肚子问题不用愁,多花点时间读英语,摄影梦提早实现了,会怎么样?但是,没实现呢,也没有关系,后半段会去修补前半段的遗憾,大概就是人生的自动设置。
1925年开始发表文章,稿费虽然只有七毛钱,但是似乎看到了遥远的光。
可惜,“你买任何东西,当差的都要拿回扣。这就是典型的老北京”,见熟人、取稿费都会被门卫要钱。“《晨报副刊》的看门人也不例外……记得有一次我拿稿费,大概十来块钱吧,他追着要钱,我把支票给了他就跑了”。
因为饥饿,好几次差点又当兵。好在自己醒过来了。“所以,是不是真正安心活下去,实在不得已的时候,我还是有动摇。就是遇到奉军招炮灰的时候,有个什么排长,拿一个招兵募员的旗子,在前面那么走,后面跟着几个面黄肌瘦的失业游民,我也跟着走过,我跟着走了好几次。走到骡马市大街,那个要发伙食的时候,就是按手印儿的那个时候,我临阵脱逃赶快跑回去了,跑了。这不失了我的来北京的意思”
沈丁恩怨,八十年代还左得那么丁玲(骂沈是反动作家)。虽然饱经磨难,但终未成阿赫玛托娃(高华先生语)。
前段时间看陈明写的《我与丁玲五十年》,打破了在牛汉《我仍在苦苦跋涉》中对晚年丁玲主持《中国》杂志,给文坛打补丁行动的好感。丁陈二人为了在一起,跟陈明的文字一样惨不忍睹啊。
这回,倒是在沈金二人对话中,再倒回来:爱打牌。追过萧乾,“在延安时使劲追过彭德怀”,果然还是那么莎菲!虽然是延安式的莎菲。
听说在纪录片《三生三世 聂华苓》(陈安琪导演)中,去西方的丁玲又有不同,这座八卦炉又有柴烧了。
《沈从文晚年口述》读后感(四):Fword先生之谜
狠批八卦一闪念,必须承认看这本书是很有些阴暗心理驱动的。以前看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对范曾老师这JP男印象很深刻。应该在那之前就看过这老君的电视上访谈,再一挖坟,对范老乃至世道民情都有了新的认识。至少在书里面,编者王亚蓉跟沈先生的关系还不错,她和较年长的王孖(?)给沈先生搞文物研究做了很大的贡献,书里都有,无需赘述。
沈先生跟丁玲的关系应该坏到了一定程度,一向觉得他是个谦谦君子,没想也毒舌,看来是被丁玲伤得很深。在去湖北的火车上,他跟王亚蓉追忆起与丁玲的恩怨,中间还来了句“她可以说乱得很,长得又不好……跟萧乾也有来往,萧乾不理……什么斯大林奖金,那个完全是政治上的”,“她写的东西跟她本人一样,只是放荡”(P184-187)。丁玲对他的营救恩将仇报,还坏了他和鲁迅的关系,到一九八一年时还是得瑟,说沈从文是反动作家。
同一部分,他还说冰心,一边骂孔祥熙的专机运自家的宠物狗(后来的钩沉文章说这事儿是讹传),一边又是被宋美龄的专机送走。还有“冰心过时啦,凌叔华没什么才气,还有几个是教书的不见特色。有一个最见特色的叫谢冰莹,她参加大革命写了一本《女兵日记》。”
逝者或者过气的准逝者,指名道姓地说还行。如今仍然活蹦乱跳的就麻烦一些,不是用代号,就是故意含糊其辞。不用说,范大师就是其中一位。陈徒手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出自《人有病,天知否》一书,引用的是黄能馥、陈娟娟夫妇的说法。我手头没书,摘豆瓣上的帖子:
“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帮助过的范曾。范曾写道:“(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一九六二年范曾来到历博当沈从文的助手,为编著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插图。此间调动工作,沈从文尽力最多。据知情者介绍,当时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有一次天刚亮就敲沈从文的家门:“昨晚梦见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从天津赶来。”
文革期间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说:
那时,范曾画了一个屈原像。沈先生看后,还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曾指着沈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记得那是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沈先生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我们家。他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采访)
这是沈从文晚年最惨痛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再也不提范的名字。 ”
王亚蓉讲了另一件事儿,是她亲眼所见,跟上文的故事很像,但明显不是同一件,只能说沈先生为人太过善良,灾难性的遇人不淑。话说回来,两件事儿又那么神似,摆在这里,大家可以自行判断:
“一九七五年夏的一天,沈先生又带我到历史博物馆,在二楼美工组那走廊似的工作室,看见一个人正在画诸葛亮像,先生过来他没有言声,先生就说:‘不要照这刻本上摹,这巾不大对。你是代表国家博物馆在画,要研究一下当时‘纶巾’的式样……’不料,‘你不要在这指指点点,你那套行不通了!’那人背靠旧沙发,翘着二郎腿上下抖动着,夹着香烟的左手冲沈先生边点戳着边说……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先生起的面红耳赤,我搀扶他的手觉得他在发抖。先生无言地盯着那人。看着那副玩世不恭的冷面,我拖着先生朝前走,‘您怎能跟着不懂事的人真生气,他是谁呀?’
‘X X。’
这就是我和X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我知道当年因他的狂傲得罪了叶浅予先生,毕业被发配往变窄,他为了前途,用心用信,使得从来不求人的沈先生为了美院的这名毕业生,找美院朱丹(原中央美院院长)和叶浅予(原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这些老友求情,未果,借总理批示服饰图录课题,要X X到自己身边协助工作,最后历博费尽周折地终于把他调给了沈先生,X X留在了京城。与X X晤面目睹的那场面,我痛彻地感觉他就是我儿时即知道的向东郭先生求救的那条中山狼。我为先生委屈,我看着先生多日都恢复不过来的情绪难过。迫于某些缘故,X X在文章上辩解说没有这回事。文革那段不正常时段过后,他也跟人讲过:我和沈先生只是思想认识的分歧……但无论怎样,也抹不去先生心头的阴影,他再不愿提这个人。我佩服X先生的聪明和才学,但总也挥不去他当面羞辱沈先生的恶劣影响。借这篇小文我替沈先生述说这个经历,为鸣不平。人在任何时候有些事情都是不该忘却的。”(P197、198)
书中所附王晓强《记学艺沈从文大师门下一二事》一文,夹了很多牢骚(我很想知道那位自以为是的W先生究竟是谁),有点无趣。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提到了一位画曹操的F先生(多么微妙,引人遐想!)。好在这次这个F没有直接刺激,只不过拒绝了沈先生的善意提醒,“你是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是参入研究服饰的人,怎么好把曹操画得像京戏上一样,留一部大胡子呢?”
沈先生在一封致王亚蓉的信件里提到了“中山狼”:“并在同一词典中出现不少现代中山狼似的作家自传,作风和你所见的某‘名画家’近似,只重在为其个人脸上贴金,只顾自己站地步胡吹胡诌……”(P254)
《中华读书报》上曾刊登过一篇范世民先生为范老申辩的文章:
“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此,在我看到、听到、了解到的两个相互关爱的同事、师生、忘年交,怎么‘一下子’、竟被写成一对怨敌?我真是百思难解。
……
史树青先生的反应则不似寒碧的语言过激,他讲得非常明确:黄能馥那天谈范曾和沈从文的事我在场,一言未发。他根本不了解历史博物馆文革时的情况,不知有什么人在后边唆使他如此做。我是历史博物馆‘文化大革命’的见证人,和沈从文关系密切,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讲过这些。范曾对沈从文一向很好,说他写几百条沈从文的罪状,完全不存在这样的情况。范曾在文革中写什么画什么我都记得,没有乱扣政治大帽子,同时轻松调侃,反而冲淡了当时的紧张气氛。范曾今后可以回答这些人,我完全可以作证。
‘我完全可以作证’。史树青先生如是说。王宏钧、李俊臣、邱关鑫、余庠诸先生也如是说,我因此感到某种释然。”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范老狂放不羁异,他的朋友也那么诡异,用“犯得上吗”去反驳别人的“语言摆脱实在之后的暴力”。陈徒手先生采访时可能有疏漏,文责应当自负,不知道新出的三联版有没有什么更新。王亚蓉女士没有点名,没招来这么一帮正本清源家。她的亲历特别有价值的一点在于,不管是谁,那样对待一个老人,都能把他气得够呛,你们造的孽不是一句“犯得上吗”就能掩盖得过去。顺便说一句,我为自己读了好几年《中华读书报》感到反胃,虽然那报纸整体上还说得过去。
好玩儿又可悲的是,另一个帖子里提到沈从文约在1966年写过的一篇类似自白的文章,提到:
我只举一个例就够了,即范曾揭发我对群众最有煽动性的一事,说是丁玲、肖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非俱乐部。这未免太抬举了我。事实上丁玲已去东北八九年,且从来不到过我家中。客人也十分稀少,除了三两家亲戚,根本就少和人往来。来的次数最多大致便是范曾夫妇,向我借书主要也只有你夫妇。你怎么知道丁玲常来我家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别的我就不提了。即使如此,我还是要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是收获之一。”
据说此文本文源自岳麓书社2002年版《沈从文别集•顾问官》(第1页——第3页)。此文写作时间为1966年7月,沈从文时任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研究员。但是目前手头没有纸质出处,但聊作参考。
怎么说呢,这文章出处如果属实,就跟大耳光,响亮的大耳瓜子差不多,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地掌嘴。你们这些目光炯炯的历史亲历者看清楚了,人家老先生是怎么说的。不诛心,也大致能想象当年的情景,深刻体会啥叫攻守同盟。同时,也可以参考范老自己的申辩:
“我怀念沈从文,那 是由于心灵深处保留着他慈祥的笑容;我同样怀念郭沫若,因为他的杰作《蔡文姬》,使我画出了《文姬归汉》,从而使我与沈从文先生结缘,虽海内外颇有扬沈抑郭的暗潮浮动,然而对于我 ,他们同样可钦可亲可敬。当年对郭老趋之若鹜、对沈从文先生弃之若屐的人,今天或者正扮演着另外的角色呢。
……
我举这个 例子绝没有为我曾写过一张沈从文的大字报辩解之意,我只是感 到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普遍受到“左”的路线的冲击,其间发生的 一切,原因非止一端,然而大家同样概莫能外地在层出不穷的运 动中颠簸,必须要你表态、排队、坚定立场、表示忠诚等,这其中包括我,也包括沈从文。 ”
不得不说,能写出这些字的人绝不是凡人。
再回到沈先生,他在另一封(1982年1月29日,致二王的)信件中提到了一个“老太婆”,没点名,也是被对方伤到很深的样子,话里话外多少有点恶毒。这个“某老太婆”说“沈某某出了一次美国就骄傲起来了,别人不敢触他,我偏要碰碰看”。沈老私下里的回应则是,“那么老太婆即或再出什么新点子骂骂,我以为还是让她骂道疲倦或病倒以至于断绝呼吸为止。让她自己也感觉到没有意思,到那时我做公民资格也就算是及格了。”(P259)据说这份冤仇的缘起是老太太请客沈老没参加,结果“恼羞成怒”了。
其余还有沈先生和夫人张兆和与美国学者金介甫的对谈,还有沈先生在“新时期”的几个讲演。前面那个对话很有价值,他在对话中回忆了自己的整个人生(里面提到苏雪林对自己“表示特别好感”,还提到韩丁的女儿)。这个美国研究者的功课做得也好,谈话能谈处许多闪光点来,值得一读。沈先生是非常爱国和认真的人(服饰研究在国内各种难产,但是他不愿意日本人先出,好像还是讲谈社慧眼识金,折腾一圈还是香港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成了主要用于充门面的国礼),可是他对自己的极力贬斥有点儿让人受不了。他一直批评自己的文学创作,这个对话的题目就是“社会变化太快了,我就落后了”。心里未必真这么想,但是长期的洗脑、自我批评无疑很到位,一派惊魂甫定的气象。
从这个角度讲,个人对授予沈老诺奖不大理解。给一个脱离文学创作这么久的人授安慰奖,迟早要算成诺奖的失误,比丘吉尔拿奖合理一点儿有限。范大师说是亲耳听马悦然讲的,这本书里也提到进入他最终决选,跟一个叫马科斯维尔的竞争,而且“基本的倾向已经是沈先生的了”。但是官家希望用B先生(巴金?可是他儿子还要有写作才能,据说“写小说语言纵横无碍,可与钱锺书先生相较”,不知道李小棠先生有没有这么强悍)置换,最终鸡飞蛋打。
那个所谓“马科斯维尔”很可能是2003年文学奖得主库切,他的全名是John Maxwell Coetzee。不过,沈先生1988年就故去了。马悦然的回忆应该靠谱,他说:
“他(指沈从文)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他去世几天之後,台湾一个文化记者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可以确证沈从文的逝世。我立即打电话向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确证此讯。然而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位于五四时代就开始写作生涯的老资格作家中的佼佼者。这位卓而不群的作家的写作生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被中断了。1987年以前,甚至台湾读者也不被允许涉猎他的作品。两个政府都没有给予文学足够的重视。”
最明白无疑的是,八七年布罗茨基拿到了奖,八八年是埃及的马富哈兹。当然,沈先生没拿奖也说不上是什么坏事儿,否则老人家去了天堂也享受不到“不折腾”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