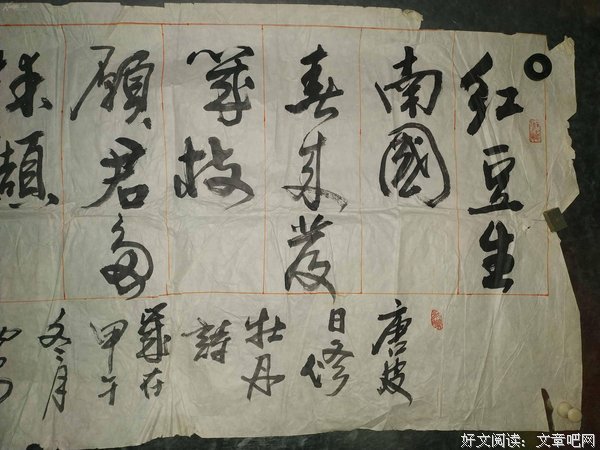《文人相重》经典读后感有感
《文人相重》是一本由马靖云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2020-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人相重》读后感(一):随翻《文人相重》
马靖云这本小册子,文章都是公开发表的短文,内容大多平淡无奇,于人物皆是赞美,八卦也多无关痛痒。闲来阅过,落花流水。不过,最大的感受是作者无意中记录的那段时光的氛围,却是真实可触,令人心悸。
此外也有几则可堪记录。
1、郑振铎死于空难,临行前本来飞机因为天气原因不起飞了,后来又说起飞,他临行时对母亲说:“妈妈,这次我再也不回来了。”p10。案这个“遗言”“谶语”,以前没见过,不知道作者如何得知,更不知郑振铎是什么意思。
2、记何其芳说:“我(读书)不算快,称得上快的还是数胡乔木同志,那才是一目十行呢,我亲自见得,很厚的一摞稿子,他用十分钟就看完了。那真是快!”p54
3、李健吾1982年去西安开会,看望瘫痪在床的清华老友,拍了照片。结果回到成都冲洗时曝光了。他又专程返回西安再拍,担心朋友身体虚弱,去晚了就赶不上拍了。结果,李健吾后来先离开人世,而老友在作者撰写文章时的2001年还在世。p111
总之,书中虽然料不多,但能让后人察觉当时的氛围,作者似乎并未察觉此种氛围有何不妥。这就是本书的最大价值了。
《文人相重》读后感(二):文学研究之旅
文学创作一直是我最热衷的一件事,可以说从小到大一直没有放弃过,可是任何创作都要经过前人的经验从而减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其实我之前一直都是通过阅读文学大家的传记来寻找启发,但看到了这本《文人相重》如获至宝,书中记录的都是那些文人的工作经历,刚好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如果不是马靖云,我可能一直不知道他们的工作方式是如何。
当看了那些作家平时在工作中的状态时,我发现确实都是有两把刷子的,可以看出他们的作风和笔下的文章是对应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读者信服。文人的工作氛围与我们平时的工作不同,他们都是思想工作者,也就是说他们的阅历要比常人丰富的多,对于别人的看法很重视,在交谈和管理的时候就能够做到换位思考。尤其是从何其芳身上能够体现出来,可能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作者才对其使用了相对丰度的描述。
文人就算是出名了也不会有大架子,如果这些人放在如今,应该就是那种综艺花多少钱都请不来的,只是静下心去创作的状态。在这样的氛围中工作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从日常的对话中就能够学习到非常多的知识。所以真正的大家脑袋中是有取之不尽的素材的,我想这和天赋有很大的关系,眼界越广的人看到的也就越多,自然不需要刻意去学习,这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十分明显。
在看待身边琐碎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持一种质疑的态度,总是想得太多,把单纯的事情想得复杂。我经常失眠,每天我都会做梦,如果遇到不顺心的事我会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这种生活其实是很累的,我曾尝试过寻找生命中的那些隐藏着的美,我总是失败,我觉着这个世界也许就是这样,不会变得更好。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只有遇到不好的,好的才会出现。
真正的文人不一定非要写文章,当然文章是很直白的一个表达方式,我认为支撑他们的还是脑海里对于一切事物的看法,这些都是很独立的。学习永无止境,哪怕是大家也会有犯错的时候,更何况我们呢。
《文人相重》读后感(三):文人相重,重在相互之间的真挚对待与友善相处
初看此书的名字,一时间以为自己的眼花了。听说过“文人相轻”四个字,似乎没有听说过“文人相重”这个词的。俗话说同行是冤家,若是放在自持清高,又颇具酸腐的一些文人身上,这怕是显现的更明显,所以曹丕才会在《典论.论文》中提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看来这在古人的眼中,早已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不过凡事都是不能够一概而论的,有“相轻”者,自然也会有“相惜”者,这“相重”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本《文人相重》,来自于一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科研管理工作的人员马靖云多年来在工作生活中的亲见亲闻。她曾于这些赫赫有名的中国文人共事多年,其书中真实恳切的记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郑振铎、何其芳、沙汀、陈荒煤数任所长的诸多生活点滴,以及俞平伯、钱锺书、王伯祥、李健吾、杨绛、罗大冈、罗念生等多为知名文人学者的日常琐事。这既是作者自己的一本回忆录,也是一份有关于部分知名中国文人的历史记录见证。
书中的文字大多来自于作者这些年来发表于各个大小刊物中的回忆文章。她用平和细腻的语言文字,对曾经所经历的事,所接触的人做了详细生动的讲述。言语并不华丽经验,很有时代的味道,就好像是一位老朋友在与你如数家珍的闲话家常。
在此之前,也曾经在别的文字中读到过一些那个时期文人的逸文,其中也不乏一些彼此之间矛盾重重的事情传出。不过在马靖云的这本书中,倒是几乎看不到什么不和谐的内容。在她的笔下,几乎每一个人都亲和友善、彼此之间一团和气。她对每一个人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充满赞誉的,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值得尊敬的。想来作者也是一位性格宽厚平和的人,如若不然,在她的眼中所见到的,心中所感受到的,必定不会如此的美好祥和。
我们通过作者的文字,对其所熟知的文人心生敬佩,赞叹他们所拥有的优秀品格。同时也通过作者的文字,感受到了作者的个人修养以及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事实上作者的确是一位朴实无华、为人谦逊、亲和的人。她尊敬着身边所接触的每一个人,同样他的同事也是依赖信任她的。
文人相重,重在相互之间的真挚对待与友善相处,这彼此的态度还真的是很重要啊!
《文人相重》读后感(四):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似乎是大多数学者之间的通病,每个人的领悟都不同,又大多恃才傲物,所以历来就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之说,可是偏偏就有“文人相重”之人,比如雪莱与拜伦的志趣相投,川端康成与三岛由纪夫的亦师亦友,白居易与元稹的息息相关,李白的“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都是文人相重的典型,而看完由马靖云所著的《文人相重》之后,会对这种情感有更多的体悟。
马靖云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文学研究所科研管理工作,协助了很多文学所方针任务制定以及科研管理工作,也与许多大学者、老专家们共事,接触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其中不乏一些珍贵的史料,如毛泽东对《不怕鬼的故事》送审件的批示,何其芳在藏书中的批注,郑振铎的《最后一次讲话》,何其芳的《关于科研干部培养问题》的报告。何其芳的报告中,既有研究方法的制定,也有读书方法的讲解,这些报告与讲话,既是时代的见证,对于每个人的工作学习不无裨益,也让人看到这些大家身上的治学精神。
在这些资料之余,也不乏文学所诸位同事的点滴小事,钱钟书先生的各种笔名,俞平伯先生评职称的故事,李健吾先生创作到人生最后一刻,老舍先生种植的三百多株菊花,何其芳先生失而复得的扇子,毛星先生的不图名利生活简朴,王瑶先生的悠闲淡定,路遥先生的匆匆相见与对文学创作的追求,都是这些学者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何其芳与俞平伯两位之间的情谊,何其芳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听过俞平伯讲课,之后一直以学生自居,在筹建文学研究所之初,俞平伯就被调入,并做《红楼梦》八十回本校点工作。何其芳对于俞平伯一直是照顾有加,六次批判的保护,虽被批判依然评为一级研究员,即使在十年浩劫之时,两人都被关进“牛棚”之后还是互相帮助,何其芳喂猪,俞平伯种菜,两人劳动场地相近,彼此相互照应,所以才有“犹记相呼来入苙,云低雪野助驱猪。”这让人感动的诗句。
在这些亲切的文字中,还有一个背后的主角,那就是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几经搬迁与变动,历经风波浩劫,起到了引领激发国内文学创作的作用,从访谈中看得出来,现在的文学研究所依然具有超前意识,这本书无疑成为了一种述往与承继的方式。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这本《文人相重》是学者惺惺相惜的回忆,是为文为人的兢兢业业,是对于文学所发展历程的记录。那是认真科研勤恳勤奋的精神,那是学者之间惺惺相惜互相体恤的精神,那也是共同为文学事业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如今能在书中感受得到,并且激励着一代人。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关于阅读这件小事儿
《文人相重》读后感(五):文学研究所前辈剪影
《文人相重》是马婧云回忆文学研究所里共事的众多文学大家的工作片段的回忆文集。马婧云曾在文学研究所从事科研管理工作,能够近距离接触到所里各位文学大家,包括郑振铎、何其芳、俞平伯、钱锺书、李健吾、老舍等。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历史上也的确出现过很多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文人之间互相比较、彼此轻视的状态。但是,翻看马婧云的一篇篇回忆会发现,文学所诸位前辈,虽然都是文学大家、各自都有大成,却没有丝毫骄傲之气,反而虚怀若谷,彼此之间互相支持、非常亲和,可以说学养和品格并重,自有大家风范。
这些回忆片段最珍贵的一点是,马婧云是从同事的角度观察各位大家,从他们的日常小事中,看到他们在文学成就之外的真性情、真品格,留下的是文学所前辈们鲜活的人物剪影。比起他们的头衔,这些工作和生活中的形象更亲切活泼,有烟火气。
从这些回忆点滴中可以看到,各位前辈不仅工作上勤奋认真,生活中还很幽默逗趣,他们由衷地热爱文学,并且自得其乐,更珍视彼此间的友谊,甚至在艰难时期愿意共患难,是实实在在的“文人相重”。这本书中有多篇回忆何其芳的文字,展现了何其芳工作生活中不同的侧面。
文人珍视书和纸,热爱文字,也愿意分享,这一点在何其芳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何其芳看书时,总是随手在空白处写下批注。他用纸也非常节约,反面、旧稿纸都充分利用起来。这种节约精神,让后辈惭愧。匈牙利汉学家米白曾造访过何其芳。何其芳带米白参观了自己书房的大量藏书,还亲口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听歌》和李白的《蜀道难》,并让米白录音。朗诵诗歌的过程,对何其芳来说,是乐趣也是享受。
文人也自有独特的幽默和顽皮。1977年4月1日,何其芳声称翻到两首元代人的诗,有不解之处,由何西来记录下来,让大家帮助解析。可大家解来解去,还查出几个典故,终是不得要领。最后何其芳解开大家谜团。原来,这是他自己创作的,不过趁着愚人节跟大家开个玩笑。这样的玩笑,还真是文人专属的逗趣。
何其芳先生就爱书成痴,喜欢淘书、逛书店,是很多书店的常客。在他的推动和带领下,文学所的图书馆藏书极大丰富,其中包括不少珍贵的孤本。他去世后,也把自己积累的三万余册珍贵藏书留给了北京广播学院图书馆。当然,爱书也爱淘书的绝不只何其芳一人,他偶尔也会跟好友“抢书”。他和任常侠就曾互相调侃对方把自己要的书给买走了,说完后两人大笑,真是爱书之心不相上下。
文人之间互赠些文字书画等小礼品,也是雅事。这样带着情谊和雅趣的礼品,往往更有纪念意义。何其芳在北大哲学系就读期间,听过俞平伯的课,就此结下师生之谊,并且几十年不变。马婧云回忆,速来不爱为私事麻烦人的何其芳,曾求众人帮忙寻找一把折扇,当时遍寻未果,何其芳非常惋惜。幸运的是,不久后在大扫除过程中,从沙发缝隙中寻得这把纸折扇。这把扇子如此被珍视,原来大有缘由,扇子正面是傅抱石的山水画,背面是俞平伯亲笔手录的姜夔诗。老师题赠的这把扇子,何其芳自然珍爱,之后始终妥善保管。
最能体现文学所前辈们真正“文人相重”的一点,是文学所在所内人员纷纷被批判的时期,仍能够顶着压力、坚定地互相支持。因为《红楼梦研究》,俞平伯曾经大受批判,承受很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所为大家评定职称时,何其芳仍坚持按照客观标准把俞平伯评定为一级。这不仅是何其芳作为学生表现出的尊师重道,更是他作为同事和友人所提供的肯定与支持。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也没有丝毫“相轻”之举,敢于共患难,真正做到了“文人相重”,惺惺相惜,这才是文学所诸位大家最令人敬佩的品格。
2020.01.05雾凇
《文人相重》读后感(六):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有人不同意……
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意思是说,文人之间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这句话虽然不大好听,但似乎可以举出来的例子却有不少,不但有政见上的“相轻”,还有写作上的“相轻”……总之一句话,就是别人不如自己,自己才是最好!其实就心理学进行分析的话,“文人相轻”多半源于唯我独尊、妄自尊大、过于自恋。
但从1956年到1988年,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多年的马靖云看来,她所见识到的那些大作家,所领导也好,普通人也罢,从来没有过“文人相轻”的表现,反而可以用“文人相重”来形容。为了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工作,不仅进行文学创作,还进行文学理论研究,有的还要负责行政业务,或者别的琐碎事务。
马靖云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她可以在“文学研究所”这一个小小的所里,或者通过文学研究所,与那么多知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近距离地结识,甚至耳闻睹他们的言行举止;当然,能看到《文人相重》这本书的读者们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有了当年马靖云记下的工作笔记,她得以在几十年后把她的所见所闻转化成为文字,让更多的人得以与那些大作家们“面对面”
细细数来,一大把的老作家在《文人相重》这本书里“迎面走来”:郑振铎、何其芳、俞平伯、钱锺书、周扬、李健吾、毛星、老舍、沙汀、路遥、王琦……或许有些作家不怎么广为人识,但从马靖云的回忆里,真的可以算是“认识”!所里当然会有领导,不过这些大作家,无论郑振铎还是何其芳,都没有什么架子,而是非常诚恳。比如马靖云,她刚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因为工作中遇到了苦恼,第一次见面就不揣冒昧地向所长郑振铎倾诉;而郑振铎也“立刻认真地做出了回答”,正是他的几句话,让马靖云此后受益匪浅。比如第二任所长何其芳,对待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但他自己却觉得自己做得还很不够,不止一次检讨:“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像郑振铎和何其芳这样的领导,在今天还真的不是很多了。不摆架子就已经很不错了,更何况要做到那么谦虚谨慎呢?毛泽东当年讲过“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话说得很简单,但真要做起来却很不容易;一辈子一以贯之地做到“两个务必”,那就更不容易了!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马靖云在《文人相重》里进行了记录,那就是当俞平伯因为《红楼梦研究》受到批判,以至于那些批评、批判“像台风一样席卷全国”的时候,作为所长的何其芳做得就很得体。他说:“尖锐的批评是需要的,但尖锐不等于粗暴。学术问题常常是比较复杂的,必须进行自由讨论。有不同的意见应允许大胆发表。被批评的人也可以进行反批评。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学术问题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解决办法,只能服从真理。”这话放到当时那一种大气候下就已经难能可贵,直到今天仍足以让人觉得,说得真对!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当时碍于形势做得过火,如果以后能认识到错误并且改正,那就还是个好同志,可以原谅。
看来,只要坐得直、行得正,即使真的“相轻”,也真的没有什么;更不用说,那些老作家做得很好,把“文人相轻”变成了“文人相重”,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文人相重》读后感(七):文人的故事:文学研究所忆事
主要内容:作者马靖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她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众多文学名家工作中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看到大家们的风范与工作精神,有非常独特的文学参考价值。
我读:
这本书中提到的文学名人非常多,而且都是耳熟能详的,相信爱读书的人对于他们的作品会有一定的了解。即使是部分了解,也可以通过此书更多地了解作家们生活中的一面,非常难得。
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2月22日,原附属于北京大学,郑振铎为所长。1958年郑遇难,何其芳继任。研究所搞的是文学研究,提倡的是集体创作,方针是总结经验,探索文学规律等,基本就是这么个概况。
在这本书中,作者对何其芳的笔墨尤其多,大概是接触时间长,留下的印象比较多吧。
何其芳的书我并不是很了解,可是通过这本《文人相重》我对他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首先,他是领导,领导很忙,所以既要工作又要读书学习创作,就需要平衡好这个时间的问题,为此他获得了“重脑力劳动者”的戏称。
书中对他的很多轶事都有描述。我总结了一下何的几大特点:
1爱书成癖。这个不用多说,在那里工作的人都爱书,看到好书还要给所里提供购买的清单,为研究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读书有方法。他读过的书批注极多,可见是边读边思。以前总不知道何为批注,看了书中举出的几个例子,算是明白了。不论什么样的感想皆可写,正是这些小想法可以作大文章。
3节约纸张。用过的纸也要把背面或者空处都写满。
4为人率真。文人大抵有这个劲儿。而且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为了保护许多文化工作者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敢于直言。
5爱惜时间。这个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讲到他进办公室立刻办公,与来汇报的同志绝无废话,直奔主题。我喜欢这种工作方式。废话让生活变得无意义。
6读书丰富。在书后有一份他开列的必读外国文学书目,前面文中提到有三百本,我没数后面的书目是否三百本,但确实很多。而且很大一部分都是我们现在常见必知的书目,五六十年代开列的书目到现在还有很多被沿用,可见其读书之丰。当然他们工作条件有利,可以接触各种好书。我们七八十年代时却什么也接触不到。那些书目中还有一部分我是近来才知道的,还有一些是当今中学生的必读书目,总觉得看到了很感慨。
书中还提到钱锺书、周扬、李健吾、沈从文、沙汀等很多人的往事。但都没有何其芳的篇幅多。有两件事让人唏嘘。
一是沈从文后来与记者说,当年自己扫厕所扫得特别干净。说着就哭起来,一直哭。
第二件是路遥想去研究所工作,觉得那里的文化环境好。因为下班了,就和作者见一面。作者告诉他研究所是搞理论研究的,不能一门心思搞创作。路遥听后就走了,再也没来过。
所以作者在思考,究竟研究与创作是否有必要分得如此明白。
看完此书综合感受:作者实在是太幸运了,能在这么好的环境里工作一辈子,真是让人想也不敢想。
此书前面有三人作序。前两位是同事。但第一位的序写得味同嚼蜡,好像没文化的碎嘴子。后两位的序虽然短,但读起来让人舒坦。
青年人读此书,可学习名家种种,不失为一本了解文学往事的可读书。
《文人相重》读后感(八):《北京晚报》:文学所的“活档案”
《大百科全书》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词条编写者马靖云今年已经91岁了,从1956年到“文学所”工作,之后的32年中,她作为社科院的科研管理人员,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亲历者。
马靖云根据亲见亲闻,真切记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郑振铎、何其芳、沙汀、陈荒煤数任所长的诸多生活点滴,以及俞平伯、钱锺书、王伯祥、李健吾、杨绛、罗大冈、罗念生等学者的日常琐事、丛脞遗闻,率皆秉笔直书,首重实录,集结成书《文人相重》。对于李克农、罗青长等中共隐秘战线的几位卓越领导人的追忆,构成了此书的另一重要内容。
述往丛书之《文人相重》 马靖云 北京出版社
述往丛书之《文人相重》 马靖云 北京出版社现在的年轻同事们都用“老文学所”称呼他们这批老人,同事钱中文回忆,当年马靖云作为何其芳所长的得力助手,他们一见到她就说:“马大秘来了!”她总是大声“哈哈哈哈”地笑着说:“别开玩笑了!”他看到马靖云的回忆文章后觉得看来写的是点点滴滴,但却是确确实实,真实自然,特别是她的经历和感受,独此一家,极有价值。马靖云尽管年过九十,但“笑声还是脆生生的,而且不无风趣”,细数往事,“有声有色、准确无误、有盐有味,”张大明在序言中说,她再现了当年的场景和人的风貌,她文思敏捷,精力充沛,根本不像老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建立于1953年,最初附属于北京大学,原名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郑振铎任所长、何其芳任副所长,两年后归中国科学院。郑振铎逝世后,由何其芳任所长,1976年社科院从中科院中分离出来,文学所自然也随之更名,沙汀任所长,陈荒煤、余冠英等任副所长。
作者马靖云早年从军,进城后多年从事繁重、冗杂的科研管理工作,平生因缘际会,得与学术殿堂内的众位泰斗共事;她经历了文学所最辉煌的大师齐聚的年代,她的回忆中文人之间的情谊更是令人唏嘘。这些忆旧随笔文风平易,一般对传主的刻画也只寥寥数笔,却绘声绘色,可以说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见证。
她进入文学所工作遇到的第一位领导便是郑振铎先生。“当时我年轻幼稚,不顾身份高低,第一次见面就不揣冒昧地把自己工作中的苦恼向他倾诉起来。”马靖云写道,而郑振铎不但马上回答了她的问题,还建议她在繁杂的工作时坚持记工作日记。这一习惯不仅令当时没有工作经验的马靖云受益匪浅,也为现在的作者和读者无意间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史料。
“文人相重”的“文人”一开始指的是何其芳与俞平伯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何其芳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时曾在清华大学听过俞平伯先生的课,他视俞平伯为师长,称呼他俞先生。1952年何其芳受命筹建文学所时,将俞平伯调入文学所,何其芳反倒成了俞平伯的领导。在作者马靖云的记忆中,关系的变化并没有让他们之间的感情受到影响,在那个年代,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受到一次又一次激烈的批判,何其芳作为其知己,深深理解而尊重俞平伯,主持批判会议时也尽力保护他,但他当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两难的局面,自己每天也沉浸在写检讨之中,检讨书摞起来有一尺多厚。“何其芳珍惜俞平伯的才干,赞赏他的文学鉴赏力,专门找俞平伯谈心。”马靖云写道:“后来,俞平伯说:‘何其芳是知识分子的知心人。’”
在那样的气氛下,何其芳与文学所的领导们共同争取为俞平伯评定了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一级研究员的职称。一级研究员文学所初拟时有三名,为钱锺书、俞平伯和何其芳,何其芳还将自己主动降为二级。当时许多人对将俞平伯定为一级研究员表示反对,何其芳坚持,学生是一级,老师是二级,这是不对的,力排众议。作者看来,当时所里上下内外阻力很大,执行起来也很困难,“然而何其芳勇敢地坚持了自己的主张,做到了无私无畏”。这对俞平伯的生活有很大改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一级研究员在当时享受一级补贴,每月有肉票、豆票、鱼票、油票。之后形势恶化,两人都被关进“牛棚”,在下放河南时,何其芳喂猪,俞平伯种菜,还去帮他赶猪。
“现在,文学所初期的老人所剩不多了,健在的也都是耄耋老人了,由于年纪、身体状况原因见一面也非常之难。”1953年,“文学所”成立,《文人相重》的序言中与作者马靖云前后脚来到“文学所”的王平凡透露,马靖云多年来参与了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几十年来,她保存了许多本工作笔记和生活日记,如今看来弥足珍贵,因为她“记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事件’、细节、经过,篇篇都有史料价值”,她对于“经历过风风雨雨的文学所的人与事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常常被所里人称为‘活档案’”。
推荐阅读:述往丛书
本文首发《北京晚报》2020年5月15日
《文人相重》读后感(九):清风一缕见史入心——在《文人相重》中找寻文学所的点滴过往
何其芳(1912.2.5—1977.7.24)【述往】
对于享誉中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对于何其芳、俞平伯、钱锺书等著名专家、学者,在过往的几十年间,人们从文学的视角写过不少文章,进行过许多研究,但是像《文人相重》的作者马靖云这样,以回忆录的形式,从一个学术建构和科研管理者的层面,回忆文学研究所的历史移位,以及在学人治学方面的亲身经历,非常难得。所以读到《文人相重》一书,我既觉得独特又感到亲切。
本书作者马靖云长期在何其芳身边做秘书工作,除了完成科研管理的具体事务,还有送往迎来的外事活动。说得具体点,就是科研规划、课题设置、外事交流、文献整理、会议筹备等等一系列工作。但这些工作也使她见多识广,她养成了重视观察、重视历史档案,讲究实事求是,少说话、多用心、善思维的工作习惯。这也决定了她的文章有亲见感和纪实感,亲闻性和在场性。《文人相重》没有声嘶力竭的叫喊,没有耳提面命的说教,书中的语言娓娓道来,就像淡淡的一抹白云,轻轻的一缕清风,却能沁人心脾,撼人心灵。这就是《文人相重》的魅力。应当说,作者马靖云画出了文学所这样一个中国最高的文学研究机构的魂魄所在,一点一横、一闪一耀贯注到书中的字里行间。这魂是什么?就是大家能够各自按照国家需要,根据个人专长,确定研究课题,专心致志做学问,一做就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毕其一生。在这里,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在渐渐地得以延续,学术的基业不断地铸造着辉煌。
人毕竟是决定成败的主体,是统领千军的关键。《文人相重》对整个文学所的书写,还原了历史,还原了生活,写活了人物,突显了精神。本书不是高头典章,皇皇大论,而是娓娓道来,绵绵叙述,如炉边絮语,路旁闲话,其中却寄予着半个多世纪沉沉的思忖与深深的怀想。马靖云写文章很会剪裁,会运用手中的史料,心中的故事。点点滴滴,披沙沥金。从题目上看,她的写作是在怀人、忆旧。其实,书中还写了一个国家顶级研究所的创立和发展,还原了这个中国现代“翰林院”的活生生的历史。她不是为文学所写史,也不是为所领导、专家学者写传,但若将其书写的点滴汇总,全书体现了总体的宏放,更有生动的细节,文学所的总体风貌就在这两极的呼应之中,浩浩乎文哉。
我叹服作者通过在郑振铎、何其芳等人身边工作,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并且通过大量档案材料,感知、体验这两位所长的亲力亲为,了解他们为建构文学所这座学术的大厦所付出个人的历史。他们把文学研究管理上升为一门科学,在科学的层面加以规范,提炼出管理学、研究学的宏大构想。本书作者用鲜活的材料,活灵活现地还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所的筹建、创立以及发展过程。何其芳把研究所的管理作为一门学问,一种科学,常说“管理是需要钻研的”。他和郑振铎在50年代初白手起家,建立文学研究所。把文学研究变为一种学科,一种事业。在人员调配、学科设置、课题落实、图书征集和购置设备等等方面,筚路蓝缕,辛勤耕耘,既是领导者,又是拓荒者,既是规划者,又是践行者。反观历史,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论阿Q》在学术史上固然了不起,可以划出一个时代的学术标志,但在文学研究学科的建立和完善机制上,他的贡献更值得大书特书。他们在前无古人的基地上,从奠基开始,颠颠簸簸,一路走来,最终建构成一座参天大厦。对这个历史功绩的铭记,我们终于在《文人相重》这本书中找到了共鸣。
一个最高学府所属的科研单位,最要紧的是人才的调集和科研队伍的建设。这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和起点。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组建到60年代文学所的第一次辉煌,郑、何两位创始人,能将国内文学(含外国文学)专家几乎全部召集到旗下,实实在在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是创造历史的大手笔。这一支队伍在《文人相重》一书中多次出现。他们是郑振铎、何其芳、俞平伯、钱锺书、孙楷第、王伯祥、余冠英、吴世昌、吴晓铃、陈涌、蔡仪、唐弢、冯至、卞之琳、罗念生、罗大冈、李健吾、潘家洵、戈宝权、缪朗山、沙汀、陈荒煤、许觉民,以及由他们培养出来的一支中青年学者队伍。文学所为这些专家、学者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反过来,两代学人以其经典著述建构了文学所这座学术的殿堂。如果说本书有一种贯穿始终的人文观念,那就是在一些看似轶闻琐事与经典历史的细节中,反映出了这种相得益彰的辩证关系。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在文学所里面人与人之间所建立的那种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砥砺的学者风范,也许就是本书所言说的文人相重吧。
本书的五大附件——郑振铎的《最后一次讲话》、何其芳的《关于科研干部培养问题》,及何其芳开列的《世界文学名著阅读篇目》、唐弢推荐的《文章做法精读篇目》、文学所80年代初推荐的《文艺研究学习书目》,件件是硬通货,无不具有真知灼见。尤其是三个书目,不是谁都开得出来的,没有大学问大胸怀垫底,没有理论的眼光,不能烛照探幽,没有视野的宏阔,不能横扫三军,气贯长虹。后生学者,照此阅读,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就囊括于胸,清晰在握。20世纪60年代初,我还是在校大学生,见到何其芳开的书目,竟至惊得发呆!何其芳能够开出那样的书目,说明他有学识,有眼光。从行文中不难揣度,这个书目,马靖云也读过,至少是其中大部分。学海泛舟,近朱者赤。这使她的工作有深度、厚度、广度,有思想,有美学成分。作者多次提到,何其芳对读过的书,都有批注。如有好事之人将何注编为《何其芳批注集》,除了它本身的学术价值而外,更有启发意义:可见诗人读书之广,之勤,之多。不停地读,反复读,读名家名著,记下自己读书的味道。这是求学之道,写诗之本,是游弋学海,与前贤对话,与人类的智者交心。
本书涉及的学者、名流一大串,书的封面列有的与记述的包括郑振铎、何其芳、俞平伯、钱锺书、周扬、李健吾、毛星、老舍、王瑶、沙汀、路遥、王琦、李克农、罗青长等,书中捎带写到的著名人物更多。回忆文章少不了的是细节,它们是不能删夷的枝叶,是带露折花的晶莹剔透的珠子。如作者说何其芳“书”多,装书有书架、书橱、书柜之别,由何其芳的“书”,旁及孙楷第、王伯祥、俞平伯、唐弢、吴世昌、吴晓玲的藏书之差异,更及大学问家钱锺书却室内“无书”。在此,我首先佩服作者观察之细,从这细分之中,真实反映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个人生活水平提高(变化)的历史,兼及个人性格、兴趣之迥然。全书虽未专门论述,仅偶有涉笔,却尽显情趣,且无不发人深思。
《文人相重》也有笔墨凝重之处,如《永不停止转动的齿轮》一文写何其芳做实事、重效率、忌空谈。《荒煤重返文坛》一文写陈荒煤笔墨潇洒,一个曾经的副部长,而今指挥书籍的装车、卸车,重显当年本色。他力挺解放思想的新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及其作者唱赞歌。他笔立潮头,保护新生力量,奋然前行。文字不多,但为时代留下了影像。他的《阿诗玛,你在哪里?》,呐喊之声,从云贵高原夺腔而起,回荡太空,镶嵌于历史的天际。
就本书作者马靖云的潜质和文笔来说,她不应该只提供136千字的《文人相重》就戛然而止,她还应该有续篇。而今,她虽然年过九旬,却还思维敏捷,记忆凿凿,笔力遒劲。就文学所而言,依然以科研为视角,至少还有两方面的人可书写,而且有价值、有市场。一是从延安来的、从解放区来的老革命,如王平凡、唐棣华、朱寨、贾芝、力扬,他们或当领导,或为学者,稍加发掘,均可能得富矿;二是一大群中青年学者的涌现,如曹道衡、胡念贻、刘世德、陈毓罴、蒋和森、钱中文、樊骏、袁可嘉、陈冰夷、柳鸣九、陈燊、董衡巽,等等,无不学有专攻,有故事,记录下来,就精彩,甚至就是诗。
作者:张大明,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前主任,研究员 本文首发《光明日报》2020年3月12日
《文人相重》读后感(十):柳士同:细述文学所往事
郑振铎 何其芳 俞平伯……
2020年1月,《文人相重》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九十高龄的作者马靖云女士曾在文学研究所工作32年,先后协助过郑振铎和何其芳两任所长。该书收录了她从20世纪80年代起发表的近三十篇回忆文章,记述了文学研究所十余位学者作家的往事。
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原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1955年归属中国科学院,改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文学研究所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该所首任所长为郑振铎,副所长为何其芳;1958年郑振铎因空难辞世,何其芳继任所长。那时,我正痴迷于文学,读过郑、何二位的许多著作,如今再读回忆他们的文章,感到分外亲切。
上中学时,我读过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首先是出于仰慕郑先生的大名,同时也感觉这套书所用的史料多而细,是最好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当时,学界就有“以论带史”还是“以史带论”之争,我倾向后者。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我看来正是“以史带论”的典范。但毕竟太年轻,所学实在肤浅;如今读到《文人相重》中有关郑先生的回忆,才认识到这部文学史的价值远不至此。书中还附录了郑先生遇难前的一份“检讨”,这份“检讨”后来以《最后一次讲话》刊载于《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二期。郑先生检讨了自己“封建文人的文学批评观点”,可这些观点如今看来,有不少都是郑先生的洞见,是对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比如,“强调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认为送子观音是受圣母的影响”,“说释迦牟尼的脸是希腊人的脸”,还“特别强调印度的影响,说变文是一切近代文学的祖先”,“认为印度受希腊影响,中国受印度影响,结果还是中国受希腊影响”等等。这些观点无疑很有见地,很值得文学批评界重视与思考。再比如,郑先生检讨自己“喜欢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可比较研究不过是“运用比较方法,对不同民族的文学现象进行综合分析,探讨彼此的相互影响及其与时代、社会、文化间的关系”,仅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研究方法。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不就是从比较文学开始的吗?鲁迅先生的《摩罗诗力说》就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郑振铎于20世纪30年代写就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使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不仅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事情,也是他对19世纪起滥觞于欧洲的“比较文学”的成功借鉴。 大家小书 《唐五代两宋词史稿》 郑振铎 著 北京出版社
大家小书 《唐五代两宋词史稿》 郑振铎 著 北京出版社《文人相重》里回忆文学研究所第二任所长何其芳的文章有12篇,书名《文人相重》用的正是其中一篇的标题。此篇记述的是何其芳与俞平伯的师生兼同事之谊。中国历来有“文人相轻”一说,可马靖云从何其芳身上看到的,却是“文人相重”的一面。何其芳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但他就读期间经常去中文系听俞平伯的诗词欣赏课,二人从那时起“结下师生之谊”。1954年由“两个小人物”发难,在全国展开了对俞平伯及其《红楼梦研究》的猛烈批判,从那时起,到1957年“反右”、1958年“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俞平伯都无一例外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而“无一不涉及何其芳对俞平伯的种种‘包庇’”,其中“反复被提到的就是,被批判的俞平伯为什么仍然被评为一级研究员和被推荐为人大代表这一 ‘错误’”,待到60年代中后期,“这些‘错误’就升级为‘罪行’了”。郑振铎遇难时60岁,何其芳病故时65岁。
1987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为纪念何其芳逝世十周年,编选了一本怀念文集《衷心感谢他》。年老体弱且早已“谢绝宾客”的俞平伯先生,却“慨然允诺”为文集写了一篇《纪念何其芳先生》,并收录两首吟诵他俩半生情谊的七绝旧作,作为文章的结尾:“晚岁耽吟怜 ‘锦瑟’,推敲陈迹怕重论。 ”
近代以来,研究“红学”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我最看好的是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此文最早刊载于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集刊”,后又与何先生的其他四篇古代文学论著一起,以《论<红楼梦>》为书名结集出版。这篇内容厚重分析精辟的长篇论文,堪称红楼梦研究的扛鼎之作。何其芳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在那个年代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大家小书 《史诗<红楼梦>》 何其芳 著 王叔晖 绘 蒙木 编 北京出版社
大家小书 《史诗<红楼梦>》 何其芳 著 王叔晖 绘 蒙木 编 北京出版社有关何其芳50年代末对 “大跃进民歌”的批评,《文人相重》中虽未提及,但不妨赘言几句。 1958年掀起一股全民写民歌的高潮,甚至提出“村村都要有自己的李白”。周扬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道路》的报告,又与郭沫若共同署名,编选了《红旗歌谣》一书,共收入新民歌260首。就在整个文艺界乃至全民头脑发热的时候,何其芳出奇地冷静与清醒,他到河南、陕西等地农村考察民歌创作的实际情况,披露了一些造假、浮夸的事例。他写了一篇《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发表在文学期刊《处女地》上,没想到引来许多责难和批评,于是他又撰写了长文《关于诗歌形式的争论》和《再谈诗歌形式问题》,相继发表在《文学评论》1959年第一期和第二期上,进一步陈述自己的观点,反驳了各种非难。在他看来,“民歌虽然可能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形式,未必就可以用它来统一新诗的形式,也不一定就会成为支配的形式”,新民歌的具体限制在于 “它的句法和现代口语有矛盾。它基本上是采用了文言的五七言诗的句法,常常以一个字收尾,或者在用两个字的词收尾的时候必须在上面加一个字,这样就和两个字的词最多的现代口语有些矛盾”。
《文人相重》一书颇值一读,仅书名提出的命题就很值得我们深思。文人相重的“重”指的是看重、尊重,而不是吹捧、“站台”。在我看来,“文人相轻”固不可取,“文人相捧”的恶习更须鄙弃。
述往丛书
本文首发《青岛早报》2020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