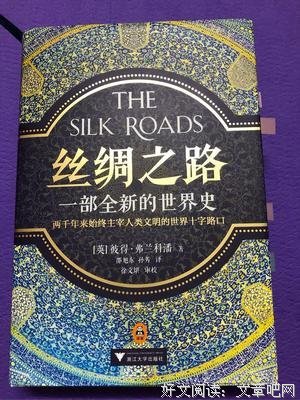现代欧洲史(全6卷)读后感摘抄
《现代欧洲史(全6卷)》是一本由[美] 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 / [著作,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0,页数:33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代欧洲史(全6卷)》读后感(一):工业革命与欧洲社会的重建(书摘)
长远看来,这是工业化两个方面的直接作用:首先,是欧洲的整体繁荣,使得欧洲可以从外国进口食品;其次,是运输网络的优化,使不易保存的物品能迅速运到远方。即使在人口激增的时代,欧洲人民依旧衣食无忧,这便是工业革命带来长远利益的明证。
《现代欧洲史(全6卷)》读后感(二):光荣与阴霾:欧洲的现代历程
《现代欧洲史》是一套六卷本、厚达3300页的历史著作,由美国历史学会首位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主编,尤金·赖斯(Eugene F. Rice)等10位历史学家参与修订。
作为欧美高校沿用50年的教科书,它的最大特点是简明清晰,尤其紧扣“现代”二字,以传统的线性叙述方式,阐析各类标志性的大事件,展现了欧洲从文艺复兴到欧盟的500年文明发展历程。
《现代欧洲史(全6卷)》读后感(三):垃圾翻译,贻害无穷,买到就是亏到!
《现代欧洲史(全6卷)》读后感(四):宿命
以下文字算不上书评,只是读完这六卷本的大部头之后的一点点感悟而已。
三国演义所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用在欧洲历史也颇为贴切,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分分合合,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文明和战争,让人爱之深又恨之切。细究这一切,无不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而最终通过国家这一组织而具体体现出来罢了。如果欧洲一直维持着罗马帝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统治,而没有之后的分裂和战争,到现在还真不知道是怎么一个结局。我认为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些推进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和技术,一定会大大的延缓,甚至大概率不会产生。这些璀璨夺目的思想和科学成果,应该是诞生于无数次的冲突甚至于战争的大环境之中,只有碰撞才会产生火花,让人想起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许这不仅仅是巧合,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宿命吧。
民族主义,宗教分歧,经济差异,这种种因素在当今像一个个幽灵一般盘旋在欧洲大陆的上空,其实也同样威胁着全世界。一个统一和谐的欧洲,一个推进全球化的世界,是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愿意看到的。可是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妒忌,不诚实,这些恶的因子,都在阻止着这一切的发生。英国的脱欧,中美的贸易冲突,欧洲的难民问题,种种事件都预示着世界向保守主义回归。人是健忘的动物,虽然距离两次世界大战不到百年,但是战争的创痛似乎已经被彻底忘却了。这样发展下去,局部甚至全面的战争是一定会发生的,而面临浩劫的人类社会能否再次安然无恙,不得而知。
回到书的本身,要写一部现代欧洲的编年史,这么长的时间跨度,这么多的国家,这么错综复杂的头绪,难度太大。整部书缺乏明确的主线,让读者感觉支离破碎,虽然很多地方不乏闪光之处,却难以把涓涓细流汇集成大江大河,让点滴心得达成认知的突破。读完全书后,仅仅了解了很多未知的东西,却无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升华,实在是有点可惜。再加上不知道是原著的原因,还是翻译水平不给力,文字的流畅度不够,阅读感觉很生涩,尤其是对本书这么长的篇幅来说,可以说绝对影响到了读者们的体验。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史书会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之分了,显然,对于记述欧洲现代史来说,编年体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现代欧洲史(全6卷)》读后感(五):大航海时代的光与暗
大航海时代的光与暗
文:渭水徐公
现代欧洲的历史是一幅光怪陆离的画卷。当人们在偶然间拥有了更高超的手段时,生活便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发生变化的趋势日益加快。驱动一切手段变革的诱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益。
在现代欧洲历史的初期,人们刚刚从蒙昧的中世纪解脱出来。那时的保质手段不甚高超,肉类经常会在炎热的天气变质。而人们发现,来自东方的香料胡椒洒在肉类上的时候,可以消除掉那些令人不快的气味,所以胡椒的价值一跃而上。其实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唐朝时的宰相元载在被吵架时,也被搜出了八百石胡椒。
当时陆地上的胡椒贸易被阿拉伯商人所垄断,在威尼斯可以买到胡椒,但是价格昂贵得离谱。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了大航海时代的探索,这探索原本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新的航线,没想到,却发现了更大的世界。
1497年7月8日,葡萄牙贵族瓦斯科·达·伽马奉葡王之命,率领约170名船员、分乘4艘船,从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他在1498年4月到达肯尼亚的马林迪。在这里,遇到有经验的阿拉伯水手阿哈默德·伊本·马吉德。在他的领航下,沿着中国和阿拉伯海员早已熟悉的航线横渡印度洋,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次年9月,达·伽马率领满载香料、宝石的船队回到里斯本,受到奖赏和隆重欢迎。这次航行所得纯利为航行费用的60倍。
早期的殖民国家为了争夺海上资源,所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生怕被对方抢了先,一方面疯狂抢夺着殖民地的资源,给当地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痕;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国家的船只发放私掠许可证,允许他们打劫其他国家的商船,成为官方海盗。
但是这场运动并未给国家带来什么实质性的进步。大量的贵金属涌入国家,反而加速了通货膨胀,航海家暴富的同时却挤占了其他平民的资源。唯一的历史意义,便是进一步完善了世界地图,为人们带来了更广阔的世界。
《现代欧洲史(全6卷)》读后感(六):一部欧洲崛起的史诗巨著-《现代欧洲史》1-5卷书评
《现代欧洲史(全6卷)》读后感(七):非意图后果的变革
大体以公元1500年为界,世界历史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自此与原先那个古典诸文明并存的世界作别——先是部分地区的部分人,渐渐地全球几乎所有都跨入了“现代”。这一结果虽然人所共知,但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样的变化、这一切又是怎么会发生的,却至今没几个人能得清楚,不过,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这一变革的发源地是在欧洲,更确切地说是西欧。
尽管也有人声称这不过是欧洲人的运气较好(“他们能这样,只是因为碰巧发现了新大陆”),但在如此重大而复杂的历史现象面前,这样的看法所带来的疑问似乎比它能解释的问题更多。不必说,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为接受变革做好准备,那么就算有发现新大陆这样极具冲击性的事件发生,它是很难内在自发地生成一套创造变革内驱力的结构的,这就不能归结为“运气”。就此而言,现代的曙光最早出现在西欧这个欧亚大陆的偏僻角落,实非偶然。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或许是因为,在一个社会逐渐现代化之后,发生在其中的重大事件所导致的因果链条已变得太长太复杂,以至于根本无法穷尽所有的可能,就像在一口已有了一千种原料在起剧烈化学反应的坩埚里,谁也无法判断新加入一种化学物质会导致产生什么新的反应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行为完全可能导致他事先想像不到、乃至根本不想要的结果,这不是他意图好坏、道德高低的问题,而是他无法控制所有这些变化。正因此,在现代欧洲史上出现了许多始料未及、出乎意外,甚而根本事与愿违的事件,如果说“在1715年,没有一位先知能够预见未来的事件和发展”(本书第二卷p.453),那并不奇怪,这甚至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可以说,对当时的欧洲人而言,这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也不可控意外的时代。
当然,新发明和新思想往往也是双刃剑。由于其释放的力量难以料见,有时甚至无法控制,因而现代社会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就是弗兰肯斯坦隐喻——人所创造出来的某个威力巨大的新事物,最终脱离了控制,反过来伤害了创造它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科学获得极大发展的进步时代,人类感受到的却是幸福与恐惧并存。新技术威力太大、对普通人而言太陌生,而精英们的誓言一次次被证明为不可靠(比如宣称可控的核电站却还是出事了),以至于人们渐渐丧失了安全感;然而如果以此为由去踩刹车,那势必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发展的停滞,到头来仍必须维持某种“可控的开放”。
英国人常常爱说,他们是在“不经意间”得到大英帝国的(当然,他们后来也在不经意中失去了),这个看法值得认真对待。这种“无意中征服半个世界”的说辞有时隐含着某种克制的洋洋得意,并且正如Ronald Steel曾说过的,“不情愿这一主题是在殖民主义史中发现的最为普遍的解释之一”;不过确实,无论怎么谴责英国的殖民主义,但英国人从来没有一个想要建立帝国的清晰计划,甚至没想过派往东印度的一家特许经营公司,最终能成为印度的主人。这种顺势而为的政治观念恐怕也和英国人对市场经济的态度一致:遵从“无形之手”,用哈耶克的话来说,不要计划,而寻求“不经意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
当然,任何社会的新生事物往往都是在不经意间萌生的,就像火药也是中国人炼丹时搞出来的副产品,但问题在于:新事物的存续,无法仅靠人们偶发的善意,欧洲的特殊性,乃在于它的多元性使得这些新事物和意外结果很难被单一的力量阻止。欧洲在中世纪就已呈现极大的多样性,在社会政治构造上则是诸国林立、封建分层、政治与宗教的二元权威并存,这就确保了社会结构中有大量海绵状的“孔洞”,可以让那些不受待见的异端和创新有容身之处——不要说别的,连印刷书籍在刚诞生时都有许多人反对,但这无法阻止它在别处流行。从传统与进步力量的斗争中就可以看出,教会等保守势力“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也就是说,它们并非完全没有预见到新事物可能带来的威胁,但要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环境中阻止其发展却是不可能的。
因此,要回答为何这些变革发生在欧洲,还得从欧洲内在的驱动力去寻找答案:是什么使得欧洲具备一个不断生成变革能力的结构。这种变革的初始动力应该承认是来自欧洲社会内部,正如书中所阐明的,欧洲的海外贸易和扩张活动本身就是国内相应活动的延伸,只是对外扩张最终又反过来推动着内部发展模式的变革(第一卷p.61)。此外,社会的多元化与分权,使得社会力量的活跃成为可能,而印刷术带来的自由交流,又使得“一些之前不相关的技法和学科产生碰撞,并最终形成了新的东西,这在文艺复兴时期常有发生”(第一卷p.145)。新事物未必就此取代旧事物,有时还引发了经久不息的冲突,但由于权力分散之下没有一方能以彻底压倒告终,因而这一斗争过程最终使社会进一步丰富化了。
要概括欧洲五百年来的复杂变化,这显然是极难的事,即便是六卷本也未必能胜任。全书显然不把土耳其视为欧洲国家,倾向于低估它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也不大涉及欧洲对外的移民、扩张,似乎并未将之视为欧洲历史运动的驱动力之一。不过大体而言,在这套由美国诸多史家操刀的系列中,还是相当深入浅出地画出了这一宏大变迁的主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政治史之外,书中特别强调了新文化史的视角,更突出了宗教在现代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而这是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常常淡化乃至忽视的。
作为面向公众的读物,本书的许多章节常能简洁生动地刻画时代的主要特征,这即便对于深知那段历史的人而言也是不无启发的——这其中,给我本人印象最深的是第五卷中关于拿破仑三世、克里米亚战争及俾斯麦的外交策略,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俾斯麦的成功“大多得益于耐心和时机”,兼具灵活、敏锐与精明的特性使他几乎每一步都战胜对手,而他那节制的罕见品性则让他凡事留有余地,从而将德国的利益最大化;然而这套制度却只有他玩得转,他拒绝向下属授权,设计的国际关系又太过复杂,以至于他只能在坟墓里看着自己毛手毛脚的后继者将一切搞糟——或许这也是他本人不曾预料到的结果吧。这再次证明,即便是俾斯麦这样老练精到、掌控自如的政治家,如果不能设计一套可持续、有保证的制度,那么他的高超技能,最终只能证明是后继者的灾难:他们往往因无法模仿他而归于失败。
已刊2017-5-29《经济观察报》,标题改为《计划还是意外:近代文明为何发源欧洲?》
------------------------------------------------------------------------------------------------
勘误:
译文出自多人之手,可能未加统校,以致某些名词译法不一,如第二卷p.5:新教不仅没能出现可以与路德、温格利、卡尔文等人相提并论的神学家:此处“温格利”即Zwingli,通译“茨温利”(如第1卷,及本卷地图p.21)或“慈运理”,而“卡尔文”在下文称为“加尔文”(如p.7)。更有甚者,意大利的撒丁(王国/岛)出现了三种译法,第一卷地图页p.25:Sardinia萨丁尼亚王国:全书多译作“萨丁尼亚”,如p.183“萨丁尼亚岛(Sardinia)”;但第4册地图作“萨丁尼亚王国”;但第2册p.416作:“奥地利的萨尔迪纳(Sardina),第4册p.47“意属萨丁尼亚区(Sardinia)”当时也应是撒丁王国;第5册地图p.15图例上标撒丁王国,然而同页及地图p.13又作萨丁尼亚王国,p.291则提到意大利统一后,南方人憎恨“外地人”萨丁尼亚岛人,其实也应指原撒丁王国人(不仅限于撒丁岛)
第一卷
第二卷
初版前言p.10:由于宗教和文化的差异,奥斯曼的土耳其人和莫斯科人被其他欧洲国家孤立了:此处“莫斯科人”应指莫斯科公国的俄罗斯人,这样直译易于引起误会 初版前言p.13:[1559年哈布斯堡家族两大分支]统治的地盘加起来,相当于今天14个欧洲国家和3个北非国家:按,哈布斯堡家族未曾统治北非,此处疑有误 地图p.25:Holstein荷尔斯泰国:国=因 地图p.39:Azov亚述:亚速;“亚述”一般对译古代中东帝国Assyria p.19:意大利共有居民1100万人,是一片人口稠密的区域,人口数量几乎相当于西班牙的一半:似应是“几乎比西班牙多一半”,因为据p.16所言,西班牙三个部分的人口总和在800万左右,p.31又提到16世纪时法国人口“增至将近2000万,是西班牙人口的2倍”,也表明西班牙当时人口也只1000万左右 p.19:16世纪晚期,人口超过10万人的欧洲城市,每12个中,就有5个在意大利:事实上,当时超过10万人口的欧洲城市,总共就只有12个(有些学者估计只有10个),其中5个在意大利(罗马、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巴勒莫),故不应说是“每12个” p.23:每杜卡克重约3.56克:杜卡特 p.79:博伊尔(boyars):通译“波雅尔” p.97:鲁塞尼亚人(Rumanians):鲁塞尼亚人是Ruthenian,此系罗马尼亚人 p.100:这些外国国王缺少王室土地、预算、军队,以及西部王国的官僚机构:此处“西部王国”应指西欧民族国家 p.104:对16和17世纪俄罗斯人口的估算纯属猜测,但无论你认为是最低值400万,还是最高值1700百万:“百万”应为“万”,1700百万则是17亿人,现在俄罗斯人口也不到这个数字的1/12 p.129:瑞士吞并了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西部:瑞士=瑞典,p.435正确地作“瑞典的波美拉尼亚” p.271:在法国人民上缴的税费中,只有25%进了国库。而另外的75%消失在了税农、贪腐官员及王室债务的利息支付上:此处“税农”原文应是farmer,应译为“包税人” p.284:他们通过一系列叫作“克拉伦登代码”(Clarendon Code)的迫害法令:Code此处系指“法典” p.401:[路易十四]归还1679年至1681年吞并的卢森堡,洛林和部分阿尔萨斯地区承认威廉英国国王的地位:句意易产生歧义,应将“卢森堡”之后的逗号改顿号,并在“阿尔萨斯地区”之后加逗号,因为“承认威廉英国国王地位”的主语是路易十四,而非洛林和部分阿尔萨斯地区 p.416:英格兰和苏格兰于1707年成立议会联盟,组成了大不列颠王国(Kingdom of Great Britain),自此以后被称作英国:此处“英国”的原文疑是United Kingdom,从句意看宜直译为“联合王国” p.419:克恩滕州:克恩滕在当时是一个公国,直至1918年后才成为奥地利的一个州 p.421:从主河流域(Main River area):此处指的是“美因河”,法兰克福全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即因此得名
第三卷
地图p.19:“五大农场”关税区边界:按此是18世纪法国地图,此处“农场”原文“farm”,指包税区 地图p.19:Toulouse (to the Pope):图卢兹(属于教皇):译者理解错了地图上的标注,前页原图上图卢兹是朗格多克地区的城市,而to the Pope一词指向的是图上未标明的阿维尼翁地区 p.23:Ft. Dusquesne杜根堡:p.78又作“法属迪凯纳堡(French Fort Duquesne)” 地图p.27:Caucus MTS.考克斯山:高加索山脉 地图p.27:Manchuria满洲里:满洲 p.4:《一位爱国君主的观念》(The Idea of Patriot King, 1738):译文有歧义,此处并不指某一位君主,而是指“爱国主义国王”这一观念 p.11:路易开展了一场政治和文化的统一运动,他将之称为“忠于国王,贯彻法律,同一信仰”(“one king, one law, one faith”):宜直译为“一个国王,一部法律,一个信仰”,现意译与原意不尽相合 p.55:为与普鲁士结盟,英国向其提供了一笔高达60万英镑的援助金(这几乎相当于英国前一年全国税收的总额):英国全国税收总额才60万,数字低得不可思议,应是6000万,因“60 millions”而误。后文p.60也作“七年战争中资助普鲁士的60万英镑”,但同页又说七年战争时英国军费开支827万英镑仅占全国总收入的14%,则其总收入确实应是6000万英镑左右 p.77:[1762年俄国沙皇彼得三世]决定停战,归还普鲁士东部省份,同时放弃支持奥地利夺回西里西亚岛:应是“东普鲁士”,而“西里西亚”(Silesia)也是一个内陆地区,并非岛屿,译者可能将之与“西西里岛”(Sicilia)弄混了 p.78:法国迅速主动出击,在1757年至1758年间先后占领多个英属殖民地,从印第安(加尔各答)到地中海(米洛卡岛):前文谈到七年战争在北美的形势,故译者误以为India是“印第安”,其实七年战争的战场遍布全球,此处毫无疑问是指印度 p.79:蒙特卡姆将军路易斯-约瑟夫(General Louis-Joseph de Montcalm):蒙特卡姆是此人的姓氏,此处宜直译为“路易-约瑟夫·德·蒙特卡姆将军” p.109:在匈牙利、波兰和几个德意志州:此处“州”原文应是states,在当时语境下应指“邦国” p.204:与享受特许政策的公司进行合作的那些享有特权的商人同局外人(也被称为“闯入者”):此处“闯入者”应是interloper一词的直译,此处指“无执照营业者”,在英国史的语境中一般意译为“私商” p.220:[1830年]棉线的价格与18世纪70年代相比,下降了大约5个百分点:疑是下降到5% p.249:1784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1789年 p.252:澳大利亚博特尼湾殖民地区:Botany Bay通译为“植物学湾” p.279:如休谟、亚当·史密斯等大多数苏格兰启蒙时期的作家:Adam Smith通译“亚当·斯密”,如p.314 p.280:瑞士首都日内瓦:日内瓦不曾当过瑞士首都 p.327:根据官方定义:这里official的意思是“正式”而非“官方” p.328:麦逊共济会(Masonic lodge):所谓“Masonic lodge”只是共济会(Freemasonry)的基层组织单位,一般译作“共济会会所” p.331:波兰女爵(Duchess of Portland):波特兰女公爵,作为国名的“波兰”是Poland p.332:“全球性”源自一个概括性的词汇,即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一个游历世界的人不会仅仅认同本国的文化群体或政府,而会变成所谓的“世界公民”:此处“全球性”的原文疑是cosmopilitan而非globality,应如上文所译作“世界性”,这两个词在语义上不是一回事 p.338:达恩顿描绘了伦敦格拉布街(Grub Street)的形象,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后来将这种形象传播开来:Robert Darnton是现仍在世的美国学者,比蒲柏晚了两三百年,译者可能是误解了原文的从句,其本意或指“达恩顿描绘了那种后来被蒲柏传播开来的伦敦格拉布街形象” p.343:大学是自治的共有团体,几乎完全依赖全国性教堂的管理和赞助:此处church指“教会” p.345:[亚当斯密]将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描述为:疑此处“哈佛大学”应是“牛津大学”,因Oxford与Harvard相近而误。亚当斯密了解牛津、剑桥这两所大学,特别是牛津,但未闻他的生平与哈佛有何关联。同页下文“这两所大学要求所有教职工和学生信奉英国国家,并服从其教义”,应是“英国国教”,如是,那更证明应是牛津而非哈佛 p.388:萨克森主魏玛公爵:应即同页前文的“萨克森-魏玛公爵(Duck of Saxe-Weimer):Duke? p.401:数以千计的摩拉维亚教徒(Moravians),都重新登记为新教徒:摩拉维亚并非一个教派,而是一个地区,此处译作“摩拉维亚人”即可 p.457:彼得三世统治了俄罗斯11年:其实不到1年,此处应有误;下文“直接引发了莫斯科中部地区的农民大起义”也是指“俄国中部地区”
第四卷
地图p.13:Maine缅因,按在美国为缅因州,但在法国则通译为“马恩” 地图p.21:Rep. of Cracow克拉科共和国,到地图p.25译作“克拉科夫共和国”,是 p.3:在革命爆发前的八年间,法国的手工业和工业生产翻了两番,此外,它的殖民贸易增长了十倍:应是“八十年间”,参见第3册p.203 p.37: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被废黜的普鲁士国王,于1786那年继承腓特烈大帝的王位):腓特烈·威廉二世未被废黜,自1786年至其1797年去世均为普鲁士国王,此处说的“被废黜”,原文可能是“uncrowned”,亦可指“未正式加冕的” p.64:有了泰普·沙西(Tipu Sahib,1782-1799年在位)做同盟军,法国便能控制印度。要知道,沙西是当时很有势力的王子:此人其实是当时印度迈索尔王国的国王,“王子”的原文应是prince,指君主;Sahib一词通译“萨希卜”,原意是“大人、老爷”,并不是此人的姓氏 p.72:这一庆典被称为“上帝节”(the Festival of the Supreme Being),罗伯斯庇尔想借此开创一种新的公民宗教,以取代天主教:此处说得明白,这一节日是基于理性的自然哲学设想,Supreme Being不是天主教的“上帝”概念,此处宜直译为“最高存在节” p.83:19世纪90年代的“丑陋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丑陋”二字似为译者自加 p.111:建立了赛普丁修拉共和国(Septinsular Republic):Septinsular即拉丁语“七岛” p.185:美国在1850年之后的工业化进程也是相当惊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们的人均产值已经超过英国40%:从下一页表格看,1913年美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5307美元和5032美元,似未有40%这么大差距 p.189:即便在意大利1860年正式宣布统一之后:意大利正式完成统一要到1871年,此处可能是指1861年宣布建立意大利王国,则可能应作“1860年代” p.222:认为资本主义是造成社会隔绝和感情疏远的罪魁祸首:此处的“感情疏远”,与下文的“情感疏离”,疑原文都是alienation,这是特殊术语,宜译为“异化” p.230:在实际情况下,共|产|主义革命却集中爆发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而且在战争和殖民地统治的遗留问题的影响下,政治基础都受到了动摇:这一句颇难理解,疑是译者误解了原文从句,作者本意应指:爆发这些革命的多是在那些因战争或殖民地统治遗留问题而政治基础受动摇的国家 p.251:[斐迪南一世]恢复了葡萄牙贵族和教士的特权地位:此处所指是那不勒斯所在的两西西里王国,提到“葡萄牙贵族和教士”不合情理,疑因上一段谈到葡萄牙,故译者自行添加 p.251:很多反对斐迪南的声音都来自此前支持西班牙叛军的群体:从上下文,此处应指起义军,英文中rebellion可泛指反抗的叛军或起义军 p.287:[德国体操之父雅恩]他在体育界发起了名为“特纳”(Turner)的运动:“turner”一词在此意为“体育协会会员”或“体育家”,下文p.337提到他“组织过体操社(Turngemeinden)”,可见turner的含义 p.293:1815年的辉格党和多利两党还依旧处在土地贵族的控制中:前文和下文均作”托利” p.322:讽刺画家奥诺雷·杜米埃(Honoré Daumier,1808-1879)……把国王的头画得像一只梨:此句疑有误,下一页配图标示这位讽刺国王的画家系Charles Philipon,是 p.326:[1815年]当时比利时的人口比荷兰要多200万到350万:1815年荷兰人口是223万,比利时人口的估算则在360-410万之间,似不可能多350万这么多 p.340:在鲁尔山谷出现了深矿井:鲁尔地区因鲁尔河流经而得名,此处valley非指“山谷”,而应是“河谷”、“流域”之意 p.344:于是采用了奥地利皇帝的年号:年号=称号 p.357:新希腊王国的成立遭到了两名德意志亲王反对,最终,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之子奥托于1832年2月承认希腊独立,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此处指希腊独立后,从德意志王族中寻找人来担任国王,但屡遭拒绝,最后奥托才接受了王位,并非指“承认希腊独立” p.366:在亚历山大的兄弟中,康斯坦丁与其年龄最接近,当时正担任荷兰总督:康斯坦丁未曾担任荷兰总督,而应是波兰王国总督(Governor of Poland Kingdom) p.380:集中反对派对势力:反对派对=反对派 p.381:初期的温和派共和党人从激进派中得到了三个人的帮助:社会学家路易·勃朗(Louis Blanc):按,此人非社会学家,可能是译者将socialist(社会主义者)误认成了“sociologist”(社会学家) p.420-421:《渡过难关: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阶级家庭》(Weathering the Storm: Working-Class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Fertility Decline):原文中并无“家庭”,而漏译了末尾的“繁荣衰退” p.421:《成为民族的:一位读者》(Becoming National: A Reader):按,此处reader指“读本”,可译为《民族形成史读本》 p.421:安东尼·史密斯在《民族的种族起源》(The Ethnis Origins of Nations):Ethnis应系Ethnic之误,可译为“民族的族群起源”,“种族”则是“race” p.422:伊萨卡岛:此处是表明书籍的出版地点,应非希腊的伊萨卡岛(Ithaca Island),而是美国纽约州的同名城市,系康奈尔大学所在地
第五卷
第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