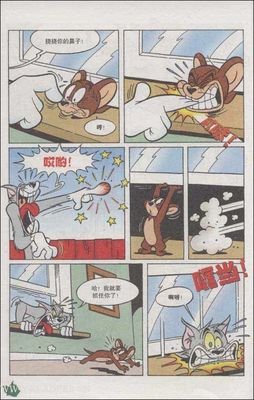《流动的房间》经典读后感有感
《流动的房间》是一本由薛忆沩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流动的房间》精选点评:
●一开始抱着随意的心态去读的时候 读不进去这本书 觉得好难懂 泡着脚认真看倒觉得蛮好理解了 因为这本书 我记住了一个厉害的作家 写法不像中国的作家 颠覆了我对中国作家的看法 我喜欢这种写法
●某几篇 读来时有障碍。停滞一段时间,然后畅快无比。#咳咳豆瓣阅读有售#
●翻一页就开胶了。 一脸懵……
●薛忆沩80年代后期就开始搞小说艺术写作,光是这点,我就有打五星的冲动。因为这不仅需要勇气,而且他很好地实现了自己内在的需要。
●重读依然感动,薛忆沩的文字营造了一种丰满的氛围,另人沉浸在时间的边界和雨后黄昏中的城市里,尤其是《流动的房间》和《两个人的车站》的开头。
●哐嘡 的场景感。
●还是出租车司机好。
●最喜欢深圳的阴谋
●视觉是有些特别,但是仪式感太强,玩弄文字。
●《出租车司机》。经历死亡时刻,才对生命的真实看见,也为自己带来新生的希望。这样的代价太大。不要因生存的需求而陷入被动和麻木的生活常规,看见生的活泼,真情的可贵,活出生机和爱,这样的觉悟,我相信可以通过一篇小说而得到。
《流动的房间》读后感(一):薛忆沩“中国的博尔赫斯”:文学即宗教,写作即献祭
一个阅读习惯,给读过的篇目取了新名字,以示自己读过了,内化了。《有人将死》取名《苦思冥想者》或《生·死·情》,开篇的第一个词语和全篇主人公就是“苦思冥想者”,很少见,故印象蛮深刻。《乳白色的阳光》取名《税务员》,向卡夫卡致敬;《公共澡堂》取名《推销员》,向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致敬;《那位最后到会的代表》取名《公务员》,就不致敬了;《走进爱丁堡的黄昏》取名《年轻的哲学家》,向卡夫卡《饥饿的艺术家》致敬。《手枪》取名《中国大陆留学生》。《已经从那场噩梦中惊醒》取名《鳏夫》,这样更简洁明了。《“深圳的阴谋”》取名《深圳女白领》。《两个人的车站》取名《小说作家》,向作者薛忆沩致谢;或取名《另一个自己》。《无关紧要的东西》取名《美丽的女人》;《我们最终的选择》取名《一个作家》;《“你肯定听不懂的故事”》取名《一片薄薄的膜》,如果这些新命名被采纳,是否能多买几本,不得而知。
最写实让人眼眶为之一热、心头为之一痛的当属《出租车司机》,这部短篇大概也是作家薛忆沩最广为人知的一部作品,深受评论者好评的力作,体现了作者薛忆沩接地气、讲好故事的一面。2019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建国70周年优秀文学作品精选·短篇小说卷》收录了这部短篇(胡迁《大象席地而坐》亦收录其中)。《流动的房间》其篇名成为本部短篇小说集名字,对于文字极其苛刻严格像极了宗教献祭般自我严苛的作者,可见其对这篇文章的看重,的确是最富于哲思、最“薛忆沩式”的代表作,薛忆沩被誉为“中国的博尔赫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流动的房间》读后感(二):20130203
我这人懒,看书也有点随遇而安,要靠点缘分。开始看薛忆沩也不知道是运气还是真有只看不见的手。那时候人很迷茫,以为继续读书是盘定局,我再彷徨再不愿意,生命也只有这一种可能性。逃避去图书馆时,在一二年一本《收获》上看到他的《异域的迷宫》,才给我开辟了另一种可能。
那时想,信号通路之类的科学问题我研究得再透彻,也不能解决我心里的疑问和困惑,何况还得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和时间,前方黑茫茫一片,焦躁不安。看了他的经历后才轻舒一口气。看原版《遗弃》的时候,冲击很大。他的文字和我的思想阅历相当吻合,且在平面和第三维度上都有延伸。 我在日记里写:
可我庆幸什么呢?我似乎不能从里面得到什么。庆幸这个人有同样经历甚至体会得深得多得多?不,这只让我挫败和惋惜。书出版的时候,他二十四。我现在二十三了,才看到他十五岁的开端。还差着时代赋予的经历。庆幸这个人用平实、尖锐、顺畅、异样的语言和令人惊叹的结构把这些经历和想法写下来了?可是这对我的寂寞并不能撼动分毫,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甚至带上更多的死气。我恐惧惊诧讶异喘不过气来,但在平静的表面下仍潜伏着惊涛骇浪式的兴奋、喜悦和颤栗。我欣赏句子与句子,段落与段落,似乎没有空隙能让我停一停。刚开始还大段大段摘抄,到后面我却放弃了。每一个细节都有他自身的完美,而所有这些细节又组成另一幅完美。可悲的是,当我为其曾经的文字欣喜悲伤时,此时的他,已经远离这段岁月,已经到了可以回顾、俯视从前的地方了吧。记忆无法复原曾经,未来无尽飘渺,现在才有最大可能。所以,不论何时何地,这种寂寞,这条不是路的路,也只能我自己承担。
一二年夏,薛忆沩包括《遗弃》在内的五本新书由上海三家出版社同时推出,这次的回归委实有点大手笔。我庆幸终于不必各处搜集他的关于“人”的叙述和关于“书”的叙述,也庆幸终于有了《遗弃》的纸质版。这一次,我把它放在床头,每天阅读一点。第二次阅读还是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快感,书页的空白处被我写满了文字。但是它带给我的愉悦仅局限于小篇幅、某个段落、某个句子,或是对他的前后呼应微微一笑,再没有整体浩瀚磅礴的心灵和情绪上的大冲击。当时我不清楚问题出在哪。是因为改写使得文字叙述更符合他现在的心态,而远离了他当初的冲动和激情?还是我的心情已趋于平和,时过境迁。
这一次阅读他重写的《流动的房间》,我终于找到点痕迹。我选的开局方式很不好,我不知道这样的选择会带给我怎样的“纠结”和“痛苦”。在阅读完第一篇《有人将死》后,我翻出200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老版本逐字逐句核对,想看看他到底做了哪些改动。我知道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他的语言已越来越成熟,节奏也把握得更好。但是对完前半部分之后,我开始纠结。老版更容易引发我的视觉想象,这样即便有语言上的问题也会被快速的阅读带过去;而且我喜欢的丰田汽车广告、头长得像马又像狮子的巨龙都在新版中退居幕后。这样的改变让我痛苦,不得不说我是个念旧的人,尤其在我还不太理解新版的意义时。我在阳台上踱步,心里被几千张蛛网密密团住,脑袋里的蜜蜂飞舞不停。
还好,我还是成功地解救了自己。我将新版《有人将死》从头到尾诵读一遍之后,终于释然于它给我造成的听觉和节奏上的享受。而且不得不说,主题更加突出。或许我的固执和幻觉正是带来这场“痛苦”的原因。第二天,就在去长沙的火车上,我再次体验到了阅读的快感,并且得到了视觉的回归。我合上第二篇,抬起头,仿佛看见一束乳白色的阳光透过车窗,停留在我的肩膀上。
至于这些新的体验,请允许我在新的篇章中述说。
《流动的房间》读后感(三):存在困境中的个体 (《北京青年报》)
文/ 冯新平
薛忆沩称他的一生终将是“苛求语言的祭品”。这种“苛求”促使他不断重写已获得好评的旧作。新版《流动的房间》就是他这种重写的范例。通过重写,薛忆沩的作品对存在困境中个体的同情显得更加强烈。
直面死亡时的恐惧不安和寻找自我中的孤独焦虑,是薛忆沩在《流动的房间》中呈现个体存在困境的两大母题。《有人将死》和《税务员》堪为表现前者的代表作。税务员在一场怪病后发现以往熟悉的世界突然变得陌生,死亡的问题如阴魂般盘旋于他的内心,人与世界的疏离感如大山般压在他的头顶,即便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马略面对这个终极性的问题都无以言对,反而是小店主质朴的话语启发了迷惘中的他,“人哪怕是死了也同样还会遭受陌生感的折磨”。这样的领悟是悲观和透彻的。而在小说的结尾,“税务员朝回家的方向走去”。这句话之前的税务员是悲观、回避和消极的,之后的税务员则显示出积极和抗争的悲剧精神。
与直面死亡而获得向死而生的生存方式不同,《有人将死》中心灵苦闷的“苦思冥想者”,从起初认为“死亡”是最重要的事情到最后意识到“生日快乐”才是重要的事情,这种转变呈现了死神笼罩下生命积极的意义。生之本质在于死,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恐惧。死亡并不是存在敞开的唯一可能,正如死亡可以照见存在,欢乐也同样可以使存在呈现。这两篇存在主义的好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存在主义。
结构颇为相似的《两个人的车站》和《流动的房间》在小说集中分量很重。摧毁一切的“时间”是两篇小说的隐含主题,而与之呼应的补充主题就是“记忆”。记忆既是这两篇小说的叙事结构方式也是主题呈现模式,孤独焦虑中的“我”在唤醒过去的同时隐含着当下的向度,回忆既是沉溺过去,找回过去的自己,更是建构此在,对此在的“我”的认定和救赎。但是,失去的时间真的能被找回吗?自我真的能够被确证吗?
在《两个人的车站》结尾处,“你”关于非意识记忆的碎片经验瞬间就把“我”依靠想象力构建的精彩回忆击得粉碎,所有的记忆都不能复活一个人活着时就已那样无名的内心世界,所有的往事都不能重现一个人在世时就变动不羁的完整自我,而《流动的房间》这篇作品本身则更为悲观:人生就是死亡的一个注脚,我们在欢笑时不知道欢笑只有此时,我们在悲伤时不知道悲伤也是一种奢侈。
这种生命及欲望与时间的冲突在《我们最终的选择》中有进一步的体现。此在的“我”一无所有,只能凭借过去发生的一切确定自我,但消逝的时间在记忆中变成了乌有的空间,曾经的“故乡”已是时光流逝中的幻象,往昔真切发生的一切变为回忆中的“浮光掠影”,这就是追寻自我的悖论和困境,尤其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时间成为永远的现在时而具有了空间性,而随着时间纵深感的消失,心理归趋和稳定感也就失去了,其表现就是孤独、焦虑,烦躁和抑郁。所以,《走进爱丁堡的黄昏》中的主人公崇拜古人的生活,向往灵魂可以自由徜徉的空间和心灵能够随意放飞的时间。这样的存在境界也是其他短篇主人公求而不得的。
同样,无论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和《你肯定听不懂的故事》中的“爱情”故事,还是《手枪》中的“侦探”迷宫,抑或《深圳的阴谋》里的“悬疑”叙述,在作者双面隐喻的叙事手法下都呈现了存在困境中个体的心理状态。
薛忆沩的小说着力于开掘普通人的人性深度,趋向于对人的意象性呈现,表现的是生命的荒诞与虚无,人生的孤独与无奈,人与世界和他人的疏离,观照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和对非人化处境的揭示和抗争。其多重叙事使得小说话语在表层结构上是对故事的陈述,但叙述效应却又把读者导向其隐喻性的深层结构和深邃的象征性空间,叙事艺术如此高超的作品中流露的是作者的悲悯和诚恳,我以为这是大器之象。
《流动的房间》读后感(四):薛忆沩:善设隐喻的写作者 (by 南方都市报)
《流动的房间》,有两个版本,一个是2006年的旧版,一个是2013年的新版。新版收入《公共澡堂》等十四篇中短篇小说,这十四篇都经作者重写。旧版之《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等九篇,没有收入新版,原因不明。本文所写,主要为新版所收作品。两相对照,旧版更尖锐,新版更委婉,可以看出,薛忆沩对“同情”的把持度,有了变化。无论新版还是旧版,篇篇皆堪称精品。有些意思的是,这些篇目在集结成书之前,就已在坊间流传,尤其是知识界,对其篇目的熟识,甚至超过对作者名字的熟识。如《流动的房间》、《出租车司机》、《公共澡堂》、《那位最后到会的代表》等篇目,还有长篇小说《遗弃》等,以口口相传的方式私下流传,人们乐意像猜谜一样去传阅薛忆沩的小说。这一读写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时段里,极为少见。中短篇小说的篇名,能让读者记住的,在当代,也不多见。在“创作”盛行、语言难以精致的今天,“牢记”其实就是对写作者最实在的认可。
《流动的房间》显示出薛忆沩驾驭故事及铺设隐喻的过人才华。或者这样说,在薛忆沩的小说里,故事及隐喻混为一体,故事即是隐喻,隐喻自成故事,两者的结合,有如天作之合。最妙的是,故事中的隐喻,隐喻中的故事,创造出独特的思想识见。可见,薛忆沩并未止步于写作的“游戏”,他的小说,有不凡的思想抱负,有对人性困境的深刻洞察。《有人将死》里的“重要事情”,是绝妙的隐喻。“重要事情”打乱了计划。由此可以问,计划的人生,究竟是热爱生命还是逃避生命呢?“重要事情”逼问出了“逃避”这一离经叛道的答案。《乳白色的阳光》通过税务员的陌生感揭示了人的永恒困境,陌生感是孤独感的世俗化身,“人哪怕是死了也同样还会遭受陌生感的折磨”,孤独的你与我,每时每刻,都在与最心爱者“分手”。《公共澡堂》的预言精准:公共澡堂营造出幻象,暖气升腾,看似有希望,但事实却无法让人取暖。暴力让私人生活“呼吸困难”,能赋予尊严的事物,彻底丧失。《那位最后到会的代表》里的“暴动”是神来之笔。作者以“暴动”暗喻性生活,这性生活显然“干预”了“开会”的程序。性的亢奋、暴躁、疲倦,是否正好挑战了权威?淫乱里,是否也有深深的恐惧?《走进爱丁堡的黄昏》的核心词是乡愁,在疑似辉煌的过去及未来之间,年轻的哲学家永远“走”在异乡的旅途中,是不是未来与进化把人都变成了异乡人?
薛忆沩善于把人心引向人迹罕至的悬崖绝壁,只有在那些绝境,至美才能与绝望真正相知相遇。《出租车司机》称得上是薛忆沩写得最“言情”、最世俗的小说。也许,《出租车司机》充满了内疚与忏悔之情,对妻子的,对孩子的,对父母的。死亡只是一种象征,在任何时候,你对他们的爱,都是“隔”着的,无论其爱是专制还是开明,都一样。《两个人的车站》所含的信息量巨大,小说里既有不同文明的互相爱慕与拒绝,又有个人灵魂的内在冲突。《流动的房间》构思精妙,思想最为宏博。作者以“城市”喻人生及人世。这座看不见的城市,有“非常复杂的记忆”,知识、物质、女人等等,各占据一部分记忆。欲望是挣脱宿命最生猛的力量,但时间———小说中时常出现的闹钟———按时敲响终结之声。对凡俗的溺爱,对黑暗的洞察,在这里,同等重要。信仰与理性,实乃使人高贵之法,而非救赎之法。这也是为什么,救赎之外,始终有灵魂冲突的存在。看到这一点,也能够理解,为什么神学不能统治人的精神世界,而文学永远在人的精神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向生的恐惧,终归需要“逃避”来承担。所以,人极度贪恋世俗生活,家、乡愁、婚姻、爱情、亲情、友情、美貌、书本、身体,能抓住什么就是什么。这样的贪恋,在时间里变得虚幻的贪恋,值得同情。写世俗人生,极为细腻,苦思冥想,去到极致,很少有薛忆沩这样的作者,能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运笔自如———小说出世越深入世越深,既懂得享乐生活的难,又懂得沉思生活的好。
薛忆沩看似远离祖国,却最知她心,他不是看不到她的祸福前程。但如果你执着于挖掘隐藏在小说中的那些历史与现实,那你就中了薛忆沩的圈套。历史与现实,即使分量极重,在薛忆沩这里,也只是走向“终极”的过程,他无意审判孰是孰非。在禁忌为核的语境里,隐喻无疑是表达“历史”的最高明办法。愤怒的写作者,执着于社会与现实的隐喻,只有聪明的写作者,才能越过社会与现实的障碍,看到人性中那些值得同情的罪恶及其苦难。薛忆沩,是聪明的小说家。以生与死搭建生命的故事,最是精彩,读薛忆沩的小说,有如打探语言与知识、历史与现实、思想与灵魂的神秘城堡,劳心伤神,但个中的思维乐趣,却又无穷无尽。
本文作者:胡传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