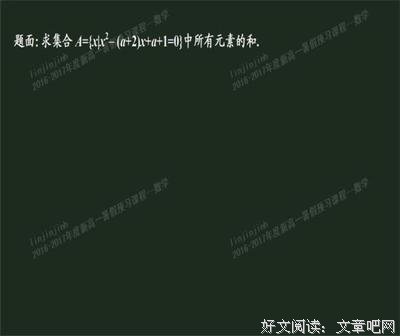埃及的革命考古學读后感精选
《埃及的革命考古學》是一本由何偉(Peter Hessler)著作,八旗文化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NTD 600,页数:2020-1-2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埃及的革命考古學》精选点评:
●没想到读的时候最无趣的就是讲那些政治人物的章节,像一篇篇时政报道。这也说明了对于任何国家的人来说,政治人物毫无任何魅力而言,真正有魅力的人是那些学会在垃圾堆中寻找生活、担忧自己同志身份活生生、具体而微的人。
●何伟让阿拉伯之春不为人知的历史活了过来,以别具匠心的方式,将他对开罗岁月的回忆与埃及百姓私密的生活交织在一起。
●还是熟悉的何伟,只可惜我对埃及不是太感兴趣
●语言、汽车、小人物,还是熟悉的配方,但是读不腻的是他永远能把这些底层人物写得淋漓尽致,在一个充满混乱的环境中,我们却分明能感受到每个人充满了生命力,你会在合上书的那一刻,希望不管是同性恋翻译、捡垃圾的,他们一定都要好好的生活着,因为何伟总有办法让你对“人”产生感情
●何伟在埃及与在中国一样,先是从学习埃及阿语开始,随着他精妙的叙述,你会发现语言是打开一个民族心灵的钥匙。 何伟这本书从几千年前法老的考古分析一直写到今天埃及各色人等的生活现状,力求探寻埃及的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让读者感受到埃及在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艰难与受到历史桎梏的宿命般的悲哀。他语言平易,力求客观、克制,却又饱含感情,在埃及最后离开前与垃圾收集者萨伊德一家告别,看得出他对这块土地与人民有了一种家国般情怀,他既迷茫又有一点淡淡的希望。 我记住了他两个双胞胎女儿的名字,一个叫爱丽儿,一个叫娜塔莎。
●熟悉的何伟三式:从身边的底层人展开人际网,学习语言时引申到国民性和文化,开车寻路扩大素材范围。印象最深的反而是他偶尔提到的家庭生活,跟太太张彤禾精神的高度契合,两人都从年轻时怀着对世界的探索和好奇,人到中年仍然期待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学一门新的语言;本来也一直不在乎形式没有结婚,为了签证不被刁难才在出发前一天领了证,在埃及的暴乱动荡中一起抚养双胞胎女儿,并在家里用相邻的两个房间作为各自的办公室,各自写关于埃及的书。神仙眷侣莫过如是。
《埃及的革命考古學》读后感(一):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埃及变革
何伟在中国生活了多年,又在埃及生活了五年,在他的笔下常常出现对两个国家的对比,这也是这本书吸引我之处。
埃及和中国都是古老又年轻的国家,都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都在二十世纪才开始现代化进程,但命运却如此不同,原因何在?
何伟在埃及五年经历了两场革命,推翻穆巴拉克的阿拉伯之春和推翻民选总统的军人干政。革命没有给埃及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有的似乎只有街头流血和走马灯似的政权更替,西方设想的“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
埃及空有几千万25岁以下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地处欧亚非三洲焦点的优越地理位置,而制造业占比却只有10%几(对比中国占30%几),造成大量失业人口和革命火种。这似乎不是一次民主选举所能改变的,相反民主化带来社会混乱和经济倒退,反而让有些埃及人开始怀念穆巴拉克那稳定的岁月了。
埃及的妇女结婚后必须放弃工作,使得埃及工业园里的中国公司招不到熟练女工(女工做几年赚够嫁妆就不做了),男工又懒惰,不能承受三班倒运转,效率较中国工厂低很多。没有男女平权的社会革命,埃及想通过发展制造业提高GDP,创造现代化国家难上加难。
《埃及的革命考古學》读后感(二):法老靜默凝望
前幾年聽聞何偉寫中國寫得好,早就想讀一讀,可惜直到現在三部曲一部都沒有機會讀到,只讀過《奇石》。即便《奇石》零零散散,還是不影響我欣賞他的文筆。話説回來,當時查到他去了埃及,以爲應該不會再寫中國了,還感到遺憾,現在他去川大教書,於情於理都還會再寫中國。
圍著密不透風的尼卡布,不能出去工作意味著她們沒有經濟能力、必須成爲男性的附庸,長期待在家裏成爲生育機器,極少接受教育甚至以不識字爲榮,還要處處要保持男女的差異。作者舉的破產工業園例子就很典型:只有未婚女性才會去工廠工作,而且她們不會在工廠——家以外的地方過夜,意味著每天要在交通惡劣的路上浪費數小時的時間,也意味著工廠不能在夜晚運作;而男性往往過於懶惰,不能勝任工作且難以管理。雖然中國婦女地位在東亞來説已經算高的了,但是我們仍然能發掘更大的進步空間,如果說追求男女平等是一場八百米長跑而中國已經跑到了四百米,那埃及應該算是剛從起跑綫出發不久,甚至還想放棄比賽。女性狀況如此,更別説恐同、反猶導致很多人逃離埃及,前往歐洲或者新大陸,只爲了過上平靜的生活。
埃及老師會叫學生把歷史課本的某幾頁撕掉只是因爲他們不想講,這個國家到處都是沒有什麽作爲的便衣警察,精英階層寧願將孩子送往外語學校,喝酒的穆斯林不少——薩伊德總能在垃圾堆裏翻出酒瓶子,他們沒有表面上顯示出來那麽虔誠,含糊不清的法律加上臃腫的執法系統,法治可謂說聊勝於無,透露著民族主義的陰謀論:美國資助、以色列顛覆。最值得思考的是中國商人的例子,他們開了一個簡陋的塑料瓶子回收工廠,不僅是當地第一個有環保意義的企業,還帶動了就業——收瓶子的孩童、運瓶子的司機、流水綫的工人,而西方數以億計的金錢援助流入政府口袋后像是憑空消失。
這個國家離我們很遠,文化差異很大,但是不經意的一瞥感覺很相似,細看又有不同。
何偉在川大教的是非虛構寫作,希望以後能有機會聽一聽。
《埃及的革命考古學》读后感(三):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有意义的选举要以一定水准的政治组织为前提。关键不在于举行选举,而在于建立政治组织。在许多现代化中国家,选举只会有助于增加捣乱分子和反动势力的力量,并且会毁坏公共权威的结构。”
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写下的这段话,为发生在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做出了完美诠释。这场不流血的革命以民主的胜利为头阵,以军事政变为后续,最终依旧让埃及陷于混乱与无序中。由此看来,民主政体并非天然优异于极权政体。倘若没有相应的政治秩序为基础,民主政体并不保证和平与发展。
“政治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是否能够动员新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摆在埃及人民面前的问题就是,民主选举没有完整有效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竞选人仅仅有美好的意向,没有提出能够落地的措施,而且也无法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政治,于是革命流产了。
这提醒我们,任何极权政体倘使想转变为更为合理的民主政体,切不可急于求成。对于埃及来说,摆脱独裁统治,进行民主选举自然是好事,但对于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了吗?或许革命引发的阵痛需要时间来缓和。至少他们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至于前路如何,就端看时局的变化了。这如同一场豪赌,胜负听天由命。
事实证明,民主政体在社会管理上并不比独裁政体更具有优势,甚至因为社会制度的限制,民主政体比极权政体更容易引来混乱。此次新冠疫情的爆发,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突发社会事件具有的优势,原因就在于极权政体有更加完备的政治秩序,从而能让社会管理更高效,虽然这建立在违背人性的基础上。
相反,欧美自由主义国家应对此次疫情的无力,也有其制度原因。相较而言,民主政体比极权政体在“生命政治”的治理方面天然具有弱势,民主政体无法进行全面集中的地毯式规训,从而需要从其他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民主政体有其绝对优势,只是这种优势的发挥也要建立在合理有序的政治秩序之上。
如此,亨廷顿才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以这句话为首展开全书的论述——“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这两种政治之间的差异,要比民主制和独裁制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政治统治程度的低效,是摆在埃及人民面前的致命困境。
如果中国想实行民主选举,必须提前思考这个问题。突然的革命是否会遭受“阿拉伯之春”同样的问题,到时社会便不是进步,而是倒退。因为没有相应的政治秩序作为辅助,社会必然陷入无序,经济必然遭遇阻滞,这对于有十三亿人口的超级大国来说尤为严峻。
《埃及的革命考古学》对于我们,不只是一段革命历史纪录或民俗风景画,更像一面镜子。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埃及上下六千年的历史,当下埃及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境况,同样重要的是:民主不可一蹴而就。想想台湾民主政治的混乱现状吧,跳梁小丑陆续登台,执政如同儿戏。
《埃及的革命考古學》读后感(四):一本埃及的当代民族志
如真主所愿,在我花了将近四天的时间后,我终于读完了这本台版的何伟的新书《埃及的革命考古学》,这本书的英文名是The Buried,书中指一处埃及埃及古迹“陪葬”。
这是何伟的出版的第五本书,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原因,我只觉得只有很少一部分我在《奇石》中看过。我不免想对比下书中的人物。
萨伊德一家如《寻路中国》中魏子淇一家,相似点是不知道是不是结识何伟的缘故,家庭都跟之前有所不同,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一个是思想上,一个是经济上。这里我也不免觉得魏夫和萨伊德夫人有那么几分相似,她们也想自己做点什么,决定些什么,却受制于自己的丈夫。作者“开箱”萨伊德孩子的小学课本,一如他翻开魏子淇孩子的小学课本和日常行为规范。
马努的篇幅虽不如萨伊德一家,却惊心动魄也格外让人揪心,一如《甲骨文》中西域人一样,巧合的是,他们最后都通过寻求庇护与移民完成了身份转换与对自己的救赎。
而那些上埃及的遗迹彷佛中国的防御工程——长城,不同的是,这些遗迹不是并不是防御工事,或许是王权,也或许是循环与永恒时间的象征。作者也经常往返于这些工事与首都之间。今天,或许这些工事赋予这个国家的意义都已经和远古不同了。
阿语学院的两位老师也和涪陵师专的两位中文老师一样,可能有时候会和何伟意见向左,这也让何伟迅速地了解当地。阿语笔记本如同《江城》中的中文笔记本一样,记录着这个国家的教育者最想让人了解什么。看到书的最后,那些毫无意义的阿语词汇的突然出现,又和那些龟甲上的甲骨文字一样,连接着过去。
这个蜘蛛网大楼也和那幢老北京的四合院一样巧合,后者是赵老先生和梦家的联系,和北京城的联系,后者是和从埃及逃离的犹太人阿尔伯特的联系,也是阿尔伯特和他在埃及那段时间的联系。
上埃及的Selection和《寻》中的那次扣人心弦的Selection一样,让人觉得像似看了好多的集电视剧。
何伟用近似的考察方式给读者呈现了两个国家这样或者那样的区别。
我最近看了《穿越百年中东》,《为了萨马》,看这些作品期间,恰好看到了2月25日穆巴拉克逝世的新闻,又得知穆尔西已经于去年暴毙于一场庭审。又看完这书,真是令人唏嘘不已。加上之前看到的《乐园之桥》以及《阿拉伯的劳伦斯》,算下来看过的中东作品也有五部了。
他们分别从中国人、殖民者、反对者、观察者和参与者与叙述者的角度分析了中东的现状,每个人的角度不同,每个人最终的落脚点也就不同。
何伟总是从细微处出发,令人见微知著,他的观察点与中国人不尽相同,他没像中国作者那样分析木埃及留马克的传统,也少分析两任总统上、下的因果。而他把目光锁定在了那些几乎永恒的东西,女性和年轻人没什么社会权利的体系。
这体系似乎数千年来在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怎么改变过。
这本书确实是一本当代埃及的考古人类学与宗教人类学的民族志,它挖掘了当代考古团队和远古盗墓者的关系,中国人与埃及人的关系,权利中心与外围的关系,埃及似乎恰好处于王铭铭所讲“三圈理论”的“中间圈”。以及当代与远古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今天复杂的埃及。
何伟看上去似乎却有民族学家打算“改造”一类人的想法,我们无法揣摩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但确实性别平等、性向平等无论在哪里却都应该做到。
何伟非虚构戛然而止的写作手法真是引人入胜,让人难以自拔。总觉得故事应该是to be continued.
这是我啃的最辛苦的一本何伟的书,台版的翻译确实比起李雪顺的翻译差了很多。李雪顺翻译的书我基本上两天左右的上班时间都能读完,即网络译者翻译的《甲骨文》我也读得很快。这也是我第一次读完一整本台版书籍,他竖向排版,繁体印刷,中国台湾的繁体字有不少在内地看来算是异体字。我又要不断地查字典推测这本书是什么字。译者还会用些内地几乎不会用到的成语。
再次感谢何伟为我们带了这么精彩的非虚构作品,期待他有更好的作品,如果真主允许的话。
《埃及的革命考古學》读后感(五):循环与永恒的永恒
何伟离开中国之前,我曾经见过他。当时是那本Country Driving的分享,那是五六月份的光景,初夏黄浦江传来阵阵汽笛声,一个宁静美好的夜晚,他分享着他当时在东部沿海驾车采访的故事,我也是在那次有些意外地得知了他即将前往埃及,后来几个月后他便动身前往了,在纽约客发表那篇Go West之后。。由于是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因此特别关注他后来在纽约客上的埃及故事。后来也发现,除了时政类的速写报道,何伟并不急于发表自己的文章,很多后来在纽约客读到的故事,都是一两年前的故事,这种沉淀后的时间差给阅读带来一种别样愉快的体验。
何伟到了埃及之后写了好多封Letter from Cairo,但由于阿拉伯之春的早期我对穆斯林兄弟会、埃及政治体系这些实在是不够了解,感觉也比较零散,加上后来的总统更替太快,政变、示威的频繁,让我也没有能够跟上他的报道节奏(其实更多是由于我对阿语地区地缘政治的不熟悉所致),也倒是这几年在纽约客上写的捡垃圾的Sayyid,同志翻译Manu还有猫咪Morsi的文章深得我心,而这些恰好是埃及普通人和他生活的日常故事。去年在纽约客上得知这本书出版后第一时间就买了,但确是拖拉了几个月,直到春节疫情的缘故,才有大量专注的时间把书反复看了好几遍。
The Buried在书里面其实被指的是一片被埋葬的考古区域,台湾译本翻译成“陪葬”,但我觉得这一点值得商榷(不晓得何伟自己是否喜欢这样翻译),我自己更喜欢翻译成《被埋藏的:埃及革命考古》,因为“被埋藏的”不仅有未曾发现的尘封历史,还有埃及普通人在革命浪潮里的生活。毫无意外的,正如书名一样,故事由一条在阿拜多斯的考古挖掘线索开始,贯穿着这几年埃及的革命变化,加上Sayyid、Manu、Riffat(何伟的阿拉伯语老师)的三条支线共同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叙述载体,中间还有零星穿插拜访在埃及的中国商人以及中埃工业园的故事。主线的考古挖掘有好几个研究机构的人,革命政治线索也采访国会议员、司法机构、政治人物等等。政治人物线里面我喜欢的是何伟抛出问题的直白。
捡垃圾的Sayyid支线的是我最喜欢的。因为他开朗、幽默和快意是埃及老百姓让人喜欢的一面,由他在H Freedom Kiosk的见闻和捡到的垃圾,带出了这一片居住区域的人们的故事以及所处的家庭,交织出生动的埃及生活画面,描述了当下埃及革命浪潮下的人民。同时Sayyid的家庭故事和婚姻矛盾,中间又体现出了埃及人的宗教观念和家庭组织,以及对教育后代子女的观念,中间Sayyid的絮絮叨叨和唯唯诺诺,更让我像何伟一样为他担心。Sayyid在书中代表的其实是传统的底层埃及人。
同志翻译的Manu支线,让我看到了全球化洗礼浪潮下一个埃及同性恋对自己追求认同最后勇敢迈出行动的过程,他的冷静、坚毅让我刮目相看,被警察逮捕后回到Port Said(塞得港)和父亲出柜的故事让我落泪,他年少时遇到的朋友、亲人分道扬镳又让我为他感到未知未来和只身上路的孤独。他跟着何伟拜访考古遗迹、采访政治人物和穆斯林兄弟会,Manu的故事结束在了一堂德语课,未来充满无尽想象。(Manu的故事何伟还写过一篇A Gay and A Thief发表在2018年的纽约客)
阿语老师Riffat的支线,是语言学和当下埃及政治精妙结合的部分。我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埃及阿语和传统阿语是不一样的,埃及阿语的很多地方又是没有书面语的形式,因此很难表达下来。所以某部分的阿语词汇是没有程度之分,我累了、我病了、我非常不舒服在埃及阿语中是同一个词汇。何伟的阿语老师是喜欢用当下的时政进行备课的一位老师,因此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很多阿语词汇。在此中,他也描述了学习中文、埃及阿语的经历和教材的不同。结合到我最近读的《东方主义》一书,我也才了解到其实“阿拉伯语”“中东”这些概念是十分的狭隘和局限。尤其是书中写的科普特人Coptic和埃及犹太人的描写,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对埃及的了解是有多么狭隘。Riffat最后的离去让何伟一家人感到难以释怀,我当时读到也有点意外和可惜,Riffat的阿语词汇是基本上是串起每一个章节的线索。这三条支线,何伟都描述了他们的政治观点,矛盾而又爱国的Riffat、暧昧而纠缠的Manu、无条件信任的Sayyid,在阿拉伯之春的政治浪潮下,小人物的想法被他一一记录下来。
他者叙述的历史概念是书中反复呈现的。埃及的考古挖掘工作经常是外国研究机构主导,是别人书写的历史,也曾有殖民的意味,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埃及一些城市的建设,还体现在学者对埃及历史编年体的记录上。不同于埃及,中国人一直在书写自己的历史,何伟对中国人实用主义的看法倒是贯穿其中。外人建设的城市、外人写的历史、他者的时间、埃及的永恒,何伟以他者的角度观察到卖女士内衣的浙江商人与穆斯林的互动是里面非常有趣的场景,也是观察中国和埃及两种文明的互动。其中中国商人因为看到没有塑料回收就自己修建了一条塑料回收生产线,还有那幕穆尔西受审时碰到的那位中国记者,他们的叙述都体现了当下中国在时代变迁中的姿态。中国人不关心、不了解就一定是不好的吗?中国人只关心你需要什么、他们可以做什么,他们不喜欢干涉别人的文化、政治体系,这一方面来说,中庸之道其实就很pragmatism,扯远了说其实里面埃及民众对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些感受很像现在一部分中国人对美国的感受一样,觉得一切的事情都有美国在背后撑腰(然而没有实际的证据)。何伟没有写什么价值判断,但我感觉得到他对埃及这一文明足够的尊重和客观,这种抽离感未必是为了讨好来自不同背景的读者,但他的叙事角度很好,能够来自不同语言文化的人都能够对这样的场景进行反思。
我想到了去年拜访柏林新博物馆是一个下午,没什么人,初春的柏林莺飞草长。在一家中国餐馆吃过午饭之后,我在闲静的博物馆里见到了娜芙蒂蒂的胸像,一束柔和的白光倾斜而下,照在娜芙蒂蒂的脸上,每一个到达这处展厅的人都放慢了脚步,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看着这座胸像。何伟的这本书,为我去年柏林之旅画上了最美的句号,看完这本书,我的柏林之旅才正式结束,那次见到娜芙蒂蒂的胸像,便仿佛是为读这本书而准备的一样。也如同他在埃及居住的蜘蛛网大楼曾经的住户、曾经玩耍的双胞胎,再到几十年后何伟的埃及之旅一样,很多时间的相遇是缘分,这本《被埋葬的:埃及革命考古》意犹未尽而有充满希望地结束了。
合上这本书,那个充满希望而富有力量的结尾让我突然意识到,何伟书里写的所有埃及政治人物都是云烟,故事的主角其实是那三位埃及人。书名“革命考古”欺骗了我,其实上“被埋葬的”是这个埃及这个国家不被他人理解的历史和每个人的生活。埃及人民刚毅的精神和坚强而充满智慧的人性,便是埃及留存的内在价值,比永恒不变的考古遗迹更加隽永、比动荡激情的革命更显珍贵。那些温暖人心的故事,以及没有收录其中而在纽约客写过的他在埃及养的那只与埃及第一任民选总统穆尔西同名的埃及猫Morsi,才是埃及故事里真正的永恒。
也是在这里,一瞬间五、六年的光阴飞过,我读懂了埃及阿语里的永恒之意。
2020年3月1日,写于香港
——————————————————————————
记后:我很感谢何伟,我第一次看他的书是2007年读大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这位优秀的纽约客驻华记者,他的River Town是我看的第一本英文原版书,当时他还少为人知,那本书上面记满了笔记和生词,而纽约客后来也成为了一本我读了十多年的杂志。何伟离开中国去到埃及后,我的人生也有了新的经历。我感谢他和他的作品,在人生道路上给我的激励,深深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