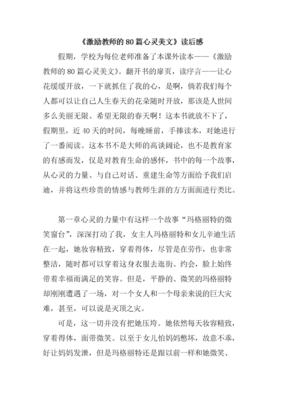《万智有灵》的读后感大全
《万智有灵》是一本由(荷) 弗兰斯·德·瓦尔著作,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450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19-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你觉得哪些动物拥有智能?很多动物我们都不会和“智能”联系在一起,比如乌鸦、鹦鹉、浣熊,还有章鱼。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我们不要光问动物是否有智能,更应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聪明到足够了解别的动物有多聪明吗? 章鱼其实很聪明,它知道怎么拧开罐头瓶子的盖子。但是一开始科学家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一个透明的罐头瓶子,里面放一只小龙虾,章鱼却什么都不会做。是那只章鱼笨,还是它没胃口?都不是,只是因为章鱼不依靠视觉来捕猎,而是靠触觉和化学信息。如果给罐头瓶子外面涂上小龙虾的分泌物,章鱼能闻到气味,它就会很快开罐子了。科学家掉进了以自我为中心的陷阱,人类主要依靠视觉来获取信息,就天然认为别的动物也是。要打破“动物不智能”的刻板印象,其实是要打破人类以自我为中心这种幻觉,背后个神奇的动物世界
●动物的智能永远无法和人的智能相比
●得到APP每天听本书分享:首先,传统的研究方法是有缺陷的,或者最少说是不完备的。他们都认为动物没有智能。而这些观点,已经被许多研究结果推翻了。然后,德·瓦尔向我们展示了许多动物的行为,这些行为只有建立在动物有智能的基础上才说得通。那些人类似乎独一无二的能力,其实并非人类所独有。最后,德·瓦尔讲到了智能的演化。既然地球上的哺乳动物都来自于同样的祖先,那么在演化过程中出现相似的能力也就是顺理成章的。这种相似不仅存在于身体上,也同样存在与头脑中。智能的演化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没有根本上的不同。这些观点和事实,打破的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偏见。我们曾经宣称自己是万物之灵,是地球这颗不起眼的小小行星上的唯一智慧生物。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万智有灵。
●想要打破“动物不智能”的刻板印象,其实是要打破人类以自我为中心这种幻觉,然后你才会发现,背后是一个神奇的动物世界
●每天听本书
●认识科学
●我们所观测到的并非自然本身,而是自然根据我们的探索方法所呈现出来的现象。
《万智有灵》读后感(一):关于演化心理学、科研方法以及非人类中心主义
阅读的初衷:自去年读了戴蒙德的《枪炮、细菌与钢铁》(GGS)以来,对从演化的视角来理解人类有浓厚的兴趣。最近看了北大顾红雅老师的《生物演化》课程,一下子又打开了对很多物种的认知。再加上近来在读《认知心理学》教材,对认知也非常有兴趣。所以我想这是一本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来介绍动物智能或者心智的书,想必是有趣的,会有很多让我惊喜的小知识。
从这个目的来说,完全符合预期,de Waat作为动物学家提供了大量基于动物研究的案列分享,从章鱼奇特的神经系统、鸦类展现的客体永久性、北方造纸胡峰具有辨认同类的脸的能力、黑猩猩的奉从主义、人类与鲸鱼和海豚的合作等等。在呈现这些研究结果的同时,作者还就研究方法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这一点很有收获,深刻体会到科学的精神是怀疑和严谨,以及非常重要的:科学在人之下。“作为科学家,方法论便是我们的一切。”其中重点批判了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强调对所研究的物种要有真正全面的了解(关注某一生物的周遭世界,即以其自我为中心的主观世界),并且设计适合不同物种的实验去研究。
在阅读的过程中,除了惊叹于不同生物的颇为奇特的种种技能外,也是一个不断挑战“人类中心主义”的过程。设计并使用工具的能力、心理时间旅行、自知感等在针对不同物种的研究中被逐渐证实。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之前想当然地认为人在某种意义上是独特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促使我去重新思考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这种全新的视角让我更加理解人本身即意味着局限,谦卑的意义,以及对不同生命怀有更多敬畏。此外,从演化的角度来看认知,很容易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演化具有连续性,这一点也适用于对认知的理解。心智能力是演化的产物,不同的物种演化出了和人类所使用的认知能力不同的能力。这些以非常相似或截然不同的方式存在的能力往往都是适应性的产物。
此外,阅读的过程中也让我对合作和联盟的重要性进行重新审视。如果从自然中不同物种的生存策略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关系、政治、等级制度,那么简单来说,这些都是适应性的产物。
《万智有灵》读后感(二):2016年“美国豆瓣”Goodereads年度最佳推荐图书《万智有灵》
《万智有灵:超出想象的动物智慧》一上市就入选了2016年“美国豆瓣”Goodereads年度最佳书单, 被评为《纽约时报》畅销书之一 。作者弗郎斯•德瓦尔被《时代》周刊评选为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也被《发现》杂志评为最伟大的头脑之一。
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弗郎斯•德瓦尔上图中的男子就是弗郎斯•德瓦尔,以及《万智有灵:超出想象的动物智慧》英文版。这位美国荷兰裔动物行为学家和灵长动物学家,超过一半的人生都奉献给了动物世界。他的动物行为学研究不只是在研究动物的行为,以及他们之所以为什么是动物,同时也是在反问我们自己:“人类为什么是人?”
他的第一本畅销书《黑猩猩的政治》将黑猩猩政治斗争中的钻营及谋划与人类政客的这些行为作了比较。从那以后,德瓦尔便一直将黑猩猩与人类的行为进行对比。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了二十多种语言,也使他成为了世界上最受瞩目的生物学家之一。他的这本新书《万智有灵:超出想象的动物智慧》同样再次挑战了人类对于自身独特性的根基。
2016年Goodreads读者选择奖书单
在2016年, 美国Goodreads网站发起的年度【读者选择奖】(Goodreads Choice Awards)评选中,由350万读者票选,每个图书类别仅设一个获奖名额,最终选出20本必读好书。《万智有灵:超出想象的动物智慧》进入了20本必读好书名单中,并获得了最佳科技类作品。
那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呢?这是一本颠覆你所有对动物和人类智能认知的书。当人类在考察动物的认知时,常常采用人类的视觉,从而低估了动物大脑的潜力。我们一起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在这个猫咪行为学研究中,研究人员将家猫放在一个小笼子里。猫会在笼子里走来走去,不耐烦地喵喵叫,并同时磨蹭笼子的内壁。这样磨蹭的时候,它们会碰巧蹭开笼子的门闩,于是得以走出笼子,并吃掉笼子附近的鱼肉。一只猫经历过的实验次数越多,它逃出笼子的速度也就越快。所有受试的猫都表现出了磨蹭行为,其行为模式一模一样。研究人员对此印象深刻,认为这些猫为了得到食物奖赏而学会了这种行为。
几十年后,美国心理学家布鲁斯·穆尔(Bruce Moore)和苏珊·斯塔特德(Susan Stuttard)重复了这一研究。但是他们发现猫的这种行为并不特殊——这是在所有的猫科动物,从家猫到老虎中都很常见的“伸头”行为,用于问候和求偶。它们会把头或侧面在它们喜欢的对象身上蹭来蹭去。如果它们无法接触到自己喜欢的对象,那么它们会转而磨蹭无生命的物体,比如桌腿。要让猫做出这一行为并不需要食物奖赏,唯一需要的是有对猫友善的人在场。当笼子里的猫看到人类观察者时,每只猫都会在门闩上磨蹭自己的头、侧面和尾巴,然后逃出笼子。这根本不需要训练。
这给我们上了一课:在对任何动物进行测试之前,科学家需要先了解该动物的典型行为。毋庸置疑,条件反射确有其作用,但早期的研究者们完全忽视了一项关键的信息:他们没有像洛伦茨所建议的那样考虑整个生物。动物有许多非条件反射行为,还有一些行为是天然形成的,其物种中的所有个体都具备。奖励和惩罚可能会影响这些行为,但并非这些行为的成因。在上述实验中,所有猫都做出了同样的反应,其原因并非操作性条件反射,而是猫科动物天然的交流方式。
书中举出了很多例子,不止包括我们熟悉的猫咪,狗狗,大猩猩、猴子,还包括大象、海豚等哺乳动物,还有鸟类,爬行动物,甚至是属于无脊椎动物的乌贼。德瓦尔用第一手的科研资料,讲述了你从未听到过的动物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动物以及人类的智慧。读过这本书之后,你会拥有更加广阔的思维,这是一本颠覆你所有认知的书。
《万智有灵》读后感(三):子非鱼,安知鱼不高兴?
英国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写过一本科幻小说叫《银河系漫游指南》。小说一开头,人们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地球上的海豚都消失不见了。主人公的外星人朋友告诉了他真相,地球要被毁灭了,因为要在地球所在的地方修建一条超空间快速通道。
换句话说,银河系要修建高速公路,而地球占道了,要被拆迁。这么重要的消息,地球人不知道,反而海豚却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主人公的朋友说,在这个星球上,最聪明的生物并不是人类,甚至人类只能排在第三位。排第二的就是已经搬家的海豚,而排第一的则是地球真正的主人——老鼠。地球就是老鼠们给自己定制的家园。
有意思的是,在搬走之前,海豚们曾经无数次尝试着提醒人类危机将近。但绝大多数的沟通行为却被误读为逗人发笑的顶球表演,又或者是为了求得几口零食而吹口哨。海豚最后终于放弃了努力,在外星人来临前不久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离开了地球。
亚当斯是我见过的最具幽默感的科幻作家,他用这个脑洞尽情地嘲讽了人类的愚蠢和自以为是。而我们读到这里,恐怕也只是会心一笑,把这看作是上等生物的自嘲。我们始终相信,自己才是这个星球的主人,这个星球有两种生物:人类,其它生物。
然而另一位作家却以更严肃的口吻告诉我们,人类的确是既愚蠢又自以为是,不仅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其他动物。这位作家叫弗兰斯·德·瓦尔,荷兰动物行为学家,而且他还要证明人类愚蠢,而他的证据都写在了新出版的这本《万智有灵》中。
或许在很多人眼里,动物的那点儿智慧,跟扫地机器人差不多。而过往的动物学研究,则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这个认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们中学都学过的巴浦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了。一提到这个理论,我就会条件反射地想到烤鸭。持这种观点的学派叫行为主义学派,他们认为,动物没有智能,不会想要什么,更不会有什么感受。
而这之后,又出现了动物行为学派,他们的理论不再停留在动物被动的条件反射上,而是开始观察动物的自发行动。但动物行为学派也不认为动物有什么智能,他们认为动物的种种行为,都是遗传带来的本能,都是千百万年演化的结果。比方说鸠占鹊巢的现象,鸟类根本认不出哪些是自己的蛋,都傻乎乎地孵化。这不是本能是什么?
说起来对动物的认知,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我们无法钻进动物的脑子里,真正搞明白它们到底在想些什么,或者它们是不是在思考。这倒应了惠子那句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所以人类能做的,就是从动物的行为出发,去推断动物的认知能力,这就对人类提出了考验。
这个考验就是,我们该如何观察动物,又如何设计研究实验,才能够真正准确地反映动物的认知能力。在德·瓦尔看来,动物研究者曾经走了太多的弯路,而这背后,凸显的是人类自身的傲慢和忽视。就好像人家海豚试着提醒人类危机到来,可傲慢的人类却把人家的警告当做是杂耍表演。
书中举了一个真实案例,我们都知道大象很聪明,但动物学家们又一度认为大象不够聪明,起码不会使用工具,因为它们总是无法完成拾起工具去够食物的实验。后来人们才意识到,大象的鼻子不比人类的手,它不仅仅是工具,还是大象的触觉和嗅觉器官。而一鼻不可二用,你让大象用鼻子卷起工具,它们就没法同时找到食物在哪里了。
后来研究者把获得食物的工具从棍子换成了盒子之后,大象就很快学会了用盒子垫脚,然后用鼻子去够食物,这时候你敢说大象不会使用工具吗?在这里我还可以补充一个大象使用工具的铁证。今天刚好在网上看到一张GIF图,一头大象正在用鼻子卷着一根小棍子刮自己脚上的泥,聪明的简直像成了精。
抠脚大象所以不是动物不够聪明,而是我们的研究方法出了问题,我们总是想当然地按照我们人类的经验去研究动物,但动物有自己的特定环境和思考方式。所以要真正理解动物,就必须找到它们的节奏,否则我们就弹不出准确的曲调。
而通过研究,德·瓦尔得出结论,人类的认知能力和其他动物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所以,人类只是地球生物一条连续不断的谱系上的一环,这里并没有什么质的区别。
人类的傲慢或许就源自于最近两百年来的技术爆炸,这让我们获得了高高在上成神的感觉。渐渐地,我们对于自然不再心存敬畏,我们提出了“人才是目的”的口号。于是整个地球上所有的资源,无论是动物、植物、矿物、水、空气……都要为人所用,为人服务。而结果则是焚林而猎、涸泽而渔。
倒退回一万年前,当人类还同动物在自然里竞争的时候,人类对于自然充满了敬畏,所以那时候人类的信仰,不是人类自身,也不是以人类为蓝本的神明,那时候的人们相信万物有灵。当然,这种认知的形成源于人类的懵懂和恐惧,而现在,动物学家再次提出万智有灵,正源于我们所信赖的科学。
这或许能够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改变我们和动物的相处方式。在过去,我们轻易地将动物物品化和资源化,我们在动物身上予取予求却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就像行为主义学派所说的,我们相信动物没有智能,没有感受。我们有同理心而无法接受杀人,但却没有同理心去拒绝杀鸡。
进而我们还会为动物能够为我们所用而沾沾自喜,看看那些种群最繁荣的动物,鸡鸭鹅猪牛羊,恰恰都是为人类做出贡献的动物。它们为人类提供了肉蛋奶,而人类则让它们的种群没有灭绝的风险。可就个体而言,这些被拘禁、被投喂、被宰杀的动物,它们的一生只能用悲惨来形容。而如果我们知道它们拥有智能,能感受到人类的残忍,这会不会让我们感到不寒而栗?
基于这样的认知,“人就是目的”这个观念被动摇了,如果其他的生命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无知无觉,那么凭什么它们就应该为我们所牺牲,而不是把它们也看做是一个个小小的目的。当然,我们不大可能因此而让人类统统都变成素食者,我们也要为自己的生存着想。这是大自然的残酷法则,但残酷仅仅是中性词,就像狮子老虎,可人类的某些行为,却只能用邪恶来形容。如果说智能并非人类所独有,那么邪恶却是。
德·瓦尔的研究,让我们有机会反思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以及我们的态度。就像德·瓦尔自己说的:“真正的同情,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不应将人性作为一切的判断标准,而是需要根据其他物种本来的样貌,来尝试理解它们,并且一起探寻更好的生存之道。”
《万智有灵》读后感(四):所罗门王的新指环
动物的智慧
首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很小的时候曾经学过,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后来人们发现,很多灵长动物都会用树枝“钓”白蚁,用石头砸坚果。
https://sciencevibe.com/2016/03/03/brilliant-capuchins-skillfully-use-tools-to-crack-nuts-video/于是,这种区别就变成了“人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但是科学家又发现,黑猩猩可以把两根以上的竹竿子或木棍拼接起来,组成更长的杆子,去够更高位置的香蕉。这种制造工具的能力甚至不限于灵长动物。乌鸦可以用喙把直的电线弯成钩状,勾起了装有肉的小桶。
在工具“失灵”之后,人们最常用于区分人类与动物的一把标尺就是语言。科学家承认,动物的叫声是天生的,不像人类的语言是习得的。不过,这和证明动物不懂语言是两回事,因为你要证明动物不懂语言,就还需要证明动物不具备学习语言的能力。但事实上,猿类像人一样有手势语,而这种手势语的确是后天在群体中习得的。不仅如此,有些猿类在接受科学家的语言培训后,可以理解一些简单的人类口语指令。
https://geekologie.com/2014/07/scientists-decipher-chimp-communication.php如果动物也具备语言能力(尽管只是少数动物,而且能力还不及三岁儿童),那么我们就需要重新选择一条区分标准。此时,科学家转向了心智理论,去研究动物能否理解其他同类的精神状态。结果发现,灵长动物不但会猜测同类的心思,还会欺骗同类。当然,它们也有同情心,会帮助同类,能够理解同类的需求。
科学家在考察一项又一项标准之后,最终得出的结论似乎是动物具备人类具备的一切:社会关系、权谋政治、分工合作、情景记忆、计划安排、延迟满足,甚至是元认知——知道自己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
著名动物行为学家、美国埃默里大学教授弗朗斯•德瓦尔在《万智有灵》一书中展示了动物在上述所有领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智慧——他更喜欢称之为“认知”能力。如果你细细阅读书中近百个实验和案例的话,你一定会认同全书开头引用达尔文的那句话:
人的头脑与高等动物的头脑固然有着许多不同,但这些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异,二者的本质其实是相同的。人类的智慧
如果这只是一本展示动物认知能力的书,那么它与市面上的儿童科普读物可能没有太大区别。但本书的价值显然不限于此。
本书的英文标题为Are We Smart Enough to Know How Smart Animals Are?直译过来就是“我们的聪明程度足以理解动物有多么聪明吗?”这个标题似乎暗示我们,作者更强调“Are We Smart Enough”(我们是否足够聪明)这一部分。
Are We Smart Enough to Know How Sma8.8Frans de Waal / 2016 / W. W. Norton & Company果不其然。作者在第一章就列举了多个例子,向我们展示人类在验证动物是否聪明的实验中曾犯下过愚蠢的错误。
比如,科学家为了测试长臂猿是否具有使用工具的能力,在其笼子外放置一根香蕉和一根棍子,长臂猿只要拿起棍子把香蕉拨近点就可以吃到。但长臂猿做不到这一点,而黑猩猩和其他一些猴子可以做到。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科学家后来意识到,长臂猿的手掌结构与其他猿类和猴类不同。长臂猿的大拇指很难与其他手指对握,其余四指很长,像钩子一样适合吊在树枝上。其他灵长动物的手则更适合从地上捡起并抓握物体。科学家把实验任务改成了拉绳任务,长臂猿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http://www.handresearch.com/news/primate-hands-finger-length-social-behavior.htm再比如,研究人员把家猫关在笼子里,笼子外面是鱼肉。家猫会在笼子里走来走去,同时磨蹭笼子的内壁,某一时刻会碰巧蹭开笼子的门闩,逃出笼子,吃掉鱼肉。一只家猫参加这种实验越多,逃出速度就越快。于是,研究人员认为,家猫为了获得奖赏而学会了这种行为。
几十年后,又有科学家重复了这一实验,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猫科动物都有把头或侧面在喜欢的对象上蹭来蹭去的习惯。如果看到自己喜欢的对象却无法触碰,就会去磨蹭无生命的物体。要让猫产生这种行为,并不需要食物奖赏,只需要对猫友善的人在场就可以了。换句话说,这个实验研究的不是猫的学习能力,而是问候方式。
https://www.suggestedpost.eu/cats-love/书中还有很多人类犯错的例子。德瓦尔用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动物有多么聪明暂且不论,如果人类自己不够聪明,就无法正确评价动物的智力水平。
当然,只要科学家认真思考和总结,这种技术性的错误不难排除。真正的难题在于,动物行为研究领域在早期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派——由比较心理学家组成的行为主义学派和由生物学家组成的动物行为学派。这两大学派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德瓦尔在书中指出人类研究方法的常见错误之后,紧接着就介绍了这两大学派对认知研究的深刻影响。
行为主义学派在研究动物行为时强调“刺激-反应”关联,倾向于在人为控制的实验中,检查动物“学习”的效果,认为这种“操作性条件反射”对行为有很强的调节作用,而否认动物具有可以调节行为的“认知”能力。具体可以参见上文猫的实验。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比较心理学奠基者之一B.F.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该学派心理学家尤其喜欢把饿着肚子的老鼠放进以斯金纳命名的斯金纳箱里做实验,考察奖励/惩罚对动物行为的刺激,并将研究结论延伸至人类心理学。
斯金纳箱 https://www.simplypsychology.org/perspective.html动物行为学派研究动物的习惯与本能,虽然不排斥实验室研究,但更看重观察动物的自发行为。代表人物是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和尼科•廷贝亨(Niko Tinbergen)。其中洛伦茨在我国知名度颇高,其科普著作《所罗门王的指环》虽写于1949年,但影响力经久不衰。洛伦茨在书中描述了他散养在家里的各种动物,践行了这一学派重视观察动物自发行为的信条。这一学派的动物学家强调,在做实验之前,应了解这种动物的典型行为,对动物有完整的考察。动物行为学派的贡献在于将形态学与解剖学融入研究之中,例如上文考察长臂猿手掌解剖结构的案例。该学派善于分析演化和自然选择对动物行为的影响,强调行为的功能性,但也因此绕开了动物的智能和认知问题。
康拉德·洛伦茨 https://www.famouspsychologists.org/konrad-lorenz/可以看出,这两个学派虽然观点迥异,但都反对过度解读动物的智能和认知。这种情况直到演化认知学的出现才有所改观。从理论脉络上看,演化认知学是这两个学派结合的产物,它吸收了两派的精华,采纳了比较心理学的受控实验方法以及动物行为学的演化框架和观察技术。
实际上,本书作者德瓦尔的学术生涯就是这种结合的生动写照。德瓦尔的研究生导师是荷兰动物行为学界的领军人物赫拉德•巴伦兹(Gerard Baerends),而巴伦兹是动物行为学开山鼻祖之一廷贝亨的第一位弟子。我们可以看到,洛伦茨、廷贝亨、巴伦兹都是欧洲人,动物行为学派的重心在欧洲。作者在致谢中提到,他接触比较心理学则是到美国工作之后的事,而美国是比较心理学的大本营。
这些内容出现在《万智有灵》的第二章,而作者从第三章才开始介绍动物的各种神奇认知能力。这番用心良苦的安排,显然是希望帮助读者首先理清演化认知学的历史渊源,熟悉这门学科的两大利器——受控实验和演化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后面章节中的科学实验和研究结果。
达尔文的事业
如果说在洛伦茨的比喻中,所罗门王的指环是作为主体的人理解作为客体的动物的工具,那么演化认知学完全称得上是一枚“新指环”。这枚新指环的主体当然还是人,但我们要理解的客体不仅仅是动物,还包括我们人类自己。
达尔文在一百多年前用演化论把人类从万物灵长的位置拉回到万物之中,把神创的人类变成了猿猴的同类。他的思想立即遭到宗教界和科学界保守势力的强烈抵制。一百多年过去了,如今绝大多数人都承认,人类在生物学上的地位与其他动物相比并不特殊。
但是,在智慧和精神层面,我们大部分人依然相信,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界线。德瓦尔写道,与达尔文同时提出自然选择学说和演化论思想的英国自然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曾认为“演化止步于人类大脑”,试图为人类的特殊性保留最后一份荣耀。我们人类在古希腊时代就赞扬人体的力与美,在文艺复兴时期又重新发现人的价值,在强调个人价值实现的今天,谁愿意接受人类认知与动物认知并无本质区别这种说法呢?
然而,这不正是达尔文尚未完成的事业吗?像德瓦尔一样追求真相的科学家将再一次打破我们的幻想,再一次把人类拉回到万物中间。从这个意义上看,《万智有灵》续写了《物种起源》,像达尔文用自然选择解释万物的演化一样,德瓦尔用演化认知学解释万物的认知。他们共同说明,人类无论是生理层面,还是智力层面,与其他高等动物或许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不同。
《万智有灵》读后感(五):智能不是人类的专利
(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9期。)
非洲灰鹦鹉亚历克斯面前摆着3个倒扣的杯子,有些小物件扣在杯子下面。实验者艾琳依次拿起杯子,停留几秒钟后再扣回去,以便亚历克斯能够看到这些小物件。最后,3只杯子都扣放在它面前。艾琳问它:总共有多少物件?在10次测试中,亚历克斯有8次答出了正确的总数。答错的那两次,它重新听一遍问题就答对了。
一只鸟居然会数数,会做加法?也许,也许不然。要做出清晰的回答,不仅需要参照其他大量的观察和实验,还需要重新审视“加法”这一概念。不管最终答案如何,这个实验,以及其他无数观察和实验,不能不让我们对很多动物的认知能力刮目相看。
美国荷兰裔动物行为学家、灵长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图片来源:kmuw.org)《万智有灵》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动物认知。通过大量的实例,作者德瓦尔(Frans de Waal)尝试表明:动物并不只是通过条件反射来学习,很多动物像人一样,在恰如其分的意义上具有认知能力。动物认知与人类认知构成了一个连续统,从前标注为人类独特性的很多能力,都需要重新加以审视。(“人和动物”有语病。人当然也是动物,而且主要是动物,不是智能、天使或电脑程序——人若不首先是动物,我们就无法适当地理解智能和道德。本来应该说“人和非人动物”,只是那样行文过于累赘。)
年轻的雄黑猩猩步坐在屏幕前,屏幕上随机地先后显现5个个位数字。步要在触摸屏上把这些数字依照它们显现的顺序按出来,一旦它开始按,这些数字就被白色方块取代。步只需对这些数字看上大约1/5秒就能完成这项任务。数字增加到9个,步仍能达到80%的准确率,迄今为止,尚无人类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类案例显示,在有些特定方面,动物拥有更强的认知能力。
按说,达尔文以后,物种间的连续性是默认的前提,否则,我们怎么会为了治疗人类的恐惧症去研究大鼠脑的杏仁核呢?我们现在都知道,黑猩猩与人的基因相差甚少,黑猩猩的脑比人类小,但其构造跟人脑没什么不同。但另一方面,人类与其他动物实在太不一样了,难免让人觉得两者之间有一条鸿沟。无论东西,失去人性的人常被称作禽兽。笛卡儿认为惟人有心智,动物实则只是机械。与达尔文同时提出演化论的华莱士,主张人的头脑是演化的例外,只能归因于“不可见的精神宇宙”。从古到今,人类不断尝试发现人类的独特性:人是唯一一种没有羽毛的两足生物,惟有人手上长着对生的拇指,惟有人没有门齿骨;惟有人会使用工具,或至少,会制造工具;惟有人拥有语言;惟有人拥有心智、认知、意识;惟有人会模仿,有文化,能够合作,还能够做出纯粹利他的活动——道德,是啊,惟有人拥有道德。
人们曾经认为,人与动物的重要乃至首要的区别,在于人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现在,人人都知道不少种类的动物会使用工具。海獭会用石块砸开蚌壳,秃鹫会从空中掷下石块砸开鸵鸟蛋。
也许有人愿意把这些行为称作本能而非智能,毕竟,这些动物只在一种情况下使用工具。那么,下面的事例就很难视作本能了。乌鸦会用喙把直电线弯成钩状,以便把装着一块肉的小桶从透明管子里拉出来。管子里的水面上漂着一只黄粉虫,乌鸦把喙伸进管子,仍然差一点儿才能够到,结果,它们像《伊索寓言》里的聪明乌鸦那样把小石子投进管子,水面上升,它们果然如愿以偿。大猩猩在蹚水过池塘之前会用棍子测量水深。黑猩猩会自发地把两根短竹棍插到一起做成一个长竿来够笼子外面的香蕉,会把矮箱子叠高来够高处的食物。大象会把箱子放在食物下面,踩上去够到挂在高处的食物,它还会跑到离食物很远的地方去找来箱子。野生黑猩猩在去采蜜之前就会准备好五件套的工具包。
动物不仅会制备、使用工具,它们还会玩各式各样的游戏。很多动物都喜爱游戏。我们多半听说过,乌鸦有贮藏食物的天赋。这不仅是储存食物的简单本能,乌鸦还会由此发展出它们乐此不疲的游戏。德瓦尔经常跟他养的寒鸦玩藏东西游戏,把橡木塞子之类的小物件藏在枕头下面或花瓶后面,寒鸦来找,或者它们藏东西,他来找。这类游戏还表明,乌鸦有关于物体持存的认知——这的确可以适当地称作认知,认知发育研究的先驱者皮亚杰(Jean Piaget)曾针对儿童何时发展出物体持存认知做过出色的实验。
智能较高的动物尤其乐于游戏。猿类不仅游戏,而且常常发明新游戏。作者那里有一群黑猩猩,它们发明了一种“烹饪”游戏:在泥土上挖个洞,用桶到水龙头下接水,然后倒入洞里,围坐在洞周围用树枝搅拌。这个游戏让猩猩群津津有味地玩上了几个月。
说到游戏,离文化不远了。日本幸岛上有一群猕猴,其中一只雌性最先开始用海水来洗红薯,后来,岛上几乎所有的猴子都学会了这一做法。这个案例已成为习得性社会传统的最为知名的例子。在另一个事例里,一只雌性黑猩猩率先把一根草秆插在耳朵上走来走去,给其他黑猩猩梳毛,随后几年里,群里其他的黑猩猩都跟着学会了这种“妆容”。在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实验人员给猴子两种颜色的玉米,一种颜色的玉米可口,另一种掺了难吃的芦荟。猴子学会挑食前一种颜色的玉米。后来,他们不再在另一种颜色的玉米里掺芦荟,但猴子始终不再选这种颜色。奇特的是,新出生的幼猴和临近区域迁移过来的猴子也不选这种颜色的玉米。
从前,人们倾向于用条件反射来解释动物的学习,实验人员通过即时奖励来诱导它们学习。上述的事例显示的则是颇为不同的结论。动物互相模仿,形成新习惯,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获得归属感而不是获得奖赏。这些集体游戏和风尚是不是文化?这也许主要是语词问题,它们跟人类文化的相似之处一目了然。
人类常标榜自己是唯一拥有道德的生物,虽然我们很难确定人类做过的缺德事儿更多还是道德事儿更多。而近年来,道德研究往往绕着合作研究打转。我总觉得这是个古怪的倾向——恐怖袭击通常需要良好的合作,党卫军比犹太难民合作得出色很多。君子不党,小人喜欢拉帮结派。
且不论合作的道德方面,只说合作的能力,动物那里颇不乏其例。大量的观察和实验表明,猴子、鬣狗、鹦鹉、秃鼻乌鸦、大象都会合作。它们会合力拉一条绳子——如果独自一个拉不动——把牢笼之外系在绳子另一头的食物拉到身边来。座头鲸会合作围猎鱼群;猿类会合作抬很重的树干;一只黑猩猩会扶着树干让一个同伴翻过障碍。
通常,合作是为了分享合作的成果。可还有不少案例表明,动物会超出就事论事的互惠,做出单纯的利他行为。一只未成年的黑猩猩被一条绳子缠住,差点儿被勒死,雄性首领跑过来,把它举起来,小心翼翼地把绳子解开,救了小猩猩一命。海豚也会营救受伤的同伴——一次爆炸炸晕了一只海豚,两个同伴从两侧游过来,把伤者架到水面上,让它能够呼吸。拥有水果的猴子会主动把食物分给两手空空的伙伴。猿类会跳进湖里营救同类,而且它们不会游泳,营救伙伴的行为有可能危及它们自身。观察者发现,在野外,绝大多数互相帮助的事例都发生在没有亲戚关系的猿类之间。
从认知方面看,这些案例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很多动物会转换到他者的视角上来看待问题。如果首领猩猩使劲拉扯那只小猩猩,那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猴子会分享食物给伙伴,但若它们的伙伴刚刚吃过,它们就会变得吝啬。“令人惊异的是它们考虑的是另一只猿遇到的问题。”(77页)
德瓦尔用perspective taking(观点采择)来概括这些现象。不妨更平白地称之为“他者视角”。实验人员安排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在院子里分别藏起一只香蕉和一根黄瓜,地位较低的黑猩猩雷内特看得到他们的活动,地位较高的乔治娅则看不到。他们放出这两只黑猩猩。雷内特走来走去,同时慢慢把乔治娅吸引到藏黄瓜的地点,后者刨出黄瓜吃起来,这时,雷内特来到藏香蕉的地点,开始享用它的香蕉美餐。黑猩猩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一旦东西到了你手上或嘴里,那它就是你的了,哪怕你的地位较低。事情还没完。几次实验之后,乔治娅琢磨出个中奥妙,它会仔细观察雷内特的眼光所向,利用对方的知识,抢先找出香蕉。拥有他者视角的不仅是猿类。松鸦藏虫子的时候如果发现被同伴看到,会在同伴离开后把虫子换个地方藏起来。
灵长类能够形成特定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受试猕猴可以看到实验人员把生菜或者香蕉藏到杯子下面,它被放出来以后,无论找出哪一样,都会开心地享用。但若让它看见藏的是香蕉,放它出来前却偷偷换成了生菜,受试猕猴就会拒绝生菜,同时向实验人员尖叫抗议。
这类情景记忆与表征式的预期可以连在一起。有时,黑猩猩第二天要起早赶到某处无花果树林,它们前些年曾在那里找到丰富的食物,现在它们要抢在其他动物之前去享用早餐。黑猩猩不惯摸黑赶路,但这种情况下它们会克服恐惧,天不亮就起身上路。如果那些无花果树距离较远,它们就会动身更早,不管去哪里,它们都会在差不多的时间抵达。
这说明黑猩猩是在为未来行为做出计划吗?我们都知道,松鼠会在秋天收集坚果,藏好,以备冬天和春天食用。我们能把这种行为称为计划吗?可是该怎样区分松鼠的行为和黑猩猩的行为呢?心理学家恩德尔·塔尔文(Endel Tulving)提出两条标准:1.动物现在的行为不能直接来自当下的需求和渴望;2.该行为必须使这一个体为某个与当下情境不同的未来情形做好准备。雌性倭黑猩猩莉萨拉捡起一块巨大的15磅重的石头,放到自己的背上,它的宝宝则紧贴在它的下背部。路上它停下一次,放下石头,捡起一些棕榈果,然后重新背上石头继续前行。这样走了500米,来到一块上面平坦的大石头跟前。莉萨拉清理掉石面上的落叶碎石,放下石头和宝宝,把棕榈果放在石面上,用那块15磅重的石头砸开这些坚果。莉萨拉的行为跟松鼠贮藏坚果的做法大不相同。松鼠的做法受限于单一的环境,而且,这一物种的所有成员都这样做——只要松果成熟、白天变短,幼年松鼠也会做同样的事情,虽然它们对将要来临的冬季毫无经验。前面说到,野生黑猩猩在去采蜜之前会准备好5件套的工具包,这却只能视作事先计划。
事先计划涉及推理能力,而从前,人们普遍认为推理能力独独属于人类。德瓦尔不敢苟同。只举一个实验为例。黑猩猩能够看到两个封闭容器,一个装香蕉,一个装苹果;把黑猩猩领开之际,实验员取出其一;然后把它领回来,当它的面吃掉香蕉;这只黑猩猩立刻知道装香蕉的容器已经空了,它会到另一个容器里找出苹果。
这些认知能力跟通常所说的意识有密切关联。在动物有没有意识这个问题上,人们争论不休。一部分麻烦显然是由于很难确立拥有意识的标准。人们当然也会争论什么叫制造和使用工具,但这里的标准比何为拥有意识要清晰很多。
若说意识跟脑的发展相关,那么,有些动物的大脑分量不轻。人脑1.35公斤,海豚的大脑1.5公斤,大象的4公斤,抹香鲸的8公斤。当然,大象的体重不止人类的两三倍,但为什么紧要的是大脑重量对体重的比例呢?为什么不是神经元的数目呢?大象的脑中有2 570亿个神经元,是人类的3倍。
在一个实验中,两只僧帽猴需要合作完成一项任务,奖品是黄瓜片或它们更加喜爱的葡萄,如果得到同样的奖品,它们就会很好地完成任务,但若一只得到的是黄瓜片另一只得到的是葡萄,前者就会暴怒不已,扔掉自己的奖品。猿类的反应更加奇特,得到葡萄的那一只也同样可能拒绝领取自己的奖品。不过分挑剔的话,蛮可以说猿猴具有某种公平意识。
本书作者走得很远,乃至于主张所有物种都有意识。这超出了我们平常说到意识时所设想的范围。在这类事情上的考虑很容易陷入字词之争,避开这个陷阱,要看我们怎样界定意识,才能使得有意识和没有意识的界限具有实质内容。这一点在自我意识概念上更加突出。
不少心理学家用镜像测试来研究动物是否能产生自我意识。镜像测试指的是受试者把自己的镜像与身体联系起来,并据此检视自己身上的记号。只有黑猩猩、大象、海豚等少数几个物种能够不经训练就通过这一测试。不过,虽然大多数动物无法在镜子里识别出自己,但它们对镜像的反应是不同的。小型鸣禽和斗鱼会对自己的镜像求爱或进行攻击。猫、狗、猴子却不会这样做,它们能学会无视自己的镜像。猴子还能把镜子用作工具,轻易学会借用镜子来找到藏在视线不及之处的食物。猿类更进一步,它们会用镜子来检查自己的口腔内部或臀部,借用镜子来清洁耳朵。
德瓦尔反对将镜像测试视作自我意识的标准,一个理由就是“对镜子的理解有许多不同的阶段”(293页)。的确,何为自我意识这个问题要求大量概念层面上的考察,镜像测试至多能提供很多线索中的一条。而且,如德瓦尔在多处强调,各个物种的认知并不能排列成一条整齐的序列,同理,我们也不要指望能为自我意识提供一个普遍适用的简明定义。
动物也有意识,会推理,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要说有什么是动物没有的,那就是语言了——“我们人类是唯一有语言能力的物种”(126页)。
当然,动物之间随时在进行各种交流,包括用信号交流。蜜蜂可以传递远离蜂巢的花蜜的位置,青腹绿猴针对猎豹、老鹰和蛇有不同的预警叫声。有些种类的猴子没有针对各类天敌的特定叫声,但它们会把同样的叫声用不同方式组合起来,用于不同的场合。猿类有大量特定的手势,例如在另一只猿头上挥动自己的整个手臂以表明自己的优势地位。它们的手部信号极为灵活多变,通过有意使用使信息交流更加完备。
包括德瓦尔在内的绝大多数论者认为,所有这些交流方式都不是语言。流行的语言定义,简单说来,要求包括象征符号、句法规则和递归性这些要素。并不是所有论者都接受这个定义。我最近读到丹尼尔·L. 埃弗里特的《语言的诞生》(中信出版社即出),埃弗里特主张语言起源于100多万年以前的直立人,与之相应,他所界定的语言较为简易,不包括层级语法和递归性这些要素。在他看来,很多有意义的会话并没什么语法。“象征符号加线性顺序,我们就拥有了语言。”(该书第257页)德瓦尔在《万智有灵》中不是从语言结构着眼,而是从语言功能着眼:动物的交流内容几乎完全局限于当时当地。一只黑猩猩在打斗中受了伤,它无法事后告诉另一只黑猩猩它当时是怎么受伤的。
动物没有语言能力。尝试教会黑猩猩说话的大批实验都以失败告终,表明语言是种十分独特的能力。不过,德瓦尔认为,语言能力并不是一项孤立的能力,而是由多种能力汇集而成。其中突出的一种,是用象征符号标注物体。很多动物拥有这种能力。非洲灰鹦鹉亚历克斯面前摆着一些小东西,研究人员指到钥匙、三角形、正方形的物品,它就能以极高的准确性说出“钥匙”“三角”“四角”等等。当然,亚历克斯说出的并不是语词,但以最低限度来看,这里出现了对物体的识别——如前面说到过,鸟类有关于物体持存的认知。要用象征符号交流,这种识别能力是必需的。
在识别物件以及用象征符号标注这些物件之外,动物还表现出更复杂的认知。大猩猩科科在见到斑马后,自发地把“白色”和“老虎”两个符号组合在一起。黑猩猩苏瓦把“水”和“鸟”放在一起来标注天鹅。在一些鸟类实验中,受试的鸟面对一个装满物件的托盘,这些物件有的是木头的,有的是塑料的,有的是羊毛做的,色彩缤纷。实验人员把这些物件一一拿给它,它需要用喙和舌头感受每个物件。然后,实验人员把这些物件放回托盘,并问它那个蓝色的、有两个角的物件是什么做的。它会正确地回答:“羊毛”。这些实验结果让人惊奇。由于刺激和所提的问题在不断变化,这些鸟不大可能靠死记硬背给出正确的答案。也就是说,正确地答出“羊毛”,这只鸟需要将它关于颜色、形状和材料的知识以及对那个特定物件感觉的记忆结合起来。
我们不是很清楚,科科和苏瓦的符号组合是否可以算作“象征符号加线性顺序”,我们也不知道,动物在上述实验中的表现是怎样发展成语言交流的。但若语言能力的确是多种能力的汇合,动物已经准备好了可以产生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能力。
动物认知研究近年来获得了长足进步。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有很多障碍要克服。很长一段时间里,行为主义观念占据统治地位,行为主义连人的认知都不大愿意谈起,遑论动物。那时候,用“故意的”之类的语词来描述灵长类行为都是犯忌的。
由于一开始就高度怀疑动物拥有智能,研究者不大愿意做这方面的实验。在为数不多的实验里,实验的设计往往也很不恰当。在人脸识别的实验中,其他灵长类的表现大不如人类幼儿。然而,这些实验相当荒唐,因为动物对识别人脸兴趣不大,它们感兴趣的是识别自己物种的个体。实验表明,绵羊、乌鸦、胡蜂都具有这类面部识别能力。(我自己人脸识别的能力很差,比较而言,识别中国人人脸比识别黑人或阿拉伯人要容易一点儿。)另有不少实验表明,有些种类的动物颇有能力识别不同人类群体,也能识别人类个体,但它们不一定是通过人脸来识别的。
有一些实验研究猿类和人类儿童的社交技能,实验过程中,孩子会通过实验人员的微笑等细微表现不断得到鼓励和帮助,而在测试猿类时,实验人员跟猿类没有任何嬉戏或友好接触,受试猿类很难放松下来。其实,通过人类与猿类的互动来测试猿类的社交技能本身就很成问题,猿类不那么热衷于跟人类交往,那些不是由人抚养长大的猿类更是如此。有实验表明,猿类会更为紧密地追随另一只猿的视线,而不是人的视线。这个结果委实在意料之中,也解释了为什么猿类在这类实验中往往表现不佳。
还有些时候,简简单单就是因为实验太简单了,受试动物感到无聊,就被实验人员判为表现不佳。
一些误导的事例和草率的结论也加深了人们对动物认知的怀疑。这方面最出名的例子是“聪明的汉斯”的故事。汉斯似乎会做加减法——他的主人让它计算3×4,汉斯会用它的马蹄在地上敲12下。后来的研究表明,汉斯是通过感知主人的细微表情和姿态来回答问题的——他的主人自己也不曾意识到这一点。
行为主义侧重于人工控制下的实验,动物行为学则侧重观察动物的自然活动。想要训练浣熊把硬币扔到一个盒子里,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浣熊更喜欢把硬币抓在手里使劲摩擦。动物行为学家也做实验。洛伦茨(Konrad Lorenz)是动物行为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小鹅刚孵出的时候,只有他守在边上,后来,他走到哪里小鹅就跟他走到哪里,由此确立了“刻板行为”这个概念。洛伦茨带着他的寒鸦散步,时不时把它们招呼到自己身边。这些也是实验,有人类的目的与行为参与在其中,但研究的仍然是动物的自发行为。
所罗门王的指环 [奥] 康拉德·洛伦茨/著刘志良/译中信出版集团,2012-11
当然,对动物行为的解释需要十分谨慎,以防实验人员被随机的巧合误导。但研究者今天不必忌讳“故意”这样的用语,它们比行为主义的刻画方式更贴切地描述动物的行为。接吻鱼通过互相接触突出的嘴部来解决争端,把这种行为方式叫作“接吻”当然是误导。不过,猿类小别之后的确用这种方式互相问候,称之为“接吻”并无大碍。
今人说到科学,多以物理学为标准。这一观念在好多方面造成危害。今天,物理学已经差不多完全依靠人工控制下的实验,这是正常的,因为物理客体没有内部心智的一面。动物学,乃至心理学,若一味模仿这条道路,必然会变得越来越贫瘠。固然,科学研究总体上不同于日常经验,然而,绝不能认为科学方法可以归为同一套方法。每一门科学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目标,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
《万智有灵》一书用丰富的案例表明,智能不是人类的专利,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人与动物在认知方面也是连续的。但这不是说,各个物种的认知排列成一条整齐的序列。智能不是整齐的阶梯,更像是枝杈丛生的灌木。海豚、澳洲野犬、金刚鹦鹉与猴子,它们各有自己的生态环境和生命周期,各自有其周遭世界——鼹鼠、松鼠、狐狸,生活在同一棵树上,但它们对这棵树的感知全然不同。各种动物的周遭世界对每个物种都提出了独特的认知挑战——它若要延续生命都需要知道些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物种可以作为所有其他物种的模型。”(324页)
猫聪明还是狗聪明?爱狗人和爱猫人永远不会达成共识,这不仅因为人们各有偏爱,还因为本来就找不到通用的标准来测试狗的智能和猫的智能。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的身体构造,有它自己的生态环境要去应付,它们由此发展出形形色色种类的智能,而不是发展出一种通用智能。大象的鼻子上有4 000块肌肉,由复杂的神经网络调节,它既能够拾起一片小草叶,又能够掀翻一头河马。理所当然,大象的智能是高度特化的,不妨称之为“象鼻智能”。
要把所有动物都包括进来,大象跟我们人类算得上是近亲。章鱼离我们就远了不少。章鱼有近2 000个吸盘,每个吸盘都有自己独立的、由50万个神经元组成的神经节,各个神经节与大脑相连,神经节之间也彼此相连。跟脊椎动物的中央集权式的大脑不同,头足纲的神经系统更类似于互联网。章鱼的感官和解剖结构,以及它的分散的神经系统,使它的认知方式独一无二。
在否认通用智能标准方面,德瓦尔也许走得太远了。我们似乎无法否认人类智能的巨大优越。人发明了文字,建造了飞机,跑到月球上去溜达,在那里不可能遇见自己组团前来一游的海豚或老鹰。可是,另一方面,人类跟猩猩拉开这么大的距离,主要是在最后几万年的短短时间里。这个事实也许有助于我们思考人类认知跟动物认知究竟在哪里区别开来,并且把这一思考延续到人类其他行为与动物行为的区别。发展到今天,人的确成为了一种十分独特的动物。独特,但不一定更优秀或更优越。没有别的动物写出《红楼梦》,解出高斯方程,但也没有别的动物把成百万的同类关到集中营里折磨致死。我们还可以沿着这一方向来思考所谓人工智能。生物为了存活下去发展出它的智能,各个物种根据它们各自的生命周期和生态环境发展出形形色色的智能,计算机在哪种意义上拥有“智能”呢?
虽然已经写了很多,但本书中还有不少内容我没有提到,例如,黑猩猩的社会交往行为,虽然它们格外精彩,让人对动物的认知能力印象更加深刻。作者的另一本书——《黑猩猩的政治》,就此有详细生动的述论。几年前,我读到这本书,手不能释卷,放下书又到处向人推荐。
感谢德瓦尔又赠给我们一本好书。同时还要感谢译者的出色译笔。读译本,写得好还不够,译得好同样重要——唉唉,多少好书被译者糟蹋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