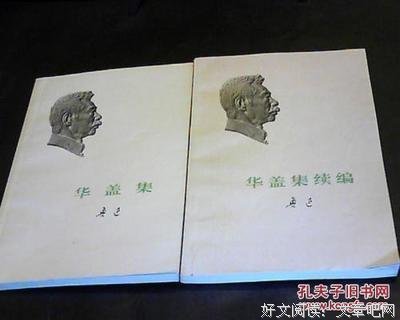三闲集读后感摘抄
《三闲集》是一本由鲁迅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1.00元,页数:1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三闲集》精选点评:
●《无声的中国》指出了在中国如何开窗的方法,就是利用善于调和这一特点。讲自己与《语丝》的过往也让人唏嘘。还讲了写《野草》的心境。其他文章包括那些通信和序言,虽然也语重心长,颇多议论,但看完并没有多少印象留下。
●这一集里不了解时代背景的话有很多篇我是读不懂的,因为不知道鲁迅具体在骂谁。事实上我去查了查他骂的人,倒是个个比鲁迅活得长,评价也都很正面,但早就湮没无闻、身与名俱灭了(我等小白看见名字要去查才知道对方下落,便是旁证)。所以读了一小半我便去读了钱理群的《与鲁迅相遇》中最后一讲,才大概弄清楚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是怎么回事,也才清楚写这一集的杂文时鲁迅所身处的备受攻击的状态,对他所发的关于革命、关于文学、关于“革命知识分子”的议论才理清一点头绪。另外,喜欢两篇夜记以及《太平歌诀》《革命咖啡店》几篇。
●《语丝》时期的读者来信问答很是精彩。关于文学的社会功用的讨论,民十完胜现在
●几乎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关于文学革命的论争,最后还讲了自己和《语丝》的关系。
●爱骂人也爱吃,反正嘴不闲着,哈哈哈。
●...一半没看懂
●之前看《华盖》《华盖续》《而已》觉得他抓住一件事絮絮叨叨有些搞笑又有些烦人 到现在才觉得他真的是孤独的猛士在黑夜中果敢独行
●很一般
《三闲集》读后感(一):三闲集
1932年出版,正如序中所述,所选篇较杂,1927-1929年间其作品及文字收录,包括往来书信,演讲,摘报,杂文,时事感言,书序等,这里面更多的是生活化的鲁迅,没有浓浓硝烟味,没有《彷徨》、《呐喊》里的黑暗、压抑之词,比较闲散,也可一窥当时的社会形态及社会趣闻,比如舍家财求为人字。
《三闲集》读后感(二):读鲁迅
《三闲集》读后感(三):《三闲集》读书笔记
《三闲集》为鲁迅的第五本杂文集,收1927年至1929年所作杂文三十四篇,1932年所作一篇。此前大都是一年文章编一集,现在是三年才凑成这么一薄册,而且不乏序言和琐碎的论争。 1927年至1929年是鲁迅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转为左翼立场前的过渡阶段。在广州的时候被人当枪使,目睹四·一五大屠杀,到了上海又受到创造社、新月社、太阳社的文字“围剿”,被判为“有闲阶级”、“封建余孽”、“没落者”、“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此时的鲁迅对革命文学心灰意冷,忙于翻译外国著作、帮扶文学青年,很少创作杂文。 《无声的中国》和《夜记》两篇是《坟》那类的文章。小杂感写得少,印象最深的是“影响罪”一词,可以和“可恶罪”相媲美。还有件有意思的——杭州有个人自称鲁迅,到处吹牛逼,还到苏曼殊坟前题诗,鲁迅不得不在上海登启事澄清。
《三闲集》读后感(四):有闲、有闲、有闲的第四部杂感
鲁迅被迫离开北京,在革命策源地「广东」被悬置了一番,并不如革命群众所愿那么革命,而后来到了上海,结果又遭到众社文豪们笔尖的围剿。其中有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诺,咋一看,这些光明美好的词汇都快被占全了。
他在序言中说得明白:
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于是便承接了这「有闲阶级」的指控,是为《三闲集》。所涉及的文章大抵除了补完「而已集」 1927(广东)外、主要于 1928-1929 在上海。
在香港《无声的中国》中,鲁迅讲到了自己批判的一个策略,可以看到他之所以几乎彻底否定中国古文化,并非姿态甚至义理之争,而是着眼于实切的改变: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幻灭的悲哀不在假,而在以假为真,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难道鲁迅先生竟看不出我们的缺点么?」鲁迅来到广州,说不出话,就遭到碰瓷、乃至官司伺候。其实他是想喝一杯牛奶、一颗杨桃,胜过宣扬去革命的。「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在钟楼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旧社会死去的苦痛,新社会生出的苦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视无睹!《鲁迅先生往那里躲呢》?在书斋里他只知道叶遂宁和梭波里自杀结局:
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他只得最后躲到上海去了。上海文艺真是繁荣呀,不愧是魔都,简直群魔乱舞。
结果创造社的人很不爽了,开始指摘鲁迅的错误。错处有三:一、态度 ;二、气量;三、年纪。论战变成态度战、气量战和年龄战,这是鲁迅实在始料不及的。好在被嘲与自嘲之下,鲁迅自知之明之外还有他知之明,自知是自己这老头子被嫌弃是太趣味而不够革命了。就连之前他们称赞自己够革命的小说,也只不过是一种凸显公正的手法。
不过,可悲、糟糕、无奈、还有一点囧的是,之前他的文章,真不小心被当成蛊惑的宣传,有青年找他算账了:
精神和肉体,已被困到这般地步──怕无以复加,也不能形容──的我,不得不撑了病体向「你老」作最后的呼声了!──不,或者说求救,甚而是警告!好在你自己也极明白:你是在给别人安排酒筵,「泡制醉虾」的一个人。我,就是其间被制的一个!——《通信》这个自述被做成「醉虾」、身家被「革了命」的青年,让鲁迅好好再反思了自己,除去卖文糊口、秉随自己的趣味、不得不承认自己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性」未除。但文章既出,其立意与风云变幻,就并非他自己所能控制了。只不过依然坦言认罪的是:
至于希望中国有改革,有变动之心,那的确是有一点的——《通信》鲁迅并为文负责,对他进行了剖析。
1. 第一、我以为你胆子太大了,没有认识到黑暗的可怕
2. 第二、就是太认真,不计利害,以至于遗产被革去。
3. 第三、是你还以为前途太光明,所以一碰钉子,便大失望,根源还在「太」字。
在观念的空话之外,告诫他最重要的实际考量就是
• 第一、要谋生,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
• 第二、要爱护爱人。
一出出正剧也好,闹剧也罢。鲁迅对文学、阶级性、革命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
凡人皆具有个性,提倡个性并非利己主义;个性中性格、情感等受经济影响,因此凡人都具有一定阶级性,但是并非是只有阶级性。人被阶级性决定是不对的,超乎一切阶级的人也是没有的。
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文学与阶级》然而有趣的是,鲁迅认为存在阶级性这点,后面又会被某些文豪拿来抨击了,在这些博爱的文艺家看来,鲁迅实在太狭隘、简直是在挑起阶级斗争……甚至可能他也是拿了卢布的(《二心集》)
《三闲集》读后感(五):《三闲集》读书笔记
简要地看了一下那本《麦肯锡精英高效阅读法》的书评,想着也就着模板写一写,就当日记了。
阅读这本书的目的?
最被是看了这个广播才看的这本书,目的的话,大概就是别人说好的东西,自己也想体会一下吧。再说今年的目标本来就包括看完《鲁迅全集》,所以才开始读。
这本书讲了什么内容?
迅哥说“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吃过一些苦,但编集还是想编集的”。
本书中你最有收获的点是哪些?
迅哥说中大老鼠多;知道了开窗和拆屋顶的出处。能有什么收获呢?我也只不过和迅哥一样,舍不得我这些感受罢了。所谓的收获,也只是在看文章时,联想到现实的生活而已,对照时代才发现并没有什么不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你不赞成的作者的观点有哪些?
对于迅哥,我是有些盲从的。不赞成的观点当然会有,又不能像李长之先生那样写出《鲁迅批判》来,自然也无多大必要写出来。
鲁迅批判8.1李长之 / 2003 / 北京出版社这本书里讲到的哪些观点是你可以在今后的生活中用起来的?你打算怎样用?
在《无声的中国》快结尾时,他说,
“ 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简要地来说,就是JUST DO IT .
全书最后,他说,
“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并不明白文艺的理论而任意做些造谣生事的评论,写几句闲话便要扑灭异己的短评,译几篇童话就想抹杀一切的翻译,归根结蒂,于己于人,还都是“可怜无益费精神”的事,这也就是所谓“聪明误”了。”我想历朝历代,大家都会钦佩埋头做事最后成功的人,但又希望自己成为得到命运垂青,少奋斗十几二十年的人。我一直不知道这多出来的十几二十年会被怎么利用,会有意思吗?就像所谓的财务自由之后,一切就都结束了吗?我也知道我在很幼稚地思考,或者不能叫思考吧,我只是想不清楚,不知怎么去做。就像我怕选择和决定,但最后都由不得我。
阅读此书后,会采取哪些行动?
没有,开始读下一本吧。
3个月后会做什么,有什么样的改变?
3个月之后再说吧。
以下是微信读书上的笔记,自己喜欢的句子
网易蜗牛读书是按年份来分的,微信是把这本书分成十三章,所以有些没有题目,网易又不能导出,我也懒的每一处去写文章的名字了。
鲁迅全集(全20卷)
鲁迅
68个笔记
三闲集,序言
gt;> 好象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
gt;>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gt;> 《无声的中国》,粗浅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的。是这样的香港。但现在是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
《无声的中国》
gt;> 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gt;>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gt;> 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gt;>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怎么写—夜记之一》
gt;> 有时有一点杂感,子细一看,觉得没有什么大意思,不要去填黑了那么洁白的纸张,便废然而止了。好的又没有。我的头里是如此地荒芜,浅陋,空虚。
gt;> 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
gt;>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gt;> 恰如冢中的白骨,往古来今,总要以它的永久来傲视少女颊上的轻红似的。
gt;> 是一种期刊,封面上画着一个骑马的少年兵士。我一向有一种偏见,凡书面上画着这样的兵士和手捏铁锄的农工的刊物,是不大去涉略的,因为我总疑心它是宣传品。
gt;> 切己的琐事总比世界的哀愁关心
gt;> 照例的坏脾气,从三十二期倒看上去
gt;> 纪晓岚攻击蒲留仙的《聊斋志异》,就在这一点。两人密语,决不肯泄,又不为第三人所闻,作者何从知之?所以他的《阅微草堂笔记》,竭力只写事状,而避去心思和密语。但有时又落了自设的陷阱,于是只得以《春秋左氏传》的“浑良夫梦中之噪”来解嘲。他的支绌的原因,是在要使读者信一切所写为事实,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所以一与事实相左,那真实性也随即灭亡。如果他先意识到这一切是创作,即是他个人的造作,便自然没有一切挂碍了。
gt;> 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
gt;> 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
gt;> 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
《在钟楼上—夜记之二》
gt;> 倘说,你就死心塌地地从饭锅里装饭吃罢,那是不像样的;然而叫他离开饭锅去拚命,却又说不出口,因为爱而是我的极熟的熟人。于是只好袭用仙传的古法,装聋作哑,置之不问不闻之列。
gt;> 我住的是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一月之后,听得一个戴瓜皮小帽的秘书说,才知道这是最优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但后来我一搬出,又听说就给一位办事员住进去了,莫明其妙。不过当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总还是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办事员搬进去了的那一天为止,我总是常常又感激,又惭愧。
gt;> 我何尝不想了解广州,批评广州呢,无奈慨自被供在大钟楼上以来,工友以我为教授,学生以我为先生,广州人以我为“外江佬”,孤孑特立,无从考查。而最大的阻碍则是言语。直到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语,除一二三四……等数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几乎无不因为特别而记住的Hanbaran(统统)和一句凡有学习异地言语者几乎无不最容易学得而记住的骂人话Tiu-na-ma而已。
gt;> 吾师太炎先生的错处了。记得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存在广东,读若Tiu。故Tiuhei二字,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我不记得他后来可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动词,非名词也。
gt;> 那时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
gt;> 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
gt;> 现在想起那时的辩论来,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呵。
gt;> 有人说,文化之兴,须有余裕,据我在钟楼上的经验,大致是真的罢。
gt;> “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
《“醉眼”中的朦胧》
gt;> 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了。
gt;> 那成仿吾的“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切齿之声,在我是觉得有趣的。因为我记得曾有人批评我的小说,说是“第一个是冷静,第二个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冷静”并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着了这位革命的批评家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闲暇”也有三个了。
gt;> 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现在创造派的革命文学家和无产阶级作家虽然不得已而玩着“艺术的武器”,而有着“武器的艺术”的非革命武学家也玩起这玩意儿来了,有几种笑迷迷的期刊便是这。他们自己也不大相信手里的“武器的艺术”了罢。那么,这一种最高的艺术——“武器的艺术”现在究竟落在谁的手里了呢?只要寻得到,便知道中国的最近的将来。
《在上海的鲁迅启示》
gt;> 我自到上海以来,虽有几种报上说我“要开书店”,或“游了杭州”。其实我是书店也没有开,杭州也没有去,不过仍旧躲在楼上译一点书。因为我不会拉车,也没有学制无烟火药,所以只好这样用笔来混饭吃。因为这样在混饭吃,于是忽被推为“前驱”,忽被挤为“落伍”,那还可以说是自作自受,管他娘的去。但若再有一个“鲁迅”,替我说教,代我题诗,而结果还要我一个人来担负,那可真不能“有闲,有闲,第三个有闲”,连译书的工夫也要没有了。
《文艺与革命》
gt;> 因为并非艺术家,所以并不以为艺术特别崇高,正如自己不卖膏药,便不来打拳赞药一样。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的人生记录,人类如果进步,则无论他所写的是外表,是内心,总要陈旧,以至灭亡的。
《路》
gt;> 文艺家的眼光要超时代,所以到否虽不可知,也须先行拥篲清道,或者伛偻奉迎。于是做人便难起来,口头不说“无产”便是“非革命”,还好;“非革命”即是“反革命”,可就险了。这真要没有出路。
《通信》
gt;> “令弟”岂明先生说得是:“中国虽然有阶级,可是思想是相同的,都是升官发财”,
gt;> 我在先前,本来也还无须卖文糊口的,拿笔的开始,是在应朋友的要求。不过大约心里原也藏着一点不平,因此动起笔来,每不免露些愤言激语,近于鼓动青年的样子。段祺瑞执政之际,虽颇有人造了谣言,但我敢说,我们所做的那些东西,决不沾别国的半个卢布,阔人的一文津贴,或者书铺的一点稿费。我也不想充“文学家”,所以也从不连络一班同伙的批评家叫好。几本小说销到上万,是我想也没有想到的。
gt;> 至于希望中国有改革,有变动之心,那的确是有一点的。虽然有人指定我为没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状元么──的作者,“毒笔”的文人,但我自信并未抹杀一切。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所以从前并未将我的笔尖的血,洒到他们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头子差不多了,然而这是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之下,势所必至的事。对于他们,攻击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来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发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实在并不在欺蒙阅读的青年。
gt;> 立意怎样,于事实是无干的。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但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你看革命文学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风吹草动,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铁丝网,将反革命文学的华界隔离,于是从那里面掷出无烟火药──约十万两──来,轰然一声,一切有闲阶级便都“奥伏赫变”了。
gt;> 我先前是立意要不讲演,不教书,不发议论,使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算是我的赎罪的,今年倒心里轻松了,又有些想活动。
gt;> 革命是也有种种的。你的遗产被革去了,但也有将遗产革来的,但也有连性命都革去的,也有只革到薪水,革到稿费,而倒捐了革命家的头衔的。这些英雄,自然是认真的,但若较原先更有损了,则我以为其病根就在“太”。
gt;> 真话呢,我也不想公开,因为现在还是言行不大一致的好。
gt;> 我得先行声明:等到前来问罪的时候,倘没有这一节,他们就会找别一条的。盖天下的事,往往决计问罪在先,而搜集罪状(普通是十条)在后也。
gt;> 先生,我也劝你暂时玩玩罢,随便弄一点糊口之计,不过我并不希望你永久“没落”,有能改革之处,还是随时可以顺手改革的,无论大小。我也一定遵命,不但“歇歇”,而且玩玩。但这也并非因为你的警告,实在是原有此意的了。我要更加讲趣味,寻闲暇,即使偶然涉及什么,那是文字上的疏忽,若论“动机”或“良心”,却也许并不这样的。
《太平歌诀》
gt;> 近来的革命文学家往往特别畏惧黑暗,掩藏黑暗,但市民却毫不客气,自己表现了。那小巧的机灵和这厚重的麻木相撞,便使革命文学家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
恭喜的英雄,你前去罢,被遗弃了的现实的现代,在后面恭送你的行旌。
但其实还是同在。你不过闭了眼睛。不过眼睛一闭,“顶石坟”却可以不至于了,这就是你的“最后的胜利”。
gt;> 我就想发一点议论,然而立刻又想到恐怕一面有人疑心我在冷嘲(有人说,我是只喜欢冷嘲的),一面又有人责罚我传播黑暗,因此咒我灭亡,自己带着一切黑暗到地底里去。但我熬不住,──别的议论就少发一点罢,单从“为艺术的艺术”说起来,你看这不过一百五六十字的文章,就多么有力。我一读,便仿佛看见司门口挂着一颗头,教育会前列着三具不连头的女尸。
gt;> 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
《革命咖啡店》
gt;> 这样的乐园,我是不敢上去的,革命文学家,要年青貌美,齿白唇红,如潘汉年、叶灵凤辈,这才是天生的文豪,乐园的材料;如我者,在《战线》上就宣布过一条“满口黄牙”的罪状,到那里去高谈,岂不亵渎了“无产阶级文学”么?
《文坛的掌故》
gt;> 向“革命的智识阶级”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我以为这是很可惜,也觉得颇寂寞的。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gt;> 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诸君说什么话了,因为革命以来,言论的路很窄小,不是过激,便是反动,于大家都无益处。
gt;>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为什么呢,因为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
gt;> 我们“皇汉”人实在有些怪脾气的:外国人论及我们缺点的不欲闻,说好处就相信,讲科学者不大提,有几个说神见鬼的便绍介。
《柔石作“二月”小引》
gt;> 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是都觉得诧异的。
《流氓的变迁》
gt;> 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
gt;> 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者在。
gt;> 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七侠五义》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gt;> 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
《书籍和财色》
gt;> 则买书一元,赠送裸体画片的勾当,是应该举为带着“颜如玉”气味的一例的了。
gt;> 医学上,“妇人科”虽然设有专科,但在文艺上,“女作家”分为一类却未免滥用了体质的差别,令人觉得有些特别的。
gt;> 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给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可惜美的书店竟遭禁止。张博士也改弦易辙,去译《卢骚忏悔录》,此道遂有中衰之叹了。 #哈哈哈,神他妈第三种水不是在开黄腔#
《我和“语丝”的始终》
gt;> 虽然因为毁坏旧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面所藏的旧物来的一种突击之力,至今尚为旧的和自以为新的人们所憎恶,但这力是属于往昔的了。
《鲁迅译著书目》最后一点点
gt;> 最致命的,是:创作既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翻译又因为缺少外国语的学力,所以徘徊观望,不敢译一种世上著名的巨制。
gt;> 因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就永远只能得传扬一个可惊可喜的消息;然而静夜一想,自觉空虚,便又不免焦躁起来,仍然看见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象一块很大的“绊脚石”了。
gt;> 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并不明白文艺的理论而任意做些造谣生事的评论,写几句闲话便要扑灭异己的短评,译几篇童话就想抹杀一切的翻译,归根结蒂,于己于人,还都是“可怜无益费精神”的事,这也就是所谓“聪明误”了。
gt;> 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我愿意竭力防止这弱点,因为我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但灯下独坐,春夜又倍觉凄清,便在百静中,信笔写了这一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