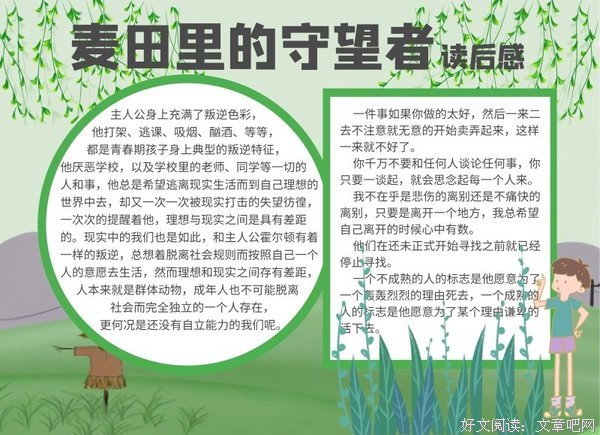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1000字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本由塞林格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60元,页数:446页,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麦田里的守望者》精选点评:
●青春的日子,总是要破坏一些东西,才会收获另一些东西。曾经的肆意,换来了今日的清醒,时光雕刻了我们的面颊和心智。
●恰恰想法,我原有的一本是精装的,这却是简装的。喜欢后面的9故事。
●啊哈就是这个封面的。我喜欢施咸荣的翻译
●我第一次读大概是初中的时候,那时候要做读书笔记,就从书架上随意拿了几本书。后来就没有完整的读过了,只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断断续续地又看过了几遍。 这种小说对我来说更大的意义是写作方法,就跟《少年维特的烦恼》是一样的。琐琐碎碎,零零星星但就是能拼出来。
●我实在搞不清楚就这样一本只有一个漂亮名字的脏话,废话,蠢话,无聊话集合到底有什么魅力让那么多人都说他好。我觉得我在看它就是浪费时间。一个笨蛋少年的琐碎事竟值得那么多人为之欢欣。难道是我太过庸俗了。看不出这是本难得的奇珍?还是其他人都在装B,因为它是名著于是争相捧之。读英文书看外国电影对我来说都多多少少有些别扭。那些说话方式,语法,以及一些他们拼命想表达我却没办法理解的言语都成了我不能特别钟爱他们的原因。但不能否认的是。很多东西还是很好的。前半部分我基本上是本着尊重作者的原则坚持下来的,但好在后半部分让我看到了这本书的一点价值。和我有了点小共鸣。对于现代社会一些虚伪做作的“假”行为看不惯,但却不得不予以顺应。但作者又有些太过偏执了,书中有一个他最喜欢的一个小女孩问他:“他在这世上是否有真正喜欢什么东西?”他答了半天也都是些没谱的事儿,实际上在这世上的任何事他都看不惯,所以才想去做那不会与人接触的麦田守望者,我也是不想过多的去接触社会才选择虚拟的营生,自然我的父母也是百般的看不惯,毕竟现在这行也不吃香,但我想或许我也就这点特别在行了。只能努力去做一下了,为了让他们能够哑口无言,我必须努力去做。就这样而已。但结论是我仍旧不那么喜欢这破书。别人怎么喜欢我不管,但我就是不喜欢。即便我的这篇短评的说话口气像极了作者。
●其实想读的是《抬高房梁,木匠门•西摩:小传》,但只下到了这个版本的,貌似这个老版更合理一些,把《九故事》和这篇原译做《木匠们,把房梁抬高些》的短篇放在了一起,在《九故事》之前看完了这篇木匠,本身就是件挺奇妙的事情。
●小时候读了好多遍!!!!!!!!
●上大学听懂了like a rolling stone,读懂了麦田里的守望者。骆胖刚po了一篇写荷顿的旧文,他的专栏也停在了666期。那我的666本读过就添上这本吧
●塞林格死了,他带来的那个时代是否也死了?我们生活在时代之后,追赶潮流,追赶金钱,毫无价值。
●麦田里的守望者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一):麦田
在这个世界上还长着比我的嘴唇更枯燥的草,
心甘情愿死在我的脚下,
这些没有大脑的家伙信奉原野里冷冷燃烧的火焰,
他们从未信任过我。
那个送给我红色苹果的人在一个阳光灿烂的黄昏对我说:
别让他们耍你
这就是他的遗言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二):当青春还有热血
就是在那个年代,
我爱上了冲动的音乐,
爱上了晦涩的哲学,
爱上了盲目而畅快的表达,
爱上了穿过树叶的阳光,
爱上了闻者春天的香味儿幻想,
爱上了一个人骑自行车在大街小巷游荡,
爱上了下雪后的铅灰色天空,
爱上了在那片建筑物中间的路灯下彷徨......
初次阅读正在上高中,薄薄的简装本,被我包了个书皮儿,像本旧书。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三):守望者
六点到酒店的时候疲惫不堪,痛风后遗症的脚不堪重负,看了会书,沉沉睡去,九点多被龚俊庆电话惊醒。起来继续看书。
我记得我是看过这部书的,但是情节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塞林格是个极其孤独的人,犹太商人家庭出身,所以不差钱,写作成名后,去乡村买了几十亩的土地,就此与世隔绝,他每天把带上面包和水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写作,不过奇怪的是,他的作品非常少,最长篇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也不过190页罢了,剩下的都是些短篇。我感觉塞林格的素描应该很好,表现在他的短篇小说里,就是极短的文字就可以把人物交代的很漂亮,有些人物甚至无需出场,就栩栩如生了。
塞林格小说的精神世界是极其孤独的,他的人物普遍有精神疾患,加上揉杂了东方佛教,道家的东西,他的人物跟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这是塞林格小说的最大特点。黑塞笔下的人物也相当孤独,但是黑塞的笔调比较暖,塞林格更寒冷一些。
某种意义来讲,塞林格的所有作品合起来才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麦田里的守望者篇幅最长,也不过描写了主人公从被学校开除到圣诞节前几天的遭遇罢了。他的故事主要靠对话,描写不多,有一些内心活动,所以其实没法跳着读,每句对话都要一点点品读,谁让他的人物都是些神经病呢,不过我喜欢,基本没人能够走近我,我几乎跟任何人都保持距离,我听人唠叨,我很少跟别人唠叨,工作之外,我很少跟人往来,同学亲戚一概不联系,我不去别人家,也不邀请别人去我家,我对集体活动毫无兴趣,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一个人待着。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四):作为故事,或者寓言——评小说《献给艾斯美的故事:怀着爱与凄楚》
作为故事。
一如塞林格的其他小说一样,《献给艾斯美的故事:怀着爱与凄楚》也讲述了一个情节生动的故事。
小说首先以第一人称叙述。我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放弃出席一个在英国举行的婚礼。但是,为了不使一场婚礼平淡冷清,我在婚礼举行前,写下了一些有关新娘的笔记,其中透露了些我约六年前与她相识时的事。约六年前,也就是一九四四年四月,我们六十名美军士兵,在英国德文郡接受英国情报机构组织的特别进攻训练。这六十个人都不善交际。不善交际的六十个人都喜欢写信。于是,写信像进行训练一样是一种集体行为。倘若没有训练或写信这样的集体活动,大家就各干各的。我一般晴天散步,雨天读书。三个星期后,特别进攻训练结束。为了准备六月六日的诺曼底的登陆,我们将按计划离去。因为还有些时间,我便决定去镇中心散步。那是个雨天。我漫无目的。先是去教堂听少年合唱团的唱圣歌训练,注意到一个十三岁左右的小女孩与众不同:她唱圣歌时的厌倦神色,她的高音区的宽广音域与优美音色。后来我去喝茶,而那个小女孩也去了,连同她的弟弟查尔斯,还有他们的家庭教师。小女孩发现了我,过来与我说话。说她的理想,问我的情况,谈粗俗的美国人,谈她所看出的我的孤单。我询问了她的名字——艾斯美。这时,她的弟弟过来调皮。艾斯美又谈及她弟弟,她死去的父亲。之后她向我要求为她写一个悲惨凄楚的故事。她还礼貌的要了我的通信地址。离别之后,艾斯美又带着查尔斯回来了,为了满足查尔斯向我吻别的愿望。
接下来,小说转为第三人称叙述。这所有的第三人称叙述也就是第一人称叙述中,我所允诺的悲惨而动人的故事的写作。二战胜利日几周以后的一天,参谋军事X出现在巴伐利亚一个叫高福特的地方。他百无聊赖。他反复的读某几段小说,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一小时一小时的嚼胶姆糖,他回忆起他生病住院,他读书——《没有先例的时代》,他读信。Z下士过来与他聊自己的女友对X病症的看法。后来,Z走了,X继续百无聊赖。无意中他发现了艾斯美寄给他的信与包裹,他阅读了信,他拆开了包裹。然后,他昏昏然来了睡意,睡了。
作为寓言。
《献给艾斯美的故事:怀着爱与凄楚》是一个寓言。一个关于人的某种生存状态的寓言。
对于生存于世作为个体的人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作为个体的人的主体性地位,即“我”。因为只有“我”,才能去感觉,去思维,去直观、去感情、去愿望、去活动、去爱。可以说,在“我”之外,作为个体的真正的人不存在。而事实上,每个人都有维护“我”这样一个一己本能。小说里提及的战争状态恰恰是要摧毁作为个体的人这样的一己本能。所谓的战争,实际上是将“我”涣散的一种荒唐的人类生存方式。战争中,人们被恶魔般的力量推动向前:攻击与被攻击,伤害与被伤害,仇恨与被仇恨。所以,那与战争直接关联的士兵们出于维护“我”的一己本能才那么热爱写信。通过写信,让被战争(不断地受训,进攻,再受训,再进攻)吞噬的“我”在自由严整的叙事中发些声音,而不是一味的涣散、零乱。
如果说,大多数士兵是出于一己本能来维护“我”之存在。那么小说中第一人称的我,是深深地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磨难。很明显,他之所以在写信之余,还要读书与散步,表明写信不足以让他将自己作为“我”来维护。然而,他主体性的危机更多的是显露在他在教堂里一下子注意到了艾斯美的与众不同的行为,和此后他在喝茶时与艾斯美和他的弟弟查尔斯的三十分钟接触。
教堂里,少年合唱团的圣歌练习中,艾斯美能够引起他的注意,全在于在合唱指导教师控制的这个团体里,艾斯美不是老老实实地听命于指导教师,她有对此的厌倦神色,她有在唱圣歌的间隙中打哈欠的举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艾斯美在合唱指导教师控制下的厌倦神色就像他在战争的情境下的写信、读书与散步。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艾斯美与他遭遇着同样的精神磨难呢?
当我们从他那里得知,“她的高音区,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唱起来自然流畅”时,当我们听到艾斯美与他谈话时说她“要做一名职业歌手”时,我们知道,艾斯美始终守着“我”。这尤其表现在她对自己的头发的多次注意:
她说起自己的理想时,她注意着自己的头发。
“说着,她用手掌摸了一下她湿漉漉的头发。”
她动用自己的判断力时,她注意着自己的头发。
“可能吧,”我的客人说,但那口气并不坚决。她再次抬起手,向自己湿漉漉的头摸去,然后,又挽起几缕柔软的金发,想盖住她裸露的耳轮。“我的头发湿透了”她说,“瞧我这难看样儿”她看看我,又说:“如果不湿的话,我头发都是卷着的。”
“是的,看得出来,是卷的。”
“实际上并不是卷,而是有许多波纹。”
她直接评价自己时,她注意着自己的头发。
她点点头,“我想你会感到的,”她说道,“在我这个年龄的人中,我是比较喜欢交际的,”她又试探地摸了一下头发说,“我的头发这个样子,真是抱歉。”又说,“我蓬头乱发的,准跟个丑八怪似的。”
“才不呢!更何况我看头发上有好多波纹都已经显出来了。”
她又很快地摸了摸头发,问,“最近你还会在来这里吗?”她说,“我们每星期六练完歌都来这里。”
其实,正是艾斯美对“我”的强烈守护,才使他这个守护出现危机的人强烈地注意到艾斯美。
他注意着艾斯美之为艾斯美的品质,除了她的声音,她的神色,当然还有她的头发。
教堂里,他注意到她“留着齐耳的浅亚麻色直发”。
茶馆里,艾斯美出现,他看到“她的头发淋得透湿,两个耳轮从头发下面露出来”。
艾斯美离去时,他又描写到,“她沉思着,慢慢地走了出去,并又摸了摸头发,看它是否干了。”
所以,艾斯美没有和他遭遇同样的精神磨难。至少要比他所遭遇的精神磨难程度轻得多。毕竟艾斯美有才能,而且合唱团指导教师的控制也并不能压抑她才能的发挥,这使得她可以固执地守着“我”。而他就不一样了,战争似乎将他埋葬。正因为如此,艾斯美才会在临别时告诉他,“我希望战后你回家时,能好好保留下你的全部才能。”
然而,一旦“我”涣散,要聚拢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战后他的那种百无聊赖状态。其实,这一点在茶馆里,他对查尔斯的主动接触与悉心观察中已经显而易见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主动接近查尔斯并不是出于礼貌,更多地是出于无力维护“我”的痛苦。因为,“我”的状态是一种非常自足的状态,这种自足状态也可以说是种孤独状态,它离童年很远。正如克尔凯戈尔所言,“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在多长时间里,以及在怎样的层次上他能够甘于寂寞,无需得到他人的理解能够毕生忍受孤独的人,能够在孤独中决定永恒之意义的人,距离孩提时代以及代表人类动物性的社会最远。”
即便如此,“我”的状态的获得还是要建立在他人的理解之上的。这个他人,不是麻木地跟随时势的Z下士,也不是Z下士那念心理学做精神分析的女朋友,而是艾斯美与查尔斯。艾斯美带给他的是作为同行者的温暖鼓励——“D日登陆时我们感到极其兴奋,也令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们希望它会使战争尽快结束。”艾斯美在信中给他希望。而查尔斯带给他的是对痛苦的纯洁慰藉,他刚刚学会写字,他在信中写道: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爱你 吻你 查尔斯
在这种鼓励与慰藉之下,“突然间,他感到一种近乎心醉神迷的感觉,昏昏然来了睡意。”他获得了希望,他觉得,总有希望再次度过艰难,好好保存下他的全部才能。
当然,我们也相信,他能够保存下他的全部才能。因为小说中的人称转换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称的转换表明他已经能够审视自己了。这种直面自己的状态就是“我”的那种自足与孤立状态。并且,我们还可以从第三人称的叙述中找到例证。面对扉页上的简短题词——“敬爱的上帝啊,生活就是地狱”,他写道:“师长们,我考虑了什么是地狱这个问题。我坚决认为那是由于无力去爱而引起的痛苦。”这也就是说,“我”的状态是一个真正人的状态。它要求着爱,即朝向“我”的渴望,它也要求着朝向“我”的渴望受挫的人们承担凄楚。所以,为了抵达“我”的状态,是怀着爱与凄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