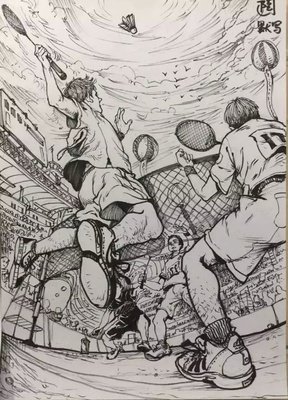画者诗心,非易得也 | 秦丹
没有灵气的文字,带着浊气的文字,不堪称之为诗。
今天,不仅是诗词大会火了,书画家也开始喜欢写古诗了。
我想书画家开始喜欢写古诗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此君的确有才,不患才之不足,惟患才之有余,有如松江陆机,清流闻鹤唳,气胜于人。二是,以前的书画家学养丰赡,诗、书、画、印皆能,较之前贤若不能诗,四美不足,学以添之。三是,对诗歌有持续不断的爱好,且把爱好当才华,自吟自足。
说实在话,很少当今书画、篆刻家的诗,有那么一种能量,能让我放下诗抬起头看他的人,审视这位赤子被感情和激情折磨过的脸,想象着他用心中按捺不住的能量给文字排序,并赋予文字以能量。
文字,实在是应该被敬畏的。以前在农村,即便是农民也会教育孩子纸片不可以踏在脚下,写有文字的纸一定要拂平放好。诗这种文字,较之于其他文字形式带有更大的灵气。没有灵气的文字,带着浊气的文字,不堪称之为诗。
诗学,是一门学问,关于这门学问,我国不少学府还设有博士点。别的不要说,就屈原的《天问》,每一词每一句所承载的能量,何其澎湃?闻一多曾拿其与《圣经·旧约·创世纪》相提并论,屈原这位诗人心中的能量,可谓究天人之际,守望天道思考之门。
如此几千年一遇的诗人,且不去说了。仅看看历代画家的诗:唐代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堪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唐人比如顾况的“上林花开春露湿”,贯休的“峰头雪满床”,都是富于盛唐气象的诗国上品;宋代苏轼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王诜的烟江叠嶂“惯见岭云和野烟”,赵佶的“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等,又别是一番宋诗的韵致;宋元人赵孟頫的“久之图画非儿戏,到处云山是我师”,黄公望的“山碧林光净,江清秋气凉”,王蒙的“一卷黄庭看未了,紫藤花落鸟相呼”,可谓参透变化、放眼自然……再说近的。吴昌硕金石大家,以画名,大写意画长款题跋,没有点诗韵功夫,何以成就画坛盟主地位?他的题画诗,因用典而雅,因阳刚、雄浑之意象而气象不凡,灼灼其华,繁英紫玉。再如齐白石,木匠出身,但悟性天成,其诗斜阳古树,油灯鼠子,鸡冠花开,似打油而非打油,人情练达,返璞归真。再如故山入梦的张大千,诗书承大家,咏诗经年不辍,极具艺术自信。更不要说谢稚柳翁,郑重先生抄下他累年写的诗,并编在为他写的传记中,读之令人景仰。
有大胸怀、真性情,文心与时空、自然交汇者,方有好诗。我一直认为,画家题画时抄一首唐人诗、宋人诗,算是文化传承。如果尽写些胸无点墨、平仄不论、不知典故、意象颠倒的诗,文不文,白不白,就不要丢人了。天下没有学不会的事,但诗这东西,是一种自由灵魂的歌唱,要歌唱,先从尘俗中解放点自己吧。
(刊于2017年11月02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品艺版)
点击下面链接,可读“朝花时文”上月热读文章:
王春鸣:好看的皮囊背后
奚美娟:一位让我在想象中怀念不已的前辈艺术家
于文岗:这是个嘚瑟的年代吗?
唐吉慧:醇香过心,人生艳丽
詹克明:关于绿萝的无言大义
陈鲁民:鲁迅还很“值钱”
何永康:在秋雨里想起余光中
王坚忍:啊,想起那些年的橡皮鱼
“朝花时文”上可查询曾为解放日报“朝花”写作的从80岁到八零后的200多位作家、评论家、艺术家和媒体名作者的力作,猜猜他们是谁,把你想要的姓名回复在首页对话框,如果我们已建这位作者目录,你就可静待发送过来该作者为本副刊或微信撰写的文章。你也可回到上页,看屏幕下方的三个子目录,阅读近期力作。
苹果用户请长按并识别二维码,向编辑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