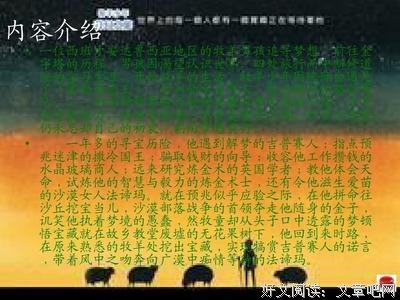《胡若望的困惑之旅》读后感精选
《胡若望的困惑之旅》是一本由[美] 史景迁著作,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2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胡若望的困惑之旅》精选点评:
●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但刘姥姥是新鲜和打趣,胡若望则是麻烦制造机器。虽然我承认这是不对等的书写,也承认中西文化刚刚碰撞之际,肯定会产生各种困扰。但从最基本的普世价值观来说,一个没有契约精神(不遵守承诺)、言行粗鄙(经常与人动粗,不遵守规矩)和不知感恩(总觉得别人对不起他,到处给别人添麻烦)、没有工作道德(没有完成誊写工作),充分证明了胡若望此人的可鄙。简直是丢脸丢到国外去了
●没有走完胡的困惑之旅。
●翻译太拗口。
●史景迁也还罢了,令人震惊的是基督教会,竟然网罗了这么多的人才,还保存了如此琐碎的历史资料,使中国历史上藉藉无名如胡若望者亦能留下真实的印记。
●胡可以算是为国争光了吧,怎么看起来都带有喜感
●法国的收容制度源远流长啊,管不得福柯会写《疯癫与文明》
●胡若望就像个猴子一样,令人费解,在这本书里。我很想从这个书的写法里面获得一点启发。
●15/08/04
●中国人在外国,语言的不沟通,之间的不理解:( 天主教
●结尾的一句话从琐碎的沉闷转变为无限的温柔
《胡若望的困惑之旅》读后感(一):翻译得不好,影响了这本书的可读性
翻译得不好,影响了这本书的可读性,里面有很多汉语里不会出现的长句子,翻译腔浓厚。如果可以看到台湾人翻的就好了。
不过书里介绍当时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生活,挺新鲜的。都是不会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的历史。好像是有一种三百多年前的记录片感觉。
《胡若望的困惑之旅》读后感(二):不对等的交流
宽泛的讲,此书从个人之间交往为立足点,展示了18世界中国人与西方世界的交流。作者是很会讲故事的,添枝加叶显得都很自然而不做作。只是,看完书后,我有些感慨,历史究竟在哪里?
作者很庆幸傅圣泽牧师即便自己很生气,但还是尽量保留了他和胡若望之间交往的历史证据,功过是非留给后人去评判。而这也是西方人的一种历史素质。历史其实就是历史,我们应该尽可能的保留好历史证据,而不是天天做好真理部里的工作。我们可以试想,为什么胡若望在作者的笔下形象是一个有点疯疯癫癫、好逸恶劳之人?而他在做看门人的时候却一切正常?或许是异国他乡让他无法适应。但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他的形象基本就定格了。注意,这些资料都是西方人提供保存的。我们连塑造另外一种形象的机会都没有。我想,这是历史的力量,一种无声而强大的力量。
《胡若望的困惑之旅》读后感(三):史景迁从一开始就没想讲一个对等的故事
史景迁从一开始就没想讲一个对等的故事。且抛开东西文化背景不谈,故事的两个主角---胡若望和富凯,就不是对等的关系,尤其在知识层面上。一个是教堂的门卫,粗通笔墨,一个是教会神职人员,知识分子。史景迁明显在认同感上倾向后者。作为一个仆从,胡若望的怪诞、叛逆几乎读起来无法忍受,而他最终拥有的那个较光明的结尾,还是因为教会对一个教徒的包容所致。
书中多次提到,胡若望是打算写本游记的,不过由于他的蛮愚,这个计划成了泡影。胡若望在这段公案中,属于自己的材料就只有区区两封信而已。这样,他在书中地位就很暗淡了,所有的历史证据都指向他行为不端,愚笨不堪,至多对他的辩护不过就是他没有精神错乱。
史景迁在书中唯一对胡若望的声援不过一句:“仅仅那样的一张由当权者发出的简函,竟能将一个独立的个体---人,不经任何审讯,扔出社会之外,并整整好几年!”其他时候,史景迁笔下,依靠史料证据的笔下,胡若望全然是个猥琐者在文明的法国胡作非为的旅游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和殖民时期西方人的笔记中描绘的未开化民族的形象多么接近!史景迁选择了一个俯视的角度,当然就谈不上什么对等的交流。
其实,胡若望的故事从心理学的角度开看,不是没有可发掘的东西。比如,在那个时期一个东方人做为异乡者在欧洲游历,他的无助、茫然是否会导致不知所措的反常行为?他的宗教背景和他对天主教信仰的中式理解(书中有很多关于胡对宗教的表象描述)放在原生地的差异感是否会给人精神错乱的假象?长达几年地无法语言交流(唯一能和他交流的富凯又比较鄙夷他)是否会形成行为自闭?这些问题史景迁本可利用手中的史料来一一剖析的,可惜,他却仅仅略带嘲讽的口气在讲一个小人物的可笑故事......
这本书,和它的翻译一样,令人失望。
《胡若望的困惑之旅》读后感(四):夸张的翻译错误令人不敢阅读
今天有人截取了本书的一段,问我能不能读懂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这段话是:
中译本P8我实在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到底方济各会的什么别称可以和“圣公会”同音异字,于是我找来这本书阅读,希望从中找到有用的帮助。结果没相当,首先是给我当头来了一棒——你知道这个译者说的“圣公会”是什么吗?看图:
中译本P7上图注1看在天主的面上!这是什么鬼翻译啊。首先,什么是“福音传信部”啊?你看括号里那个英文,能对上吗?——事实上,这是译者伟大的发明创造,这个组织叫“传信部”(Sacred 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直译:信仰传布圣部),后来改成今名“万民福音部”(Congregat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Peoples),译者天才般地把这两个名字合并为一个,创造了一个震古烁今的“福音传信部”。
当然,这还远远不够令人叹为观止。更令人惊异的是,译者居然把头截掉了,单独创造出了一个“天主教圣公会,也译作罗马神圣会”(the Sacred Congregation)。罗马教宗表示情绪稳定,坎特伯雷大主教表示同上。——不开玩笑了。事实上任何一个对于基督宗教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圣公会”是“安立甘宗”(Anglicanism)的中文译名,因此就算译者不知道在天主教语境下Congregation表示教廷的职能机构“部”,也绝不应该翻成“圣公会”。
对此我必须提出严肃的批评,因为这不是在一本专著中的某个无伤大雅的边角历史信息,而是作为原文中核心线索的重要概念,为什么这个Sacred Congregation可以“代表教皇”?为什么它的管理员可以和教廷通信啊?因为这个机构就是教廷的下属部门啊!结果你这么一翻,这层直接的意思变成暧昧不清了。
好吧,至此我们解决了一个疑问,然而并不足以回答中译本P8的问题。因为我们仍然难以理解,方济各会究竟有哪个中文别称可以和传信部在中文里同音。
为此,@ 狡兔三窟__ 帮忙找到了英文本原文,我一看,真是呵呵了。上图:
英文本P6人家原文写得明明白白:
该侍从没有把这封信交给一位耶稣会士而是交给了一位方济各会士,因为尽管他们的汉文姓氏写起来是相当不同的表意文字,但听起来是一样的。天!哪!这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错译,到底要怎么样翻译才能错成这样?我已经不想对此进行任何评论了,基于这个错误,即使我没有读这本译作更多的内容,我也要直接给这本书下一个宣判:
有理由怀疑,这本书的翻译完全是不可信任的,阅读甚至引用这本书完全是在挑战读者的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