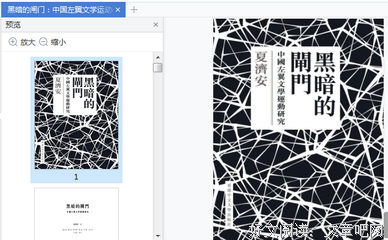黑暗的閘門经典读后感有感
《黑暗的閘門》是一本由夏济安著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USD 27.00,页数:35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黑暗的閘門》精选点评:
●夏济安先生这本书中的不少论述,在今天看来也绝不过时,阅读过程非常愉悦,就像读人物小传一样。但不仅限于此。其中对左联五烈士被杀害背后的党内派系斗争的考察,对鲁迅与左联关系的阐释,对瞿秋白身上的传统文人情愫的挖掘,乃至对蒋光慈的性格悲剧的揭示,都非常有见地。附录部分的中共小说中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也像大家说的,有解构的意味。
●谢蔚宇借书之谊。关于左翼文学研究,看惯了大陆学者假意或真心的“同情之理解”,读此书真感耳目一新。夏济安虽也明确反共,下结论却不似其弟那般翻烙饼,资料匮乏时对左联内务的推断居然丝丝入扣,宜与王彬彬《并未远去的背影》共读,恰好相互补充。附录文章分析周立波两篇小说和青春之歌、红日,大有症候式阅读和解构主义的风味,比李杨他们早了几十年。
●需要注意作者非常有偏见的观点,作为“正统”近现代文学史的补充不错,以此为纲要只怕也是要走偏
●夏氏兄弟的意识形态之强烈类似同期大陆的文学研究者。好在具体行文时能够让文本说话,不至于太偏颇。 书中提出的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以左翼文学为例分析也特别有启发性,对大陆常见文学史也是一种补充。 瞿秋白的软弱,蒋光慈的自大粗率自相矛盾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如同人物小传。鲁迅的暗面,文艺工作理论的分析都值得一读。
●虽然这本书写作的时间很早了,不过书中的一些见解在今天还有参考价值
●讀魯迅部分。第三章左聯的部分似乎印證了竹內好所說的「他不屬於任何派別,又多多少少含有派別的特質」,寫得很詳;第四章《魯迅作品的黑暗面》與李歐梵的《「傳統」與「抗傳統」》聯讀,西方文學與中國文學傳統的「幽靈面」,魯迅作為「中間物」,有意思。這倒恰好讓人想起他寫童年的「赤練蛇」與永恆不死的巨蛇,二者在那夢境裡重合了。蔣光慈部分寫得挺會意,柔石《二月》也講得好。另外一提,開頭的六十年代序極唏噓,以及沒想到在這裡也能偶遇tl老師的瞿秋白一章⋯(明天要上課了我怎麼還在熬夜?)。
●略读 唐老师的课
●我想打六星。其中还是写鲁迅那两篇最好看,夏济安想必写得很动情。
●夏濟安文筆極佳,雖說是60年代之作,所持之論亦未必公允,但對人情事故的理解,文學作品的解讀,極精道。
《黑暗的閘門》读后感(一):杂感
其中有几篇文章是大二就读过了,这段时间又重新拉出来给读完了,对于瞿秋白,从读他的《赤都心史》和《俄乡纪程》,乃至于后来的《多余的话》,总觉得他是一位有着浓厚的悲观色彩的人,至于“软心肠”的概述,挺有趣的,最后登上最高领袖的位置对他来说到底是幸或者是不幸,怕也只有他自己能够定义的了,至于他的牺牲,那自然是某些不可抗力因素罢了。
蒋光慈从他改名蒋光赤就可以看出他的热忱与圆滑了。
左联的存在与解体,以及和鲁迅的关系,错综复杂,鲁迅先生是个聪明人,不过有些时候聪明不免也会用错了地方,反到最后变成了一团“在梦里梦到做梦”的虚无了。
关于五烈士的某些论述,我最好奇的还是胡也频的妻子丁玲,她应该清楚自己的丈夫究竟是怎么一会儿事,还毅然决然的投奔到延安的怀抱,就不免有些让人浮想联翩了,其中到底有没有夹杂着个人情感的某些因素,而且再联系到她日后的所作所为,倒是有研究的空间。
在读的期间一直有一个想法,d的地位到底是怎么塑造起来的,也许正是在政治胁迫下的笔杆子的宣传,导致一种集体效应,而群众正是起着推波助澜的绝妙作用,但却并没有配套的机构,导致一种断层,往后自然就有种种变迁,不过,1930年左右,绝对是个至关重要的时间转折点。
《黑暗的閘門》读后感(二):中國左翼文學的悲劇命運 ——讀夏濟安著《黑暗的閘門》(轉)
中國左翼文學的悲劇命運
——讀夏濟安著《黑暗的閘門》
顏純鈎
原載於《明報》2月28日刊
知道夏濟安的香港年輕人應該很少,若說他是夏志清教授的哥哥,就會有一點聯想,若說他是白先勇、劉紹銘、陳若曦等著名作家學者的老師,那就大體知道他的來歷了。
「書信集」有大量史料,合該慢慢讀,這本《黑暗的閘門》研究的對象,都是我有興趣的現代文學作家,因此先讀為快。
這本書包括六個章節:一、瞿秋白:一名軟心腸共產主義者的煉成與毀滅;二、蔣光慈現象;三、魯迅與左聯的解散;四、魯迅作品的黑暗面;五、五烈士之謎;六、延安文藝座談會後的二十年。還有一篇附錄:中共小說中的英雄與英雄崇拜。
作者選取這幾個對象均有相當的典型意義:瞿秋白是作家兼革命領袖;魯迅是作家兼革命同路人;蔣光慈是作家兼革命逃兵;五烈士是作家兼革命犧牲者;至於延安文藝座談會,則是左翼文學正式回到黨的旗幟下的一個標誌性事件。整部著作研究的就是文學與革命的關係。
《黑暗的閘門》读后感(三):《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已經出版
lt;图片1>
香港中文大學,2016年一月出版
購書請移步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官方網站
https://www.chineseupress.com/index.php?route=product/product&path=59_63_89_256&product_id=3383
更多信息,敬請關注
微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微信「CUPress」
~~~~~~~~~~~~
夏濟安先生所著《黑暗的閘門》(The Gate of Darkness)自1968年英文版問世以來,便在英文世界產生極大 影響,成為中國左翼文學研究領域一本劃時代的傑作。儘管該書部分篇章曾翻譯成中文並以單篇論文形式發表, 遺憾的是此後近半個世紀之久,中文讀者始終無緣窺其全貌。此次中文大學出版社對英文版全書重新翻譯,增錄夏濟安先生另一篇相關的重要論文,並邀請翻譯學研 究專家王宏志教授對譯稿全文審訂,首次推出這本經典著作的完整中文版。
本書細緻梳理文學與時代政治的糾纏,深入揭示 左翼文學運動的兩難境地。書中所論作家包括魯迅、蔣光慈、左聯五烈士以及瞿秋白等人,他們都是1949年以前共產黨理念的同情者乃至實踐者。在1960年 代國際上反共仇共的大環境中,夏濟安下筆敏銳痛快而不失同情,充滿耐心,既給左翼作家及其作品一個恰當公允的評價,更為他們身上的悲劇意義而深深歎息。
夏濟安先生對1930年代左翼運動集團內個人和官方的複雜衝突,作出了開拓性的研究,至今我們仍然從中受益。他通過細讀所能找到的所有資料,描繪了一個四面 受敵和憤怒的魯迅,他名義上是左聯的領袖人物,卻成為左聯新生小輩的犧牲品,如今已有更多的材料和個人回憶印證了夏先生的觀點。通觀夏濟安先生的著作,沒 有因為炫耀甚麼理論術語以至破壞了他優雅的散文文風,或者損害了他原創性的洞見,出版近半個世紀之後,這本著作的光芒絲毫沒有減退。
──李歐梵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
夏 濟安是中國現代文學領域中最重要的批評家之一。《黑暗的閘門》探討中國左翼文學的消長,反思革命文人的抉擇。全書從社會、文化與知識史角度,論述文學與意 識形態的辯證,並深入倫理、審美、政治的複雜關係。從魯迅到瞿秋白,從左聯到中華蘇維埃,見解獨到深刻,議論愷切動人。任何治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政治的讀 者,均不應錯過此書。
──王德威教授,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
《黑暗的閘門》读后感(四):《黑暗的闸门》短札
夏济安的作品远比王宏志序言来得丰富。2010年的王宏志,鉴识仍然不及1960年代的夏济安。不过他找到了非常好的译者,尤其是第四章的译者万芷君。夏济安的英文原作一定恣肆,译者的中文也是相当灵活,读来竟然优美。第五章是全书最有含量的一篇,也应该相当难译,裴凡慧的工作也是相当出色的。真的是有价值的一份工作。
夏济安在这本书里充分展现了他强大的阅读能力。大量材料中披沙拣金,佐以细腻的文本鉴赏和敏锐的反读功底,这几乎是研究者进入中国左翼文学必备的修养。否则真的会被作者牵着走,被层层阐释的话语带着走。和夏志清相似,夏济安也是持了一把尺子(英美文学)来俯瞰中国现代文学,这种分析得益在看得老辣,弊在尖刻。分析鲁迅《女吊》虽只寥寥几笔,既暗合于王瑶先生的分析,而王风老师后来的讲稿也没有超出他框定的范围。分析殷夫诗的童心、分析柔石的朴讷、分析《青春之歌》中女主人公的小知识分子狂热(尤其是抓那段林道静如何回避江华的对话)、分析丁玲《一九三〇春上海》的叙事重心,都相当精彩。而他比夏志清强大的地方在于他试图把握文字背后的更深层次的“情感问题”。夏济安的论文里,用夏志清的话说,是“带着嘲讽的共情”。确实。夏济安mean起来,说蒋光慈“心智在19岁以后就停滞不前了”,这是相当尖刻,但又不得不承认是有见地的批评。这一点上,其实阿姨论近现代人物可以参照。
但如果回到所谓“政治与艺术的两难困境”,和夏济安所操持的英美文学典律,其实也是今日宜打破的东西。毕竟“革命之所以为革命,其定义即是暴力、混乱和残酷”(裴宜理语),小资产阶级们随着形势动荡波转的现状勾勒得很清晰,但具体如何判断,则要更打开一些。
《黑暗的閘門》读后感(五):同情之瞭解:夏濟安的魯迅研究考辨
本文原版獲得2019年香港青年文學獎文學評論公開組亞軍獎,此處有刪改。內容提要:
「文論」指陳一組文類、性質各不相同的表述方式,在此之下,作者或讀者來思考文學,或更廣義的人生、社會現象。夏濟安(1916-1965)常被標記為英美「新批評」或「人文主義」傳統在現代中國的重要人物,其文論帶有一定冷戰立場。隨著《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47-1965)》完整公諸於世,夏濟安文論的人文學價值有待重審——個中影響尤為突出者,當屬其袪魅式的魯迅研究。通過重新勾勒冷戰早期夏濟安的文論與強勢政治論述間的互動,不難看出他在批評魯迅的同時,實際還積極介入了彼時文學與政治相關議題中曲折的現實論辯,結果其新古典主義美學旨趣凸顯了冷戰中國文論的駁雜面目和自身強韌的文學性。
關鍵字:
夏濟安、冷戰、新批評、魯迅研究、現代中國文論
一、 引論:夏濟安、魯迅與冷戰早期的中國文論
據相關中外學者的討論,中國「文論」(literary thought)是:「一些屬於不同體裁的具有豐富多樣性的文本」,來「解釋文學在文明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描述文學和文學作品在思想和社會生活領域引起的迴響」——相較於純粹「理論(theory)為體,批評(criticism)為用」的文學研究體制,以中西彙集、古今交雜為主要特點的現代中國文論的建構,除了正視西學體制在現代中國獨特的接受脈絡,力求擺脫生搬硬套的學術惰性,澄清西方文學理論在引入中國語境後的質變,以及文論家詮釋文學的創造力外,還包括文化政治意義的不得已:對理論的援引動機動輒得咎,表明政治的冷戰興許只異化為文學論述無休止的立場糾葛而已。[1]這意味著我們處理現代中國文論時,不僅不該被既定的西方學制所囿,以及回避、粉飾其中文學和政治的曖昧,反而要追蹤辨析其中的運作和變異。
在世界文學的尺度下觀照二十世紀的中國文論,它和政治論述的糾葛可以說在冷戰早期(1950s-1960s)到達頂峰,政治立場對文學觀念的表達的侵犯同時又是全球性的;自俄國形式主義學派以來,二十世紀同時又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反復強調所謂文學性(литературность,英文literariness)的時代,即便是處在冷戰中的中國文論其實也不例外。遺憾的是,對這一時期中國文論與政治論述關係的刻畫,仍停留在政治一邊倒,文論家完全被動的消極局面。隨著近年來相關材料的發掘,夏濟安(1916-1965)的文論是一個值得展開的例證,使我們相信有必要值此良機重審冷戰早期文學與政治論述的互動。
由於著述、史料的不易得等原因,過去的夏濟安常在各樣場合被標記為英美新批評(New Criticism)或人文主義傳統在中國的傳人,[2]不容於當時「感時憂國」的主流話語;時過境遷,他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著述也因此被一律烙上「意識形態偏見」的標記。[3]隨著2019年5月《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47-1965)》(以下稱《書信集》)完整公諸於世,不乏細節表明「新批評」或「人文主義」的印象過於寬泛刻板,只能歸因於人們對夏氏兄弟批評文本的膚淺觀察:夏氏兄弟正式的學術著作不算豐富,在冷戰重重封鎖的危機時刻,他們往往一邊靠匱乏的材料死磕文章學術,同時也忍不住在相互交流的片語裏毫無保留地延續「文心」:他們著手批評具體作家的同時,自己也衍化出一套有關文學與世界(尤其是政治)關係的獨特論述。對於夏濟安而言,單評價《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1968,以下稱《黑暗的閘門》)而忽略私人化但不乏識見的《書信集》,以及因故重見天日的若干軼文(詳後)所扮演的同等重要的角色,不繼續追問和複盤批評文本內在的分裂、發展脈絡和所指涉的現實議題,無異於見木不見林。
由於動搖了魯迅(1881-1936)文學史上一貫公認的崇高地位,在其全部批評中,夏濟安有關魯迅的祛魅式批評無疑最引人注目。身兼文學作者和政治人物兩重身分,因而極具話題性和代表性,兩方面影響力最能貫穿「現代」和「當代」的現代中文作家,首推魯迅。對於夏濟安而言,作為批評對象的魯迅獨具文化政治方面的典型意義:被兩岸神化/醜化的作家魯迅,一種被高度政治化的魯迅文學,[4]如何在冷戰早期——又一輪中國與世界的激烈衝突,不同意識形態的嚴陣對壘當中,被遊走於中、英文語境的夏濟安質疑、祛魅和延展,想必最為考驗他對新批評的創新性改造程度,對魯迅作品裏文學創作和政治實踐關係的思辨能力,對中國現代文化政治傳統的眼力,進而左右他在現代文論史中的位置。以往的討論常忽略,在夏濟安的信件中,魯迅的名字不少見,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存在還直接影響到夏濟安的政治思想和文學判斷展開良性互動:如何重新認識他對魯迅的理解,學界亟待根據新發掘的材料調整。[5]
與夏濟安過往甚密的中國古典文學學者陳世驤(1912-1971)認為,夏乃是其時少數真正身體力行地實踐了「同情的批評」這一理念的批評家,[6]但並沒有進一步解釋其所謂「同情」的具體所指。在1965年離世前,夏濟安頻繁給胞弟夏志清(1921-2013)寫信吐露心聲,於字裏行間留下了大量針對中國現代文人與作品的評騭,其中便費了不少筆墨談論魯迅。與夏志清的直截不同,夏濟安對魯迅其人其文可謂饒有興致。而且研究左翼文學或中國知識人精神史貌似一貫以現身說法者為上,可夏濟安一來毫無革命鬥爭的經驗,又遠離現場,學術為文化封鎖所阻礙,然而他卻能啟發如李歐梵、王宏志等後世學者的魯迅論述,成為海外魯迅研究學者中的標杆人物,著作《黑暗的閘門》也因此超越冷戰的時代限制而成為經典,竊以為什麼「同情的批評」或「人文主義」的標籤很難透徹解釋這種深遠的影響。
王德威指出,夏氏昆仲所秉持的新批評精神,不僅強調細讀文本,審美判斷也延伸到政治思想和情感語境,包括道德判斷和政治判斷。[7]這種延伸有意提醒,受強勢政治背景的擾動,不可無視夏濟安的新批評與文本外部世界的劇烈變動的有機聯繫,畢竟審美觀念的落實某種程度有賴於後者帶來的啟發,性質上不僅遠不止於針對具體作家的批評,亦已然有別於傳統的只退守文本本體論的新批評,而內化為現代中國文論的一部分。通過複盤夏濟安魯迅研究的來龍去脈,我們不但要重新詮釋他的現代文論史意義,考慮到文論當中文學性與政治性互搏的語境,我們還需進一步揭櫫貫穿文本內外的批評意圖(intention)——此說借鏡英國政治思想史學者斯金納(Quentin·Skinner)的歷史語境主義詮釋學,有意關注批評文本的行動維度,旨在把批評文本叢聚精煉而成的文論系統,看作是作者介入不斷進行的文學和政治的辯論之中的結果,以喚醒文論內蘊的思辨人文的能量——[8]重新勾勒冷戰早期現代中國文論與強勢的政治論述間的互動,指出其實他還積極介入中國和世界、文學與政治的曲折論辯,努力凸顯著文論本來的駁雜面目和自身強韌的文學性。
二、 魯迅作為思想對象:從新批評走向新古典主義
有別於胞弟夏志清的順風順水,夏濟安輾轉於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臺灣以及美國西海岸四地的人生後半程可謂漂泊無定。然而作為一個有感於世變的文人知識人,去路之曲折,經歷之動盪也促使他不斷反思中國文學和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種種起伏運命。在這樣的背景下,向來無感於中國現代文學,秉持新批評趣味的他,竟然著手研究當時仍被認為主要是左翼作家的魯迅:《魯迅與左聯的解散》(1959)和《魯迅作品的黑暗面》(1964)主要針對魯迅與自身、集體的關係展開論述。唐小兵指出,當前涉及左翼知識人的研究「絕大部分只停留在作品或者文本分析的層次,甚至滯留在意識形態再闡釋的境地」,相比之下,夏濟安的左翼文學批評勝在「對左翼文學優劣之洞察、對人性在歷史與政治困境中的掙扎之深度理解,以及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內在悲劇感的通透把握」。[9]但這些褒獎一旦與支撐該研究的美國「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這種冷戰學術體制,以及夏濟安的自道相比照,卻難免引人困惑:
我與任何形式的馬克思主義運動都毫無聯繫……我做的研究是傳記性的和歷史性的,並不是自傳性的。所有材料都是調查所得,亦即在圖書館閱讀所得。全書全無個人經驗,除了我自己的觀察和評價。[10]以其魯迅研究為例。在材料匱乏且全無親身經歷的情況下,僅依靠傳記性寫法和所謂的「同情的批評」,興許在文本細讀和人文主義文化理想的基礎上,心理分析和介入式的方法會為他提供進入作家內心世界的便利,[11]對魯迅「黑暗面」的發掘也展現了形式主義文論家上乘的美學素養,卻不足以充分解釋夏濟安洞察魯迅背後,對時代巨變深切的生命體驗,對中國現代知識人和中國現代文學由來已久的現實關懷,以及關懷與審美判斷的頻頻互動;不足以回答他何以憑區區兩篇論文就足以於學術史留下重要一筆——毫無革命鬥爭經驗,又不見得負有「黑暗閘門」重擔的夏濟安,何以與徘徊在古典與現代、個人與集體的魯迅心心相印?
他首先關心的是魯迅在左聯這一兼具文學與政治性的組織裏的活動和心路。通過對照魯迅的書信和作品,《魯迅與左聯的解散》還原了一個苦悶者的形象:「他嚴厲的外表下掩藏著敏感的神經,『最硬的骨頭』旁跳動著一顆溫柔的心。」[12]面對「我方陣營」的冷刀暗箭,夏濟安認為,軟心腸的表現只會讓魯迅倍加痛苦:
這種緊張的衝突,這種我方陣營裏的敵意,這種必須「瞻前顧後」而荒廢精力的無奈,所有這一切本可以讓他變得更加智慧,甚至孕育出偉大的作品,然而他從中毫無得益。幸或不幸,他對革命的深厚熱情讓他在有生之年沒能目睹革命的另一面,更無從與之鬥爭了。[13]若以《書信集》的披露為准,夏濟安最早在1959年10月4日提及研究中國的事宜,一個月之後便開始撰寫該文。[14]時間看似倉促,但只要將該文與他早先發表的《中國知識人的命運》(1951,The Fat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對讀,不難發現「對革命的深厚熱情讓他在有生之年沒能目睹革命的另一面」,實是因襲和發展了1951年的「中國人是一個軟心腸的民族,很少有人有勇氣直視任何事情被徹底剖解」的宏論,表明夏濟安在中國現代文學方面的學術準備由來已久:
在此變動時代,懷疑主義,或者說一種對人類價值觀和信仰的徹底修整,固然會引起許多人的反感,但在理清思想、界定觀念這個方面,可能利大於弊。但在過去的五十年裏,我們卻並未見到一個當得起懷疑主義者之名的人。這也許是因為中國人是一個軟心腸的民族,我們很少有人有勇氣直視任何事情被徹底剖解,並從中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15]鮮少有人能檢視在學術研究的史前時期,夏濟安對文化和政治的現實關懷,更別提將這種關懷與他日後的文學研究事業相聯系。與之同年發表在《自由中國評論》雜誌上的還有《1919及其後》(Nineteen Nineteen and After)和《中華文明的未來》(The Futur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16]而從論述的完整性和嚴謹性來看,《中國知識人的命運》以犀利的眼光批判中國知識人「軟心腸」,缺乏理智感的內在缺陷,堪稱其中的代表。雖然處在1951年這一政治局勢相當緊張的時刻,文本不免夾雜作者的情緒,但這也恰好說明夏濟安的學術事業很大程度乃因世變而起——據筆者觀察發現:這些文章發表以前,夏濟安全無闡述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的議論;發表後,他對此興趣日益加深,執教臺大外文系期間即已迭出相關論作,並最終在1959年後上升到嚴肅研究。加上在中國文化的世變之際,出於對自身認知的調整,做出不同抉擇的文人都會比以往更關注「何為知識人」和「知識人何為」的課題,包括作為流揜者的夏濟安。考慮到此文重大的著眼點及其深切的現實關懷,《中國知識人的命運》大可被看作夏濟安後期文學思想的總綱或索引:爾後無論是正式論文抑或書信內的美學觀念,都能在此聽見先聲。
在他反思中國現代知識人命運的過程中,由於統合了文學和政治兩方面的複雜性,魯迅順理成章成為最值得首先關注的個案。回到夏濟安筆下的魯迅,可見反思知識人精神的議題獲得了饒有自覺的對象化,而魯迅的代表意義又補充並深化著議題自身。魯迅貌似有直視任何事情被徹底剖解的道德勇氣,1927年後的左右彷徨卻又代表他另有用意——因著這層特殊的共鳴與間隙,夏濟安得以洞燭魯迅「冷眼」和「熱心」微妙的倫理機微,進一步詮釋中國現代知識人在文學和政治實踐過程中遭遇的轉型困境,使作為觀察對象的後者更立體生動。但與此同時,如果看不見夏濟安背後的複雜政治背景和作為思想仲介的魯迅的關係,上述這些聯繫並不足以真正坐實。
被個體/集體撕扯的政治體驗,無疑給夏濟安把握魯迅在左聯活動中始終跳動的那顆「溫柔的心」提供了可參照的現實情境,而作為當時島內「禁書作家」的魯迅也被夏濟安主動選為觀照和批判現實的思想仲介。在1951年3月22日的信中,他交待《中國知識人的命運》的寫作離不開他對「戒嚴」時期臺灣島內文壇、政界風氣的針砭;[17]日後他選擇滯留美國遲遲不歸,正是因為「覺察出危機」,強化著對政治情勢的省察:1959年11月臺灣「正預備開國民代表大會」,政治局勢甚不明朗,各方勢力蠢蠢欲動——夏濟安遭英千裏(1900-1969)、雷震(1897-1979)等自由主義政治人物的拉攏,但他對政治的態度相當冷靜,身處漩渦中唯有飽受「黨爭」之苦。在這種情勢下,魯迅似乎給了夏濟安某種啟發:照其觀之,魯迅的風範能一掃臺灣文人、政客烘出的「烏煙瘴氣」。[18]別忘了我們是在帶私密性質的書信中觀察到夏濟安的思想活動的:這種寫作一方面揭示了文論家在冷戰早期所承受的政治壓力,有其時代的典型性,同時夏濟安之所以能把魯迅的政治鬥爭史分析得頭頭是道,這些相關政治的經歷幫助不小;此外從生命體驗的對象到學術研究的對象,夏濟安對魯迅認識的遞進提醒我們,冷戰早期的文學文化生態難以用文學與政治的二元對立範式來涵括,有必要重新構思兩者的關係。
這一共鳴加深著他對魯迅的認識,並促成著文論和政治論述兩大類話語資源的相得益彰。對於彼時臺灣的知識人和政治的關係,夏濟安以思想的自覺換行動的「自覺」,避免了政治上的風險之餘,在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問題上的認識更進一步。1963年8月9日,當談起弟弟和普實克(Jaroslav·Prusek,1906-1980)的筆戰時,他直言「很怕和人筆戰」,原因之一即「受魯迅影響太深,一筆戰恐怕要犯魯迅的尖酸刻薄強詞奪理的毛病」,雖然「在臺灣時,頗有筆戰的機會」,但他的態度卻是「一概不理」,有其對魯迅思想的自覺取捨。[19]回到1959年10月18日的臺灣觀察,文學主體和政治介入的緊張感實在演繹他內涵豐富的政治觀:「政治很複雜,問題如單線解決,總是顧此失彼的」。[20]下文的生動譬喻,用大半從文學作品中領悟出的世情道理來詮釋政治行動本身的曖昧:學者文人涉足政治多出於一廂情願,最終難免被政治所反噬。由此而來的暴露亦反襯著文學話語的批判本色——如此便解釋了《魯迅與左聯的解散》裏,夏濟安對魯迅熱衷「普羅」之餘的「顧此失彼」所持的批評自覺:
學者文人加入某一政治團體,大約同女人和某個男人結婚情形相若。可能她只是想男人,而偏偏該男人追得甚緊而手段高妙,她就結婚了。事實上,她不一定就對該男人滿意的。[21]《書信集》的意義在於它從共時性的角度出發,讓讀者意識到形式主義文論家把握美學細節的同時,有可能也在頻頻「背叛」自身立場而自覺地思考政治——包括政治對作家的形塑以及作家間的政治——並於日後將這些思索經驗內化到自己的批評論述當中,成為挖掘作品美學特質的一大發力點,從而辯證地彌合了傳統新批評的主張裏原本一向被割裂的家國政治和情感審美;未必如一般文學史家想像的那樣,只是死板保守的形式主義分析機器或某種僵化意識形態的附庸。
四九年前後的世變,以及貫穿其生活的文學、政治的多層次互動足以推他走向視野更開闊,更具文學性的實踐,夏濟安的魯迅研究背後針對的文化學議題也逐步浮出水面:文學、歷史和政治多重線索的交錯推進,迫使他不得不回到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的座標原點——五四新文學那裏展開根本性思考。
第一個表現是在五四運動的範疇下,建構出胡適-魯迅-周作人的序列。對於當時普遍政治化的文學史觀來說,將這三位走向迥異的知識人放在一齊討論,顯然怪異。而提出這樣的獨特序列正好能說明,夏濟安在何種視野下開展他的魯迅研究:
如果把五四運動看作除舊立新的群眾運動,魯迅的確不能作為真正的代表人物。……他從未達到胡適、周作人的寧靜境界,但比起這兩人,他也許才是更加偉大的天才。[22]其次是對五四運動的整體看法:
五四運動被人認為是個人的覺醒,但五四以後個人地位越來越不重要。舊桎梏,本已腐朽,而新桎梏束縛力度之大,更是前所未見。一切問題,只求現成答案,個人心智很少有展開的表現。[23]所謂「只求現成答案,個人心智很少有展開的表現」便概括了魯迅悲劇性的政治境遇,但更重要者是說明,他也是在試圖真正解放被壓抑的「個人心智」:1964年發表的《魯迅作品的黑暗面》對魯迅文學中私人化美學的發掘,堪稱絕佳例證。與此同時,這種發掘也是受到了夏濟安對五四以來「知識人」概念的個人化解讀驅動,後者也直接指向他對五四新文學現代性的批判和期望。
在文化新舊交替的轉型期,「知識人」的身份、責任和知識趣味往往容易讓人比附帝國時代的「士大夫」。在夏濟安這裏,由於接引了艾略特(T·S·Eliot,1888-1965)和休姆(T·E·Hulme,1883-1917)等與新批評關係甚密的文論家的理論資源,相對於冷戰早期政治局勢嚴峻的語境和以「感時憂國」為旨歸的五四新文學傳統,「士大夫」反而在文學審美和知識趣味上有意破除五四以來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而向傳統回歸,帶著相當靈活有力的理智感和批判性整合不同源頭的文學資源,毋寧說早已突破傳統新批評,而具備了一種融文學、歷史和政治於一爐的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美學旨趣。[24]
投射到其魯迅研究中,首先在反映魯迅的人格特質和文化趣味方面,他從其早年觀賞目連戲的經歷入手,對魯迅作品裏民間舊文藝元素的現代性格外關注:
目連戲的人物以無常、女吊最為突出,他們可怕的外形讓魯迅一生都為之著迷,而魯迅也以他們為題,用最佳的文才創作出兩篇奇文。把這兩篇文章放在魯迅的全部創作裏來看,這些鬼魂不僅體現出他的學識、機智與懷舊之情,更重要的是,他們還代表死亡的可怕和美麗,以及濃妝豔抹背後生與死的謎題。[25]若僅止於評述魯迅的表現,夏濟安的美學很難稱得上新古典主義。通過對《野草》展開介入式批評,他還主動設想了可能的魯迅——批評隱含的主體暗示,這裏的「他」未嘗不是可能的自己「我」:
但他如果把這夢的煩擾寫成詩,現代詩也好,古詩也罷,原本可以將中國詩歌引入一個新的境界,在傳統古詩的豐富內涵之外,傳達全新的主題,表現恐懼與焦慮,刻畫現代的經驗。[26]所謂「新古典主義」一說,並非遺民式的消極保守主義,不在於形式、內容的擬古復古,它視古典傳統為革新文風的契機,追問前者在現代表達中的可能性。引胡適的樂觀、周作人的悲觀作對比,夏濟安指出,魯迅以敏銳的洞察力和微妙深刻的感情,記錄了「光與暗之間,無數深淺的灰」,進而指出「他(魯迅)代表的是新與舊的掙扎,和超越歷史存在的更深層次的衝突」。[27]體會作家的苦衷之餘,夏濟安的介入式批評也給出魯迅創作的別樣可能:可這種設想與其說替魯迅考慮,不如說暗示了在夏濟安看來,傳統資源和現代經驗完全可以交相輝映,多了更多對話、切磋和相互促進的機遇,而不再陷於僵戰狀態,表明他同時也在宣示自己的新古典主義志向,銳意革新冷戰早期中國文學的慘澹現狀,企圖借魯迅的「黑(灰)暗面」來召喚文明重生的光明面。
關於新古典主義的文學觀,夏濟安早有論述:在《文學雜誌》的發刊詞《致讀者》(1956)中,他便明確提出雜誌要「繼承數千年來中國文學偉大的傳統,從而發揚光大之」,宣導「樸素、理智、冷靜」的文風;[28]《舊文化與新小說》(1957)甚至類比俄國文化、英國新教文化和美國南部文化,設想利用傳統中國的儒教文化來創作現代小說——[29]類似的觀點頻現,皆與新古典主義的文化理想相合。
在夏濟安對整個五四新文化傳統的新古典主義反思中,其魯迅研究可謂一個頗具代表性的批評嘗試,在一個本可能無甚作為的時代裏,豐富了現代中國文論的內涵。倘若運氣稍好些,他如自己所計畫那般寫出完整的《魯迅傳》,[30]讓彷徨的魯迅走向前臺向不明真相的讀者傾訴,另一方面更全面、系統地呈現夏濟安個人對文學和歷史的情志,想必能在現代文論史上佔據更為重要的位置。只可惜天不遂人願,1965年2月23日,夏濟安在美國三藩市猝逝,享壽49歲。
三、 小結:重審冷戰早期中國文論與世界政治的互動
夏濟安逝世後,在為《夏濟安選集》所作的序中,陳世驤有感於相通的「新潮」世變——無論是西學衝擊中學還是文學陷落於政治的形勢,冷戰早期和南朝梁代頗有相通之處——有意並置夏濟安和著名的南朝梁文論家劉勰(約465-約520)。[31]通過再澄清夏濟安批評魯迅的意圖,其實還能這樣理解陳世驤的並置:同樣標舉文學的自覺,夏濟安讀魯迅之書知魯迅之人論魯迅之世,也是將新批評的精神創造性轉化,詮釋自己所處時代的人之「文」,而與千年前的劉勰有了相互對話的可能——說明在中、西文論資源的地位極度不平衡時,現代中國的文論家仍有足夠的智慧來回應本國悠久的文論傳統。
既往印象相信,特別在冷戰早期的全球政治體制面前,敵/我分明的立場高壓迫使一切文學家坐以待斃,這一時期也堪稱文學活動的「至暗時刻」。然而中國和世界輾轉離散,文學與政治此起彼伏,夏濟安對魯迅的祛魅式批評及其文論的新古典主義內涵卻讓我們探聽到「執拗的低音」:新批評的美學理想一再堅持以文本為本位,從而拒絕討論外部因素對文學的影響;但受冷戰政治生態的壓力,鮮明的政治批判態度也在他身上屢屢反向破壞這種「獨立性」,兩者不相上下反倒引發張力,實際擔負的政治壓力、深受冷戰背景制約的立場批判等看似「為政治」的負面因素得以被有機轉化為批評的動能,使得夏濟安已昇華至融文學、歷史和政治於一爐的新古典主義文論,有足夠的洞察力直指五四精神悖論性的一面,結果凸顯了冷戰早期中國文論的駁雜面目和自身強韌的文學性。
文末我想用夏濟安寫於1961年7月19日的信作結。作為可能是對他的文學研究事業的最佳寫照,這段真心話想必已明示讀者,他的文論究竟是為政治折腰,還是向文學禱告:
我們中國人犯不著軋在美國人淘裏去爭閒氣。你上次信上說,少討論中共,多研究古代中國,我是很贊成的。我們總會有我們的影響——讀我們的文章的人,和我們在友善的空氣下談話之人。[32]注釋
[1]王德威:《現代中國文論芻議:以「詩」、「興」、「詩史」為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17年第65期。
[2]「夏先生這一看似任意、輕鬆的定義,讓我聯想到的,是夏濟安、夏志清兩兄弟在世俗實踐層面上作為人文主義者的形象。」宋明煒:《夏氏兄弟與人文主義》,《新民週刊》2005年11月9日。與夏氏兄弟關係密切的李歐梵也有同樣的說法,見:李歐梵,《光明與黑暗之門——我對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2期。事實上「人文主義者」也是對夏氏二人最為流行的評價。
[3]陳建忠:《「區域研究」視野下的文學研究——冷戰時期夏濟安與夏志清的魯迅論》,《世界魯迅與魯迅世界——媒介、翻譯與現代性書寫》,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18頁。
[4]關於兩岸對魯迅的神化/醜化,參見古大勇:《臺灣「戒嚴」時期和大陸「毛澤東時代」兩岸的「魯迅書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1期。
[5]關於夏濟安的魯迅研究,可參考王琳:《去神化:夏志清、夏濟安的魯迅研究之比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8年03期;張德強:《夏濟安魯迅研究的個體精神史側面——以<魯迅作品的黑暗面>為中心》,《現代中文學刊》2018年05期等。就筆者所見,這些研究都是以靜止化的眼光關心夏濟安其論點的特色和重要性,但極少留意其文學研究和政治思想的良性互動。
[6]陳世驤:《序》,《夏濟安選集》,臺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第5頁。
[7]王德威:《有聲的香港》,「五四之後:當代人文的三個方向」學術研討會主題演講。文字稿由豆瓣網友整理發佈:https://www.douban.com/people/124764727/status/2493493268/,瀏覽日期:2019年5月11日,本文特此致謝。
[8]斯金納:《談文本的解釋》,賞一卿譯,《國家與自由:斯金納訪華講演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6頁。
[9]唐小兵:《左翼知識人與中國革命——評夏濟安<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二十一世紀》2017年12月號。
[10]夏濟安:《一部關於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書稿序言》,《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萬芷均等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xxxi頁。轉引自書中夏志清撰寫的《導論》。
[11]張德強:《夏濟安文學批評方法淺析》,《開封教育學院學報》2017年04期。
[12]夏濟安:《魯迅與左聯的解散》,《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第108頁。
[13]同上,第107頁。
[14]夏濟安:《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四(1959-196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78頁。
[15]夏濟安:《中國知識人的命運》,原載《自由中國評論》1951年4月。關於夏濟安的著作目錄,較完整的可參見王愛萍《夏濟安論》(蘇州大學2017年碩士學位論文)的附錄——筆者十分吃驚,這篇論說竟不見於夏濟安任何一本公開出版的著作。原文為英文,由南京大學文學院2013級博士生陳通造首度全文翻譯:https://www.douban.com/note/704266207/,流覽日期:2018年7月8日,本文特此致謝。
[16]夏濟安:《1919及其後》,《自由中國評論》1951年5月;《中華文明的未來》,《自由中國評論》1951年9月。
[17]夏濟安:《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二(1950-195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第48頁。
[18]夏濟安:《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四(1959-1962)》,第92-95頁。
[19]夏濟安:《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五(1962-196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年,第329頁。
[20]夏濟安:《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四(1959-1962)》,第94頁。
[21]同上,第95頁。
[22]夏濟安:《魯迅作品的黑暗面》,《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第139-142頁。
[23]夏濟安:《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五(1962-1965)》,第183頁。
[24]「提倡古典主義,反抗五四以來的浪漫主義。中國文壇現在很需要一種新的理論指導。我很想寫一部中文的《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夏濟安:《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二(1950-1955)》,第37頁;「近讀Eliot的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我覺得我可算是社會中的elite的一分子。但我是屬於封建社會的……」夏濟安:《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一(1947-1950)》,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第328頁。
[25]夏濟安:《魯迅作品的黑暗面》,《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第139頁。
[26]同上,第133頁。
[27]同上,第139-142頁。
[28]夏濟安:《致讀者》,《夏濟安選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9頁。
[29]夏濟安:《舊文化與新小說》,《夏濟安選集》,臺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第10-11頁。
[30]「我這樣弄下來,寫full-length魯迅傳記也不是件難事。」夏濟安:《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四(1959-1962)》,第103頁。
[31]陳世驤:《序》,《夏濟安選集》,臺北:志文出版社,第4-7頁。
[32]夏濟安:《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四(1959-1962)》,第4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