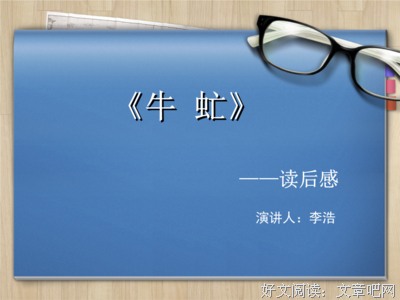《非人》读后感精选10篇
《非人》是一本由[美国] 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著作,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80元,页数:2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非人》读后感(一):过去的和更好的理性
作者的观点集中于“非人化”和创造“假种族”这两个概念,试图用这两种行为方式来解释人类残忍的暴行。作为伟大存在的最底层的人类,政治性是残忍的必要条件。残忍是具有描述和程度性质的名词,因而只有人类拥有,动物的暴行最多是毁灭,是没有生存之外的理由的。
政治家想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就要先创造一个假想的恐怖群体,民众的恐慌情绪是政治家希望看到的,宣扬的理想未来和一个必须依赖的强权便横空出世。
约翰洛克甚至也曾称北美的土著并非是人类,与其说是为了其自然主义做牵强的解释,不如说是为新英格兰的殖民做辩护。
胡适曾说他愿意看到沉船的时候大家想的是先去自救。的确,人类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并不需要我们去操心。我们能做的就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为自己和周围人的自由和幸福努力。
《非人》读后感(二):政治与非人逻辑 ——对大卫•L•史密斯《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的评论
记得在一次讨论课上,我与学生在讨论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位学生很敏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无论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的“无知之幕”下的重叠共识所形成的正义理论在证成上多么精致,但回避不了一个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参与协商,参与政治程序的个体都是人,那么,不算人的存在物能参与政治程序并让自己的权利得到保障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无论罗尔斯再怎么提出“权利优先于善”,但必须针对的对象是人,自由原则保障的是人的权利,而最小最大化原则所保障也是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存状况。那么,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人是什么?
阿甘本的《神圣人》(Homo Sacer)实际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于阿甘本来说,无论对于极权主义的全权国家政治,还是自由民主下的协商政治,都回避不了,政治或者法所施用的范围问题,也就是说,政治的范围绝对不是真正普世的,它只有相对于“人”(Homo)这个概念才是普世的,对于非“人”我们大可不必用严肃的政治和法律来对待他们,或言之,对于这种非“人”,它们根本不配在政治和法律中作为主体出现,而这种被剥夺了人的尊严的存在物,变成了“神圣人”(homo sacer),即一种被牺牲的被还原为赤裸生命(bare life)的人而存在,它们在我们身边,即便活着,也是一个非在(non-existence)。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卫•L•史密斯的《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就是阿甘本的《神圣人》的一个通俗化的版本。尽管作者所用的标题是Less Than Human,而不是Inhumane,但实质上,主题是一致的,即在我们的政治理论和政治生活中,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人是什么?或者说人的本质(essence)是什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谓人的本质就是让人成为人的东西,而人与动物的不同就是人拥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而奴隶和野蛮人虽然具有人形,但他们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不能成其为人。大卫•L•史密斯提到,拉丁语中没有亚里士多德中的“如是其所是”的表达,便生造了一个词essentia,因为esse在拉丁文中表示“是”,而后来这个词变成了英文的essence(本质)(第21页)。那么这个essence成为了划分人与非人的鸿沟,具有这种essence的就是可以以政治的方式对待的人,而不具有这种essence的就是一种非人。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思想不仅在古代,对于现代启蒙思想家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如康德就曾提出过:“人不应该像对待动物那样对待他人,而应该将他们视为拥有同等自然天赋的人。”康德在这里的潜台词是,对待人和动物(作为非人)是不一样的,而如何对待人取决于人的essence。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个所谓的essence并不是自然或者先天的,而是一种被人为塑造出来的东西,按照史密斯的说法,这种essence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我们都会塑造出来不同的关于人的essence的标准,即分辨哪些人可以称为人,而另一些则不算人。不过,史密斯的视角不是单一,而是三维的,用他的话说,他是在生物学(biology)、文化和人类理性结构三个方面来谈论人的本质的(第3页)。在文化和人类理性上对人的本质的界定论述较多,比较有趣的是史密斯的生物学角度,因为在政治学研究中,由福柯提出,并在阿甘本和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得到倡导的概念——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尽管在哲学和政治学中,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生命政治的翻译,但是无论是在福柯那里,还是在阿甘本那里,这种生命政治与生物学是息息相关的,即从生物学上所界定的人的概念,而通过生物学对人与非人进行直接还原,如生物学上用的测颅法,来测量黑人的大脑容量,从而得出了黑人是介于人与黑猩猩之间的物种的结论。也即是说,确立人与非人之间的界限,我们必须确立一个在生物学上的标准,而洛伦茨、艾布尔-艾贝斯费尔特等人则在这个领域充当的先锋。
对于人与非人之分,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对非人的存在用非人的方式来对待,而大可不必承担理性或者良心的谴责。对于被汉娜•阿伦特谴责为“平庸的罪恶”的艾希曼,正是带有这样一种思维,在他的集中营里,被集体屠戮的犹太人是非人,对他们的清洗无关乎罪恶。这正是非人逻辑的最邪恶的潜台词所在,当宗教提出“人人皆兄弟”的时候,你首先必须是一个“人”,否则你就不可能是兄弟,而是被屠戮的羔羊。在战争中,尤其是对于与种族有关的战争中,我们总是倾向于将敌方贬斥为非人。如中国将边境的异族部落贴上戎,狄、蛮、夷,实际上,这几个汉子都带有非人化的特征,史密斯提到,戎字带有“犬”的字型,而狄实际上是指“狼”,蛮下面有一个“虫”字,夷则与“蛇”有关。总而言之,这些被称为戎狄蛮夷的人,都是可以在战争和掠夺中被屠戮的对象。而史密斯在书中提到的西班牙的在俘获了印第安人之后,像卖猪肉的屠户一样,将印第安人的尸首倒挂起来,并切四肢。总而言之,有了人与非人之分,非人便被排斥在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对他们的尊严和权利的践踏,无关乎法律和正义。
实际上,这种非人的逻辑并不止在战争状态下存在,即我们用非人不仅仅侮辱的是敌人,也包含一些社会在我们身边的群体。在巴迪欧看来,生活在欧洲的那些偷渡而来的无证移民就是一种非人化的存在。实质上,在今天的中国,农民工也扮演了这种非人化的角色,因为对于一些城里人来说,我们需要的是农民工的劳动力(即一种生产力意义上的存在),而不是他们的在城市中的生活,他们被干净整洁的城市排斥到一个污秽肮脏的边缘地带,如同不存在。当然,今天政治社会对待非人的方式不再是简单的屠戮,而是一种冷暴力,即我们对他们的存在的视而不见,这种视而不见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而且也是政治上的,即他们如果想与我们一样分享我们的生活,如享受权利、享受生活保障、享受教育,连门都没有!
《非人》读后感(三):白马非马,他人《非人》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在这里分享一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赵国的公孙龙先生骑着白马儿(BM牌),哼着曲儿,吃着槟榔进城。眼开要进城了,被拦住了:城门的看守官说,依照规定马不可以进城。这可不行,今儿是公孙龙先生上《非诚勿扰》的大喜日子,这不,除了穿了CUGGI,还带了房产证,公孙先生这次是志在必得的,怎么能被一个小小的规定给挡了这人生美梦呢。于是公孙龙先生展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开始论证 – 白马非马,最后他成功说服了守城官,于是就骑着他的 BM进城去鸟。公孙先生一战成名,从此称霸江湖,至今依然横扫江湖。虽然随着辩证法的进步与发展,到了20世纪,人们已经找到了他的致命处:把物质的共性与个性割裂开来看,只有对立没有统一。
但是虽然我们找到了白马非马的逻辑漏洞,但事实是,在公孙龙成名后的2000多年中,人类依然还陷在他的这样的思维中,就是本书要阐述的观点,即:将他人与自己对立起来看,在这种对立关系中,将他人非人化。
《非人》第一章《无处不在的“非人化”》就通过种种事例说明这种情况“非人化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是一种心理润滑剂,既可以消解我们内心的种种限制,又可以点燃我们具有毁灭性的激情。”所以我们会用上动物和贬低来表达对他人的憎恨与厌恶:狗东西、畜生、婊子、流氓、变态。。。。。。
这种将他人非人化处理的作用就是减轻心理压力。当我们把他人视为非人时,进行辱骂与施暴就没什么压力了。因为对方不是人,当然不能以人相待,所以就可以进行迫害与施暴。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压力?
因为人的本能。
我一直在想,所谓的良知是什么,想来想去,觉得就是古今中外的一句话: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所谓的良知就是我们以他人对待我们的方式来对待他人。
所谓的道德就是基于这种良知而形成的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
这种良知道德已经成为人的本能。
这种本能是我们之所以能生存与生活的根本。
这种本能是所有人的行为底线,也是整个社会正常运作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这种本能用现在的名词说叫为他人设身处地思考的同情。用佛教的说法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非人》中说:“因为有同情本性,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对他人施暴难上加难。这些抑制是将人类共同体联在一起的社会约束,也是本(人类)物种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
这种本能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必须用一套东西,一套我们觉得合理的,能够接受的,不容置疑的说法,甚至是另一种本能才能让我们能对他人施暴而心安理得,避免来自良心的压力与谴责。
在这种非人化的过程中,他人被比喻成为动物细菌一类令人厌恶的东西,或是敌人魔鬼能对人产生生命威胁的东西,为后面采取行动奠定了心理准备。作者说“在将目标人群定义为外来的自然人类之后,通往大规模暴力行为的第二步就是将亚人类本质加于其上。敌人不再是另一种人类。敌人就像披着狼皮的羊,是带着人类面具的另一个物种。他们只不过表面上是人而已。”
二战中德国法西斯的宣传工具说犹太人是虱子(犹太集中营的毒气室模仿的就是灭虱室,送犹太人去毒气室也是说是去洗澡除虱子);
文革中我们把他人打倒成为“牛鬼蛇神”、“黑五类”、“毒草”而可以任意侮辱与践踏;
波尔波特则宣称“党内有疾病。。。。。。。如果我们不及时处理,细菌将会产生真正的危害。”而成为了大清洗的正当理由;
图西人被形容成为蟑螂,针对图西人的行动会以“灭蟑螂行动”来作为代号;
打黑行动就更简单了,直接说对方是黑社会的就可以不用任何合法的手段来对待了。
所有这些悲剧的发生第一步就是非人化。
非人化可以去除我们的道德压力;
非人化可以正义化我们行动的理由;
非人化可以化解我们的本能;
非人化可以让我们肆无忌惮地宣泄我们的仇恨与愤怒。
非人化也让我们滑向成为恶魔的倾向。
因为当我们非人化他人的同时,我们自己也非人化了。
因为当我们把他人从人抽离出来,不成为人时,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逻辑,我们也把自己置于人非人这一端。
无论是丑化还是美化,都有一点:对人的非人化处理。
把我们把人的共性抽离出来,我们就开始了非人化过程,也开始为一种悲剧开始创造条件了。
如何避免这一过程呢?
就是紧守我们的良知与道德之根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始终把对人当成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和你我一样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人文主义,人文精神,即:以人为本。
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一直缺乏人文教育。人文精神的缺失,白马非马的故事在中国屡见不鲜。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曾被形容为万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在了我们前面。
而我们中国的马加爵,死后他父亲连骨灰都不敢领。
无论他人做了什么坏事,无论是对谁做的,我们都要紧记这一条:始终把他人当人看。尊重他人,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尊重。对自己的尊重,一定是来自对他人的尊重。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事实上避免白马非马的错误与悲剧。
《非人》读后感(四):对不起,我是个一个很恶心的人。
我是怀抱着”为什么用非人来将行为正当化的行为是错的”这个问题买这本书的,我以为答案是社会契约,但是作者没有往这边想。好吧。
因为有刚性的支撑,所以可以让人胡思乱想。
或许以德治国是更高的境界也说不定,但是失德的人要怎么办呢?如果你在受苦,而我笑得很高兴,是不是就是缺乏想象力呢?我想象力好得很,但是为什么要用在你身上呢?
对不起,我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如果你可以,请救救我吧。不,请证否我吧。没有力量的怜悯和同情,光凭天真让我让我恨透了。
《非人》读后感(五):重叙述、轻说理的书
这不是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哲学著作或者政治哲学著作。书讨论的话题是后现代的,那就是不再谈人的尊严,而是谈人为什么不是人。有了人,才有非人,人是建构的,或者说人的待遇,境况都是建构的。
但如果是这样,这本书就太无聊了,不过是历史事实的陈列,而没有思辨的效果。
亚里士多德的精英主义,人的不平等的天然存在,甚至可以让某些人成为奴隶,是一种理论建构,还是现实体察?如果奴隶有了好环境,会不会成为主人?或者社会总有些智力不成熟的人,乃至同性恋、反社会分子、精神病人、黑人等等,都被囊括进来了。
这是一种经验意义上的区分,某些人没有资格成为人,比如在中国,黑五类,都不是平等的人,而是敌人。农民,进城了没有权利,就很简单,你是外来的人。
我的观点:人有不平等,有差异性,也有高低。仇恨会剥夺人的人格,让某些特性遮蔽他作为人的整体性。这是非人的根源。
《非人》读后感(六):非人:制度改变人性
以粗俗污秽之语骂人,原本是市井之民不入流的不文明作法,但如果在民主制度下,采用非人化、漫画式的方式来形容和自己观念不同的人,则被称之为“民主斗士”,其中的差异,耐人寻味。虽然,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观点已经得到了有识之士的认同,但政治家为了发动群众,候选人为了拉到选票,公司为了瓦解对方的信心,非人化的称呼与描摹仍然随处可见。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的选举,经常被称之为“驴象之争”就是一例。而由此所带来的新闻报道中的各种非人化标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坚定的理性就是最浪漫的感性。当人已经到了只相信数据,而不会自己去听去看的时候,当人已经到了只会根据电脑提示中显示的制度来回答问题,而不会自己去思考的时候,人其实就已经是“非人”了(马克思将其称为“异化”)。心理学告诉我们,本质的存在和认定往往来自于人的直觉,并非有一整套的科学方法和现成的规则制度来进行确认。无论是按照以往经验所形成的规则,还是按照天才经过理性分析后所设计的制度,都难免陷于偏颇。封建时代礼法制度残害妇女,农奴制度则使得黑人背井离乡,民主制度的选举则使得政党和族群之间相互攻击、谩骂,甚至大打出手。我们希望使文明得以存续的制度,却成了灭绝人性的机器——这是上帝的嘲弄,还是魔鬼的诅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