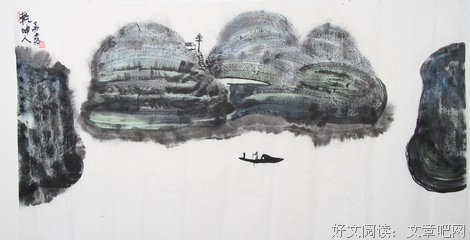国礼大师孙亚青:一辈子为扇而生的女人
一把黑纸扇,需经86道工序方可完成,成品投入沸水烧煮48小时,取出依旧不走样、不褪色、不破纸;一把檀香扇,镂空红楼人物,表情细微至眼睑,雕、嵌、刻、画、烫道道手工制作,连锯齿也由师傅亲手打磨;它是王星记,御用贡扇,G20国礼,杭扇传奇。
“G20期间,我每天一进厂就穿上围裙、戴上手套往那一坐,开始摸扇。40年的手感,一摸一个准,好的留下不好的重做,就这样每天14小时,整整一个多月,不知摸破了多少双手套,足足摸了4万多把扇,摸出一手的茧,还得了腱鞘炎,这才交出了3万多把成品扇。”她边说边摊手给我展示那一手的老茧,“你别听什么大师喊着好听,其实那都是一身的伤病。”
从小技工到门市经理再到董事长,她让王星记从绝境中走出一个又一个传奇,她就是扇艺大师、王星记当家掌门人——孙亚青。
熟悉她的人都说,她三句话不离扇,是一辈子为扇而生的女人。
迷上橱窗里的工艺扇,“王星记”烙入心中
1959年,孙亚青出生在杭州一个普通家庭。打从孙亚青记事起,杭州的夏天除了荷花便是骄阳,人手一把芭蕉扇是那个年代最时兴的标配。
14岁那年,孙亚青放学回家,眼角余光中,一抹艳色引起了她的注意。路边透明的橱窗里摆放着好几把扇子,团扇、折扇,把把争红斗艳,精美异常。“原来竟有这么好看的扇子!”孙亚青抬头看了看门上的牌匾,“王星记”三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
从那以后,孙亚青每天放学路过,总忍不住要在王星记门前停一下,一来二去,她对王星记扇子的喜爱也与日俱增。
这天,孙亚青放学一进家门,便发现姑姑正在折纸扇。孙亚青拿起一把刚折好的白扇,竹片上竟然印有“王星记”的标志。她兴奋极了,喊道:“姑姑,我也要做!”
那时的王星记,凡是不需要技术含量的活大都承包给家庭散户加工。
当了几个月童工,孙亚青的活越做越好,一天,她对姑姑说:“姑姑,我想自己领货加工挣学费。”整整一个暑假,活泼好动的孙亚青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门心思躲在家里糊扇子。
一个多月后,孙亚青背着满满一袋扇子去王星记交货,师傅一点算,竟有15元加工费。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孙亚青如数交给了母亲,成为她挣到的第一笔学费。
很快,18岁的孙亚青毕业了,父亲想让她去当兵或谋个安稳的工作,孙亚青却说:“我就想在家门口的王星记干活。”“那就是做做扇子,没什么本事。”“可是我喜欢。”架不住女儿的坚持,父母最终妥协了。
30cm七彩螺钿漆雕边剪贴三格景泥金彩绘黑纸扇
这个学徒古灵精怪,问题多还爱挑战老经验
面试过关后,孙亚青被领到纸扇车间。王星记第一任书记指着一屋子的师傅,对她说:“小鬼,你自己看一圈,想做什么?”她一脸诚恳地对书记说:“要有技术的!”书记一听乐了,便指着正在给纸扇穿面的盛师傅说:“你看,这师傅技术多熟练,就他好不好?”孙亚青定睛一看,扇骨在盛师傅手中眨眼便穿进了扇面,完全是盲插的境界,她既佩服又兴奋,点头道:“好!”
穿面看着简单,实际却是个门道活。第一天上班,即便孙亚青死死盯着扇面的孔对准了插,还是半天插不完一张扇面。这边孙亚青还在焦灼状态,那边的盛师傅早已插完了三张扇面。看着一脸懊恼的小徒弟,盛师傅乐了:“不要急,手艺活就是指尖上的工作,靠的是熟能生巧。”
师傅的话,一下子激起了孙亚青的斗志:既然来了,就绝不能做逃兵!她开始起早摸黑地穿面、练手感。
两年时间,孙亚青从穿面、折面,到通面、糊面、翻面……各个工种学了个遍,师傅对她最大的评价是:“不偷懒,很好问。”很快,她作为厂里的后起之秀被分派到了拉花车间——王星记核心技艺檀香扇的工艺车间。
拉花车间是典型的男多女少,由于要用钢丝锯在檀香扇上手工拉出图案,要使巧劲更要有臂力。上工的第一天,师傅将一把很钝的钢丝刀递给了孙亚青,同时给了一块很厚的木板让她练习。孙亚青心里不免有些抱怨:钝刀配厚板,这怎么拉?直到中午,孙亚青偷偷听到师傅和另一个师傅的谈话才明白了师傅的苦心:“小鬼她不懂,我这是让她练臂力。没力气怎么做拉花。”
孙亚青用心练习起来。一整天下来,整只右手疼得动弹不得。师傅对她说:“这种酸痛最多持续15天,忍过去就好了。”那些天简直是度日如年。等到第15天,她惊喜地发现,自己的手似乎真的习惯了这种强度的练习,不仅疼痛缓解了,连拉起花来也比之前轻松多了。
除了不偷懒,孙亚青还是车间里出了名的“问题”学徒。“我为什么做不快?”“我为什么做不好?”“你为什么做得好?”
但比起好问,孙亚青所谓的破坏性试验更是让人头疼。精灵古怪的她总是想:如果我不按照师傅说的做,会怎样?一次,师傅教她拉四边形,考虑到木板有斜度,她自然而然地觉得锯齿要与木板平行。可师傅却说不用,她不信,非得按照自己想的试上一试,结果失败了。可她却很高兴,揪着每个环节去钻研、去突破成了她最大的爱好。
《凤穿牡丹》宫团扇
血染锯齿,母亲不心疼她也不喊累
3个月后,师傅开始让孙亚青打磨拉花的锯齿。要知道在拉花技艺中,锯齿的打磨程度直接决定了扇子的成败。
12月的杭州正值严冬,冷水磨刀更是刺骨难耐,师傅在一旁指导:“按得紧,磨得重。”没有经验的孙亚青铆足了劲地磨,两只手在水里已然麻木,她突然发现手下的盆里一片鲜红,这才意识到自己磨破了手。回到家,母亲默默给她上了药:“做事怎么这么毛躁!你既然要做,就要吃得起苦。”也正是母亲的这份“不心疼”,让要强的孙亚青吃再多的苦都不喊累、不喊疼。
渐渐地,吃过亏的孙亚青悟出了一套自己的门道:一听二看三摸。
一听,师傅拉花时,孙亚青会静心聆听锯齿拉出木屑时的声音,然后对比自己打磨的锯齿拉花时的声音,来判别锯齿是否达标。
二看,看锯齿的刃锋是否规整、间隔是否匀称。一根钢锯有七八百颗锯齿,每颗锯齿必须锋利一致,若有一颗不平整,拉花时便极易造成木材断裂。而拉花时,木屑出得越快越平整,说明锯齿磨得越好。
三摸,摸锯齿是否平整。磨好的锯齿既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必须各个角度手感一致。
一个月后,孙亚青终于拉出了自己的第一把檀香扇。当28片檀香片拼接成扇的那一刻,孙亚青满是成就感。师傅拿着她拉的扇子仔细打量,肯定道:“小鬼,拉得不错,比我拉的第一把扇还要好!”孙亚青高兴极了:“师傅,那底部备用的这一片檀香木可以给我留做纪念吗?等我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
至今40年过去了,孙亚青依然收藏着这片“处女作”,如今的她常常会拿出来跟自己的徒弟们分享:“到若干年后,拿现在拉出的作品去对比,你会有自豪感和满足感:原来这些年确实提升了技艺。”
随着技艺的提升,孙亚青的《松鹤》《红楼梦》等作品相继完成。她渐渐意识到,想做出好扇子,除了传统技艺,美术功底也必不可少。于是,她用业余时间又报了绘画班、缝纫班的学习。
临危受命当家掌门,刚中带柔、柔中有情
1994年,孙亚青已担任了厂里的车间主任。1月底,她和厂里的中高层正在临平镇开会。30日凌晨的一通电话揪紧了所有人的心:“天工艺苑着火,王星记全烧了!”一行人匆匆赶回城区,看着从车间到仓库一片灰烬的惨状,所有人都流泪了。作为手工业,当时的王星记已连续3年亏损,如今这一把火更是彻底断送了王星记所有的希望。
人心散了,工友走了,到1999年,王星记从原有的400多人锐减到了100多人,外债加身,风雨飘摇。这让孙亚青也萌生了离开的想法。可这时,领导却找到了她:“你是我们培养的中层干部,别人能走,你不能走,我们希望你能撑起这个厂子。”面对没钱、没房、没人、没订单的困境,孙亚青有些灰心:“领导,你这不是等于让我从7楼跳下去吗?”
回到家,孙亚青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丈夫,丈夫劝她:“这些年,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是三句后必然转到扇子上的?你呀,是离不开扇子的。”得知此事的妹妹送来了一本存折:“姐,这些钱你投厂里吧,我这儿能省就省。”家人的支持最终让孙亚青下定决心,挑起王星记的重担。
上任后,孙亚青很快便发现了代销存在的问题:回款慢、账目出入大、陈列损失重。于是,她陆续收回了各地的代销权。全国各地陆续退回的陈货、残货、抵债品足足挤满了两个500多平方米的仓库,孙亚青不禁想起了父亲的话:“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刚中带柔、柔中有情。”于是,她狠下决心开始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开始不停地跑展销会,她坚信:只有走出去,适应市场需求,才能谋得更好的发展。
2000年8月,孙亚青去重庆开展销会。令孙亚青意外的是,货品刚一上柜就被抢购一空,她抓着一个买扇的大姐问:“您为什么喜欢这扇子?”“这扇子图案好看,价格也适中,以前没见过呢!”这让孙亚青意识到:原来南北方的扇子有很多的差异,而作为南扇代表的团扇更是抢手得很。
两天后,一个店商找到孙亚青说:“我想在重庆开设你们的专卖店,怎么合作?”孙亚青一想:专卖店等同于形象窗口,早年王星记虽然也在北京、上海开过专卖店,但由于种种原因早已不复存在,要是如今再开专卖店,也算是重振雄风。专卖店开业那天,孙亚青带人亲自摆样、布景,还对营业员进行了产品介绍的培训。系统的管理和细致的服务,让王星记的产品在重庆一战成名。
后来,孙亚青又在北京王府井、上海城隍庙、天津文化街开起了专卖店。
孙亚青带领大伙儿走出了王星记复兴的第一步。
孙亚青在檀香扇上“拉花”
巧夺天工成国礼,振兴扇业更须传承技艺
2001年,奥组委申奥筹备,王星记作为南扇代表也在备选礼单之列。奥组委派了专人到杭州考察。专员到站后,看到迎接他的竟是一辆皮卡车,不禁有些生气:“你们厂长也坐这种车?”司机一脸坦诚道:“坐啊,不过更多的时候厂长骑自行车。”专员半信半疑地上了车。到了厂里,见到一身工服的孙亚青,顿时气消了一半。“虽然王星记处于低谷,但设计、工艺绝对是一流的。”听着孙亚青的介绍,看着陈列室里一把把精致的扇子,专员最终被打动了。
有了这一次的成功,孙亚青渐渐把眼光转到了国际上,除了外贸订单,大型活动概不错过。
2010年,上海世博会招商,可要作为特许生产商,必须有80万元入门款,那时的王星记没有那么多钱。
孙亚青带着一名骨干亲自找到了世博会招商组:“能不能给我们一次机会,10天时间,我一定能设计出最符合大会理念的产品。”招商组最终被她打动。
从上海回来,孙亚青就投入到研发工作中,她将中国鼎、外滩等世博元素和扇子的技艺互相融合,同时攻克了单边开扇的技术难关,将传统的180度扇面做成360度,使扇子做到左边打开成图、右边打开成字的双重展现效果。
10天时间,她一共做了15款样品,款款精美别致。最终,她的诚意打动了招商办,王星记以20万元保证金特例成了世博会特许生产商,还一举拿下了20把夫人礼的承办权。
2016年9月,G20在杭州召开,王星记更是作为国礼亮相世界舞台,先后制作了元首礼、夫人礼、贵宾礼、会晤礼、记者礼。光是设计稿,孙亚青就改了36次。
竹片孙亚青只用10年的老竹,且必须是生长5年以上、再经过5年存放的冬竹;扇钉她要求全部手工摇制,80下才能完成一把装订;梅雨天,扇面不干,她就带人拿电吹风一把把地吹;扇子交付前,她要求必须上脸摩擦,要保证光滑柔和,不能有一丝竹刺。
终审时,扇钉因为是手工剪断的,难免有细微的长短差异,但孙亚青一摸,就说:“重做。”真丝扇面和纸黏合,免不了起些褶皱,孙亚青瞄一眼,哪怕是1毫米的细纹,只要肉眼能看到,就绝对不过关:“重做!”
一番检验下来,返工的扇子竟是合格扇子的3倍多。大家不免怨声载道:“孙总,这也太严了。”孙亚青却说:“宁可全部重做,也不能让一把不合格的扇子流出去,这是王星记的面子,更是中国的面子。”
正是这样几近苛责的把关,47天,孙亚青从4万多把扇子中亲手摸出了3万多把国礼扇。交货的那天,孙亚青长长舒了一口气,累得整个人瘫在了椅子上。
然而,比起王星记的振兴,传承更是孙亚青长久以来的夙愿。
这些年,孙亚青不仅手把手地带徒,还组建了一支技艺精湛的大师队伍。在徒弟的眼中,孙亚青是个唠叨师傅。“以前的师傅都是粗线条,修行靠个人,可我现在就连哪里好、哪里不好、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全都说得清清楚楚,省得他们再走弯路。”
孙亚青的另一个心愿,就是建立“扇博物馆”,体现中国扇文化的发展脉络,传承给年轻人一种文化理念。为了这个想法,孙亚青拟定了“三不”原则:自己不加工资、东西能不买就不买、开支能省则省,把所有的钱都拿来收集有价值的扇子。
好多次出国办事,一群人走在路上,走着走着,朋友就发现孙亚青不见了,了解她的朋友都知道:“她肯定在某个扇子店呢,不用找,丢不了。”
有一次,孙亚青在上海收藏家李师傅手里见到了王星记创始人陈英所做的“全玉黑纸三格金扇”,这把融合了雕、嵌、刻、画、烫等诸多技艺的扇子,不仅是王星记扇子的精品,更是杭扇的精髓。她当即表示要买下:“李师傅,这把扇子是王星记老板娘做的,你若是肯让给我,我也算是给王星记找回了女儿,能让更多的人看到王星记的工艺。”拗不过孙亚青的坚持,李师傅最终同意了。
9年来,孙亚青已陆续收集了1000多把扇子,无论是自己出资还是公司出资,这些扇子都归了王星记。孙亚青说:“我人都是王星记的,扇子就更是王星记的了。”
采访到最后,我问:“您能成为扇艺大师,最主要靠的是什么?”孙亚青笑着说:“是责任、使命、执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