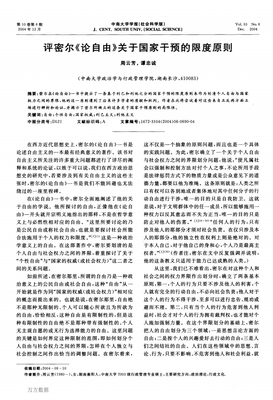《论自由》读后感锦集
《论自由》是一本由[英] 约翰·穆勒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3.00,页数:1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约翰穆勒与洛克《政府论》的遥相呼应,其行文构架之逻辑明确合辙、言辞简洁流利又议论雄壮真挚,所举例、所探讨的话题虽针对一百五十年前的英国,对今日之中国却格外一针见血,边读边心潮澎湃、神思汹涌,屡次放下文本开始在脑内想象出两方辩论… 内容:1/谈思想言论自由,要对观点进行多样化的正反面的辩论探讨,否定绝对真理,肯定争辩过程对观点活力、价值的升华;2/谈个性自由,给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充足空间,发展富有欲望、激情与创新性的性格,否定要求千人一面、集体化的固有不变习俗与高压体制。3/谈社会对个人权力,个人自负责任咎由自取不干涉他人利益、所言所行符合法律和道德舆论的情况下,不应受他人干涉,所举例甚多甚精辟。4/谈自由原则的运用,最后篇幅探讨政府权力的边界,否定专制政府和网罗尽天下人才,人才要分散权力要分散互相制衡,教育要多样化,政府只应服务公共领域不应成为集权的牧羊人。 全文所探讨的具体事例与社会话题精彩纷呈,对宗教礼仪、国民教育、商品课税、个性发展、官僚机器等主题进行了发人深省的议论。 译者水平非常可以,虽未读原文,可光读雅致工整的译文即可看出译本质量之高。译注的良苦用心不由使我因颇有同感而倍觉“找到组织”。 然而,不管《论自由》怎么论,最糟糕的还是现实里人们主动唾弃自由、蔑视自由,不是吗?
《论自由》读后感(二):笔记
所谓民意,不过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压迫少数人的,类似于暴政的行为。
绝对真理在理论上不存在,因为检验真理的办法就是辩护,只有在不断地和反对声音辩论的过程中,一个思想才能逐渐接近真理。也因为这个特征,真理在理论上永远无法到达,因为在某个未来的时点,永远会有新的质疑声音出现之可能性。也正因为真理永远无法被取得,人便不应该以自我之笃定去限制他人思想的自由。
作为个人而言,必须勇于面对,或者主动寻找,甚至自我设问,与自己所信相悖的言论。只有如此才能确保自我信仰的正确性和严肃性。
当人们深信不疑的理论因年久失辩而退化成干枯的教条时,人们往往只有在犯错后才能想起这些『古训』,而不会以这些『古训』来塑造自己的行为模式。因为利益当前,教条所言又非心诚所信,自然先重眼前利。
多数情况下,新旧观念中都会包含部分真理,只有在理性的辩论中才能取各之所长。
辩论道德:编造或隐瞒事实;曲解对方的意见;强词夺理的诡辩。如上述行为为主观故意而为,则恰恰说明了他对真理之畏惧和自尊之脆弱。
村上春树说『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从社会的角度,也应给予弱势观点一侧更多宽容,绝不应用道德压力或辱骂的方式去压迫他们。给予弱势观点以辩论的机会。
人只有在个性和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时才能获得幸福并且创造最多的价值。
历史上,在封建统治时期,为了维持,不论是教皇或是统治者,的威严,以保证社会的稳定,不得不对人的个性和过于强大的才能予以压制。然而如今民主政府,当统治者以不复存在,政府作为民众的化身的时代,人的个性却被这股民意所压制。庸人不问自己想要什么?什么适合自己的性格与才能?如何才能让我身上最优秀和高尚的东西得到充分的发展?却问这样做与我身份是否相符?与我社会地位接近的人通常会做什么?甚至,比我地位高的人会做什么?
一个同质化严重的社会会失去前进的活力,因为当人们选择盲从时,同时也放弃了思考。
《论自由》读后感(三):人类通常之重视权力,远胜过珍爱自由。
洛克的《政府论》企图通过构建一个具有人民合法授权的有限政府来保障个人权利价值,而这也成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相对的,人民所服从的政府对象,必须是得到人民授权同意的政府,一旦人民自然权利(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受到侵害,人民就有反抗暴政的权利。
穆勒则在自由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认为自由(liberty)是民族活力的核心,尤其是思想言论自由,在《论自由》中通过论证个人自由而导向“限制政府权力”。
洛克谈的是(构建)政府,核心却是(保卫)权利;穆勒谈的是(捍卫)自由,核心却是(限制)政府。人们若要干涉群体中任何个体的行动自由,无论出于个人还是集体,其唯一正当目的乃是保障自我不受伤害。这便是说,唯一能对他人施加其非自愿措施的正当理由,只能是为了防止其伤害他人,除此之外任何他人利益(无论精神还是身体)都不能构成对其施以强制的充分理由。换言之,我们不能为了一个人好就强迫(或禁止)他干某些事。在穆勒的立场,纵使是为了他人的幸福,我们也只能对其进行告诫、规劝、甚至恳求,但却不能强迫。
任何个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部分才是其需要对社会负责,而对涉及自身的部分理应拥有完全的独立性。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身体与灵魂的最高主权者。
实话说,在自己有限的拜读过作品当中,应该是没有人比穆勒更坚定支持“思想/言论自由”的了:
即使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都持有一种意见,而只有那一人持有相反意见,人类(群体)也没有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其他人说话一样。不由得想起一句我很喜欢的格言:“我不赞同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毫无意外的,其在书中直言不讳的为苏格拉底叫了一次“冤”,指出“真理总能战胜迫害的说法,只是一种美丽的谎言”。
不得不承认,对整体社会而言,一些人的错误远比一些人的正确有意义的多。一个敢于质疑与思考的人,哪怕经过研究与试验得出错误结论,但相比于那些不敢(或不愿)自我思考却一味坚持己见的人而言,其对于推进真理的贡献更多。
与一般自由主义论者相比,穆勒显然要“激进”的多,认为一切重要真理如果暂时没有反对者,也必须要设想一个并为之设计巧舌如簧的辩护。
尽管认为应该给予所有个性与喜好都不应受到压抑,但我们也有权利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本身就是个人自由的一部分,更进一步的我们有权利选择疏离此人,并告诫他人也如此做。在穆勒看来,一个人的缺陷或不当虽然仅关系自身,却可能受到周遭各种形式“惩罚”,这是其缺陷“自找的结果”,而不是(也不应当是)人们为了对其惩罚而强制施加于他。
当然,穆勒也明确指出更理想的做法,是我们在一开始就出于善意对其给予建议,告诫他可能的后果,这也要求社会鼓励人们忠实的指出认为的错误(而不局限于当前世俗的礼貌观念),而不会被视为无礼冒犯或自以为是。
换言之,这即是要求社会提高“包容性”,人们乐于接受(至少不抵触)对立立场的观点与表达。放眼当下,互联网让网络世界的表达更加自由,却也让对立立场的探讨难上加难,满屏的更多是“站队”与“喷子”,也许是因为科技促进表达的同时,“包容心”不小心有点“掉队”了。
就个人而言,最喜欢的是书中关于“教育”的相关论述,在穆勒的视角,其赞同强制推行普及教育,认为政府应当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心教育就足够了,也尽可能放手让做父母的自行选择教育方式,而政府只需要满足于帮助贫寒子弟支付学费“。这简直堪称现代化素质教育的老祖宗。
全面的国家教育,不过就是一种为了将人们塑造成一模一样而特制的工具;而这一用于陶铸人民的模具,鄙视那些君主、教父或当权者的所喜欢的那种,从而建立起一种控制人心的专制。这种由国家设立并控制的教育如果非要存在,也只能作为诸多竞争教育实验的一种存在,其开办目的只是为了提供某种示范激励,以使其他方式的教育达到一定优秀标准。在21世纪的今天,仍需谨记穆勒的告诫——人类通常之重视权力,远胜过珍爱自由。
《论自由》读后感(四):《论自由》读书笔记
CHAPTER ONE
本书讨论的范畴是社会自由和公民自由,而非哲学意义上的意志自由,也就是为统治者应被容许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设置某些限制。
只要能切实让统治者对民意负责,可据民意及时撤换,国民就可以将能够自主行使的权力托付给他们。他们的权力即是国民自己的权力,只不过是经过集中并赋予了便于行使的形式罢了。然而,行使权力的“人民”和权力所施对象的人民并不总是同一的,导致了“多数者暴政”,也就是社会即便不用民事惩罚,也能有法将自己的观念和做法作为行为准则强加于异见者,防范社会束缚与自己不相一致的个性的发展,甚至有可能遏止其形成,从而使所有人都必须按照社会自身的模式来塑造自己。
异见者之所以成为了异见者,是在一种“主流”的对比下被异化的。主流从何处来?⏬
1. 无论哪一国家,只要存在着一个上流阶级,这个国家的道德原则大部分就会源自这一上流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优越感。 2. 那就是人类对他们现世主人或所奉神祇意中好恶的屈从
社会的好恶,或社会中强势群体的好恶,就这样成为实际决定社会规则的主要依据。
在英国,由于我们政治历史的独特情形,跟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尽管舆论上的压力可能较大,但法律上的束缚却相对较轻。人们一向相当嫉视立法和行政权力对个人行为的直接干涉。这倒不是出于对个人独立的合理尊重,而是出于一直延续下来的「视政府利益常与公众相反」的习惯。多数人还没有学会把政府的权力视为自己的权力,把政府的意见视为自己的意见。一旦他们这样做,个人自由就将会受到政府的侵犯,就像其在公众舆论中已然的遭遇一样。
Thesis Statement:本文的目的即是要力主一条非常简明的原则,若社会以强迫和控制的方式干预个人事务,不论是采用法律惩罚的有形暴力还是利用公众舆论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遵守这条原则。该原则就是,人们若要干涉群体中任何个体的行动自由,无论干涉出自个人还是出自集体,其唯一正当的目的乃是保障自我不受伤害。反过来说,违背其意志而不失正当地施之于文明社会任何成员的权力,唯一的目的也仅仅是防止其伤害他人。他本人的利益,不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都不能成为对他施以强制的充分理由。不能因为这样做对他更好,或能让他更幸福,或依他人之见这样做更明智或更正确,就自认正当地强迫他做某事或禁止他做某事。
一个人不仅可能因有所行动引起对他人的伤害,也会因不行动而有同样的结果,对这两种情况他都应当对他所造成的伤害负责。不过,对于后者施行强制应比对前者更须谨慎。一个人因做了伤害别人的事而被要求必须负责,这是规则,而因没能防止伤害而要其负责,相对来说就是例外。
这一范围就是人类自由的适当范围。它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人类内在的意识领域的自由:它要求最广义的良心自由,思想和情感自由,对举凡实践、思想、科学、道德、宗教等所有事物的意见和态度的绝对自由。发表和出版意见的自由可能看起来应归于不同的原则,因为它属于个人行为关涉他人的那一部分;但是因为发表出版与思想本身几乎同等重要,并且所依据的理由又大都相同,所以实际上是无法将它们分开的。第二,这一原则要求品味和志趣自由:自由地根据自己的特性规划生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愿意承受一切可能的后果;只要我们的行为不伤及他人就不受人们干涉,即使在他人看来我们所行是愚蠢的、乖张的或错误的。第三,由个人自由可以推出在同样限制内的个人联合的自由:人们可以在不伤害他人的任何目的下自由联合,但参加联合的人必须是成年人,并且不受强迫和欺骗。
CHAPTER TWO 言论自由
而且一般说来,在立宪国家,无论政府是否对人民负全责,都不必过虑它会经常对意见表达施加控制,除非它使自己作为代表一般公众不复宽容的机构,才敢这样去做。
以符合公众意见来使用强迫,跟违反公众意见来使用它同样是有害的,甚或是更有害的。
他们(gov)无权为全人类决断是非,也无权排除所有其他人的判断方式。因为他们确定一个意见是错误的,就拒绝听取,这就是把他们的确定性等同于绝对的确定性了。
那么,为什么总体上人类的意见言行还是理性者占多数呢?如果真的存在这种多数优势——我想除非人类事务处于且一直处于一种几近绝望的状态,否则这一多数优势必定存在——那是因为人类心智具有一种特质,且无论作为智识存在还是道德存在的人类,其一切值得尊敬之处都源出于此,那就是人们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
不过如果我们已经在人类理性迄今所能允许的状态内尽了最大努力,对任何接近真理的机会都未曾忽略,那么只要言路一直保持开放,我们就可以指望,如有更确之真理存在,一俟人类心智有能力接受,它就会被发现;同时,我们也大可相信,我们已经在今天这个时代所允许的范围内,获得了这条接近真理的路径。这就是作为常犯错误的人类所能获得的确定性的全部,并且是我们能获致确定性的唯一途径。
但是,确切地说,真理总是能战胜迫害的说法,只是一种美丽的谎言,人们彼此津津乐道,直至最终成为陈腔滥调,但一切经验都与之恰好相反。真理被迫害扑灭的例子史不绝书。认为真理仅仅凭其为真理,就天然具有抵御错误的力量,能够战胜地牢与火刑,乃是一种空洞无凭的侥幸心理。
但是在每一个可能具有不同意见的主题上,真理必有赖于两组相互冲突的理由的公平较量。自由讨论的缺失,不仅使意见的依据被人遗忘,就连意见本身的意思也常常被人抛诸脑后了。那些原本最能深入人心的义理,却因为言论自由的缺乏,只能作为僵死的教条而保留下来,人们根本不能通过想象、情感或理智对其有所领会
《论自由》读后感(五):想全文背诵的一本书
作者在19世界80年代的作品,探讨政府权力和个人权力,政府权力的边界,人与人之间的边界,个人自由的发展对社会的意义等。在今天仍提供很多启发。
书中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个人只要在不伤害他人的范围内,就应该拥有完全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个性自由(行动自由)。”
从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各个方面来进行论述。推理严谨,论证严密。
如作者论证政府首先得让人说话。禁止说话的坏处在,如果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人们便失去了矫正错误的机会;如果是错误的,那也不能被禁,因为
“经过真理与谬误的碰撞,会让人们对真理有更清晰的体会和更生动的印象。”证明人们在某些世俗利益或精神利益的关键点上一直存在错误,这是人类所能给予同胞的最重要的帮助。kindle p582 下同如果两种意见中一个比另一个更具优势,那么不仅要得到容忍,还应该去鼓励和支持,恰恰该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被少数人所持有的那个意见。当其时,那一意见一定代表着被忽视的利益,代表着有丧失公平对待之危险的某一方面人类的福祉。p878穆勒对宗教自由的看法我也很赞同。信什么是自由,可以信,也可以不信,只要不是伤害别人的邪教,任何人、组织或机构都不应该插手个人的信仰。同样,大众也应该对宗教的讨论等新意见多一些包容。因为这样的话损失更惨重的是整个人类社会。
众多大有前途的智慧之士,仅因谨小慎微,就不干沿着独立的思路勇敢前行,害怕使自己身陷被人指责为悖德渎神的境地;可是有谁能够计算世界因此遭受了多大损失呢?(p657)在普遍的精神奴役的氛围中给,已经出现过甚或还会再出现个别伟大的思想家。但是,那种氛围从未也决不会产生出智力活跃的民族。p644一旦某种事物不再存有疑问,人类就会放弃对它的思考,这种不幸倾向是人类所犯错误的半数原因所在。一位当代作家尝言道“定见必寝”,诚哉斯言!p805(基督教)它教人服从一切已经确立起来的权威当局;虽然还不至于当统治者命令有违宗教禁令时也要积极服从,但无论当局对人们做了多少不以之事,也不可反抗,更遑论背叛。p909论个性自由的重要性:
假如人们认识到,个性的自由发展是幸福首要而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认识到它不只是与文明、教导、教育、文化那些名词所指内容相配合的因素,而且它本身就是这些事物的必要组成部分和存在条件,那就不会有低估自由的危险,在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之间做出调整,也就不会有特别的困难。p1066如果相信人是由一个至善至仁的神所创造.......相信神乐于看到他的创造物步步接近内在与他们自身的理想观念。p1147既云天才,顾名思义,定然会比一般人更具个性,惟其如此,也比一般人更没能力适应社会既定有限模式而不受到禁锢的上海,这些模式本是社会为避免其成员各自形成性格而招致麻烦才规定的。p1191不过他们总归是群众,确切点说,就是群集起来的庸众。p1213而一个社会怪诞之行的多寡,一般说来也跟其所含创造才能,精神活力以及道德勇气的多寡成正比。p1228其以自己的方式筹划生活,就是最好的,并非因为这种方式本身就为最好,而是因为这是属于他自己的方式。p1235原来专制政府哪哪都有:
在我们的时代,从社会的最高级到最低级,每个人都生活在怀有敌意的目光与令人恐惧的审查之下。p1124全面的国家教育,不过就是一种为了将人们塑造得彼此一模一样而特制的模具;而且这一用以陶铸人民的模具,必是那些或君主、或教父,或贵族,或当今时代的所谓多数等政府中的当权者所喜欢的那种。p1848中央政府的权力边界:
如果所有这些不同事业的雇员都要由政府人名和支付薪酬,乃至终其一生每一升迁都需仰赖政府;那么纵有再多的出版自由和民主的立法机关,都不足以使英国和其他国家变得真正自由,除了徒具自由之名而已。p1922在这种体制之下,不仅无缘进入其内的外部公众,由于缺乏实际的体验,无资格批评或制止这一官僚机构的运作模式,而且,纵然由专制政体意外事故或民主政体的自然运作,偶尔将一个或几个有着改革意愿的统治者送上权力顶峰,也绣像能让任何有悖于官僚集团利益的改革得以实施。p1937在那些有着更为先进的文明且有着更多反叛精神的国家里,民众既已习惯于指望国家为他们做好每一件事,或至少如不问明国家允许他们做哪些事以及应该如何去做,就不动手为自己做任何事情,那他们自然会把一切临到自己头上的灾祸都视为国家的责任,并且一旦灾祸超过他们的忍耐限度,他们就会起来反抗政府,掀起所谓的革命;于是世有枭雄,其权威无论于国民合法与否,趁机跃上宝座,对那个官僚机构发号施令,而一切事情又一复如旧;朝代已换而官职不更,无人能够取代那个官僚集团的作用。p1944(译者的注释也意味深长:观今日我国之中,人民于国家公职考试趋之若鹜,学优则仕业已司空见惯,体制改革亦复困难重重,则读者于此段宜作深长之思,勿以等闲视之。)社会权力与个人权力的边界:
譬如,如果有人由于放纵奢靡,以致无力偿还债务......但是谴责或惩罚的理由,只能是他背弃了对家庭或债权人的义务,而不能是奢靡行为本身。p1460又如懒惰之 习,倘若其人既非有赖于公众接济,又未因懒惰而违背契约,要对其施以法律处罚,就不能不说是一种苛暴;但是如果一个人无论是由于懒惰还是出于其他什么本可避免的缘故,而不能履行对他人的法定义务,比如抚养子女,那么如无其他有效办法,强迫他劳动以履行义务,就算不上是一种苛暴。p1729但是个体不能要求别人事事合他心意,这是荒谬不堪的绝对社会权力。p1595以自己所信之宗教强令他人信奉,这种义务观念是历来一切宗教迫害的基础。而如果对这种观念予以认可,就完全坐实了所有迫害的正当性。p1610我看不出任何群体有权利强使另一群体文明化。(p1640)(让我想起来《书剑恩仇录》讨论中原与西域的一段话,金老爷子真的了不起。)要竭尽可能地获取集中权力和智慧的优势,又不至于将社会的一般功能过多地转入政府渠道;然而判断“分别这两边的界点”究竟在哪里,确实人类政治技艺中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在不违背效率的前提下,尽最大限度让权力分散;同时由一个集散中枢尽最大可能地让信息得到收集和传播。p1967国家可以用寓禁于征的方法来调整人们的行为,比如烟酒,这是可以接受的。(详见p1773)
谈论家庭与个人:
一旦一个人以口头承诺或实际行为,鼓励另一个人将其视为终身所依,将自身的希望,盘算以及生活规划全都建立在依赖于他的假设之上,那这个人便对他的许诺对象负有了一系列新的道德义务,这些义务虽能被解除,但却决不可被漠视。p1810人们几乎普遍认为,其所生子女应该被认定隶属于他自己,并且是真正而非借喻意义上的隶属。其对子女享有绝对且排他的控制权.......人类通常之重视权力,远远过于珍爱自由!作者对中国也很关注,有些话在今天仍旧不过时。
在一个人口已经过剩威胁的国家里,再去生一大堆孩子,就会带来因竞争加剧而降低劳动报酬的后果,这对所拥有依靠劳动所得为生的人都是一种严重侵犯。p1885(虽然不是说中国的,但很应景啊)因为统治者自己也成为其自身组织和纪律的奴隶,就像被统治者是统治者的奴隶一样。一位中国高官,跟最卑微的农夫一样,同为专制统治的工具和奴才。p1952一些金句:
不论是作为统治者还是作为公民同胞,人类想把自己的意见和偏好强加给他人作为行为准则的倾向,都受到了人性中所难免的一些最好的和最坏情感的有力支持。(kindle p388 )我们不禁想象,一个人竟可以有必不可少的伤害他人的权力,却根本没有只求自己快乐而不给别人带来痛苦的权利。(p1893)《论自由》读后感(六):不愧是经典,启发心灵
这本作为我本年读的第44本书,书本虽小但五脏俱全,很多时候不知道是知识的浓度还是对我本人的冲击亦或者是本来就有很多对于我原本就有想法但是不深入的进一步探进,读完以后感觉耗费了特别多的脑力体力,做了特别多的读书笔记也划了很多句子但是感觉这本书我一定会读第二遍的。
首先是这本书的译本,我选译本向来是要花点时间,好的译本是了解伟大思想的巨大帮助,这本译本总体而言非常满足尤其是很多人吐槽之前的很多译本不够好的情况下我也是很幸运的遇到了这个版本,但是有几个地方是这个译本我感觉还有一些可以改进润色的地方,有些地方可以再改的中国味一点很多一看就很重的外文风而且有的地方的文言文我觉得加得不是特别好我更喜欢少文言文的,还有这个排版文字太密集了读起来有时候会晕晕的,但是看译者的评论就是想要这种效果来让这本书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册子,但是就我个人而言首先这本书字大一点排版松一点哪怕书厚一点贵一点无所谓,而且这样也有更多的空白可以做笔记,再者这种书我真的不认为是轻轻松松的小册子读物,再我读中与读完我都认为这是一本需要打起精神好好学习的经典。
这本书真的是一本经典,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经典的力量,尤其是与现如今很多畅销书的对比。也只有在读这种书的时候感觉到自己很多地方没看懂而且很多地方不是因为作者没有传递好而是本身自己没有反复咀嚼的原因,看完之后合上书感觉小小的一本书居然蕴含着如此多如此大的能量,不会觉得像如通俗读物一样有一种浅尝辄止的感觉。读完感觉真的是受到了约翰穆勒深深的教诲,思想被狠狠的滋养了一遍,也通过这篇书评来对里面的知识做一个更好的吸收。下面我从书本一点点的翻开来推进我的想法。
首先是开篇的导读,这篇导读我觉得写得很深入没有泛泛而谈,虽然有点让人有先入为主的味道,但是这种先入为主对我来说起码是在某一个方面来说这本书能带给我很深的见解,读完本书虽然觉得导读确实存在一些片面或者说针对某一方面进行了选择性解读,但是总体而言这篇导读依然对我把握全文或者说引发了我对本书到底讲了什么的好奇心。
本书正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开篇的引论就有很多地方打动我,比如侵犯自由的不仅仅是来自对独裁集权政府的强制,同样也来自民主社会通过强迫方式来干预个人事务,无论是采用法律惩罚还是公众舆论的道德压力。并且明确提出了己所欲勿施于人的主张,也点出了全文的核心(真正的核心)理念,变为规范与准确我摘抄最后一章对此理念的再一次系统描述,如下文。
自由的两条原则:只要个人行为仅关一己利益而与他人无关,个人就不需要对社会负责,如果有人觉得有必要维护自身利益,不妨对其进行忠告、规戒、劝导以至回避,社会能够正当对其行为表达厌恶与责难的措施,仅此而已;对于任何有损他人利益的行为,个人都应对社会负责,并且如果社会接的为了自身安全必须予以某种惩罚,行事者还应受到社会舆论或法律的惩罚。(P109)
其中有两点特别强调一是作者反对自以为的善来强制他人来如何做,哪怕这种动机是好的,行为方也只能规劝或者诱导而不能强制。二是自由的边界在于是否影响他人,但是后文可以看书是否影响了他人其实是很难判定的,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判断但是据此并不能划出一条清晰的自由的边界而是存在大量的灰色区域,也可以因为辩论双方让这种模糊更大。三是“一个人不仅仅可能因为有所行动引起对他人的伤害,也会因为不行动而有同样的结果”
第二章为论思想言论的自由
主要特别让我有感悟的是对于民主或者有人民组成的政府可能一样会迫害我们的自由而且更加隐蔽在道德上或者理智上更具有欺骗性,同样只坚持一种真理或者意见同样是有害的我们的社会需要多样性或者更需要错误与反面,因为真理在正确的意见中只包含一半,而来一半在错误的与相反的意见中。只有通过容许反驳使得错误更正,在这整个对于事实的讨论与更正中使得我们的结论的正确性得到了唯一的理性保证,也只有这样才可以获得一个完整的真理。不断的检验或者辩护才能保证正确且是唯一的方法,文中称之为“获致确定性的唯一途径“。文中还有几个例子有亚里士多德被害,奥勒留对于基督教的迫害(全文里面有很多宗教的例子,很多让我觉得作者本人至少不是一个盲信上帝的信仰者或者也可能是无神论者)。
还有一段是”但是我们为此智识世界的太平景象付出的代价,却是人类心灵中道德勇气的全部丧失“可以看出来这种盲信盲从与对反对声音的不宽容与打压可能造就一个没有反对声音的世界但是这其中对于言论自由的侵犯更大更深也更隐秘,同时对于人们心灵的那种积极的或者有生命里的束缚也导致人们心灵力量的枯萎,这种束缚就是那种强制性的难以变化的法律规则习俗或者观念。
文章最后(读完全书不得不说整本书是浑然一体的更章节很有逻辑性也彼此支撑,是难得的而言也是Mill有意为之,在多次修改之后得到的非常好的效果。)对于反对意见与主流意见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非主流观点的弱势会妨碍与抑制讨论,为了解决这种对于不同声音发出也为了利于真理在争辩中越辩越明作者给出两种方法。1.建立真正的公共讨论道德,旁听者与辩护者反对者要不偏不倚,尤其是听众要公平看待双方的观点而使得这种非主流观点的弱势消失,但我认为这种方法真的太理想主义了人们很难真正的公平对待两种观点尤其是一方是自己的可能是观念的支柱,很大程度上会有先入为主的可能而且很难避免。2.为了解决这种偏见在方法上不应该采取绝对的平等而应该更加包容弱势的一方或者弥补弱势而给与偏袒。
如果做不到这些可能就会让弱势的声音哪怕是真知灼见哪怕是真理的萌芽就完全消失在真实世界中而只是在某些人的头脑中存在过就又被这种外部环境所熄灭了。
第三章论作为幸福因素之一的个性自由
这一章节有或多或少英雄史观的感觉,作者认为社会的很多推动,至少推动的原创点是少部分人完成的而且是这些少部分人的强烈的个性使然也只有这种个性被保护拥有个性自由不磨灭个性的差异这种个性的差异才能带来这种原创点也才能带来历史的进步,为人们指出道路的自由。作者特别强调不是要求我们强制遵从少数人的声音而只是应该有包容的态度让这些多元思想所产生的不同声音有机会被发出来,而不应该是大众舆论的专制。而且作者在本书中多次多次多次的强调了意见统一的不可取,意见有歧义非但无害而且有益。不盲信盲从一个哪怕是最好的意见的原因1可能有错2因为个人的不一样所以可能不适合个别的具体的人3哪怕又正确又适合这种盲从也会让人不再自我选择或者自在允许的意见中进行选择让人不再思考而是被灌输被执行变得迟钝麻木。
作者也再次提醒我们有让所有人趋同的欲望,不容的是个性,我们总是觉得只有彼此完全相似才可以做出惊人的奇迹,但是作者强调这样的确定性与单一性会让社会失去活力而止步不前——拿了中国做例子。并且强调多元性(多种多样的路径)是欧洲进步的真正原因,自由与环境的多元化。也解释了为什么目前欧洲社会会产生敌视个性希望逐渐趋同的社会的原因(一种自锁现象,正反馈循环。)
”一旦人类日久不见歧异,则很快会变得连想都想不到还有歧异这回事存在“
第四章论社会权利至于个人的限度
本章主要讨论了边界的问题以及何时可以对他人的行为进行道德与法律上的干预或惩罚,提出了公德的缺陷与私德的缺陷。并且作者强调出这并不是要求我们对于他人私德方面的缺陷表现的于是无关和冷漠而只有在侵犯我们自身利益的时候才有所行动的自私利己主义,对于他人私德方面的缺陷我们可以采用劝诱不强求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但同时人们对于这种缺陷也同样有权力来表达自己的反感(讥评与对他的不便)
但是我在这一章中对于作者在个人自由的限度也就是自由的边界上看到的是很多模糊与不确定性,因为这个世界是复杂的而且很多地方的干涉很难区别为是否违规或者跨界了,甚至于什么是正在的不损害他人的私人行为也是很难准确界定的,以至于我一度觉得这种个人可以不受他人舆论政府强迫的领域范围太小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不存在,那么这本书到底是要控制政府的力量使其收回一部分的干涉让人的自由范围扩大以至于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与生长还是说是一种阴差阳错或者不是作者主观想要达到的对自由的范围进一步的缩小呢?因为我们可以对很多个人自由的侵犯打着你影响他人的幌子不仅仅干涉而且有理有据。同时这本书对于少年与儿童还有精神病人不再讨论范围内。而且在对于教育与婚姻上作者也有一些我觉得逻辑错误的地方或者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P93-94作者认为一代人对下一代没有使其变得如同自己一般聪明良善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不尽力或者自己不够聪明良善,但是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缺乏教导良善的能力而不是因为自身良善不足或不够努力。
后文还有”却完全能够让下一代作为整体跟自己这一代一样好,并且可能还会比自己这代稍好一些“也同样讲个人的差异内化进了”一代人“中而忽视了群体中个体的差异性,而个体又是在讨论边界时作者的基本单位,群体可能整体比上一代更好但是仍然存在个体聪明良善正态分布似的差别,那么作者如何应对这种群体中天然实际客观存在的不如别人的那少数人呢?如果也不对他们进行干涉那么是否会让他们陷入自以为是后的困难处境,如果一开始社会对于他们将以强制管教或这约束可以改变他们那么哪怕是侵犯了作者所言的自由那是不是更加人道的呢?也许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作者觉得要批判的,我们不应该为他人做决定,但是社会中实际存在有聪明良善处于末尾的人如果我们只是劝诱而不是强制他们因为自身原因拒绝听从而染上了恶习或者陷入困境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哪怕这种人群不够多但是哪怕只有一个这种人社会对他的强制帮助或者管制是不是于情于理上都是更加人道更加正确各家合适的做法,虽然对于少数人的这种做法可能会进一步延申以至于开了坏头而有危害自由的潜在可能,但是害怕危害自由而一刀切的全部交给人民自己而只是负责劝导,那么如果一个人就要掉下悬崖而他掉下去只会危害自己后果也是他自己承担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是否要打破所谓的不强迫呢?如果这个例子或思想实验被作者认为不再讨论范围或这太极端或者不可能那么这种问题的边界在哪呢?减小程度在什么情况需要我们强制去救助人什么时候只是不强制的劝诱呢?道德习俗带来的制约可能危害了个人自由也侵蚀了社会的多元与多样性让社会麻木腐朽,但是习俗里面包含着人们的道德需求或者人性的光辉在什么程度上需要限制什么时候需要绽放呢?毕竟除了自由我们并不是一无所有,我们还有爱,还有人性而不仅仅是自由。
第五章论自由原则的应用
作者在实际操作方面来应用自己的原则,但是我感觉很多地方都是存在复杂性与争议性,对于毒品,酒,婚姻,生子,教育,人口理论(125)等。还讨论了奴隶制——”自由原则不允许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有而允许一个人让渡自己的自由,也不可能是真正的自由“”人类通常只重视权利,远远过于珍视自由!“
政府是否可以代做或促成某些益于人们的事情呢?作者反对政府的干涉,哪怕没有侵犯自由。原因有1.个人做的可以比政府好,如同自由贸易2.这种事情对人是一种锻炼3.”不必要的增加政府权利乃是一种极大的祸患“以及”一种政府对于自由侵害的自锁行为 如果公路、铁路、银行、保险、大型股份公司、大学以及公公慈善事业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了政府的分支;又如果城市自治会和地方议事会,连同目前所有交付它们管理的事务,都成了中央行政系统的附属:如果所有这些不同事业的雇员都要由政府任命和支付薪酬,乃至终其一生每一升迁都需仰赖政府,那么,纵有再多的出版自由和民主的立法机关,都不足以使英国和其他国家变得真正自由,除了徒具自由之名而已。并且行政机器的构建越是科学有效,即其网罗最优秀人才来操纵这架机器的办法越是巧妙娴熟,其为患也就越大“。 ”如果每一种需要有组织的协同合作或需要高识博见的社会事务,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又如果政府的职司普遍都是由最能干者来充任的,那么除了纯粹的沉思者之外,国内所有博学和实践天才都必将集中与官僚机构中,而社会中的其余人等无论追求什么,都唯有仰仗他们的意旨:普通民众在一切要做的事情上都望其指导和命令:而有能力有抱负者赖其谋求个人的升进“”统治者自身也成为组织和纪律的奴隶“——P127~129第三点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观点是
从长远来看,国家的价值,归根结底还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为了在各项具体事务中使管理更加得心应手,或为了从这种具体实践中获取更多类似技能,而把国民智力拓展和精神提升的利益放在一旁;一个国家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为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终将会发现,弱小的国民毕竟不能成就任何伟业;它为了达到机器的完善而不惜牺牲一切,到头来却将一无所获,因为它缺少活力,那活力已然为了机器更加顺利地运转而宁可扼杀掉了。
《论自由》读后感(七):论自由
论自由
统治者的权力被认为是必要的,但也是高度危险的,因为作为武器它不仅可以用来抵御外敌,还会被用来对付其臣民。
多数者暴政之所以可怕,主要是因为它是通过公共权力的措施来施行的。但是深深入地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细节之中,甚至束缚了人们的心灵本身,从而使人们更加无法逃脱。
集体意见对于个人独立的合法干涉是有一个限度的。发现这一限度并维护其不受侵蚀,对于使人类事务进至良善之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要将其付诸实践,则问题是究竟将这一界限设定在哪里,也就是如何在个人独立与社会控制之间做出恰当的调整。
没有人肯坦承他的判断标准只是他的喜好;而对某种行为的意见如果没有理由做支撑,就只能视为个人的偏好;如果理由仅仅是别人也有同样的偏好,也不过是以众人的喜好代替个人的喜好而已。但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他个人的偏好能得到众人相同偏好的支持,不仅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完美理由,而且一般说来还是其唯一的理由。看来,人们有关毁誉褒贬的意见,不免要受到各种各样理由的影响。有时人们的理由(社会的好恶,或社会中强势群体的好恶)就这样成为实际决定社会规则的主要依据;而这些规则要求人们普遍遵守,否则就要施以法律或舆论惩罚。
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一部分才必须要对社会负责。在仅仅关涉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他的独立性照理说来就是绝对的。对于他自己,对于其身体和心灵,个人就是最高主权者。
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是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追求我们自身之善的自由,只要我们没有企图剥夺别人的这种自由,也不去阻止他们追求自由的努力。对于无论身体、思想还是精神的健康,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最好的监护人。
思想自由
这是辨别真理与谬误的唯一方法。
禁止一种意见的表达,其独有的罪恶之处在于,它是对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人在内的全人类的剥夺;如果被禁止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人们便被剥夺了以正确矫正错误的机会;如果它是错误的,那么人们便损失了几乎同样大的益处,因为经过真理与谬误的碰撞,会让人们对真理有更清晰的体会和更生动的印象。
对我们所持的意见,给予反驳与质难的完全自由,是我们认定它正确的先决条件,而且除此而外,在人类智能所及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作为正确性的理性保证。
人们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人有能力通过讨论和经验修正自己的错误。而且仅靠经验是不够的,必须要经过讨论,指出经验的意义。错误的意见和做法逐步屈从于事实与论证,但是要使事实与论证对人们心智产生影响,就必须让它们来至近前。除非对事实加以评论以显示其含义,否则事实自己不会说话。由此看来,人类判断的全部力量和价值有赖于其以正刊误的特性,而它之所以可资依赖,又仅在于改正之法常不离左右。为什么某些人的判断真正值得信赖,那是如何做到的呢?这是因为他一直放开别人对其意见和行为的批评;因为他一直习惯倾听所有反对他的意见,从其中一切正确的东西里吸取益处,并向自己,必要时向他人解释错误之为错误的所在。通过吸收他人意见中正确的东西来改正和完善自己意见的坚定习惯,非但不致在用之实际时引起怀疑混乱与无所适从,反而是唯一能使其真正值得信赖的坚固基础。因为,他已经知悉一切能够给出的反对他的意见,并且从他的立场上对所有反驳者给予了回应,也就是说他已经主动寻求了反驳与质难,而不是绕开它们。所以凭借这些,他有权认为他的判断优于未经类似过程检验的其他任何个人或群体的判断。
对于任何命题,如果禁止了本来应该允许的对其确定性的反驳,还敢称其为确定不移,那就是认定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道者可以作为确定性的裁判,并且是可以不听取另一方意见的裁判。
思想自由方能产生独立的思考。
认为真理仅仅凭其为真理,就天然具有抵御错误的力量,能够战胜地牢与火刑,乃是一种空洞无凭的侥幸心理。人们对于真理的热情并不一定就强过谬误,法律或社会惩罚的多次运用,总是能成功地阻止无论真理还是谬误的传播。真理的真正优势在于,如果一项意见是真理,它虽可能被扑灭一次、两次以至多次,然而在悠悠岁月之中,总会有人重新发现它,直到有一天它的重现恰值一个有利的环境,成功地逃脱了压迫。
思想家的首要义务是跟随自己的理性而不管它会得出何种结论。一个敢于自己思考的人,经过应有的研究和准备,虽所得的结果为错,对比那些不敢自己思考的人只知持守的正确意见,其对于增进真理的贡献还要更多些。在普遍的精神奴役氛围中,已经出现过甚或还会再出现个别伟大的思想家。但是那种氛围从未也绝不会产生出智力活跃的民族。
只要哪里还存在原则问题不容争辩,事关人生最切要问题的讨论被认为已经结束,我们就肯定不能指望在那里发现普遍而高度的精神活跃。只有公开的论辩涉及的是足以点燃人们激情的重大主题,才会在根本上激发人们的心灵,且激发出来的动力足以提升智力最一般者进至人类的高贵之境。
无论多么正确的意见,如果不能时常经受充分且无所畏惧地讨论,它都只能作为僵死的教条而不是鲜活的真理而被持有。
在每一个可能具有不同意见的主题上,真理必有赖于两组相互冲突的理由的公平较量。对于某一事物,若有人仅了解自己一方,则他对此事物可说是知之甚少。其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甚至好像坚不可摧,但是如果对他来说,相反一方的理由也同样牢不可破,甚至他连对方的理由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他身处两种意见之间,必然找不到一个如何选择的根据。对他来说,理性的态度应该是暂时搁置判断,除非他满足于或是依从权威,或是根据自己情感之所偏爱,接受其中某一方。他所了解的反方论证,必须是以极尽能言善辩的形式出现的,必须让他感觉到关于该主题的正确意见所不得不遭遇且必须要战胜的困难的全部压力,否则他永远不能真正掌握足以应对并解决那一困难的真理。
一旦信仰已变成一个仅靠传承的教条,并非主动而是被动领受,当心灵再也不像当初那样被迫以其全部力量来应对因信仰而来的各种问题时,就会使人除形式以外忘掉所信的一切,或只给予其漫不经心的赞同,仿佛既经信任而接受了它,就无须再从意识上去领悟或通过亲身体验去检验一番;直到它变得与人类的内心生活几乎完全没有联系为止。于是,信仰仿佛总是在心灵之外,使心灵僵化,抵挡一切人性中更高尚部分的影响;它不能容忍任何新鲜而生动的信念进入,对人的意识或心灵可说是毫无用处。
那些原本最能深入人心的义理,却因为言论自由的缺乏,只能作为僵死的教条而保留下来,人们根本不能通过想象、情感或理智对其有所领会。这些见解为人人所习知,人人所熟道,都把它们当作不言而喻的道理。但大多数人只有在经历亲身体验,而且一般是吃了苦头而应验于自身之时,才开始真正明白这些道理的意思。不知有多少次,人们在经历了未曾料到的挫折或不幸之后,才恍然记起那些有生以来一直熟知的格言警句或古训俗谚,如果之前他们就能像现在这样明了其意思,何至于遭此不幸呢。固然有其他实在原因,令人对很多道理非亲身经历不能领会其全部意思,不一定都是言论不自由的缘故。但是,即便是对于这些道理,如果一直能听到那些能予理解之人从正反两面进行争辩,人们也会更多地理解其中的意思,且已经理解的那部分也会在他们心中留下远为深刻的印象。一旦某种事物不再存有疑问,人类就会放弃对它的思考,这种不幸倾向是人类所犯错误的半数原因所在。
心胸狭隘之人,对于他所热衷的每一个真理,都必然会极力主张,反复强调,甚至以各种办法来实行,就好像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真理,或者无论如何都不会有第二义能对其有所限制或可与之一争高下。那个本该认识到但却未能认识到的真理,只因出自被视为敌手的人之口,就被更激烈地排斥。片面真理之间的激烈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半截真理相镇压以致万马齐喑;只要人们还被迫兼听各方,情况就总有希望;而一旦人们只偏重一方,错误就会固化成偏见,而真理自身也由于被夸大变成谬误而不复具有真理的效用。
即使公认意见不仅正确而且是全部真理,除非它允许并确实经受了极其有力而又最为认真的挑战,否则大多数接受它的人抱持的仅仅是一项成见,对其所以然的理性根据毫无理解或体认。当信仰仅仅剩下形式,非但无益于为人增福,而且还因破坏了根基,从而妨碍了任何真实而又诚挚的信念自人类理性或个人体验中生长出来。
个性自由
在我们的时代,在仅仅关涉自身之事上,个人或家庭也不敢依照自己的意见问一问什么才是我想要的?什么才适合我自身的性格和气质?他们问自己的反倒是,与我的身份相符合的是什么?与我地位与财力相仿者通常都做些什么?更糟糕者,要问比我地位与财力更高者通常会做些什么?其实他们除了从俗之外,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嗜好。
于是,心灵本身也向束缚低头:乃至寻乐自娱,首先想到的也是要从俗合流;他们乐于混迹于人群之中;即便有所选择,也是在诸多众人惯行之事之间选择而已;独特的品味,反常的行为,在他们恰如犯罪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开始只是搁置自己的本性而不用,最终至于根本没有了可以遵循的本性,因为他们身上为人类所独具的性能已经枯萎乃至衰竭了:他们已无能力再生出强烈的愿望与固有的快乐,而且一般也丧失了根于自身或可以归之于他们自身的意见与情感。
要想让人类成为值得瞩望的尊贵美好之物,不能消磨一切个人所独具的殊才异禀使之泯然于众,而只能在无损于他人的权利和利益的范围内使之得到培育与发扬。经过这样的过程,人类生活会变得更为丰富多彩,生气盎然,还会给高尚的思想和崇高的情感带来更充分的滋养,并通过让所属族群更值得个人为之自豪而加强每个个体与族群之间的联系。随着个性的张扬每个人变得对他自己更有价值,也因此就能更有益于他人。
如今,大家阅读相同的书报,耳闻相同的论道,眼观相同的事物,去往相同的地方,所抱有的祈望和恐惧指向相同的对象,享有相同的权利和自由,其主张权利和自由的手段也无往而不同。趋同的势头仍在推进。教育的每一步扩展也在推动着它,因为教育将人们置于共通的影响之下,给了人们通往普遍事实和一般情感的门径。交通工具的改进在推动着它,因为它使远地的居民进入人际交往的范围,也使异地之间的迁居更加频繁。工商业的扩展也在推动着它,因为它使舒适环境的好处传布得更广,不管野心奢望的目标有多高,都在公开的普遍竞争之列,因而上升的欲望已不再只是一个特定阶级的特征,而是变成了所有阶级的特征。从政者一旦明确知道大众具有某种意志,其内心就连对抗大众意志的念头都再不会有。
社会之于个人自由的限度
既然每个人都受到社会的保护,就应该对社会有所回报,而且既然事实上每个人都要在社会中生活,就不得不在事关他人的行为上遵守一定的界限。首先,个人行为不得损害彼此的利益,更确切地说不得损害公众视作权利的正当利益;其次,为保卫社会及其成员免遭外侵及内乱,人人都须共同分担此项必须的力役与牺牲。如果社会成员竭力拒绝履行这些义务,则社会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强制其履行而在所不惜。
当大众对个人行为进行干涉时,莫不以自身为标准而断定那些不同于己的做法和想法为罪大恶极;而绝大多数道德家和哲学家,也在经过简单装扮之后,把这种判断标准作为宗教或哲学指令抬到人们面前。他们教导说:只要我们已经问心无愧,确定事情是对的,那它就是对的。他们告诉我们,遵从自己的内心灵明,从中寻求约束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法则。
本书所述的整个原理不外由两条准则构成,这两条准则就是:第一,只要个人行为仅关一己利害而与他人无干,个人就无需对社会负责。第二,对于其任何有损他人利益的行为,个人都应对社会负责,并且如果社会觉得为了自身安全必须施予某种惩处,则行事者还应受到社会舆论或法律的惩罚。
政府之于个人的自由
政府的预防职能,比其惩治职能更易被滥用而至于损及自由;因为借口防患于未然,人类行为的合法自由,几乎没有什么不能被认定为,甚至完全可被认定为增加了这种或那种犯罪行径的便利。
如果城市自治会和地方议事会,连同目前所有交付它们管理的事务,都成了中央行政系统的附属;如果所有这些不同事业的雇员都要由政府任命和支付薪酬,乃至终其一生每一升迁都需仰赖政府;那么,纵有再多的出版自由和民主的立法机关,都不足以使国家变得真正自由,除了徒具自由之名而已。
谋求进入这个官僚阶层,并且一经进入便谋求步步高升,就成为人们进取的唯一目标。在这种体制之下,不仅外部公众,由于缺乏实际的体验,无资格批评这一官僚机构的运作模式,而且,纵然偶尔将一个或几个有着改革意愿的统治者推上权力顶峰,也休想能让任何有悖于官僚集团利益的改革得以实施。
民众既已习惯于指望国家为他们做好每一件事,如不问明国家允许他们自行做哪些事以及应该如何去做,就不动手为自己做任何事情,那他们自然就会把一切临到自己头上的灾祸都视为国家的责任,并且一旦灾祸超过他们的忍耐限度,他们就会起来反抗政府,掀起所谓的革命。
在各种事务都要由官府包揽的地方,任何为官府所决意反对的事情都根本不可能做成。此类国家的体制,不过就是将通国的能人才士,都组织进一个纪律森严的团体,以此来统御其余人众;其组织本身愈是完善,其从社会各界吸纳和规训最优秀人才的做法愈是成功,其对包括官府成员在内的所有人众的束缚就愈是彻底。因为统治者自己也成为其自身组织和纪律的奴隶,就像被统治者是统治者的奴隶一样。
从长远来看,国家的价值,归根结底还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为了在各项具体事务中使管理更加得心应手,或为了从这种具体实践中获取更多类似技能,而把国民智力拓展和精神提升的利益放在一旁;一个国家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为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终将会发现,弱小的国民毕竟不能成就任何伟业。
《论自由》读后感(八):完成从理论到实践,只因神明驻足在细微之处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曾经认为自已对穆勒这篇论文的要点已经了然于心,而且毕竟一百多年过去了,可以略过。但是读完第一章,就已经完全颠覆了那个我认为。
我们在理论上明了的思想,有很多无法在现实中给予实践。比如说,人们都知道自己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只要是和自己不一样的观点,就会轻易认定是他人有问题。比较极端的,一个人反对别人,所以撕掉别人的banner,清除别人的poster。其实他也认为自己热爱自由,却没能从每一个细节去理解自由的含义。神は細部に宿る,神明驻足在细微之处。
是论文就少不了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反命题或逆命题的提出以及论证;文字之下,是一张结构清晰的逻辑网络。考验逻辑的时候到了。
以下第一章笔记,以及参考译文。
INTRODUCTORY
1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实施暴政的可怕之处及应对措施:
Like other tyrannies, 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was at first, and is still vulgarly, held in dread, chiefly as operating through the acts of the public authorities. But reflecting persons perceived that when society is itself the tyrant—society collectively, over the separate individuals who compose it—its means of tyrannising are not restricted to the acts which it may do by the hands of its political functionaries.
像其他的暴政一样,多数人的暴政最初是,也依然低劣地,依靠恐惧维持,其主要通过运用公共权力得以实施。但省思中的人们觉察到当社会本身就是暴政者,即当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凌驾于组成它的单独个体之上时,意味着暴政并不局限于它的那些政治机构之手的运作。
ociety can and does execute its own mandates: and if it issues wrong mandates instead of right, or any mandates at all in things with which it ought not to meddle, it practises a social tyranny more formidable than many kinds of political oppression, since, though not usually upheld by such extreme penalties, it leaves fewer means of escape, penetrating much more deeply into the details of life, and enslaving the soul itself.
社会能够并且确实在运用它所拥有的权限:但如果它行使了错误的权限而非正当权限,或者将权限付诸任何它完全不应该干涉的事情上,那么它就是在实行比任何政治压迫都恐怖的社会暴政,因为尽管它通常不是以极端惩罚的方式维持,但却几乎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逃脱,它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细节之中,使灵魂自甘为奴。
rotection, therefore,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gistrate is not enough: there needs protection also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prevailing opinion and feeling; against the tendency of society to impose, by other means than civil penalties, its own ideas and practices as rules of conduct on those who dissent from them; to fetter the development, and, if possible, prevent the formation, of any individuality not in harmony with its ways, and compel all characters to fashion themselves upon the model of its own.
防卫,因此,仅仅针对行政官员的暴政是不够的:还需要针对盛行的主流观点和情感的暴政加以防卫;即反抗这样一种倾向,社会以民事惩罚之外的其他方式,将其主张和实践作为行为准则,强加给那些异见者; 束缚任何与其道路不相和谐的个性发展,并且如果可能,阻止这些个性的形成,迫使所有人以社会模范为基准塑造自身的性格特征。
2
可以不要求个人自由的两种情况:
其一:我们是处于矇昧阶段的野蛮人。
It is, perhaps, hardly necessary to say that this doctrine is meant to apply only to human beings in the maturity of their faculties. We are not speaking of children, or of young persons below the age which the law may fix as that of manhood or womanhood. Those who are still in a state to require being taken care of by others, must be protected against their own actions as well as against external injury.
也许,几乎不必去说这项原则仅适用于心智成熟的人。我们没有在说孩子们,或者法定成年男子及成年女子年龄之下的年轻人。他们还处于需要被其他人照顾的阶段,必须像保护他们不受到外界伤害一样,保护他们不会被自己的行为所伤害。//巨婴国:此国全是心智未成熟的小孩,需要被祖国妈妈照顾,因此不能给予自由。
For the same reason, we may leave out of consideration those backward states of society in which the race itself may be considered as in its nonage. The early difficulties in the way of spontaneous progress are so great, that there is seldom any choice of means for overcoming them; and a ruler full of the spirit of improvement is warranted in the use of any expedients that will attain an end, perhaps otherwise unattainable.
基于同样原因,我们也将那些处于回退状态的社会置于考虑之外,在那里其种族可以被认为是处于矇昧之中。在早期自然而然的发展进程中,其困难之大,以至于要战胜它们的方法几乎没有什么可选余地;一位富于进取精神的统治者采用任何能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正当合理的,而其他方式则可能无法达到目的实现进步。//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只能说明我们的民族群体性心智不足。但这是事实吗。
Despotism is a legitimate mode of government in dealing with barbarians, provided the end be their improvement, and the means justified by actually effecting that end. Liberty, as a principle, has no application to any state of things anterior to the time when mankind have become capable of being improved by free and equal discussion. Until then, there is nothing for them but implicit obedience to an Akbar or a Charlemagne, if they are so fortunate as to find one.
对于治理野蛮人而言,专制独裁是一种正当的政府模式。它使他们的进步成为其目的,同时对这个目的有效的方法即为合理。自由,作为一项原则,在人类能够开始通过自由和平等的讨论得以取得自身进步的时代来临之前,必然无处适用。在这样的时代之前,人们只能绝对服从一位皇帝,比如阿克巴或查理曼,如果他们非常幸运找到了这样的好皇帝的话。
ut as soon as mankind have attained the capacity of being guided to their own improvement by conviction or persuasion (a period long since reached in all nations with whom we need here concern ourselves), compulsion, either in the direct form or in that of pains and penalties for non-compliance, is no longer admissible as a means to their own good, and justifiable only for the security of others.
但是一旦人类获得了这样一种能力,即能够以信念或劝说的方式引导其自身发展时(我们需要在此考量的所有国家到达这一阶段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强迫,无论是以其直接形式,或是对不服从施加痛苦或惩罚的形式,如果是以个人自身得益为目的,已经不再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方法,而仅在以他人的安全为目的时是正当合理的。
其二:我们是处于险境的小国家。
ociety has expended fully as much effort in the attempt (according to its lights) to compel people to conform to its notions of personal, as of social excellence. The ancient commonwealths thought themselves entitled to practise, and the ancient philosophers countenanced, the regulation of every part of private conduct by public authority, on the ground that the State had a deep interest in the whole bodily and mental discipline of every one of its citizens; a mode of thinking which may have been admissible in small republics surrounded by powerful enemies, in constant peril of being subverted by foreign attack or internal commotion, and to which even a short interval of relaxed energy and self-command might so easily be fatal, that they could not afford to wait for the salutary permanent effects of freedom.
社会在极力扩大它的努力,试图(从它的角度)迫使人们遵从它关于个人和社会优良标准的观念。古时的共和国认为它们有权利运用公共权力对所有领域的个人行为进行规范,在实践中对每位公民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全面规训让国家获益匪浅;这样的思想模式对于周围劲敌环绕的小共和国可能会被采纳,这些国家处于外国攻击或内部骚乱的持续险境之中,对它们来说,即便是活动力和自制的短期放松都可能会轻易致命,自由带来的有益自身的长期效果,它们是等不起的。
3
个人自由的范围准则:行为仅仅直接影响到自己
ut there is a sphere of action in which society,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individual, has, if any, only an indirect interest; comprehending all that portion of a person's life and conduct which affects only himself, or if it also affects others, only with their free, voluntary, and undeceived consent and participation. When I say only himself, I mean directly, and in the first instance: for whatever affects himself, may affect others through himself; and the objection which may be grounded on this contingency, will receive consideration in the sequel.
但是存在这样一个行动范围,区别于个体的社会在这个范围之内只会有间接的利益关系; 这个范围包括了个人生活和行为仅仅影响他自己的那些部分,或者,如果也影响到其他人的话, 只是缘于他们自由、自愿、未受欺骗的同意和参与。当我说仅仅他自己时,我的意思是直接影响,也就是其行为在第一时间所产生的效果:因为无论是什么,会影响他的,也会通过他影响其他人;基于这种偶发可能性而形成的异议,将会在后续中被考量。
4
强加于人的行为源自人类本性驱使,难以应对,权力越大压迫越重,如果不能弱化权力,就只能寄望自身的信念屏障。
Apart from the peculiar tenets of individual thinkers, there is also in the world at large an increasing inclination to stretch unduly the powers of society over the individual, both by the force of opinion and even by that of legislation: and as the tendency of all the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world is to strengthen society, and diminish the power of the individual, this encroachment is not one of the evils which tend spontaneously to disappear, but, on the contrary, to grow more and more formidable.
在个体思考者们的独特信条之外,世界仍普遍存在一种日渐增长的倾向,将社会权力过度延伸到个人领域,两者均通过观点影响,甚至通过立法实现:并且由于世界正在发生的所有变化趋势都是在强化社会,削减个体力量, 这种侵蚀不属于那些会自动消失的邪恶之一,而是恰恰相反,变得越来越难以应对。
The disposition of mankind, whether as rulers or as fellow-citizens to impose their own opinions and inclinations as a rule of conduct on others, is so energetically supported by some of the best and by some of the worst feelings incident to human nature, that it is hardly ever kept under restraint by anything but want of power; and as the power is not declining, but growing, unless a strong barrier of moral conviction can be raised against the mischief, we must expect, in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 of the world, to see it increase.
将个人观点和意愿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强加给他人的这种人类性情,无论是统治者或是公民同胞,受到由人类本性驱动的一些最好和最坏情感的强劲支持,几乎无法被置于约束之下,除非将权力弱化;但是由于权力没有在衰退,而是在增长,因此除非我们竖起一堵强大的道德信念的屏障,以对抗自身的这种恶念,我们恐怕只能预期,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中,看着社会侵蚀个人的这种邪恶增加。